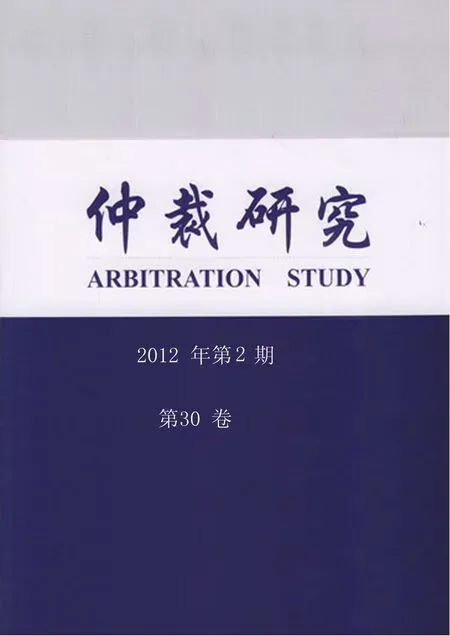普通法系國際商事仲裁裁決既判力問題的處理經驗及其啟示
——以Associated Electric v. European Re案為例
傅攀峰
普通法系國際商事仲裁裁決既判力問題的處理經驗及其啟示
——以Associated Electric v. European Re案為例
傅攀峰?
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既判力問題實踐性相當強,由于適用既判力原則的具體制度不同,各國無法在處理該問題上達到統一。普通法系在長年的司法實踐中發展出了諸如訴因禁反言、爭點禁反言、禁止濫用程序原則等一系列獨特的既判力制度,這些制度同大陸法系的既判力制度差異甚大,其背后所融入的法律思維和所追求的法律價值典型地體現了普通法系的精神。本文以Associated Electric v. European Re案為切入點,闡明普通法系的既判力制度,試圖探尋普通法系解決國際商事仲裁裁決既判力問題的路徑,并簡要總結普通法系處理既判力問題的經驗的核心之所在,以期對我國法院的實踐有所裨益。
仲裁裁決 普通法系 既判力
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既判力問題近年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①國際法協會(ILA)分別于2004年和2006年就該問題作出了兩份正式報告即為例證。在全球背景之下,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行不可避免地牽涉到不同國家,這些國家可能分屬不同法系,并在既判力制度上存在較大差異。與大陸法系傾向于針對既判力問題建構理論框架并使之成文化、法典化有所不同的是,普通法系國家往往通過長年的司法實踐發展出一系列旨在解決裁判既判力問題的具體原則和制度,比如訴因禁反言(cause of action estoppel)、爭點禁反言(issue estoppel)。
本文將圍繞Associated Electric v. European Re案,闡述普通法系理解和處理既判力問題的經驗及其對我們的啟示。
一、案情介紹
這是一個上訴到英國樞密院(Privy Council)的案件。該案主要涉及兩大仲裁法律問題,其中之一便是仲裁裁決的既判力問題。該案脈絡清晰,具有典型性,下面將簡要介紹基本案情。①Associated Electric & Gas Insurance Services Ltd v. European Reinsurance Company of Zurich(Bermuda), [2003] UKPC 11.
(一)本案的發展過程
1980年,Associated Electric & Gas Insurance Services Ltd (以下簡稱Aegis) 與European Reinsurance Company of Zurich (以下簡稱European Re)簽訂了一份自動臨時再保險 ( Automatic Facultative Reinsurance)協議。該協議包含有一仲裁條款,規定產生的糾紛在百慕大(Bermuda)②百慕大作為英國的海外自治領地,其經濟主要依賴旅游業、國際金融業和保險業。保險和再保險資產超過350億美元,規模僅次于倫敦和紐約。因不課所得稅,遂成為國際著名 “避稅地”。以仲裁的方式解決,其還對仲裁的法律適作出了規定。
隨后,兩公司之間產生了涉及European Re對Aegis履行補償義務的兩大爭議(即下文所指的爭議A和爭議B);根據仲裁協議,兩者都被當事人提交予以仲裁。③百慕大以聯合國《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規范國際商事仲裁。The Bermuda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and Arbitration Act 1993, section 23 and Schedule 2.爭議A被提交到由Stewart Boyd QC主持的仲裁專家組進行仲裁(以下將針對爭議A的仲裁簡稱為Boyd仲裁),該仲裁專家組于2000年1月作出了針對該項爭議的裁決。而爭議B被提交到由Phillippa Rowe主持的仲裁專家組進行仲裁(以下將針對爭議B的仲裁簡稱為Rowe仲裁)。在Rowe仲裁中,European Re認為Boyd仲裁中針對 “如何正確理解和適用仲裁條款”的問題的決定具有終局效力,而Aegis在Rowe仲裁中又提出了“如何正確理解和適用仲裁條款”的問題,因此European Re希望援引Boyd仲裁裁決以阻止Rowe仲裁再次處理相同爭議點,因為Rowe仲裁如果再次處理Aegis提出的相同爭議點,這將違背爭點禁反言制度。而Aegis認為European Re在Rowe仲裁中不能援引Boyd仲裁裁決的任何部分,因為這將違反仲裁保密原則。接著Aegis成功獲得了法院禁令(injunction)以限制European Re援引Boyd仲裁裁決的行為。European Re申請撤銷該項禁令,法官駁回了其申請,繼續實施該項禁令。然后,European Re提起上訴,上訴法院受理了撤銷禁令的申請,并作出了撤銷禁令的裁定。Aegis不服,上訴至英國樞密院。在樞密院的上訴程序中,Aegis提出了兩項理由支持該項禁令:第一,如前所述,向Rowe仲裁中的仲裁員披露Boyd仲裁裁決或者裁決的任何部分將違反在仲裁中普遍適用的保密性原則,而且這也違反了在Boyd仲裁中,當事人雙方共同明確同意了的,禁止將仲裁結果的內容在任何時候透露給任何人的規定,該規定還由當事人雙方和仲裁員簽了字;第二,European Re提出的爭點禁反言抗辯(plea of collateral estoppel)實體上的理由不充足,非但站不住腳,反而構成了程序濫用行為。European Re提出的辯護意見是Boyd仲裁中的仲裁員針對“如何正確理解和適用仲裁條款”的問題所作出的決定具有爭點禁反言的效力,其在Rowe仲裁中可以援引,而Aegis在Rowe仲裁中再次提出該項相同爭議點構成拒絕承認與執行Boyd仲裁裁決的行為,因此,在正確理解雙方簽訂的仲裁保密協議的前提下,European Re并沒有違背仲裁保密性的協議要求。
(二)判決意見
英國樞密院最后維持了上訴法院的裁決,駁回了Aegis的上訴,其表達的主要理由有如下幾點①Associated Electric & Gas Insurance Services Ltd v. European Reinsurance Company of Zurich (Bermuda), [2003] UKPC 11.:第一,由于前后兩仲裁程序中的當事人完全相同,且后一仲裁程序也適用不公開審理原則,因此一方當事人在后一仲裁程序中合理利用前一仲裁程序中所裁決的結果并不違背仲裁保密原則的宗旨;第二,在理解雙方當事人簽訂的仲裁保密協議時,應該考慮到該協議的根本目的并非意在阻止一方當事人行使由裁決所衍生而出的既判力抗辯權利;第三,仲裁保密協議不能得到毫無限制的解釋,否則,將導致任何裁決無法得到執行;第四,爭點禁反言不僅適用于訴訟中,且同樣適用于仲裁中,當事人如果選擇了以仲裁的方式解決雙方法律權利義務糾紛,那么仲裁庭針對相關爭議點所作出的決定具有約束雙方當事人的效力;第五,European Re在Rowe仲裁中提出的爭點禁反言抗辯,實際上是Boyd仲裁裁決賦予European Re的一項可執行性的權利,一旦仲裁員根據當事人提交的爭議,對其中一項爭點作出了決定,那么雙方當事人就不能再次對該爭點提出異議;第六,“如何正確理解和適用仲裁條款”的問題在Boyd仲裁中是一項意義重大的爭議,Boyd仲裁中的仲裁員針對該項爭議點所作出的處理決定構成了對整個爭議處理的一部分,唯有如此才是對Boyd仲裁裁決的正確解讀。
二、普通法系既判力的基本制度
分析該案之前,有必要對普通法系特別是英國的既判力制度進行交待。普通法系圍繞裁判的既判力問題發展出了一系列相當獨特的制度,與大陸法系差別甚大,理解這些獨特而又具體的既判力制度成為理解和分析該案的前提。
(一)賦予國際商事仲裁裁決既判力的前提條件
在英國,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如同外國法院判決一樣,在滿足一定的條件下,可以獲得既判力。①外國判決在英國獲得既判力須滿足以下兩個條件:第一,判決是由對案件具有合格管轄權的法院作出的;第二,判決在該國本身已產生終局效力。Peter Barnett, The Prevention of Cross-Border Re-litigation, I.C.L.Q. 2002, 51(4), pp. 943-957.
首先,該裁決必須在仲裁地獲得終局效力,且須得到仲裁地法院的承認。如果裁決得不到仲裁地法院的承認,那么將導致該裁決無法得到英國法院的承認,進而無法在英國產生既判力。②Filip de Ly and Audley Sheppard, ILA Interim Report on Res Judicata and Arbitration,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Vol.25, No.1, 2009, p. 46.然而,這種態度在近年美國的法院實踐中受到了挑戰,最富影響與爭議的案例當屬廣為國際商事仲裁界熟知的Chromalloy案。③Chromalloy Aeroservices Inc. v. Ministry of Defense of the Republic of Egypt, 939 F. Supp. 907 (D.D.C.1996).該案中,美國法院并未因埃及法院撤銷了該案的仲裁裁決而當然地拒絕承認之,相反,美國法院根據其判斷,認定埃及法院的撤裁行為是錯誤的,該仲裁裁決應當得到尊重與執行。且不論個案中可能涉及到的國家利益,單若按英國法院的態度,則類似Chromalloy案的仲裁裁決恐無法得到英國的承認與執行。Chromalloy案體現了仲裁“非國內化”(delocalization)的發展趨勢,然而,這種態度至今未成為各國法院對待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主流做法。④荷蘭學者van den Burg指出,雖然“非國內化”理論為部分學者,特別是法國的學者所推崇,但是絕大部分立法、案例以及學術著作都主張屬地理論(territoriality theory)。 Albert Jan van den Burg,Enforcement of Arbitral Awards Annulled in Russ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10, 27(2), pp. 179-198.
其次,如果前一裁決違反了英國國內公共政策(domestic public policy),那么該裁決也將可能無法在英國獲得既判力。眾所周知,鼓勵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得到順利承認與執行是各國業已達成的一項共識,也是1958年《紐約公約》的重要目的。雖然《紐約公約》將“承認或執行裁決有違該國公共政策者”( 第5條2款b項)明列為法院拒絕承認及執行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理由,但是從全球的實踐來看,各國法院仍傾向于嚴格解釋《紐約公約》第5條2款b項,不會貿然撤裁。①Troy L. Harris, The “Public Policy” Exception to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wards Under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07, 24(1), pp. 9-24.尤其在英國,英國法院不會僅僅因為一方聲稱裁決違反國內公共政策而草率地作出撤裁行為,須知在國際商事仲裁領域還存在著所謂的國際公共政策(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而國際公共政策的范圍要比國內公共政策狹窄得多。②Van den Berg認為當事人的公共政策抗辯(public policy plea)很少會導致法院拒絕執行國際仲裁裁決,其原因之一是公共政策有國內公共政策和國際公共政策之分。不難得知,法院在考慮應不應該基于違背公共政策撤裁時,國際公共政策的考量占據很重要的地位。參見ILA Interim Report on Public Policy,www.ila-hq.org,2011年12月17號訪問。.英國法院偏向于考慮《紐約公約》所隱含的國際公共政策,這在Westacre Investment Inc v. Jugoimport-SPDR Holding Co Ltd案③[1999] QB 740.中體現地尤為明顯,該案法官的意見是只有當與裁決有關的合同違背了合同履行地的公共政策時,才會被視為違背了英國的國內公共政策,因此國際因素被納入公共政策的判斷標準之中。但是,對于某些無論從國內還是從國際角度觀之都構成重大違背公共政策的裁決,英國法院拒絕執行的立場是相當鮮明的:在Soleimany v. Soleimany案中,英國上訴法院基于公共政策的理由拒絕執行了一項外國仲裁裁決,原因是走私地毯在伊朗屬于違法行為,執行該項裁決勢必會玷污英國司法程序的公正性。④[1999] QB 785.
(二)訴因禁反言
訴因禁反言(cause of action estoppel),⑤美國法律稱之請求排除效(claim preclusion),從這些表意相差無幾而表達形式卻有細微差別的現象中,可以窺見英國普通法的古老和美國對英國普通法的繼承和發展。在國際商事仲裁語境下,是指一項有關實體問題的仲裁請求,如果業已被仲裁庭裁決,自裁決生效后,當事人不得再次就同一實體問題提出相同的請求。在普通法系,訴因禁反言構成狹義意義上既判力制度的全部;廣義上,訴因禁反言無疑構成既判力制度的主體部分。如何理解“訴因”這一概念成為理解這項制度的關鍵。按照《牛津法律大辭典》的解釋,訴因“指某人據以行使其提起訴訟權利的某一事實或系列事實”,⑥戴維·M·沃克:《牛津法律大辭典》,李雙元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頁。《牛津現代法律用語詞典》亦作此解。⑦布萊恩· A·加納:《牛津現代法律用語詞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頁。在美國法律中,“訴因”可以理解為包括由當事人之間的全部或者部分交易或者一系列相關交易所衍生而出的所有救濟性權利,訴訟正基于此而發生。①Filip de Ly and Audley Sheppard, ILA Interim Report on Res Judicata and Arbitration,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Vol.25, No.1, 2009, p. 47.因此,對于美國法院,如何判斷交易的構成或者系列交易的構成,系列交易是否構成單獨的審理單元,以及將它們作為單獨的審理單元進行處理是否符合當事人的期望或者商業慣例等,則是相當重要的實踐問題。②同上。
理解訴因禁反言這一概念的另一個關鍵在于,必須以理解普通法系對“當事人不得再次就同一實體問題提出相同的請求”的闡釋為基礎。而這又需從“訴因”尋找切入口。普通法系認為,雖然一方面訴因構成當事人據以行使其訴訟權利的理由,但是針對某一項訴訟請求的終局裁決一旦被作出,那么與該項訴訟請求相對應的訴因即被融入到終局裁判之中。換而言之,訴因因終局裁決而消失。既然訴因基于終局裁決的作出而消失,那么當事人自當無理由再次就同一實體問題提出相同的請求了。然而,實踐中卻存在諸多當事人(特別是敗訴方)在一項終局裁判作出后再次針對已決實體問題提出相同的請求,在這種情形下,另一方當事人可以提出訴因禁反言抗辯(plea),裁判者如認為該項請求確已被終局裁決,那么其將會支持另一方當事人所提出的訴因禁反言抗辯,駁回該項請求。
值得注意的是,針對同一訴因,當事人可能基于不同的法律根據提出訴訟請求。例如,某些爭議當事人既可以基于對方違約提起訴訟請求,也可以基于對方侵權提起訴訟請求,在此情形下,訴因不因當事人可能從不同法律角度提起請求而分離,其仍構成單一訴因,法院或仲裁機構針對具體情況擇一角度判之即產生終局效力,訴因即行消失。
(三)爭點禁反言
爭點禁反言 (collateral estoppel)③美國法律稱之為爭點排除效(issue preclusion)。旨在阻止一方當事人在隨后的程序(subsequent proceedings)④一般來講,“隨后的程序”指隨后的另一仲裁庭的程序或者隨后的法院的訴訟程序。由于在仲裁中存在部分裁決這種裁決形式,因此,隨后的程序還可能包括同一仲裁程序之內部分裁決作出后的程序。中駁斥或意圖推翻相同當事人(包括與當事人有密切關系的人)之間在前一程序中已提出并被終局裁決了的爭點問題。這些爭點包括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爭點有主次之分,所謂主要爭點是指對案件的裁斷起關鍵作用的事實或法律問題,根據英國的實踐,只有在判案中起關鍵作用的爭點才能在裁決作出后獲得既判力。因此,判斷某一爭點對于判案是否具有“關鍵意義”是適用爭點禁反言這一制度的核心。
大陸法系的既判力理論中一直存在著是否應賦予判決理由以既判力的爭論。立法上,大多國家皆持保留態度,例如,《日本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1款規定,既判力僅及于判決主文,判決理由不具有既判力。①高橋宏志:《民事訴訟法——制度與理論的深層分析》,林劍鋒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05頁。大陸法系之所以原則上不賦予判決理由以既判力,這主要基于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從當事人的立場看,將既判力客觀范圍限于判決主文有利于保障當事人爭點處置的自由及防止突襲裁判,如果將判決理由賦予既判力的話,那么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就會計較各種細微的爭點,不會對相關事項輕易地作出自認,因為當事人擔心如果自己提出的相關爭點或者為已方辯護的理由不得再次提起的話,當事人在訴訟程序中就會更為謹慎,這勢必會阻礙程序的順利進行,浪費司法資源;另一方面,從法院的立場看,不賦予判決理由以既判力,有助于提高法院審理的靈活性,因為在判決理由不具有既判力的情況下,法院可不必按照實體法上的邏輯順序或遵照當事人指定的順序按部就班地對訴訟中所有的爭點做出審慎的判斷,它可以將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在對訴訟標的的判斷中,不拘泥于判斷理由中的某些爭點。②林劍鋒:《民事判決既判力客觀范圍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61-63頁。
雖然大陸法系將既判力客觀范圍限于判決主文的規定有利于提高法院和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的靈活性和機動性,但卻會產生一些實踐困境。以下舉例說明之。A起訴B,要求法院基于他們之間的贈與關系判決某爭議房產屬于A,法院通過確認A與B之間的確存在贈與關系后,做出了有利于A的判決,即判決該房產屬于A所有。在該案中,房產所有權歸屬屬于訴訟標的,應由判決主文確定,而贈與關系則屬于判決理由。如果B隨后就該贈與關系提起訴訟,要求法院確認A和B之間不存在贈與關系,而該法院最后判決該贈與關系不成立,那勢必會導致前訴和后訴完全矛盾的局面。
普通法系的“爭點禁反言”制度具有極強的功能主義取向,往往能克服實踐中的許多困境。上例中,倘依普通法系的理解,贈與關系無疑構成在判案中起關鍵作用的爭點,由此,前訴判決一旦生效,針對該贈與關系的裁斷也可獲得終局效力,后訴中當事人不得對前訴中的贈與關系再行爭辯。通過該例我們可以對普通法系既判力制度的靈活性和實用性略窺一二,它能夠有效避免將既判力原則適用僵硬化所帶來的問題。正是由于這些優點的存在,爭點禁反言制度得到了大陸法系國家諸多學者的借鑒。日本著名民事訴訟法學家新堂幸司教授吸取了普通法系有關既判力的理論營養,提出了爭點效理論,以解決這一實踐困境。對于爭點效的定義,新堂幸司教授論述如下,“在前訴中,被雙方當事人作為主要爭點予以爭執,而且,法院也對該爭點進行了審理并作出判斷,當同一爭點作為主要的先決問題出現在其它后訴請求的審理中時,前訴法院對于該爭點作出的判斷所產生的通用力,就是所謂的爭點效,依據這種爭點效的作用,后訴當事人不能提出違反該判斷的主張及舉證,同時后訴法院也不能作出與該判斷相矛盾的判斷。”①高橋宏志:《民事訴訟法——制度與理論的深層分析》,林劍鋒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19頁。
(四)已有救濟
已有救濟原則(former recovery)是指當事人申請仲裁以實現其請求,仲裁庭作出了支持當事人請求的裁決,且該項裁決已得到相應執行,從而其獲得法律上的救濟,在這種情形下,該當事人不得再次向仲裁庭或法院提出執行請求。普遍認為前一程序結束后,訴因也就隨之消失,一旦裁決得到執行,那么履行裁決的義務方(不論是給付金錢義務或是其他義務)就可以援用該項原則以阻止對方當事人再次申請執行該項裁決。已有救濟原則相對于前兩項原則,它更強調裁決既判力所內含的執行上的正義,這項正義要求也就是所謂的禁止雙重滿足原則(principle of double satisfaction)。比如,A申請仲裁與B之間的合同糾紛,請求仲裁庭C支持其要求B賠償違約金100萬美元。仲裁庭C通過審理作出裁決D支持申請人A的請求。隨后,裁決D得到順利的執行,A實現了其當初要求仲裁庭支持的請求。在這種情形下,根據已有救濟原則,A就不能再次向仲裁庭C或者當地法院要求執行裁決D。
(五)禁止程序濫用原則
普通法系向來以注重程序正義著稱。②喬治·P·弗萊徹、史蒂夫·謝潑德:《美國法律基礎解讀》,李燕譯,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頁。禁止程序濫用原則(abuse of process)是普通法系既判力原則中一項很有特色的制度。訴因禁反言和爭點禁反言,一般來說,針對的是已被裁決了的請求和爭議點,但是英國法院的實踐將這兩項制度的適用范圍延伸至當事人能夠但事實上卻沒有在前訴中提出的請求或者爭議點。①Denis Bensaude, The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s Recommendations on Res Judicata and Lis Penden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4(4), 2007, p. 419.換而言之,在前一訴訟或仲裁中,當事人基于非法或者其他惡意的目的,故意保留應該而且能夠在該訴中提出的請求或者爭點,待判決或裁決做出后,當事人針對前面能夠提出但事實上卻未提出的請求或者爭點再行提起訴訟時,法院將認為當事人的行為構成濫用程序,從而拒絕對這些請求或者爭點進行裁判,此即禁止程序濫用原則的內涵與作用。
禁止程序濫用原則在英國被稱作“赫德森v.赫德森規則(rule in Henderson v. Henderson)”。②Henderson v. Henderson [1843] 3 Hare 100; 在澳大利亞,禁止程序濫用原則被稱為“Anshun estoppel”; 加拿大最高法院在近年的Toronto(city) v. Canadian Union of Public Employees一案中運用了該項原則。Filip de Ly and Audley Sheppard, ILA Interim Report on Res Judicata and Arbitration,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Vol.25, No.1, 2009, p. 43.這一規則源自1843年英國法院針對Henderson v. Henderson案的判決,該判決已有一百多年歷史了,至今仍然被英國法院頻繁援用。根據Lexis法律數據庫調查顯示,近些年,19世紀英國的任何一項判例都沒有Henderson v. Henderson案的引用頻率高。③K·R·Handley, A Closer Look at Henderson v. Henderson, L.Q.R. 2002, 118(Jul), pp. 397-407.
在英國上議院作出對“Johnson v. Gore Wood & Co”④[2000] UKHL 65.案的判決后,該項規則被歸入禁止程序濫用原則的范疇,從而不再作為訴因禁反言或者爭點禁反言制度的延伸。這項原則旨在保護一方當事人免受另一方當事人程序不公行為的侵害。至于當事人行為是否構成程序不公,這完全取決于法院的判斷,因此,法官適用禁止程序濫用原則具有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⑤然而,美國法院的實踐與英國有一定差異,對于當事人能夠但事實上卻沒有在前一仲裁程序中提出的請求或者爭議點,只有在極為有限的情形下才被賦予既判力。因此,在既判力問題上,美國并沒有像英國確立一般性的禁止程序濫用原則。美國的普通法認為當事人可能有諸多原因導致其沒有在前一程序中提出某一個爭議點,比如說為了節約司法資源、保持一致性、防止對方當事人的侵擾,等等。Henry Modell & Co Inc v. Reformed Protestant Dutch Church of City of New York, 68 NY.2d 456 at 464(1986).
三、既判力原則的適用與本案的分析
(一)既判力原則適用的基本條件
既判力原則的適用涉及前訴和后訴,如果當事人在后訴中提出了有關既判力問題的抗辯,那么既判力原則的適用前提是后訴中的當事人、訴因以及訴訟(或仲裁)請求三要素與前訴一致。這一條件,無論是在大陸法系國家還是在普通法系國家基本上相同,只不過大陸法系在三要素一致的標準上更加的嚴格,并且基于其法典化的傳統將這些條件明確于法典之中,如《法國民法典》第1351條規定:“…請求之物應為同一的物;訴訟請求應基于同一的原因;訴訟應在相同的當事人之間進行,并且應是同一的原告針對同一的被告以同一的身份提起”。①《法國民法典》(下冊),羅結珍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9頁。普通法系國家對此則無成文的規定,但通過其圍繞既判力原則發展而出的一系列具體制度可以得知,前后訴當事人、訴因以及訴訟(或仲裁)請求三要素一致是既判力原則適用的基本條件。
本案Boyd仲裁在前,Rowe仲裁在后,很明顯前后兩仲裁中,當事人都是Aegis和European Re這兩個公司,兩公司之間的關系都是基于自動臨時再保險協議產生的保險法律關系,因此前后兩仲裁的訴因也一致。至于仲裁請求,在Boyd仲裁中,“如何正確理解和適用仲裁條款”的問題作為一項仲裁請求由該仲裁庭得到了明確,而在Rowe仲裁中Aegis再次請求明確“如何正確理解和適用仲裁條款”,因而,前后兩仲裁的仲裁請求也一致。由此可見,本案滿足適用既判力原則的基本條件。
(二)爭點的既判力問題
在國際商事仲裁的具體案件中,雙方當事人針對具體問題可能存在諸多爭議,仲裁庭相應地會對與案件實體問題有關的爭議作出裁斷。但是,仲裁庭針對爭議問題所作出的裁斷并非都能產生爭點禁反言效力。次要的或僅起輔助作用的事實及法律問題,雖然與案件可能存在這樣或那樣的關系,卻都不在爭點禁反言效力覆蓋范圍之內。而且,傳統上,英國普通法認為針對程序事項所作出的裁決或決定也不產生爭點禁反言效力。②Filip de Ly and Audley Sheppard, ILA Interim Report on Res Judicata and Arbitration,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Vol.25, No.1, 2009, p.42.至于一方當事人在后一仲裁程序中提出爭點禁反言抗辯符不符合相應條件,則由后一仲裁程序的仲裁員進行判斷。
回到本案中,European Re在后一仲裁程序即Rowe仲裁中,提出了爭點禁反言抗辯,認為關于“如何正確理解和適用仲裁條款”的問題作為一項爭議點,已經在Boyd仲裁中得到處理,因此該爭議點已經產生既判力,另一方不得在隨后的程序中再行請求仲裁庭處理該爭議點。而Aegis則對European Re提出的這項抗辯進行了反駁,其理由之一是該項爭點尚不滿足產生爭點禁反言效力的內在要求,換言之,Aegis認為該項爭點不夠資格產生既判力,因而,認為其有權在Rowe仲裁中再次請求仲裁員明確“如何正確理解和適用仲裁條款”的問題。由此可見,在Rowe仲裁中,Aegis和European Re雙方之間的焦點問題在于,在Boyd仲裁中已經得到處理的“如何正確理解和適用仲裁條款”的問題能否對Rowe仲裁產生爭點禁反言的效力。
為了進一步分析在Boyd仲裁中已得到處理的“如何正確理解和適用仲裁條款”這一爭議點能否產生既判力,有必要先了解雙方之間簽訂的仲裁協議,因為該爭議點正是基于雙方對仲裁協議的不同理解而產生的。在Aegis和European Re簽訂的仲裁協議中,雙方除了規定以仲裁的方式解決相關爭議外,還特別對仲裁的法律適用作出了規定。問題在于,仲裁協議其中一處規定相關爭議的解決應根據再保險慣例而非嚴格根據法律條文,而另一處卻明確規定應適用再保險公司所在地的法律,也即Aegis所在地百慕大的法律。因而,仲裁協議對仲裁的法律適用問題出現了顯而易見的矛盾,導致雙方在如何適用法律問題上各執一詞。
事實上,該爭議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Aegis和European Re雙方的法律關系為再保險法律關系,適用不同的法律將會導致案件的處理產生截然不同的結果,從而對雙方的利益產生重大影響。由此可以斷定,該爭議點并非如Aegis所言在實體上不滿足產生爭點禁反言的資格。既然該爭議點對仲裁具有重大的意義,而且構成仲裁裁決結果的前提性條件,那么Rowe仲裁中的仲裁員理應給予在Boyd仲裁中已經得到處理的“如何正確理解和適用仲裁條款”這一爭議點以既判力。實際上,前一程序中某項爭議點能否滿足產生爭點禁反言效力的條件,也完全是由后一程序中的裁判者進行判斷,這一點在英國樞密院的判決意見中得到了強調。對已被裁斷了的重要爭議點賦予既判力的法理依據在于,一方面它能避免前后程序產生邏輯上相矛盾的裁判結果,另一方面又能避免因賦予每一爭點以既判力所可能導致的程序效率的低下。這一點在上文探討爭點禁反言制度時曾有較為詳細的解析。
(三)程序濫用問題
本案中,Aegis認為European Re在Rowe仲裁中提起的爭點禁反言抗辯非但不能成立,反而有濫用程序之嫌。關于European Re提起的爭點禁反言抗辯能否成立的問題,上文已予以了充分的論證;然而,European Re提起的爭點禁反言抗辯,是否真如Aegis所認為的有濫用程序之嫌呢?
這實際上牽涉到普通法系(特別是英聯邦國家)既判力制度中很重要的一條原則,即禁止程序濫用原則。上文論述該原則時曾提到“赫德森v.赫德森規則”①Henderson v. Henderson [1843] 3 Hare 100.,而本案當事人Aegis也援引了該條規則。該規則的內容是當事人不得在隨后的另一程序中提出在前一仲裁程序中能夠但事實上卻沒有提出的請求或者爭議點。該規則和爭點禁反言有相似之處,但亦有明顯的差異,實際上,它是爭點禁反言制度的一種延伸。②Aluma Systems v. Cherubini Metal Works [2000] PESCAD 9 at par. 19.兩者差異之處在于,爭點禁反言適用于在前一程序中已為仲裁庭或法院裁斷了的爭議點;禁止程序濫用原則針對的卻是“當事人能夠但事實上卻沒有提出的請求或者爭議點”,換言之,這些爭議點事實上沒有得到前一程序中的仲裁庭或法院的裁斷。由此可見,European Re提起的爭點禁反言抗辯并非程序濫用之行為,因為“如何正確理解和適用仲裁條款”這一爭議點已經在事實上為前一程序即Boyd仲裁所裁斷,并已經在事實上產生了爭點禁反言效力,因而European Re完全有權利提出該項抗辯。
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是,禁止程序濫用原則的適用實際上具有極強的自由裁量性,這點也是其和爭點禁反言制度相區別的地方。適用爭點禁反言制度時,仲裁庭或者法院需要嚴格地考量相關可以量化的因素,而在適用禁止程序濫用原則時,則有相當的價值判斷因素在起作用。實際上,當事人在后一程序中再次提起某一爭議點的行為,本身并不構成濫用程序;如果當事人的這種行為是出于如不正當的騷擾(unjust harassment)等不良動機的話,那么就可能構成濫用程序了。③Bradford & Bingley Building Society v. Seddon [1999] 1 W.L.R. 1482 (C.A.) at 1491.至于如何判斷和衡量這些主觀性相當強的各種動機,則完全在仲裁庭或者法院的自由裁量范圍之內。說到底,禁止程序濫用原則的目的在于保障各當事人之間的公正、公平。④Ernst & Young v. Central Guaranty Trust Company [2001] ABQB 92 at par. 23.
(四)爭點禁反言的新理解
在英國,早在1783年就有案例明確了訴因禁反言和爭點禁反言同樣適用于仲裁裁決。⑤Mustill and Boyd, Commercial Arbitration, Butterworths London 2nd edn, pp.409-415.Diplock大法官在Fidelitas Shipping Co Ltd. v. V/O Exportchleb一案的判決意見中對爭點禁反言作出了如下表述:“爭點禁反言不但適用于訴訟判決,而且同樣適用于仲裁裁決。當事人一旦同意選擇將雙方有關法律權利和義務的爭議提交仲裁庭解決的話,那么他們就要接受仲裁庭對與爭議有關的任何問題的決定的約束。”①Fidelitas Shipping Co Ltd. v. V/O Exportchleb [1965] 1 Lloyd’s Rep 13(CA).對于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其要在英國境內獲得既判力,條件和外國法院判決也是相差無幾:首先,該仲裁裁決必須是具有管轄權的仲裁庭就實體問題作出的終局性判決。針對外國法院的判決,“英國普通法上所指的終局性判決是指享有管轄權的外國法院作出的終審判決,必須是已經解決了當事人之間的所有爭議且不會變更的判決;是償付稅后金錢和利息已經在判決中確定的判決;是沒有對判決的事實或適用的法律提起上訴,并且上訴期已經屆滿的判決。”②錢鋒:《論外國法院民商事判決的承認與執行》,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頁。其次,該仲裁裁決必須得到英國的承認,該點在上文探討英國賦予國際商事仲裁裁決既判力的前提條件時已述及。
然而,值得關注的是,本案中英國樞密院的判決意見認為,European Re在Rowe仲裁中提出的爭點禁反言抗辯,實際上是Boyd仲裁裁決賦予European Re的一項可執行性的權利。③Associated Electric & Gas Insurance Services Ltd v. European Reinsurance Company of Zurich (Bermuda), [2003] UKPC 11.這一觀點頗為新穎,它將爭點禁反言效力看做是一種權利執行的類型。實際上,這種理解很有道理。理論上,既判力的效力內涵可以分為終局效力(conclusive effect)和排斥效力(preclusive effect),其中排斥效力為既判力效力的主要方面。排斥效力也可稱為消極效力,顧名思義,這種效力并不具有“進攻性”,而應該是一種具有“防守性質”的效力。事實上,的確如此。既判力的排斥效力實際上就是所謂的“一事不再理”,具體是指在前一程序中已被裁斷事項,當事人在以后的程序中不得再行提起。舉例來說,仲裁庭就A、B間的爭議C做出了一項裁決,那么,在隨后的程序中,任何一方當事人都不得再次對爭議C提起仲裁或訴訟,仲裁庭或者法院也不得再次審理爭議C。如果針對爭議C的裁決是部分裁決,那么任何一方當事人在部分裁決作出后不得再次請求對爭議C進行仲裁。很明顯,排斥效力具有程序法的性質,它與當事人的實體權利義務并沒有直接聯系。排斥效力通過阻卻對已決事項再行處理,從而使既判力在仲裁或者訴訟程序中具有重大的意義。實際上,既判力問題被廣泛識別為程序上的問題,在普通法系,既判力原則被視為證據規則的內容之一,而在大陸法系,既判力原則一般規定在訴訟法中。因此,從爭點禁反言這項抗辯的實際效果來看,我們完全可以將其視為一項程序性權利。
顯然,該案中European Re提出的爭點禁反言抗辯,我們可將其理解為Boyd仲裁裁決賦予European Re的一項程序性權利,其雖不會直接影響European Re的實體性權利與義務,但通過阻止Rowe仲裁對“如何正確理解和適用仲裁條款”這一已決爭議點再行處理,能間接地影響European Re的實體性權利和義務。由此,不難看出,該案法官將爭點禁反言效力視為一種權利執行的形態,是有其內在邏輯根據的。
四、經驗及其啟示
我國是成文法國家,一切法律問題的處理原則上皆依成文法律法規。對于仲裁裁決的既判力,《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9條規定:“仲裁實行一裁終局的制度。裁決作出后,當事人就同一糾紛再申請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仲裁委員會或者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該條是對仲裁裁決的既判力所作出的原則性規定,它肯定了仲裁裁決具有如同法院判決一樣的終局效力,且不同于法院訴訟的是仲裁還實行一裁終局。然而,仲裁法第9條的規定過于原則,沒有確定既判力原則的適用條件和既判力效力的涵蓋范圍。具體來講,第一,由于仲裁裁決的既判力一般涉及到前后兩仲裁(或者訴訟),前一裁決在什么條件下對后一裁決產生既判力,這未得到明確;第二,裁決理由是否具有既判力,該條未作回答。這一方面反映了“宜粗不宜細”立法價值取向,當然,另一方面,這也為法官結合個案利用司法解釋闡明既判力原則預留了充分的空間。然而,我國法院的法官們似乎沒有充分利用粗糙的立法所預留的司法解釋的機會。比如,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2009)二中民特字第13538號民事裁定書在處理仲裁裁決“一事不再理”時,僅僅羅列完相關事實,然后對羅列后的事實僅作簡單說明,再援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9條,對前述事實及其說明進行裁斷,在該裁定書中完全無法找到既判力原則的闡釋過程和結合案件進行具體說明的言語。
回顧上文英國法院對Associated Electric v European Re案的處理,雖然英國并非成文法國家,樞密院在處理該案時未引用成文法條,但整個法律推理過程清晰流暢、說服力強。樞密院首先從三個不同角度說明了當事人在Rowe仲裁中援引Boyd仲裁裁決并不違反仲裁保密性原則,這為既判力原則的適用“掃清”了第一道障礙;緊接著其對爭點禁反言制度進行了說明,指出爭點禁反言抗辯實際上是一項可執行性的權利;最后點出“如何正確理解和適用仲裁條款”的問題在Boyd仲裁中意義重大,這一點至為關鍵,它實際上意味著該案已經具備適用既判力原則的充分條件了。
法律,無論成文抑或不成文,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皆處于沉睡之狀態,需要法官結合個案利用司法解釋去激發它們的活力。期望成文法國家對任何法律原則進行細化再細化,這不現實;過于抽象的規則在一定條件下亦有相當的潛在優勢。然而,俾使這種潛在優勢化為現實的前提是,法官必須具備高度的司法能動性,惟其如此,才能寄望其將正義輸送至每一案件之中。倘使法官不具備這種素質,則恐還需將立法進一步明確、進一步細化為好。揆諸上文之分析,普通法系的經驗為我們法官在個案中運用既判力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參考價值。我國法官在遇到仲裁裁決的既判力問題時,可嘗試吸納普通法系的經驗,采用更加靈活、更加具體的制度來闡釋既判力原則,比如引入以爭點為核心的既判力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只有對案件具有關鍵影響的爭點才能被賦予既判力,這或許更有益于法律的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達致統一。①既判力原則很大程度上代表著法律的形式正義,維護了法的穩定性,然而過于僵硬地適用既判力原則有損害法律的實質正義之嫌。任何裁判的效力并非絕對,應賦予法官足夠的自由裁量權去平衡這兩種正義之間的關系。Xavier Groussot and Timo Minssen, Res Judicata in the Court of Justice Case-Law: Balancing Legal Certainty with Legality?,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Law Review, 2007, 3, pp.385-417.
(責任編輯:姚創峰)
Common Law’s Approach to Res Judicata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Taking Associated Electric v. European Re as an example
By Fu Panfeng
Res judicata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has a noteworthy practical dimension. Rules and practic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vary in applying the principle of res judicata.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have, in their long-term judiciary practice, developed such rules as cause of action estoppel, collateral estoppel and abuse of process, which are unique to their legal system. These rules of res judicata, which are strikingly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civil law countries, embody the spirit of common law tradition. This paper starts from and analyses the case of Associated Electric v. European Re, through which to elaborate on common law’s approach to and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res judicata and finally to draw some useful experience for our country’s legal practice.
arbitral award, common law system, res judicata
?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博士生
仲裁實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