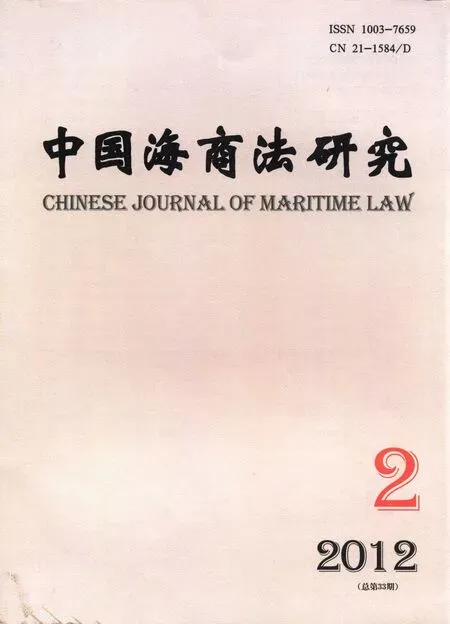論船舶油污損害的損失分擔*
郭紅巖
(中國政法大學 國際法學院,北京 100088)
郭紅巖.論船舶油污損害的損失分擔[J].中國海商法研究,2012,23(2):33-38
2012-06-11
郭紅巖(1964-),女,遼寧遼中人,法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E-mail:hongyanguo@yahoo.com.cn。
論船舶油污損害的損失分擔*
郭紅巖
(中國政法大學 國際法學院,北京 100088)
船舶油污損害損失分擔是指由導致油污損害的船舶所有人、石油進口商和船旗國等主體,按照一定的歸責原則和賠償序位,對船舶跨界油污損害的受害者所遭受的損失分擔賠償義務的法律機制。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國際社會逐步建立了船舶油污損害損失分擔的制度模式,確立了民事責任人的限額民事責任和石油進口方的限額賠償義務,但沒有涉及船旗國的國際賠償責任。從船舶油污損害損失分擔的概念入手,對現行分擔船舶油污損害損失的主體及其局限性進行分析,論述建立有船旗國參與的船舶油污損害三級賠償機制的基本框架及其意義。
船舶油污損害;損失分擔;三級賠償;船旗國的國際賠償責任
一、船舶油污損害損失分擔的概念和相關制度的確立
船舶油污損害可分為營運中正常的油類排放所導致的油污損害和由于事故導致運載的油類溢出所引發的油污損害。[1]不同的船舶油污損害涉及的主體不同,所適用的原則和規章制度也有所不同。筆者探討的船舶油污損害是指運油船舶在海上航行過程中因碰撞、觸礁、擱淺、風暴等自然或人為因素,逸出或者排放油類貨物、燃料油或其他油類物質,如廢油、油類混合物等,在運油船舶以外,因污染而產生的財產損害或人身傷亡,包括事故發生后為防止或減輕此種損害而采取的合理的預防措施的費用,以及由于采取此種措施而造成的進一步損害*參見《1969年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第1條;《1992年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第2條。。
船舶油污損害損失分擔是指由導致油污損害的船舶的所有人、船舶所運載的油類貨物的貨主等受益者以及船旗國等主體,按照一定的歸責原則、賠償序位和賠償額度,對油污損害的受害者所遭受的損失分擔賠償義務的法律機制。從油污損害賠償的現行國際立法來看,分擔油污損害損失的主體包括首位主體和次位主體,首位主體的民事責任人被確定為船舶所有人,次位主體為石油進口商。韓立新教授將其分別稱為“直接賠償義務人”——“即對其自身行為或對其受雇人、代理人的行為或與其所有或經營的船舶有關的事件所造成的人身傷亡損害承擔第一位賠償責任的人”;“間接賠償義務人”——“即對船舶侵權損害承擔第二位賠償責任的人,他以直接賠償義務人存在侵權損害賠償之法定義務為前提”。[2]為了完善油污損害損失分擔機制,稱其為“首位主體”和“次位主體”更為方便和合理。
現行船舶油污損害損失分擔機制是通過由政府間海事協商組織(國際海事組織前身)主持締結的兩個公約體系建立起來的,分別是1969年通過的,經1976年、1984年、1992年和2000年議定書修訂的《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體系(分別簡稱《1969年油污責任公約》《1976年油污責任公約》《1984年油污責任公約》《1992年油污責任公約》《2000年油污責任公約議定書》)以及1971年通過的,經1976年、1984年、1992年、2000年和2003年議定書修訂的《設立國際油污賠償基金公約》體系(分別簡稱《1971年基金公約》《1976年基金公約》《1984年基金公約》《1992年基金公約》《2000年基金公約議定書》《2003年基金公約議定書》)。
1967年,“Torrey Canyon”油污事件促使國際社會制定通過了《1969年油污責任公約》,確立了歸于船舶所有人的嚴格賠償責任,船舶所有人應對不能合理分割的所有損害承擔連帶責任。關于《1969年油污責任公約》與船舶油污損害損失分擔制度的關系,國際法委員會在2004年第56屆會議上指出*參見A/CN.4/543,第44頁,第119段。,《1969年油污責任公約》對船舶油污損害的損失分擔甚至跨界損害的損失分擔具有開山的作用,因為“該公約處理了四個重要問題,即:必須(a)協調賠償責任,由船舶所有人而不是經營人或貨物所有人承擔賠償責任;(b)確保污染者付費;(c)分擔損失和費用;(d)消除沿海國家在獲得賠償方面的管轄權障礙。”
然而,如果孤立地看《1969年油污責任公約》的內容,我們無法找出體現或直接規定船舶油污損害損失分擔的條款。國際法委員會之所以認定《1969年油污責任公約》對跨界損害損失分擔具有開山的作用,主要是因為在《1969年油污責任公約》的談判過程中,船舶所有人得到了石油進口商的承諾,將在船舶所有人以外,由石油進口商繳納進口石油攤款,建立國際油污賠償基金。當船舶所有人的保險保障限額責任不能滿足對受害者的賠償時,由國際油污賠償基金進行補充賠償。這也是為什么船舶所有人接受自己作為民事責任人承擔首位賠償責任的條件。因此,從條約的具體文字內容來看,真正體現和實踐油污損害損失分擔的第一個條約是《1971年基金公約》。
《1971年基金公約》在序言中指出,“為了保證能對油污事件的受害者補償全部損失,與此同時又能使船舶所有人方面得以解除該公約所加予的額外經濟負擔,有必要認真擬訂一項賠償和補償制度,作為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的補充。”《1971年基金公約》不僅在序言中明確表達了油污損害損失分擔的理念和思想,而且根據公約條款所建立的國際油污賠償基金及其使用的規定,都切實保證了對船舶油污損害的損失分擔。《1976年基金公約》《1984年基金公約》《1992年基金公約》《2000年基金公約議定書》《2003年基金公約議定書》使石油進口商對損失賠償的限額不斷增加,分擔損失的比例也得以逐步提高。
船舶油污損害損失分擔屬于由民事責任人和受益人分擔損失的具體模式,這種模式也被其它領域所借鑒。1996年5月3日,國際海事組織大會通過了《國際海上有毒有害物質運輸損害責任和賠償公約》,該公約即是沿用《1969年油污責任公約》和《1971年基金公約》所建立的雙重賠償主體模式,把類似于《1969年油污責任公約》的第一重賠償機制和類似于《1971年基金公約》的第二重賠償機制置于一個公約中,形成了國際海上有毒有害物質運輸損害責任和賠償的雙重賠償機制。
二、現行船舶油污損害損失分擔制度的局限性
(一)現行船舶油污損害損失分擔的主體只有雙重主體
根據《油污責任公約》體系和《基金公約》體系的規定,分擔油污損害損失的民事責任人為船舶所有人,損失分擔人為石油進口商。
《1969年油污責任公約》第1條第3款規定,船舶所有人應對事件引起的油類溢出或排放所造成的污染損害負責。船舶所有人是“登記為船舶所有人的人;如果沒有這種登記,則是指擁有該船的人。如船舶為國家所有,而由在該國登記為船舶經營人的公司所經營,‘船舶所有人’即指這種公司”。公約明確排除了船舶所有人的雇傭人員、服務人員或代理人對公約規定的油污損害的民事責任。鑒于“船舶所有人”在實踐中的具體情況,韓立新教授建議:“在燃油污染損害賠償中,船舶所有人還包括光船承租人、船舶管理人和船舶經營人”;“單船公司的船舶造成污染時,如果能夠證明其母公司具有利用該船舶登記進行欺詐的行為,或者對該船舶進行操縱或控制的,可以認定該母公司是船舶真正所有人。”[3]而且在實踐中,船舶油污損害的民事責任人確實有擴大的趨勢,船級社、航次承租人、以及船舶管理公司等都可能被確定為民事責任人。[4]但不論船舶所有人的外延如何擴大,他們的賠償仍然屬于同一層級的賠償,仍然屬于民事責任人的民事責任范疇。
石油進口商不僅是污染事故的潛在的肇事者,也是除船舶所有人以外的直接受益者。根據“受益者分擔損失”的原則,石油進口商以國際油污賠償基金的形式參與對受害者的賠償。國際油污賠償基金具有獨立的法律地位。基金款項來源于符合條件的石油進口商——基金攤款人繳納的攤款。《1971年基金公約》第10條規定,基金攤款人(contributor)是在公約所規定的日歷年度中,在締約國領土內的港口或油站收到從海上運至這些港口或油站的攤款石油總量超過15萬噸的人,或者,當在締約國領土內的任何人在一個日歷年度所收到的攤款石油量與同一締約國中的任何關系人在該日歷年度內所收到攤款石油量合計超過15萬噸時,即使其本人收到的數量不超過15萬噸,也應按其所收到的實際數量交付攤款。通常情況下,基金攤款由攤款人直接支付,不是由國家代為支付。締約國負有義務每年向基金會的主席通報其有義務攤款的石油公司的名單、地址和收到攤款石油的數量。《基金公約》體系已經明確了由石油進口商出資建立的“國際油污賠償基金”分擔油污所致損失的義務。《1976年基金公約》《1984年基金公約》《1992年基金公約》以及《2000年基金公約議定書》,不斷增加石油進口商對損失賠償的限額,分擔損失的比例也得以逐步提高。2003年5月16日在倫敦制定的《2003年基金公約議定書》第4條第1款又設立了補充賠償基金。但該“補充基金”補充賠償的條件是損失總額超過或有可能超過《1992年基金公約》的賠償限額但仍不能滿足對受害者的充分和適當的賠償。而且,該“補充基金”仍然屬于國際油污賠償基金,資金仍來源于締約國的進口石油攤款,賠償主體沒有增加,仍為雙重主體。
(二)責任限制使賠償額度有限
關于船舶所有人的限額責任,《1969年油污責任公約》中規定,船舶所有人有權將其依本公約對任何一個事件的賠償責任總額限定為按船舶噸位計算每噸2 000法郎,但這種賠償總額在任何情況下不得超過2.1億法郎;在締約國登記的載運2 000噸以上散裝油類貨物的船舶所有人,必須進行保險或取得其他財務保證,例如銀行保證或國際賠償基金出具的證書等,以便按本公約規定承擔其對油污損害應負的責任;這種保險所籌集的款項只能專款專用,不得用于其他用途;締約國應保證懸掛本國旗幟的運營船舶確已取得合格的保險或財務保證證書。
《1984年油污責任公約》不僅擴大了公約的適用范圍,還提高了賠償責任限額。該公約第6條規定,船舶所有人有權按本公約將其對任一事件的賠償責任限于按下列方法算出的總額:不超過5 000噸位的船舶為300萬計算單位;超過此噸位的船舶,每增加1噸位單位,增加420計算單位;但是,此總額在任何情況下不得超過5 970萬計算單位。由于《1984年油污責任公約》的生效條件較為嚴苛,未能生效。
《1992年油污責任公約》關于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的額度與《1984年油污責任公約》相同,只是規定了較寬的生效條件。
2000年10月18日,國際海事組織又通過了《2000年油污責任公約議定書》,該議定書已于2003年11月1日生效。該議定書的賠償責任限額與《1992年油污責任公約》的限額相比,提高了大約50%,將不超過5 000噸位的船舶的責任限額由原來300萬計算單位提高到451萬計算單位;超過此噸位的,每增加1噸位,賠償限額將由原來的420計算單位提高到631計算單位。把賠償總額由原來的“在任何情況下不得超過5 970萬計算單位”提高到8 977萬計算單位。
關于國際油污賠償基金的限額責任,《1971年基金公約》第4條規定,在每一事件中,不論是船舶所有人的致害,還是不可抗力事件,由船舶所有人和國際油污賠償基金付給受害人的賠償金合計金額不應超過4.5億法郎;如果基金大會因匯率變化等原因提高限額,最多也不超過9億法郎。
《1984年基金公約》大大提高了賠償限額,但該議定書沒能生效。《1992年基金公約》則采納了《1984年基金公約》對賠償額的調整*參見1992年《基金公約》第6條第4款(a)、(b)和(c)。。即在每一事件中,不論是船舶所有人的致害,還是不可抗力事件,付給受害人的合計賠償金額不應超過1.35億計算單位;如果攤款人在本公約3個締約國的領土內所接收的有關攤款油類總量在前一日歷年度等于或超過6億噸,則不論發生何種事故,也不論何時發生事故,賠償金額最多不超過2億計算單位。
2003年11月1日生效的《2000年基金公約議定書》規定,每一事件中,不論是船舶所有人的致害,還是不可抗力事件,付給受害人的賠償金合計金額不應超過2.03億計算單位;如果攤款人在本公約3個締約國的領土內所接收的有關攤款油類總量,在前一日歷年度等于或超過6億噸,則不論發生何種事故,也不論何時發生事故,付給受害者的賠償金合計最多不超過3.0074億計算單位。
2003年5月16日在倫敦制定的《2003年基金公約議定書》又設立了第三級補充賠償基金。但該“補充基金”只是在損失總額超過或有可能超過《1992基金公約》的賠償限額而仍不能滿足對受害者的充分和適當的賠償的情況下才適用。而且,對任一油污事件來說,在該議定書適用的范圍內,該“補充基金”與根據《1992年油污責任公約》和《1992年基金公約》實際支付的賠償金額之和不應超過7.5億計算單位*參見2003年《基金公約》議定書第4條第2款(a)。。即對于任一油污事件來說,即使有該“補充基金”的參與賠償,受害者也只能獲得不超過7.5億計算單位的賠償。美國一直未參加這兩個國際公約體系,而是制定了《1990年油污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國認為這兩個公約體系所確立的賠償數額過低。
既然現行賠償額度無法滿足對受害者的賠償,那么,能否在不增加賠償主體的情況下,以繼續提高賠償限額,甚至將限額責任變為無限責任的辦法來擺脫目前的困境呢?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全球貿易量的85%以上是通過海上運輸實現的,而海上運輸又具有較高的風險,如果不采取限額責任,不僅會阻礙航運業本身的發展,對世界貿易也是極其不利的。同時,石油行業也需要得到保護,不能讓石油進口商承擔過重的賠償義務。在這種情況下,只能考慮從主體的增加和主體“注意義務”的激勵上去解決。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引入船旗國的末位賠償,由船旗國承擔國際法上的起源國的國際賠償責任,對受害者的損失進行補充賠償。
三、船舶油污損害損失分擔賠償機制的完善
建立和完善船舶油污損害損失分擔的三級賠償機制,必須引入船旗國的賠償。只有在船旗國參與的基礎上,才能建立起真正的首位主體、次位主體和末位主體共同分擔損失的三級賠償機制。首位主體承擔限額民事責任,這種義務是基于侵權而導致的損害后果。次位主體承擔限額賠償義務,該義務不是基于侵權而產生,而是基于承諾而確立的。這兩級賠償主體也可能由多人組成,他們對受害者或者是按份賠償,或者是按序賠償。末位主體承擔補充賠償義務,這種賠償義務也不是基于侵權產生,而是基于其船旗國的身份而產生。其中,首位主體的限額民事責任是主責任,是次位主體和末位主體賠償義務開啟的前提。沒有首位主體的民事責任,就不可能有次位主體和末位主體的賠償義務,因此,次位主體和末位主體的賠償義務是從義務,是不能獨立存在的。而且,在次位主體和末位主體之間也有序位的先后,即由次位主體先在限額內足額履行賠償義務仍不能滿足對受害者賠償的情況下,才可能啟動末位主體的賠償。所以,末位主體的賠償是補充性的。
具體來說,船舶所有人作為首位主體,承擔民事侵權責任,履行限額賠償義務。船舶所有人依法履行了限額賠償后,如果仍不足以彌補受害人的損失,則啟動次位主體的賠償,即由石油進口商攤款建立的國際油污賠償基金進行賠償。如果首位主體和次位主體都履行了最高限額的賠償仍不足以賠償受害人的損失,則啟動末位主體的賠償,即由船旗國的國家財政出資建立油污損害賠償專項基金,并設置配套的財政保障制度和基金管理機構,承擔最后的補充賠償義務,這也是保護受害者權益的最后手段。
船旗國作為末位主體的國際賠償責任是船旗國以國家的名義對于具有本國國籍的船舶所造成的跨界油污損害的賠償責任。這種責任的性質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首先,它不是主責任,而是從責任,它以船舶所有人的油污損害責任的存在為前提。其次,該責任具有補充性,它只是在船舶所有人和國際油污賠償基金履行了賠償義務仍不能滿足對受害者賠償的情況下,才開始啟動,對受害者未獲償付的損失進行補充賠償。再次,它屬于起源國對國際法不禁止行為所致跨界損害的國際賠償責任(international liability),不是國際不法行為所導致的國家責任(state responsibility)。最后,這種責任具有保證性的意義,即船旗國作為海上石油運輸船舶的國籍國,負有不損害國外環境權益的一般國際法義務,船旗國應盡最大的注意,確保其運油船舶在海上航行過程中不對海洋環境或其他國家造成損害。否則,在船舶所有人和國際油污賠償基金不能滿足對受害者賠償的情況下,船旗國應當履行國際賠償責任,保證受害者獲得及時和充分的賠償。
船舶油污損害損失分擔是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在國家責任的大項目下逐漸延伸出來的一個新的議題。它圍繞污染者付費、受益者分擔損失、起源國履行國際義務的本源基礎討論這個問題。這不僅從程序上有利于實現對受害者及時和充分的賠償,在實體上也有利于實現國內法和國際法兩個層面的公平和正義。它突破了傳統的過錯責任原則以及法律的懲罰性功能,是從矯正正義向分配正義的轉變。
然而,現行船舶油污損害損失分擔制度中并沒有明確船旗國的國際賠償責任,致使船旗國疏于對船舶的有效管理,導致船舶油污損害事件頻發,在給受害者造成巨大損失的同時,也嚴重污染海洋環境。因此,引入船旗國的國際賠償責任,建立船舶油污損害損失分擔的三級賠償機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第一,有利于受害者獲得及時和充分的賠償。關于船旗國的國際賠償責任,《1969年油污責任公約》體系只是要求作為締約國的船舶登記國要履行對船舶的登記義務,并保證船舶獲得適格的保險或財務保證。《1971年基金公約》體系也只關注石油進口商的二級次位賠償,沒有涉及船旗國的賠償義務問題。2006年國際法委員會通過的《關于危險活動造成的跨界損害案件中損失分配的原則草案》將受害人獲得及時和充分的賠償作為跨界損害領域的一項基本原則規定下來,并要求“各國應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其領土上或其管轄或控制下的危險活動所造成跨界損害的受害者獲得及時和充分的賠償*參見A/CN.4/L.686,第3條、第4條。。”其中,“及時”是指時間上的即時性,即受害者能夠獲得盡可能快的賠償。“充分”是對賠償的質和量的要求。在一般侵權領域,對于受害者的實際財產損失多采取“完全賠償原則”,即侵權人對自己的侵權行為或準侵權人給受害者造成的實際損失或者說全部財產損失承擔賠償責任。[5]在船舶油污損害領域,雖然不能采取完全賠償原則,但也不能忽視給予受害者及時和充分的賠償。這不僅影響到受害者的生存和發展,也影響到社會的和諧和可持續發展。引入船旗國的國際賠償責任,完善船舶油污損害損失分擔的三級賠償機制,使對受害者的賠償主體又多了一個層級,增加了一重保障。這對于恢復受害者正常的生產和生活,維護社會穩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第二,有利于減少方便旗船舶,促使船旗國履行謹慎監督義務,減少或避免油污事故的發生,保護海洋環境。根據國際法,船旗國和船舶之間不僅要有真正的聯系,而且船旗國必須對本國船舶進行實質有效的行政、技術和社會事項的管理。《1958年日內瓦公海公約》第5條第1款規定,每個國家應確定對船舶給予其國籍、船舶在其領土內登記以及船舶懸掛本國旗幟的權利的條件。船舶具有被授權懸掛其旗幟的國家的國籍。國家和船舶之間必須具有真正的聯系,特別是,一國必須對懸掛其國旗的船舶有效地行使行政、技術和社會問題上的管轄和控制。《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91條第1款規定,每個國家應確定對船舶給予國籍、船舶在其領土內登記及船舶懸掛該國旗幟的條件。船舶具有其有權懸掛的旗幟所屬國家的國籍。國家和船舶之間必須有真正聯系。第94條第1款規定,每個國家應對懸掛該國旗幟的船舶有效地行使行政、技術及社會事項上的管轄和控制。《1986年聯合國船舶登記條件公約》在序言中指出:船旗國有義務根據真正聯系原則對懸掛其國旗的船舶有效地行使管轄和控制……確保對在該國登記的船舶的管理和經營負責的人的身份能易于識別并使其承擔責任。在第1條“宗旨”中規定,為了確保,或在可能情況下加強一國與懸掛其國旗的船舶之間的真正關系,并為了在船舶所有人和經營人身份的識別和承擔責任方面,以及在行政、技術、經濟和社會事務方面對這些船舶有效地行使管轄和控制,船旗國須適用本公約所載的條款。三個公約都明確規定了“船旗國有義務根據真正聯系原則對懸掛其國旗的船舶有效地行使管轄和控制”。但令人遺憾的是,上述有關公約并沒有對不遵守公約規定的違約行為規定具體的制裁措施,致使很多規定流于形式,方便旗船舶仍然大量存在。由于方便旗船舶的船旗國對船員的雇傭不加限制,對船舶的行政、技術和社會事項管理松懈,致使船舶在海上航運過程中,事故發生率高達非方便旗船舶的5倍左右,不僅對海洋環境造成巨大的威脅,也給受害者造成巨大的損失。
從“Torrey Canyon”事件開始,幾次影響較大的油污跨界損害事件幾乎都是方便旗船舶造成的。“Torrey Canyon”的船舶所有人是美國人,但卻在利比里亞注冊并取得利比里亞國籍。[6]8后來經調查,該油污事故是由于船長的疏忽造成的。“Amoco Cadiz”在事故發生時,屬于一家在利比里亞注冊的阿莫科運輸公司所有,該船舶在利比里亞注冊,具有利比里亞國籍,但利比里亞阿莫科公司只是美國標準石油公司的子公司,美國標準石油公司才是該船舶的真正所有人。該事故的主要原因是船舶不適航,駕駛系統已經損壞,船員也沒有受過足夠的訓練。[6]12“Prestige”是日本在1970年代生產的單殼油輪,船舶所有人是一家利比里亞公司,實際管理者和船長都是希臘人,懸掛巴哈馬國旗,也是一艘方便旗船舶。[6]39早在20世紀90年代,國際航運組織就要求各國航運公司報廢單殼油輪,但船東們置若罔聞,方便旗國家也疏于管理,最終導致了災難的發生。
方便旗船舶油污損害的事故率表明,船旗國對船舶疏于管理,使不符合航行條件的船舶在海上航行,是導致重大油污事件的根本原因。方便旗船舶屢禁不止,相應的法律規章形同虛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權利義務的失衡。方便旗國家只是收取登記費,甚至將此作為創匯的一種手段,卻不履行船旗國義務。因沒有具體的法律責任和義務的規定,“船旗國和船舶之間要有真正的聯系”幾乎成了道德規則,很難發揮令行禁止的作用。
如果對船旗國課以補充性的國際賠償責任,采取開放登記制度的國家就不會輕易賦予由外國人所有的船舶以國籍。同時,在海洋環境保護日益迫切的背景下,船旗國為了避免高額的補充賠償,必然加強對船舶的行政、技術和社會事項的管理,使運營船舶處于良好的適航狀態,減少或避免船舶油污事件的發生。在污染事故發生后,船旗國也會盡速做出反應,防止損害和損失的擴大,從根本上避免或減少船舶油污損害事件的發生,保護海洋環境。
四、結語
以《油污責任公約》體系和《基金公約》體系為基礎的船舶油污損害損失分擔制度,與跨界核損害損失分擔制度一起,構成了跨界損害損失分擔的兩種典型模式。[7]現行的船舶油污損害損失分擔同之前的僅由船方承擔賠償責任的機制相比,增加了石油貨主的賠償,使賠償機制從單重主體的損害賠償發展為雙重主體對損失的分擔,不僅是船舶油污損害賠償機制的與時俱進的發展,也有利于實現對受害者的賠償。但隨著超級油輪投入運營,油污損害災難頻發,損失的嚴重等級不斷提高,船舶所有人和石油進口商的雙重賠償機制不僅無法滿足對受害者的賠償,也無法減少或消除方便旗,無法促使船旗國加強對船舶的管理,嚴重威脅著海洋環境和安全。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完善船舶油污損害損失分擔機制,在加強船舶所有人民事責任和石油進口商損失分擔義務的基礎上,引入船旗國對船舶油污損害的國際賠償責任,形成完善的首位、次位和末位主體各司其職、各負其責的三級賠償機制,進而建立和完善使船旗國的登記收費權利與其相應的管理義務和國際責任相對應的法律制度體系,才能從根本上促使船旗國加強對船舶的行政、技術和社會事項的管理,從源頭上消除隱患,減少和避免船舶油污損害事故,保護海洋環境,增進人類福祉。
[1]林燦鈴.國際環境法[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401.
LIN Can-ling.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M].2nd ed.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1:401.(in Chinese)
[2]韓立新.海上侵權行為法研究[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475.
HAN Li-xin.Study on maritime tort law[M].Beijing: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11:475.(in Chinese)
[3]韓立新.船舶污染損害賠償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11.
HAN Li-xin.Study on legal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pollution damage caused by ships[M].Beijing:Law Press,2007:111.(in Chinese)[4]韓立新.從典型船舶油污案件看國際油污責任制度的新發展[C]//2012兩岸四地海商法研討交流會論文集,2012:265-270.
HAN Li-xin.On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of liability for oil pollution caused by ships through reviewing some typical cases[C]//Proceedings of 2012 Maritime Law Forum of Four Districts of Cross-straits,2012:265-270.(in Chinese)
[5]張新寶.侵權責任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101.
ZHANG Xin-bao.Tort liability law[M].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10:101.(in Chinese)
[6]萬霞.國際環境法案例評析[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
WAN Xia.Cases comment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M].Beijing: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2011.(in Chinese)
[7]郭紅巖.跨界損害損失分擔基本理論問題研究[D].北京:中國政法大學,2011:125-131.
GUO Hong-yan.Study on basic theoretical issues related to allocation system of loss in the case of transboundary damage[D].Beijing: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2011:125-131.(in Chinese)
Onallocationoflossforoilpollutiondamagecausedbyships
GUO Hong-yan
(International Law School,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8,China)
Allocation of loss for oil pollution damage caused by ships is an institutional system by which ship owners who cause pollution, oil importers as beneficiaries and flag states of ships allocate loss to compensate victims according to certain sequence and rules.Establishing and perfecting a legal mechanism to ensure victims for timely and sufficient compensation is important.At the end of 1960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gradually set up an institutional compensation model on oil pollution damage caused by ships, by which ship owners who cause pollution bear liability for damage and oil importers allocate some loss as beneficiaries.However, this mechanism does not address any international liability for flag state.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perfect the mechanism of three-level compensation by establishing the international liability of flag state.
oil pollution damage caused by ships; loss allocation; three-level compensation; international liability of flag state.
DF961.9
A
1003-7659-(2012)02-003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