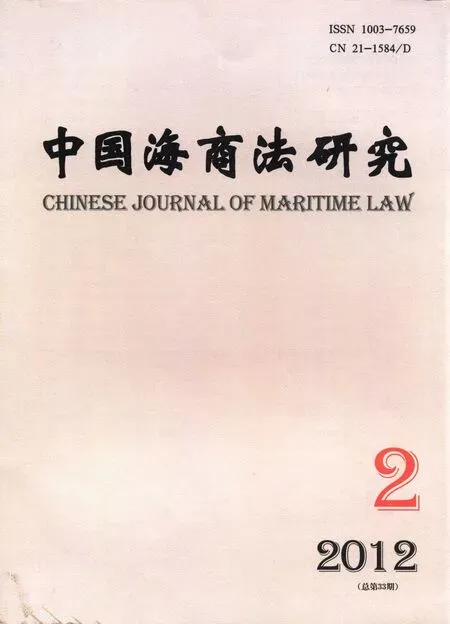船舶油污損害公約在中國的適用問題研究*
葉洋戀
(華東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上海 200042)
一、問題的提出
日益脆弱的海洋環境促使國際社會日益重視對海洋所擔負的義務,從20世紀50年代起,許多以保護海洋環境為宗旨的國際公約陸續被制定出來。致使海洋遭受污染的原因很多,海底礦產資源的開采、石油及天然氣的開發、海洋生物的過度捕撈以及核污染等等。在這些因素中,最早受到國際社會關注的是油污問題。1954年,彼時政府間海事協商組織(國際海事組織的前身)尚未成立,第一次國際防止海洋油污會議在倫敦召開,會議通過了《防止海洋油污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for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of the Sea by Oil,1954)。從這個公約開始,關于油污損害方面的公約被不斷地討論和通過。至今,這些公約已經形成了一個防止船舶油污損害的國際法律體系。[1]388-412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隨著經貿的發展和航運業的騰飛,中國也加入了一系列涉及油污損害的國際公約。公約要產生效力,就必然涉及其在內國的適用。在中國,這些公約的適用一方面促進了國內油污損害的立法進程,另一方面也給實踐中應當如何適用公約提出了一些問題。
截至2012年3月,中國已經加入的涉及船舶油污損害方面的公約有:《1969年干預公海油污事故公約》及其1973年議定書(自1990年5月24日起對中國生效,1997年7月1日對香港特區生效)、《1973年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及其議定書(1996年3月3日生效,中國是締約國)、《1990年國際油污防備、響應和合作公約》(1998年6月30日對中國生效)、《1969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簡稱1969 CLC,1980年4月29日起對中國生效)、《1969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1992年議定書(簡稱1992 CLC,2000年1月5日對中國生效)、《1971年設立國際油污損害賠償基金國際公約》1992年議定書(僅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生效)、《2001年國際燃油污染損害民事責任公約》(2009年3月9日起對中國生效)。
從性質上看,這些公約可以明顯地歸為兩類。一類以加強船舶管理和防止油污事故發生為目的,另一類則以污染事故發生后的彌補和賠償為目的。
對于第一類公約中規定的事項,中國國內有相對應的法律規范。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簡稱《海洋環境保護法》)第71條規定了國家海事行政主管部門對船舶污染事故的干預權,這種干預包括公海上發生的海難事故。這是對《1969年干預公海油污事故公約》的呼應。同樣,《海洋環境保護法》第8章“防治船舶及有關作業活動對海洋環境的污染損害”中的相關規定則是對《1973年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及其議定書精神的貫徹。國務院頒布的《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理條例》,一方面對《海洋環境保護法》及《1973年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及其議定書進行了細化,另一方面也體現了《1990年國際油污防備、響應和合作公約》中的應急事故及時處理原則。可是,在公約和國內法的適用規則問題上,究竟應當如何界定并不明確。
對于第二類公約中規定的事項,中國雖然加入了1992 CLC和《2001年國際燃油污染損害民事責任公約》,但國內還沒有關于船舶污染損害賠償的專門立法,涉及這方面的規定散見于不同的法律和行政法規之中,并且多為抽象的原則性規定和程序性規定,在司法實踐中可操作性不強。[1]416
類似情形使得在中國適用有關船舶油污損害方面的公約可能面臨兩個問題,其一是在公約和國內法均有規定的情況下,適用的規則和順序應當如何界定;其二是在僅有公約規定而無國內法規定的情況下,公約是否能夠在國內直接適用,如果能,其效力范圍又如何。這既涉及到公約在中國的法律地位問題,又反映了公約在中國的接受方式和實施情況。目前國內法對上述兩個問題并無明確規定,有鑒于船舶油污損害的危害性以及產業和環境平衡的重要性,筆者將從國際法理論出發,考察船舶油污損害公約在中國的適用。
二、國際法理論上的一般原理
關于國際條約在中國國內的法律地位問題,憲法并沒有原則上的規定。條約在中國的法律體系中處于何種地位,需要從學理上對相關法律規定予以分析。
(一)條約與國內法的關系
國際法理論中,關于條約在國內法的地位,存在許多觀點。總的說來,從理論上探討國際法與國內法之間關系的學者主要來自歐洲大陸國家,如德國、意大利和法國,而英美等普通法國家一般說來不重視理論問題,而偏重對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關系的實際解決方法以及各國在這方面的實踐。[2]
中國國際法學者李浩培先生認為,各國的現行制度可以大致分為四類:一是國內法優于條約;二是國內法與條約的地位平等;三是條約優于國內法;四是條約優于憲法。[3]323-331這種分類方式更多地體現為對國際法與國內法關系問題的延伸思考。而國際法與國內法關系的問題,又涉及到二元論和一元論的理論劃分。在這個問題上,學者們一般將一元論分類為國內法優先說和國際法優先說,[4]而二元論似乎是現代國際法學界的主流觀點,勞特派特修訂的《奧本海國際法》就是這種觀點的忠實擁護者。雖然二元論還有不完善之處,但總的說來,它關于國際法和國內法的重大區別的觀點是比較接近客觀現實的。正因如此,許多從事司法實踐的法官,特別是國際法院法官基于國際法與國內法在法律淵源和適用范圍方面的區別,也支持二元論的觀點。[5]
周鯁生先生的劃分方式有所不同,他將各國的實踐歸納為了三種形式:一種是把條約認作法律在國內當然執行,美國是采用這種形式的代表,在美國條約的效力要受到后來的與條約相抵觸的法律的影響。另一種則是英國模式,在英國條約如果沒有預先由國會通過法案,或至少從國會獲得必然通過的保證,國王是不能夠批準的。第三種為介乎于英、美兩種方式之間的德、法等國采用的方式,可以總稱為歐洲大陸的方式。[6]
所以,越來越多的法學家希望避免一元論和二元論的對立,認為兩個論點都與國際和國內機關和法院運行的方式相沖突。或許正因如此,周鯁生先生并未將國際法與國內法之間的關系簡單地歸于一元學說或是二元學說,而是提出“自然調整說”。[7]周先生認為,從法律和政策的一致性的觀點來說,只要國家自己認真履行國際義務,國際法和國內法的關系總是可以自然調整的。
(二)條約的國內法效力
調和國際法和國內法相互間的關系確是國際法在內國得以有效施行的重要原因。因此,作為國際法體系的組成部分,國際條約在中國的適用也需要調和其與中國法律規定之間的關系——承認條約的國內法效力。
日本學者曾經說過:所謂國內法中關于承認條約的國內效力的規定,具有創設的效果。也就是說,有了這種規定,條約才具有國內效力。換句話說,這種規定具有把條約全面地“納入”國內法中,使之“國內法化”的效果。正因為沒有使條約因其本身所固有的效力而理所當然地具有國內效力,才使承認條約的國內效力與否,和在什么程度上承認條約的國內效力,成了各國的自由。[8]
李浩培先生認為,一個在國際上已經生效的條約,其規定在各國國內得到執行是以得到各國國內法的接受為前提條件的。接受條約規定的各國國內法,可以是憲法、議會制定法或者判例法。接受本身可以分為兩種:一是將條約規定轉變為國內法;二是無需轉變而將條約納入國內法。前者以英、意為代表。后者以美國為代表。[3]314-318
條約是否是國內法,各國并沒有一個統一的結論,而是取決于各個國家的憲法。有的國家的憲法明確規定條約是國內法律,《美國憲法》第2條第2節即規定,“在美國的權力下締結的一切條約,與美國憲法和根據該憲法制定的法律一樣,都是美國最高的法律。”但大多數國家的憲法卻并沒有明確規定條約是國內的法律,而只是規定條約可以經過一定的程序或在一定的條件下獲得國內法的效力或具有國內法的權威。《法國憲法》第55條規定,“經過合法批準或核準的條約或協定,在公布后,具有法律的權威”。《德國基本法》第59條也規定,所有規定聯邦共和國政治關系或涉及聯邦立法事項的條約,必須要經過聯邦法律加以規定才能取得在德國法律上的效力。此外,意大利憲法、韓國憲法等也都采取這種模式。憲法規定條約具有國內法律的效力或權威,并不等于條約就是國內的法律,二者必須區分開來。如果憲法規定條約就是國內的法律,那么條約從生效之日起,本身就具有了國內法的效力;如果條約必須要經過一定的程序或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能獲得國內法的效力,問題則要復雜的多,因為其涉及到條約獲得法律效力的方式,即是通過采納的方式獲得法律效力,還是通過轉化的方式獲得法律效力。[9]
中國憲法并沒有就此作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簡稱《立法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條約程序法》(簡稱《締結條約程序法》)中也沒有明確規定條約的締結是否具有立法性質問題。根據中國法律精神,早期學者間持“納入”觀點的分析較多,近年來混合論的觀點成為了一種趨勢,持這種觀點的學者主張對待條約在中國的適用問題,應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如有學者就認為,依照中國現有的立法和司法實踐,中國適用條約的方式一般有三種:一是在國內法中直接適用國際條約;二是將有關條約的內容制定成國內法予以實施;三是只允許間接適用國際條約。雖然中國適用條約的方式有三種,但居主導地位的仍然是直接適用。[10]
按照傳統觀點,對于船舶油污損害公約來說,如果是前述第一類性質的公約,即船舶油污損害公約中以加強船舶管理和防止油污事故發生為目的的公約,問題比較復雜,需要具體分析,但大體上仍然是納入模式;如果是前述第二類性質的公約,即以污染事故發生后的彌補和賠償為目的的公約,則顯然應當直接適用。也就是說,目前在中國,“納入”(又稱“并入”)仍然是船舶油污損害條約獲得法律效力的基本方式。
三、船舶油污損害公約在中國的法律效力問題
(一)依上位法高于下位法方式決定船舶油污損害公約效力
由于中國目前并沒有關于國際條約與國內法關系的一般規定,唯一具體針對條約的法律規范就是《締結條約程序法》。《締結條約程序法》中的相關規定將中國加入的條約分為了三類: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的條約或重要協定;國務院核準的協定或具有條約性質的文件;無需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批準或核準的協定。
按照此種分類,中國截至目前加入的有關船舶油污損害的公約,性質上都屬于國務院核準的協定或條約性質的文件——根據國函[1990]6號“國務院關于加入《1969年國際干預公海油污事故公約》及《1973年干預公海非油類物質污染議定書》的批復”,《1969年國際干預公海油污事故公約》由國務院決定加入,在1990年3月12日至16日召開的 IMO海上環境保護委員會(M EPC)第29屆會議上,中國代表通知委員會中國正式加入該公約;根據原交通部2006年42號文件“關于我國加入經修正的《經1978年議定書修訂的〈1973年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附則I V的公告”,經國務院批準,中國于2006年11月2日向國際海事組織秘書長交存了加入經修正的《經1978年議定書修訂的〈1973年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附則I V的文件,除此以外,《經1978年議定書修訂的〈1973年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本身以及其他幾個附件也均由中國政府批準;根據原交通部1998年327號文件“關于我國加入《1990年國際油污防備、反映和合作公約》的通知”,經國務院批準,中國于1998年3月30日向國際海事組織秘書長交存了關于加入《1990年國際油污防備、反應和合作公約》的文件;根據原交通部1999年425號文件“關于《〈1969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1992的議定書》對我國生效的通知”,該公約的批準機關也是國務院;根據原交通部2009年第1號文件“關于國際海事組織《2001年國際燃油污染損害民事責任公約》生效的公告”,經國務院批準后,中國向國際海事組織遞交了有關加入該公約的加入書。
《締結條約程序法》并未就三類條約的效力進行明確規定。但由于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以及其他組織立法職權上的高低等級。國務院核準的協定或條約性質的文件效力似乎低于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的條約或重要協定,高于無需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批準或核準的協定。也就是說,當全國人大批準的條約與這些公約就同一事項有不同規定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的條約優先適用;當政府部門或其他組織協議締結的條約與這些公約就同一事項有不同規定的,這些條約優先適用。就前一種情況而言,由于船舶油污損害公約性質特殊,針對的也是特定事項,所以實踐中出現沖突的情形可能不多。就后一種情況而言,沖突出現時,前文所列舉的船舶油污損害公約應當優先適用。歸納起來,船舶油污損害公約之間效力等級一致,并且與上下等級效力公約沖突的可能性不大。
但如果依照這種標準,條約與中國國內法之間的效力問題會很復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簡稱《憲法》)、《締結條約程序法》以及《立法法》的精神,前述條約的劃分方式同《立法法》對中國法律法規的分類方式是相同的。那么對比適用,其效力或許依次相當于中國的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于是,有觀點認為當國際條約與國內法規定相沖突的時候,要明確其效力等級,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第一,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的條約和重要協定,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具有同等效力,適用上出現意見分歧時,由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或決定法律與條約和重要協定的優先適用問題。
第二,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的條約和重要協定,其效力高于國務院核準的條約與協定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并高于政府部門對外締結的協定及其所制定的規章。
第三,當國內法律沒有規定,或者規定不夠明確時,可以直接適用條約和重要協定的內容。
第四,國務院核準的條約與協定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具有同等效力,并高于政府部門對外締結的協定及其所制定的規章;
第五,法律明確規定某條約優先適用的,該條約得以優先適用。但是條約的效力始終低于《憲法》。[11]
(二)國內法相互之間的不同規定導致船舶油污損害公約效力悖論現象
依上文所述,似乎立法能夠給船舶油污損害公約與中國的法律法規之間的效力等級確定一個順位標準。但在中國的一些現行法律中,卻作出了與上述標準不同的規定。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簡稱《民法通則》)第142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簡稱《海商法》)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參加的國際條約同本法有不同規定的,適用該國際條約。并且,這些法律的通過機構是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以《民法通則》和《海商法》這兩部法律為例,前者的頒布機構為全國人大,后者的頒布機構則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那么,如果依據前述標準,船舶油污損害公約與這兩部法律間的關系就會出現一種悖論。
就《民法通則》而言,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與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的條約之間應當是什么關系并不明確。如果推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的條約和重要協定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話,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與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的條約之間效力的比較就如同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與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之間的效力比較。事實上,《立法法》并未明確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與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之間是何種關系。
有觀點認為全國人大與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兩個不同的立法機關,全國人大制定的基本法與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非基本法在效力上是不同的。如果依照這種觀點,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的條約效力就應當低于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民法通則》中的規定就應當優先適用,即國際條約的效力是高于國內法律的。這便與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的條約效力低于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這一前提相矛盾。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全國人大的一個常設機構,只是在全國人大閉會時行使全國人大的職權,所以事實上二者是一個機構。同一等級的法律應當適用新法優于舊法、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原則,但就船舶油污損害公約與《民法通則》而言,船舶油污損害公約規范的是特定領域內的事項,與《民法通則》就同一事項進行規范的可能性很小。條約等級比照法律的話,同一事項有不同規定的,后批準的條約效力高于先通過的基本法,后修訂的基本法效力高于先批準的條約。這樣一來,又與《民法通則》中條約優先適用的規定相矛盾。
(三)船舶油污損害公約在中國的實際地位
綜合前文所述,單純地按照制定機關的等級來確立條約在中國的地位,或者單純地認定條約在中國具有優先適用的效力,都無法較為準確地概括現階段船舶油污損害公約在中國的實際地位。這一方面與中國現階段的國情有一定的關系,高速發展的經濟使得法律難以跟上社會發展的步伐。另一方面也與世界范圍內條約在各國國內適用的發展趨勢有關,隨著國際組織的發展,國際條約的數量和種類呈現飛速發展的態勢,各國在實踐過程中也通常都采用復合方式來調整條約和國內法的關系,很少單一地采優先說。因此,雖然目前中國的憲法和法律并沒有對條約在中國的地位給出一個明確的原則,但在解釋和適用條約時,還是應當朝著融合條約和國內法的方向去走。
鑒于目前已有許多法律明確了條約的優先適用效力,從解釋一致的原則上講,在一般情況下還是應當確認條約的優先效力。而就不同機構批準的條約之間以及條約與法律之間的關系,在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還是認為同一等級條約與法律中條約應當優先適用,條約與條約之間平行,有沖突的由該等級機構進行解釋。不同等級之間的條約與法律按等級區分效力。
基于這樣的考量,就船舶油污損害公約與國內相關法律規定間的關系而言,目前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民法通則》規定了條約的優先適用效力。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海商法》也規定了條約的優先適用效力。而同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締結條約程序法》在位階上低于《民法通則》,制定時間上又早于《海商法》,并且《海商法》是特殊法,在海商海事領域應當優于普通法適用。那么,《民法通則》和《海商法》所確立的條約優先原則應當適用于船舶油污損害公約與國內法之間的關系。此種優先受到法律位階等級的限制,即船舶油污損害公約優先于國務院條例及下位法適用,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批準的條約則優于船舶油污損害公約。由于船舶油污損害公約屬于海商海事領域內的專門公約,一般而言,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批準的條約多為涉及國家與國際間的基本法律事項,國內針對船舶油污損害的法律規定除《海商法》的一般規定外均為條例和部門規章,因此與中國國內法相比較,船舶油污損害公約在涉及船舶油污損害的案件中具有優先適用效力。
四、船舶油污損害公約在中國的適用效力邊界
倘若接受船舶油污損害公約在中國應當具有優先適用效力這一結論,那么接下來要解答的問題是:船舶油污損害公約在中國有無適用邊界?如果有,如何界定?
(一)關于無涉外因素船舶油污損害案件能否適用公約的爭論
在中國的實踐中,對于船舶油污損害公約的適用范圍曾經出現過爭論。這種爭論主要集中于沿海運輸船舶油污損害賠償是否應當適用1969 CLC及1992 CLC。1999年“珠海市環境保護局和廣東省海洋與水產廳訴臺州東海海運有限公司和中國船舶燃料供應福建有限公司”一案發生后,對于進行沿海運輸的中國籍船舶應不應當適用1969 CLC及1992 CLC,存在不同的觀點。
該案中,沿海運輸船舶的船東在發生油污損害事故以后,根據1969 CLC申請責任限制。因中國目前并沒有關于油污損害賠償的專門立法,法院認為應當適用中國批準的上述公約。但沿海運輸船舶的案件當事方往往均是中國籍,案發地點也位于中國領海內,在中國法律體系中應當被認定為是無涉外因素的船舶油污案件。無涉外因素的案件是否能夠適用國際條約?
在本案審理過程中,有人主張因《海商法》沒有油污損害賠償的規定,應根據《民法通則》確定賠償數額,且沒有責任限制;有人主張適用《海洋環境保護法》;有人主張油污損害也是一種海事賠償,因此對于被告的責任限制應該適用《海商法》第十一章“海事賠償責任限制”的規定;也有人主張中國是1969 CLC的參加國,該公約于1982年4月29日起對中國生效,在國內立法沒有對油污損害民事責任作專門規定的情況下,應該允許適用1969 CLC的規定。兩原告對申請人責任限制的申請提出異議,認為“閩燃供2”號輪(鋼質油船,總噸位497,凈噸位325)不屬于公約調整的船舶。本次油污事故沒有涉外因素。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條例》(簡稱《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條例》),該案只能適用中國的有關法律。[12]71產生如此爭議的原因可概況為以下幾點。
首先,適用1969 CLC存在阻礙:其一,《民法通則》以及《海商法》關于公約優先適用的規定書寫于“涉外法律關系適用”篇章中;[12]73其二,對于中國加入的1969 CLC,原交通部1980年3月1日下發的《關于中國已接受〈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的通知》中沒有提及對沿海運輸船舶適用,《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條例》第13條也僅僅規定,“航行國際航線,載運2 000噸以上的散裝貨油的船舶,除執行本條例規定外,并適用于我國參加的1969 CLC”。所以,有學者認為,未作特殊規定的載運2 000噸以下散裝貨油并航行于國際航線的船舶,以及從事沿海運輸的油船不適用1969 CLC,仍然適用國內法。然而,1992 CLC對中國生效后,《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條例》第13條的規定是否仍然有效,具體地說,載運2 000噸以下散裝貨油并航行于國際航線的國內船舶是否適用1992 CLC,是不明確的。[13]
其次,如果不適用公約,國內法并沒有相對應的規定,出現2 000噸以下沿海運輸油船油污損害的情況時,會產生無法可依的法律真空。而對于2 000噸以上的沿海運輸油船,適用民法體系的賠償原則會與整個海商法體系中的責任限制原則產生沖突,顯然也不適宜。
最后,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對于規定不明確的這類國內船舶而言,隨著1992 CLC對中國生效,1969 CLC便隨之失效。如果這類船舶適用1992 CLC,其巨大的限額對于中國沿海運輸船舶而言是過高的。因此,學者建議應當明確無涉外因素的國內案件如何適用對中國已生效的國際公約,并且考慮中國國情,無涉外因素的國內關系一時難以或部分難以接軌的,應在批準參加公約前作好準備,在批準參加公約的同時,作出該公約對國內適用程度的規定。[14]
事實上,由于中國在公約的適用問題上缺乏明確規定,造成了法律與條約間適用的不確定。實踐中,對于海事公約,一般采用“打補丁”的方式來解決:交通運輸部發文或國務院發文規定條約的適用范圍和適用方式。即便如此,在一些無需區分國內與涉外適用的情形下,上述發文與條約及國內法適用范圍的具體表述無關。因此,在出現條約與國內法沖突(無論是積極沖突或消極沖突)的情況時,實踐中需要對相關的具有法律屬性的文件進行解釋。
(二)法律狀況變化后爭論的再討論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實踐部門和學界的解釋觀點是基于當時的法律展開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實踐的發展,法律狀況出現了變化。2009年9月2日國務院第79次常務會議通過了《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理條例》,該條例于2010年3月1日起施行。伴隨著《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理條例》的施行,1983年發布的《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條例》已廢止。相較于舊條例而言,新條例確定了三項制度:船舶污染事故賠償責任限制、船舶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強制保險制度以及船舶油污損害賠償基金制度。
《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理條例》第52條規定,“船舶載運的散裝持久性油類物質造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海域污染的,賠償限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有關國際條約的規定執行。”有關國際條約事實上即是1992 CLC。條例的此項規定,從立法上明確了船舶油污損害賠償限額適用1992 CLC的標準,解決了長期以來就限額標準而產生的爭議。
除此以外,《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理條例》第53條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海域內航行的船舶,其所有人應當按照國務院交通運輸主管部門的規定,投保船舶油污損害民事責任保險或者取得相應的財務擔保。但是,1 000總噸以下載運非油類物質的船舶除外。船舶所有人投保船舶油污損害民事責任保險或者取得的財務擔保的額度應當不低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有關國際條約規定的油污賠償限額。”與1992 CLC相比較,新條例將強制保險的投保范圍拓展至所有油輪。
條例還進一步確定了海事油污損害賠償基金制度,落實《海洋環境保護法》的規定。交通運輸部制定的《船舶油污損害賠償基金征收和使用管理辦法》對相關問題進行細化規定,該辦法目前尚未施行,但施行船舶油污損害賠償基金已經進入日程。
從整體上講,《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理條例》對油污損害賠償限額作出了適用條約的規定,并且明確適用1992 CLC。但在船舶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強制保險或者取得其他財務擔保的船舶范圍方面,相比較1992 CLC規定的要求載運2 000噸以上作為貨物的散裝持久性油類的船舶進行強制保險或取得其他財務保證,條例將強制保險的投保船舶范圍大大增加了。根據條例,所有油輪,不論其載運持久性油類或者非持久性油類,均應當進行強制保險或者取得其他財務保證。[15]不過,在投保額度方面,載運持久性油類適用的仍是1992 CLC,載運除此以外的油類物質和1 000噸以上非油類物質的船舶則比照國內法規定適用。
如此說來,《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理條例》及其配套辦法在油污損害賠償的額度、投保金額和基金方面明確了條約在其管轄范圍內適用于在中國管轄海域內的船舶油污損害,而在條約規范之外的領域則適用中國國內法。但1992 CLC的規定并不只限于上述事項,還包括了適用范圍、責任主體、民事賠償責任和免責事項、時效、管轄及判決的承認和執行問題。這些事項有的與國內法規定不盡相同,有的國內法律尚無專門規定。所以《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理條例》鑒于其本身規制范圍的限制,只是解決了一部分問題。對于相關油污損害民事賠償條約與國內法的其他沖突問題,爭議依然存在。《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理條例》的貢獻在于其給出了一個中國適用油污損害民事賠償條約甚至是適用所有船舶油污損害公約的解釋路徑,即條約管轄范圍內國內法與條約有沖突時應當適用條約。
(三)船舶油污損害公約在中國的適用范圍
就近年來所產生的爭論和相關部門的新近立法來看,在船舶油污損害公約的適用邊界問題上,中國目前尚缺乏明文法律規范。如果要給船舶油污損害公約劃定一個標準和范圍的話,上位法確立了一個大的原則:條約優先。在這個原則之下,船舶油污損害公約管轄范圍內的事項則應當適用公約規定。但《民法通則》和《海商法》均將條約優先適用規定于“涉外關系的法律適用”一章,那么船舶油污損害公約的規范范圍就被界定為涉外法律關系。如此一來,最大的問題就是,當無涉外因素的船舶油污損害發生時,應當適用條約還是國內法?
面臨的問題是,“打補丁”解決船舶油污損害公約與國內法的沖突是目前行之有效并且能夠實際解決問題的方式。當“補丁”明確規定依照條約解決相關問題時,條約當然適用于該無涉外因素的船舶油污損害。因此,事實上對于無涉外因素的船舶油污損害,依據仍然是國內法。即使最終適用條約規定,也還是要經過國內法的轉換。但“補丁”的弊端在于其有限性,目前中國針對船舶油污損害的國內法規范尚不完善,公約有規定而國內法無規定時能否參照適用公約的問題還是沒能得到根本解決。這個問題集中體現在規定船舶油污損害賠償機制,即前文所述的第二類公約之中。中國國內立法在船舶油污損害領域有一個偏向,公法性質法規較為完善而私法性質法規規定不足。現階段仍然缺少有關船舶油污損害民事責任的專門規定。《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理條例》及其配套辦法解決了一部分問題,但仍然不完整。司法案例(前述爭議案件)中法院傾向于在無涉外因素的國內法無規定時適用條約。而立法傾向則表明如果國內法有高于條約要求的規定時適用國內法,國內法無規定時根據一般原則條約法適用。
因此,中國目前在無涉外因素船舶油污損害的條約適用方面所存在的困境在于,中國加入公約之時并未作任何保留,而對于非涉外因素的包含在公約管轄范圍之內的船舶油污損害國內法規定又未得以覆蓋。面對無涉外因素船舶油污損害的法律真空,可能的解決辦法有兩種:一是逐步完善的船舶油污損害國內立法,特別是船舶油污損害民事責任立法;二是明確國內法律無規定時適用公約。相較之下,第一種辦法在現階段更為現實可行,對于產業發展而言也更為有利。
五、結語
國際法理論表明,條約在內國法上具有效力。條約在內國法上的效力及其等級是由一國國內法進行規定的。
船舶油污損害公約在中國面臨著適用位階和邊界不明確的問題。《締結條約程序法》《民法通則》和《海商法》對條約的效力作出不同劃分,單一采用任何一個劃分方式都無法解釋條約在中國的實際地位。因此,基于條約優先、特別法優于普通法、上位法優于下位法的規定,船舶油污損害公約與船舶油污法律法規相比,應當優先適用。
但這種討論的前提是涉外情形下的條約適用,在非涉外情形下,立法傾向表明國內法應當予以適用。當國內法未就相同事項進行規定時,不可徑自參照條約適用,而有待國內法的確認。
[1]胡正良,韓立新.海事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HU Zheng-liang,HAN L i-xin.A dm iralty law[M].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9.(in Chinese)
[2]王鐵崖.國際法引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177.
WANG Tie-ya.International law introduction[M].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1998:177.(in Chinese)
[3]李浩培.條約法概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LI Hao-pei.Introduction to the law of treaties[M].Beijing:L aw Press,2003.(in Chinese)
[4]勞特派特.奧本海國際法(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24-32.
LAUTERPACHT.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Vol.I)[M].Beijing:Commercial Press,1981:24-32.(in Chinese)
[5]余先予.國際法律大辭典[M].長沙:湖南出版社,1992:9.
YU Xian-yu.International law dictionary[M].Changsha:Hunan Press,1992:9.(in Chinese)
[6]周鯁生.國際法(下)[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654.
ZHOU Geng-sheng.International law(Vol.II)[M].Beijing:Commercial Press,1976:654.(in Chinese)
[7]周鯁生.國際法(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20.
ZHOU Geng-sheng.International law(Vol.I)[M].Beijing:Commercial Press,1976:20.(in Chinese)
[8]日本國際法學會.國際法辭典[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393.
Jap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 aw.International law dictionary[M].Beijing:World Know ledge Press,1985:393.(in Chinese)
[9]劉永偉.國際條約在中國適用新論[J].法學家,2007(2):143.
LIU Yong-wei.New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pplicable in China[J].Jurist,2007(2):143.(in Chinese)
[10]王麗玉.國際條約在中國國內法中的適用[M]//中國國際法學會.中國國際法年刊(1993).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4:282-285.
WANG Li-yu.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in domestic law of China[M]//Chinese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Chines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1993).Beijing:China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94:282-285.(in Chinese)
[11]宋洋.國際條約在中國內地與港澳適用的比較[J].檢察理論前沿,2008(8):39.
SON G Yang.Comparison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pplicable to Hong Kong,Macao and mainland of China[J].Prosecution Theory Forefront,2008(8):39.(in Chinese)
[12]韓立新.從一起海事案例談國際海事公約的適用[J].當代法學,2001(12).
HAN Li-xin.With a case to talk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nvention[J].Contemporary Law,2001(12).(in Chinese)
[13]司玉琢.沿海運輸船舶油污損害賠償法律適用問題研究[J].大連海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1):2-3.
SI Yu-zhuo.Application of the law on coastal transport vessels for oil pollution damage compensation[J].Journal of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02(1):2-3.(in Chinese)
[14]司玉琢,朱曾杰.有關海事國際公約與國內法關系的立法建議[J].中國海商法年刊,1999(1):5-6.
SI Yu-zhuo,ZHU Zeng-jie.Legislative proposals related maritim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nd domestic law relationship[J].Annual of China Maritime L aw,1999(1):5-6.(in Chinese)
[15]國務院法制辦,交通運輸部.《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理條例》釋義[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10:122.
Legislative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P.R.China,Ministry of Transport of P.R.China.Administrative interpretation on Regulations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Vessel-induced Pollution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M].Beijing:China Communication Press,2010:122.(in 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