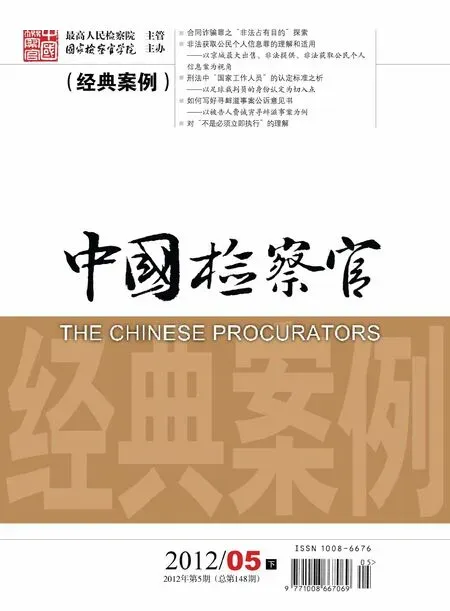交通肇事罪中的“指使、強令他人違章駕車”的理解與把握
文◎王晉岳崔勝實
交通肇事罪中的“指使、強令他人違章駕車”的理解與把握
文◎王晉岳*崔勝實**
根據2000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7條的規定,單位主管人員、機動車輛所有人或者機動車輛承包人指使、強令他人違章駕駛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具有本解釋第2條規定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這是交通肇事罪的一種特殊成罪情況。不同于機動車輛駕駛員直接導致危害結果的典型情況,這里被列入交通肇事罪規制范圍的行為并非直接導致危害結果的肇事行為,而是較為間接意義上“指使、強令他人違章駕駛行為”,是導致肇事結果之駕駛行為的原因行為。從根本上講,對交通肇事罪規制范圍的上述擴張與該罪的規范目的并不矛盾。一般而言,交通肇事罪的設定目的在于,通過對導致了嚴重交通肇事結果的違反交通規則行為的處罰,確證并引領人們遵守交通規則。就此而言,即使是那些未直接導致肇事結果的交規違反行為,也有予以處罰的必要。
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看,本條的規定是對交通肇事罪典型成立范圍的擴張。如果是這樣,那么對這里的“指使、強令他人違章駕駛”進行嚴格解釋就具有了某種必然性。而正是在這個規則的解釋適用過程中,實踐中卻存在著把握不嚴的問題。
一、基本案情
陳某承攬了為建筑工地運輸沙石建材的生意,因此購買了一輛大型翻斗車,雇傭了來城打工的李某利用夜間車少人少的時間運輸沙石建材到工地。李某之前因為駕駛違章而被吊銷了駕駛執照,但是其有豐富的大型翻斗車駕駛經驗。李某向陳某提出,等其駕駛執照重新考取之后再開始運輸業務,但是陳某為利益驅動而沒有同意,反而告訴李某“不行就換人”,同時明確告知李某:如果出了問題自己會托人處理。李某只得同意。某日夜,李某無證駕車運營,違章闖紅燈發生交通事故,導致兩名路人死亡。
二、分歧意見
對于本案中的李某,認定為交通肇事罪予以定罪處罰顯然不存在任何制度上的障礙,也不會存在什么理論爭議。但是對于陳某是否構成交通肇事罪卻存在顯著的爭議。
第一種觀點認為陳某構成交通肇事罪。因為:第一,陳某出于逐利的動機,對李某軟硬兼施,是造成李某違章駕駛行為的客觀原因,即使不能滿足“強令”的要求,也符合了“指使”的構成行為要求;第二,李某無證駕車從事建筑材料運輸業務,顯然符合“違章駕駛”的行為構成要求。
第二種觀點認為陳某不構成犯罪。因為其雖然對于李某無證駕駛存在客觀上的強令或者指使,但是李某的無證駕駛這一違反交通規則的事實與交通事故的發生沒有直接的關系,因此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釋中所要規制的“指使、強令違章駕駛”的要求。
三、評析意見
我們贊同第二種意見,理由逐次闡述如下:
在當前我國司法實踐中,過失犯成立判斷主要取決于三個要素:一是要求具有危害社會的結果;二是要求犯罪嫌疑人的行為與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三是要求行為人在主觀上對于該危害結果具有過失的罪過心態。其中,危害結果要素是追究過失責任的前提,即如果沒有導致危害社會的結果則沒有追究過失責任的必要。其次,在將過失犯設定為結果犯的前提下,犯罪嫌疑人的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是追究過失犯罪的必要要素。盡管目前我國理論上對于因果關系的判斷標準爭議較大,但實踐中采取“條件說”的觀點是可以肯定的。按照這一標準,如果“沒有行為則沒有結果”這樣一種判斷公式能夠得出肯定的結論,那么就可以肯定有因果關系。最后,在上述三個要素當中,行為人對于其行為結果是否具有犯罪過失心態,在過失犯罪司法實踐中被認為是最為關鍵的要素,也是最為困難的判斷要點。
按照過失犯的上述實踐認定模型,上例中的陳某要求李某無證駕車的行為顯然屬于要求他人違章駕駛,與李某駕車造成交通事故之間具有條件說意義上的因果關系;同時認為陳某對無駕照的李某繼續承擔營運駕駛可能造成嚴重危害后果的可能性有預見,但輕信李某的駕駛技術不至于造成這樣的結果,因而構成過于自信的過失存在邏輯上的合理性;據此認定陳某構成交通肇事罪相應地就沒有了問題。但這一結論顯然是不合理的,因為這就好比說讓一個不給孩子戴帽子的保姆為隨母親出門的孩子走路摔破了膝蓋承擔責任一樣荒謬。
我們認為,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不合理結論,是因為上述司法實踐模型重主觀輕客觀,片面強調過失心態的重要性,而將過失犯的客觀方面要件限縮為結果。眾所周知,對我國刑法中“應當認識而沒有認識”和“過于自信沒有避免結果”的解釋可能性顯然過于寬泛。具體而言,前者的寬泛性來源于“應當”;而后者的寬泛性則來源于如何理解“過于自信”。這種寬泛的解釋可能,根本無力對抗片面地從危害結果引出的處罰要求。于是,一個不容質疑的問題擺在了我們面前,此即我國傳統過失理論具有嚴重的結果歸責傾向,而這一傾向影響下的過失犯刑事責任范圍顯然難以保證其合理性。實際上,在過失犯司法認定過程中,客觀行為要件也應當被重視并且予以嚴格的把握,這樣才不至于導致處罰范圍的不當擴大。理論上正逐漸被重視的“過失實行行為”概念,實際上就是這樣一種需要的產物。
雖然有人不贊成過失犯具有實行行為,但是在我們看來,實行行為的概念只是在犯罪成立意義上對特定行為本身在質或者量上提出類型化的限定要求,這類要求對于任何犯罪而言均可提出。根據“過失實行行為”這一觀念,只要行為未達到實行行為類型要求,就并無該當于構成要件且違法的行為。結合過失犯罪的義務犯本質,我們認為,作為過失犯客觀行為要件的“過失實行行為”應當是違反法定義務,因而具有危害社會的類型化風險的行為。具體到交通肇事罪的場合,過失犯實行行為就應當不僅僅是違反了交通規則,還要求這種交通規則的違反與交通事故的發生有直接的類型化因果聯系,或者說違反交通規則的行為中應當包含著發生交通事故的蓋然性風險。比如說,明知剎車失靈仍然駕車上路,明知高速闖紅燈過路口有可能危及他人而仍然無所顧忌實施這樣的行為等,毫無疑問具有發生交通事故的蓋然性風險,將其認定為交通事故罪的實行行為顯然沒有什么問題。然而,有的違章行為與事故的發生無因果關系,如無牌照、晴天無刮雨器等,則一般不能被包含于交通肇事罪的實行行為當中,除非在具體情況下這種交通規則違反與事故的發生具有了特定的聯系。
回到之前提到的案例。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指使、強令他人違章駕駛”與作為交通肇事罪實行行為的“典型違章駕駛”具有一定的區別,相對于后者,其對于交通安全的危害相對間接。所以,2000年11月21日司法解釋第7條的規定看起來就是對交通肇事罪處罰范圍的進一步擴張。因此,應該受到上述“過失實行行為”原理的更為嚴格的限制。秉承這樣的觀念,本案中的陳某顯然不能被論以交通肇事罪。雖然在邏輯意義上陳某對于強令李某無證駕駛實施運輸業務導致危害社會的結果可以被理解成具有主觀上的過失,其強令行為與肇事結果之間也具有了事實意義上的條件因果關系,但是其“強令、指使無證駕駛”的行為根本不具有導致交通事故發生的類型化風險,真正造成兩人死亡結果的原因在于李某駕車闖紅燈的行為。所以本案應當由李某單獨承擔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責任。
*吉林大學法學院刑法學博士研究生[130012]
**吉林省通化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134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