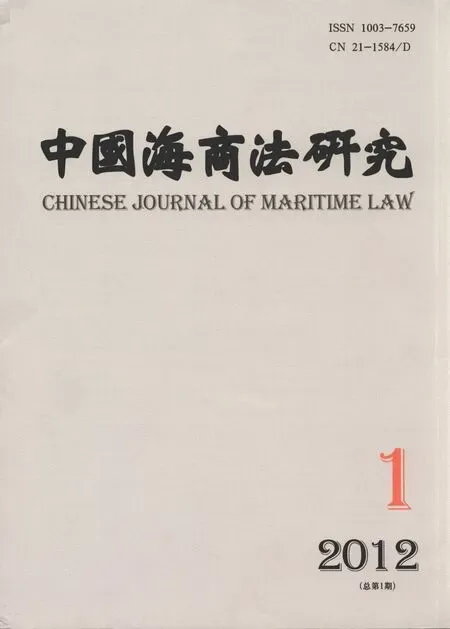歐洲水下滑翔機發展應用現狀及其法律規制——對中國借鑒意義之思考*
常 虹,薛桂芳,A lexander Proelss,于華明
(1.基爾大學國際法研究所,基爾 24106;2.中國海洋大學法政學院,山東青島 266100;3.特里爾大學環境技術法學院,特里爾 54286;4.中國海洋大學海洋環境學院,山東青島 266100)
海洋調查是用各種儀器、儀表對海洋中能表征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質學、地貌學、氣象學及其他相關學科的特征要素進行觀測和研究的科學。通過海洋調查的科學活動,可以獲取海洋環境要素資料,揭示并闡明其時間、空間分布和變化規律,為海洋科學研究、海洋資源開發、海洋工程建設、航海安全保證、海洋環境保護、海洋災害預防提供基礎資料和科學依據。真正的世界海洋調查始于由英式軍艦改裝的“挑戰者”號所進行的世界歷史上第一次有目的的海洋科學考察,并由此掀起了世界海洋科學調查狂瀾。[1]繼此之后,海洋界經歷了從單船走航調查時期,到多船聯合調查時期,再到如今的立體化海洋調查時代的演變。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海洋科學調查方法不斷面臨新的變革,傳統的海洋觀測平臺,包括海洋調查船和浮標等,能夠進行跨學科調查,但對于時間和空間分布的要求方面效果卻不盡如人意,而且成本高昂。水下滑翔機(underwater glider)作為新型海洋立體監測系統的水下監測平臺,將浮標技術與水下機器人技術相結合,滿足了海洋調查對于時間和空間上的要求,是目前國際上的研究熱點。歐洲作為海洋科學研究的主力軍,對水下滑翔機的應用及發展給予高度關注,科學界自發組織了多次專項會議促進各國之間合作,并設立數據共享平臺。而且值得關注的是,歐洲正在從法律層面對此作出制度安排,涉及港口管理、回收和管轄等問題,以保證有秩序、合理合法地進行海洋科學調查,更好地促進海洋科學研究。
一、歐洲現狀
作為智能多參數海洋觀測平臺,水下滑翔機完美地彌補了浮標和船舶觀測的不足,其作業范圍可以達到數百至數千公里,連續作業時間可達數月,不論是在時間上還是在空間上都更勝一籌。當多個水下滑翔機同時、連續作業時,就相當于在海上編織起立體的海洋觀測網。歐洲許多實力雄厚的海洋研究所都研制出自己的水下滑翔機,并成功投入使用,例如德國基爾大學萊布尼茨海洋研究所(IFMGEOMAR)自2004年以來已多次投放深海水下滑翔機并成功完成任務①參見http://www.ifm-geomar.de/index.php?id=1241&L=1。。但是這種大規模投放及應用需要嫻熟的技術和各研究單位或國家之間良好的合作。歐洲在2006年發起了“歐洲滑翔機觀測網絡”(European gliding observatories network)行動,旨在從技術、科學及組織層面協調正在進行中,以及計劃中的水下滑翔機觀測項目,從而達到成本效益最大化,提高歐洲海洋持續觀測能力,更好地服務于物理海洋學和應用海洋學。2005年10月,科學界,主要是眾多來自法國、德國、意大利、挪威、西班牙和英國的對水下滑翔機感興趣的物理海洋學家,自發倡議EGO行動。EGO最初意為“European Gliding Observatories”,但之后隨著許多來自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的物理海洋學家的加盟,EGO日益發展為“Everyone’s Gliding Observatories”②參見http://www.ego-network.org/dokuw iki/doku.php?id=start。。該行動通過網站促進各國或科研機構的滑翔機實驗及合作,不僅提供有關滑翔機項目及數據管理的實時信息,還可提供技術輔導及咨詢、相關鏈接和參考文獻。更有意義的是,EGO每年都會組織研討會商討有關科學或技術問題。除此之外,在水下滑翔機應用及發展方面,歐洲最新的動作就是GROOM(Gliders for Research,Ocean Observation and Management),致力于歐洲范圍內水下滑翔機應用的基礎設施建設研究,其中包括設計歐洲及海外“滑翔機港口”的網狀分布圖,從科學、技術和法律層面分析歐洲水下滑翔機持續觀測和研究能力,評估滑翔機持續操作所需的組織及成本,從而促進協調并融入歐盟現有的海洋觀測項目。該項目由歐盟委員會資助,開始于2011年10月1日,項目期限為3年。
二、法律規制
一直以來,影響深遠的技術進步與相應的制度變革總是相伴而行。有關水下滑翔機的制度及法律規制已經引起國際社會及歐盟的關注,相關法律規制在學術界也已開始探索。水下滑翔機的應用可能引起的法律問題首要的是管轄權問題,其次是如何避免與其他合理利用海洋的活動相沖突,再次是如何對其加以保護和回收,及其數據管理。
被譽為“海洋憲章”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簡稱《公約》)在國際社會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公約》涉及海洋的許多方面,建立了海洋各方面活動的法律框架,從而形成嶄新的現代海洋法律制度。作為新興的高科技海洋儀器,水下滑翔機主要服務于海洋科學研究及應用海洋學。《公約》的第十三部分針對海洋科學研究進行了詳盡的規定,但不可避免的是由于時代和科技的局限性,《公約》對海洋科學研究的理解還停留在較淺顯的層面:在固定的海域和固定的時間段內,以已計劃并可預知的方式來進行數據收集,這明顯與水下滑翔機的作業方式不是很符合。另外,《公約》對于什么是海洋科學研究,即海洋科學研究的定義也未作規定,持模糊立場,使得在許多情況下能否適用《公約》第十三部分變得模棱兩可。學術界對于海洋科學研究的普遍理解首先是基于科學研究的定義,科學研究是指為了增加人類文化和社會知識,對問題或現象進行調查、驗證、推論、分析和綜合來獲得客觀事實的過程。[2]海洋科學研究要求該研究與海洋環境有關,海洋環境包括水體、海床、洋底和底土,及其鄰接上空,因此海洋科學研究可以理解為為增加人類文化和社會知識,對水體、海床、底土及其鄰接上空的有關現象或問題進行調查、驗證、推論、分析和綜合來獲得客觀事實的過程。[3]若水下滑翔機明確被用于海洋科學研究,則毫無疑問《公約》第十三部分對其適用。
根據《公約》第十三部分的規定,若海洋科學研究項目在沿海國領海內進行,由于沿海國在領海范圍內享有主權,則該項目完全置于沿海國主權管轄范圍內。這就意味著該項目能否進行,如何進行應由沿海國決定,而且除某些特定情況外,沿海國可以任意拒絕研究國的請求,因為這是沿海國享有的主權。[4]即使是在對沿海國領海主權構成唯一限制的無害通過制度下,進行海洋科學研究也會使該通過變得“非無害”。
對于在專屬經濟區內和大陸架上進行海洋科學研究,《公約》首次將二者合一做了統一規定,確立了“同意機制”。根據第246條規定,任何國家或國際組織欲在沿海國專屬經濟區或大陸架內進行海洋科學研究,必須要提前獲得沿海國同意,但與領海內不同的是,此處沿海國并不享有無限制的自由處置權,也就是說不能隨意拒絕研究國或國際組織的請求。原因在于第246條第3款規定,在正常情況下,沿海國應對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按照本公約專為和平目的和為了增進關于海洋環境的科學知識以謀全人類利益,而在其專屬經濟區內或大陸架上進行的海洋科學研究計劃,給予同意。但第246條第5款進一步規定在四種情況下沿海國可斟酌決定拒絕該科研計劃,這四種情況分別是:與生物或非生物自然資源的勘探和開發有直接關系;涉及大陸架的鉆探、炸藥的使用或將有害物質引入海洋環境;涉及第60條和第80條所指的人工島嶼、設施和結構的建造、操作或使用;含有依據第248條提出的關于該計劃的性質和目標的不正確情報,或如進行研究的國家或主管國際組織由于先前進行研究計劃而對沿海國負有尚未履行的義務。最后,《公約》賦予各國及國際組織在公海和國家管轄范圍以外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進行海洋科學研究的自由。
綜上所述,《公約》對于海洋科學研究的規制主要取決于該研究項目位于何種海域之內,對于水下滑翔機這一新興事物來說,由于其可以靈活游弋于水中,盡管行進路線可以人為操控,但不排除可能受一些非人為因素,或人為因素影響而忽視海域界限,從而導致《公約》的相關規定有名無實。
(一)《公約》并不能滿足對水下滑翔機法律規制的需求
首先,有一點需要闡明的是,《公約》對于開展海洋科學研究的規定主要是針對船舶這一研究平臺,這從《公約》第248條可以看出,同時《公約》第258條至第262條也對海洋科學研究中的設施或裝備進行了法律規定,并指出部署和使用這些科研設施或裝備應遵守《公約》中在任何一區域內進行海洋科學研究所規定的同樣條件。但根據《公約》的規定,特別是第94條,國家對于船舶所享有的權利和義務與對海洋科研設施或裝備享有的權利義務是截然不同的,因此有必要對二者加以區分。《公約》及國際法都沒有對船舶做出精確定義,《1972年國際海上避碰規制公約》《倫敦傾倒公約》《聯合國船舶登記條件公約》及一些國際勞工組織的公約都從不同角度概括了船舶應有的特點,綜合來看應包括:可航行,具有一定規模,交通運輸的工具和動力方式。[5]水下滑翔機可航行,但規模很小,也不屬于交通工具,由于單純使用浮力驅動方式,其航速慢,控制和定位精準度低,在較大風浪的海況下,可能會出現隨波逐流的情況,因此不符合有關船舶的技術特點,很難稱之為船舶,在國際海洋法律制度中只能作為海洋科學研究設施或裝備加以研究。
其次,對于科研設施或裝備的管轄權問題,《公約》也未做明確規定,但根據第258條的規定,對其管轄權應該與對海洋科學研究項目的規定相符合,也就是說取決于該設施或裝備位于何種海域之內。在領海之內,應完全置于沿海國主權管轄范圍之內;在公海或國家管轄海域以外,由注冊國,若無注冊國則由所有國實施管轄;在專屬經濟區內,根據公約第60條、第246條和第258條規定,仍由沿海國對其享有管轄權①有關《公約》英文版本對應條款,學術界對于installation和equipment有相關探討,并提出《公約》第60條只針對installation,而與equipment無關。由于中文譯本很難對這兩個詞有精確區分,在此對這一問題不做探討。。《公約》對于在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上進行海洋科學研究項目所規定的“同意機制”在文字上很容易理解并掌握,但對于水下滑翔機這一高科技科研儀器來說,在實際操作中很難予以實施,原因在于,盡管其運行軌跡已預先設定,但一旦遇到強烈的海流,仍有可能“隨波逐流”,很大程度上增加其不可控性,因此很有可能會漂流至其他國家專屬經濟區內,甚至領海之內。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提前獲得沿海國的同意,因為水下滑翔機已失去控制而超出預定滑翔范圍。如果根據《公約》的規定,這一問題的解決方式應該是在放置水下滑翔機之前取得任一可能涉及的沿海國的同意,也就是說任何國家,只要是在研究海域周邊,甚至是與研究海域相鄰的其他海域的周邊國家,只要是水下滑翔機有可能進入或飄流至其專屬經濟區,就應當得到其許可。這一要求無疑會給研究國或國際組織帶來沉重負擔,并嚴重影響了《公約》所推崇的公海自由及公海海洋科學研究自由。
再次,《公約》的許多其他規定對于水下滑翔機也無法適用,例如《公約》第248條規定,研究國或國際組織有意在一個沿海國的專屬經濟區內或大陸架上進行海洋科學研究,應在海洋科學研究計劃預定開始日期至少6個月前,向沿海國提供關于該科研項目的詳細說明。但是對于水下滑翔機來說,無法提前6個月預知什么時候將會進入沿海國專屬經濟區,因為其運行軌跡和速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即時的天氣狀況和海流狀況。《公約》第253條規定沿海國有權要求暫停甚至停止在其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上進行的海洋科研活動,對于水下滑翔機來說,由于其在海水中的不可控性,很難滿足馬上暫停或停止數據收集活動的要求。
由此可見,《公約》中許多有關海洋科學研究的規定已經不能滿足對水下滑翔機法律規制的需求,除了管轄權等上述問題,如何收集和回收水下滑翔機,如何防止其運行受到其他海洋活動的干擾以及對其的安全保護措施等問題都需要合理解決,在這一背景下,歐洲開始探討可能有效的法律規制。
(二)對于水下滑翔機法律規制的探討
完善對水下滑翔機的法律規制最直接的方法便是修改《公約》,但鑒于《公約》第312條至第314條規定的復雜的修改機制,其所具有的成員國互相妥協和“package deal”的特性,修改《公約》并不能成為上策。[6]
海洋數據收集系統(Ocean Data A cquisition System s,ODA S)是由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yCommission,I OC)和國際海事組織前身——政府間海事咨詢組織(Inter-Governmental MaritimeConsultative O rganization, IMCO)在20世紀60年代初提出的②參見http://odp.oceandataportal.net/odp/resource?id=CN—NMD IS—01。。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在海洋數據收集系統的實施過程中也遇到許多法律問題,[7]情況與如今水下滑翔機的應用很相似。對于該系統的法律規制問題,國際社會各方面,特別是I OC與國際海事組織( IMO),一直在斷斷續續地起草與修改相應法律文件,因在實際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問題與日俱增,最終仍未有一部統一的公約,只有1993年曾出臺過一部公約草案。[8]該草案中有一些規定可以為水下滑翔機法律規制所借鑒,例如儀器的回收及返還問題,安全措施問題,警示信號與識別標志,污染及碰撞責任,這與《公約》的相關規定一致,但對于水下滑翔機最關鍵的問題,即由于“同意機制”和其不可控性所引發的法律問題,ODA S公約草案沒有涉及,因此對于這一問題的解決還沒有經驗可以借鑒,現在還處于不斷探索過程中。
I OC及其下屬的法律專家咨詢機構(ABELOS)在促進海洋科學研究以及解決水下滑翔機相關法律問題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2001年,ABELOS發起了有關浮標等海洋觀測儀器的法律問題的探討,并于2007年發布了相關實施原則草案(T he D raf t P ractical Guidelines)③參見D raf t P ractical Guidelines of IOC,within the Context ofUNCLOS,for the Collection ofOceanographicData by SpecificMeans,Seventh Meeting of the Advisory Body of Experts on the Law of the Sea(I OC/ABE-LOS V II),19-23March 2007,L ibreville,Gabon。。該草案只針對剖面浮標和表面浮標,對于水下滑翔機并不完全適用,但是對管轄權、通知及告知義務等問題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除此之外,另一有效解決問題的方法便是根據《公約》第247條的規定①《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247條規定,沿海國作為一個國際組織的成員或同該組織訂有雙邊協定,而在該沿海國專屬經濟區內或大陸架上該組織有意直接或在其主持下進行一項海洋科學研究計劃,如果該沿海國在該組織決定進行計劃時已核準詳細計劃,或愿意參加該計劃,并在該組織將計劃通知該沿海國后4個月內沒有表示任何反對意見,則應視為已準許依照同意的說明書進行該計劃。。I OC作為海洋界久負盛名的國際組織,有權通過適用第247條至其主持或參與的海洋科研項目中,如全球海洋觀測計劃(GOOS)和ARGO計劃,簡化“同意機制”從而促進全球海洋科學研究的發展。雖然現在I OC對于ARGO計劃還未適用《公約》第247條,但對于區域性或全球性的水下滑翔機應用同樣具有參考意義。
由此可見,《公約》不能滿足對水下滑翔機法律規制的要求,而新的法律秩序仍在不斷探索過程中,在此期間需要國際社會,相關國際組織及各國海洋科學家共同努力,早日將水下滑翔機的廣泛應用引發的法律問題納入到國際法律規制之中。
三、對中國的啟示
中國關于水下滑翔機的研究起步較晚,在剛剛結束的第二次西太平洋海洋科學共享航次考察中,中國科學家成功實施了中國自主研制的水下滑翔機的海試實驗,這標志著中國水下滑翔機系統技術基本成熟②參見http://www.sciencehuman.com/party/achievements/achievements2011/achievements201108j.htm。。作為當今最先進的海洋環境觀測設備之一,水下滑翔機的早日推廣應用有助于推動中國海洋調查事業和海洋科學研究事業的發展。但是在水下滑翔機經過推廣并廣泛應用于海洋調查事業之后,必將會面臨如何對其加以規制的問題。如今歐洲正在緊鑼密鼓地籌備解決這一問題,由歐盟委員會資助的最新項目:水下滑翔機的海洋研究、觀測及其管理(gliders for research,ocean observation and management)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中國也應緊跟國際步伐,展開一些研究,為中國與其他海洋科研大國合作創造條件,加快中國海洋科研事業的發展。
在中國現行的涉海法律法規針對的客體都是船舶,或其他有運載功能的海上交通工具,對于水下滑翔機這一新生事物并不適用,因此若想要使用法律或行政手段規制水下滑翔機的應用,方法有兩個:要么修改現行的法律法規,要么制定新的法律法規。現行的涉海法律法規可能會涉及到水下滑翔機應用的主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海洋科學研究管理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上交通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港口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域使用管理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等。面對種類如此紛繁的法律法規,若要使其在水下滑翔機的應用方面達到相互協調恐怕很難,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針對水下滑翔機的應用制定新的法律或行政法規。從縱向上來看,對水下滑翔機應用的管理應涉及到其放置、回收、港口管理、對其他合理利用海洋的活動造成的干擾以及涉外水下滑翔機進入中國海域或反之的相關管理等等。這就要求立法者首先要對水下滑翔機的應用進行細致了解,全面考慮其應用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問題。從橫向來看,還可以根據水下滑翔機的應用目的,如海洋科學研究,海洋資源的勘探開發等進行分門別類的規定。就海洋科學研究來說,如今水下滑翔機的研究和應用是許多國家的研究熱點,對中國來說很可能會遇到涉外合作的問題,因此這就需要對水下滑翔機在涉外海洋科學研究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問題進行全面分析,并做出相關法律規定。
先進的技術變革一定會帶來相應的制度變革,如今對于水下滑翔機應用的法律規制是國際社會及科學界的研究熱點,對于中國來說沒有太多的經驗可以借鑒。但中國若能夠提早為水下滑翔機廣泛應用做出制度安排,特別是要注意與國際研究步伐接軌,則有助于加強中國與其他海洋科研大國之間的聯系,創造合作機會,也有利于中國緊跟國際海洋科技發展的步伐,提高中國的大國影響力。
四、結語
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海洋科學調查方法不斷面臨新的變革,而調查方法的變革又會帶來相應的制度變革。水下滑翔機的問世超出了在締結《公約》之時對海洋科學研究的理解,使得《公約》對于規制水下滑翔機的應用顯得有些力不從心。有關水下滑翔機的研究如今是歐洲乃至世界的熱點,相關法律規制的研究也處在起步過程中。隨著其在海洋科研方面的廣泛應用,研究并出臺彌補《公約》不足的相關法律規制勢在必行。中國應抓住這一機遇,積極參與國際合作,使中國更好地融入國際海洋科研事業,增加中國的大國影響力,同時也促使中國盡早出臺有關水下滑翔機應用的法律法規。
[1]侍茂崇,高郭平,鮑獻文.海洋調查方法導論[M].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08:1.
SH IMao-chong,GAO Guo-ping,BAO Xian-wen.Introduction to marine survey methods[M].Q ingdao: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2008:1.(in Chinese)
[2]WEGEL E IN F H T.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the operation and status of research vessels and other platform s in international law[M].L eiden:Martinus N ijhoff Publishers,2005:11.
[3]SOON S A.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law of the sea[M].N etherland:The Hague A sser Institute,1982:124.
[4]CA FL ISCH L,P ICCARD J.The legal reg ime of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thir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J].Zeitschrift fuer auslaendisches oeffentliches Recht und Voelkerrecht,1978(38):889-901.
[5]BORK K,et al.The legal regulation of floats and gliders——in quest of a new reg ime[J].Ocean Development&InternationalLaw,2008(3):298-328.
[6]FREESTON E D,EL FER I N A O.Flexibility and innovation in the law of the sea-w ill the LOS convention amendment procedures ever be used[C]//Elferink.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Law of the Sea:The Role of the LOS Convention.L eiden:MartinusN ijhoff Publishers,2005:169-221.
[7]PA PADA KIS N.Some legal problem s associated with the ocean data acquisition system,aids and devices(ODA S)[J].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75(5):825-837.
[8]D raft convention on the legal status of ocean data acquisition system,aids and devices(ODA S)[EB/OL].[2012-01-25].http://unesdoc.unesco.org/ images/0009/000979/097992eb.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