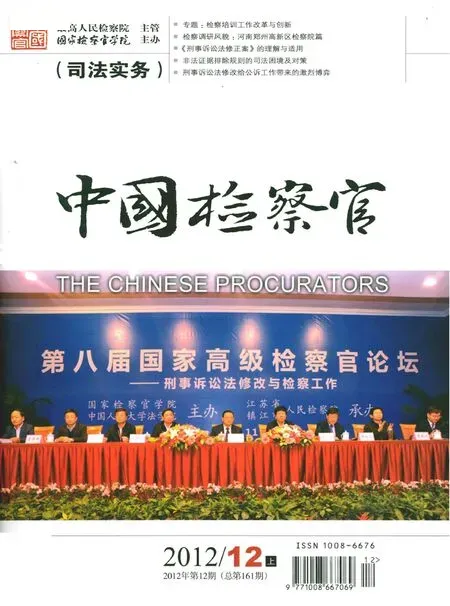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司法困境及對策
文◎郭天明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司法困境及對策
文◎郭天明*
*廣東省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檢察院,中國人民大學在讀博士生[100872]
20 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合頒布了《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及《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非法證據排除規定》)并于2010年7月1日施行。學術界對此進行了充分的肯定,認為是改革完善刑事證據制度的重大成就,是保障死刑案件質量的一個重大舉措,并對該規定能減少刑訊逼供、保障被追訴人的人權,促進司法公正抱著很高的期望。然而,兩個規定實施一年半以來,在司法實踐中取得的效果卻不甚理想,非法證據排除難的狀況并沒有明顯改觀,各地亦鮮有非法證據排除的案例。以至于有的學者指出,因為相關的配套制度跟不上,在操作和認定的時候比較困難,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宣示意義大于其實踐意義。
一、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司法實踐困境及成因分析
在兩個規定頒行實施后,縱覽各地的司法實踐,主要做法有兩種:一是檢察機關建立以審查起訴環節為中心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以筆者所在的羅湖檢察院為例。該院在兩個規定的指導下,制定了自己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建立起以審查起訴為中心環節的非法證據排除體系。在啟動方式上,以辦案檢察官審查和嫌疑人、辯護人申請兩種方式來啟動程序,并設定書證、物證、證人證言等九類證據的分類審查規則和證據標準。經過審查后,認為需要對非法證據進行排除的,一般案件經過承辦案件的檢察官審查后,并報主管檢察長審批即可。對于社會影響重大、當事人反映強烈的案件,如果證據的排除對于案件的定罪量刑影響較大的,為保證程序的公開透明,以聽證會的方式進行,聽取嫌疑人、被害人及偵查機關等各方面的意見。
另外一種比較普遍的做法是建立以庭審為中心的非法證據排除體系。即由法庭經過審理,來決定是否對非法證據進行排除,如江蘇鹽城中級人民法院的做法。其與中國政法大學合作在鹽城市市區兩級法院試點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雙方制定了非法證據排除試行規則,為試點法院制定了一整套具體可操作性的程序,包括啟動程序、聽證程序、決定程序、補救程序,并為各個程序設置了相應的規則。從各地的實踐來看,無論是以審查起訴環節為中心的排除規則還是以法庭審理為中心的排除機制,一般有啟動、聽證和決定程序。從效果來看,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存在很多問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司法實踐中遇到了啟動難、舉證難等問題和困難,非法證據規則的整體適用情況不容樂觀。
一是啟動難。在司法實踐中,啟動排除程序的案件數量非常少。以筆者所在的單位為例,2011年全年共辦理刑事案件2200余宗,而納入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不到5宗,只占全部案件的千分之二。鹽城法院的試點情況亦是如此,法官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案件以及真正最終排除證據的案例仍然非法罕見。
根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規定第3條、第4條和第5條的規定,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方式有兩種,一是由檢察機關依職權啟動,二是經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申請啟動。
對于第一種啟動方式,《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第3條有明確規定,這一規定既賦予了檢察機關排除非法證據的權力,也明確了檢察機關主動排除非法證據的職責。然而司法實踐中,檢察官卻不愿意啟動程序。一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定》可操作性不強。雖然第3條規定了檢察院在審查批準逮捕、審查起訴中,對于非法言詞證據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但是如何排除卻沒有明確規定,而且何為刑訊逼供也沒有給予明確的界定,造成司法實踐中操作的困難。二是控方地位也決定其不愿意輕易啟動。檢察官承擔的職責就是指控犯罪,這和偵查機關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而且案件的成功起訴及判決還要依靠偵查機關緊密配合。若關鍵的證據被排除,則會使指控十分被動,案件可能無法定罪,檢察官自己要承擔指控不利的壓力和責任。三是考核指標的限制。上級檢察機關對于下級檢察機關的考核以及檢察機關對于檢察官的績效考核中,不起訴率、撤訴率和無罪判決率都是很重要的指標。尤其對于撤訴和無罪判決的案件,一般都認為是案件辦理質量不高,在年終考核時,要給予扣分,這往往會影響辦案人員的聲譽、評獎及升遷。在當下日趨行政化的司法機關中,辦案人員的確無法不考慮。再者,排除非法證據,需要啟動、調查核實等程序,花費巨大的精力,在案件高發的今天,司法機關辦案壓力本已很重,再加上非法證據排除,無疑更是雪上加霜。同時排除非法證據還可能費力不討好,一方面影響了和偵查人員的關系,另外一方面可能使得案件的另外一方當事人不滿,尤其有被害人的案件,被害人往往會采取鬧訴、上訪等手段。在當前穩定壓倒一切的大環境下,顯然不是辦案人一人能承受之重。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刑事訴訟中被追訴的對象,面對公權力,其處于弱勢地位,權利最容易受到侵害,且案件的定罪量刑和其本人的權益密切相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理應享有啟動權。因此《非法證據排除》第4條規定明確賦予了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的程序啟動權,要求被告人提供涉嫌非法取證的人員、時間、地點、方式和內容等相關線索或證據。然而,由于犯罪疑人及被告人一般都是處在羈押狀態,所以只能陳述自己受到了毆打,但是很難向法庭提供具體的人員、時間和地點。再者我國尚未確立訊問時律師在場制度,律師也無法提供具體的線索。在庭審中,如果被告人提出刑訊逼供的異議時,法官往往要求被告人提出具體的人員、時間、地點等證據,一般被告人都無法提供,法官本就不愿意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一般對被告人的申請予以駁回,最多要求辦案機關出具一份是否刑訊逼供的說明予以了結。
二是調查舉證難。《非法證據排除規定》第7條規定,公訴人對于偵查機關的證據是否合法享有調查權,其可以調閱案卷和錄像資料,也可以要求偵查人員出庭。《非法排除規定》第6條則規定被告人要提供偵查人員非法取證的相關線索。
然而,在司法實踐中,不但被告人舉證困難,就連檢察機關調查也是困難重重。(1)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公檢法三家分工配合、相互監督、相互制約。然而由于事實上的偵查中心主義,檢察機關無法及時介入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其往往僅通過事后審查、書面閱卷的方式來評判刑事偵查活動是否合法。即使在審查起訴過程中獲悉了偵查機關非法取證的線索,其啟動法律監督調查往往因事過境遷、場景變換、證據滅失、關鍵證據毀壞、犯罪嫌疑人無法有效提供非法取證的線索或證據而難以全面客觀收集、固定偵查機關違法取證的證據材料。(2)由于中國尚未建立偵查訊問律師在場制度,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在封閉的場所內,羈押的狀態下被取證,其無法對抗偵查機關。而只有在審查起訴和庭審中,其才能提出有效對非法取證提出控告,正是由于非法證據的形成和提出之間存在 “時間差”,偵查機關有充足的時間將非法證據變成合法證據,讓非法證據在偵查筆錄中“消失”,這也為非法證據的調查取證帶來難度。(3)對于非法取證所留下的主要證據即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傷情,偵查機關往往不允許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及時檢查或者鑒定,往往以抓捕時不配合所留下等理由予以推脫。(4)訊問人員出庭對質證流于形式。現實中由于抓捕人員與偵訊人員的分離,嫌疑人往往也不知道是誰對其刑訊逼供,刑訊逼供者不出庭,讓沒有刑訊逼供的偵查人員出庭作證。作證的結果顯然是不存在刑訊逼供,而被告人又無法提出有力的證據,造成雙方各執一詞,無法決斷。更有甚者,部分偵查人員以工作忙、出差等理由拒不出庭,法律上又沒有規定偵查人員不出庭要承擔法律責任,所以法庭也無可奈何,最后只能以查無實證,不能認定非法取證來處理。而在很多西方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的港澳臺地區都規定警察必須出庭,否則構成蔑視法庭罪。
三是排除難。司法實踐中,能納入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案件相當少,而運用排除規則排除主要證據的案件的則少之又少,事實上來說,即使非法取證嫌疑很大的案件,非法證據的排除也很困難。一是因為我國長期重打擊、輕保護的執法理念一直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司法工作人員。在部分法官的內心中,對于刑訊逼供具有一定的包容度,對于偵查機關持有同情心。二是如果認定刑訊逼供而導致證據的排除,不但會使法官本人背負了巨大的壓力,而且容易招致偵查機關及檢察機關的抵觸情緒,造成檢警與法院的緊張關系,從而招致領導的責怪。而且,我國在庭審程序中直接進行非法證據排除,均為同一法官進行審理,而不是像國外那樣建立獨立的排除程序和“預備法官制度”,所以庭審法官容易受到那些具有實際證明價值的非法證據的影響。在我國,暫且不論通過非法口供所獲得實物證據這種類型的“毒樹之果”,非法口供所承載的案件事實內容能否排除就是一個問題,犯罪嫌疑人被打以后可能會變得很“老實”,在本次交代和以后的交代當中都會保持供述內容的穩定性,甚至案件由偵查階段轉到審查起訴階段,情況也是如此,如果我們只排除“打”了的那一次的口供,而對于與被打這一次口供相同內容的其他多次口供無動于衷,那么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那種通過規制取證權力濫用或者誤用的立法目標就根本難以實現。
二、應對非法程序排除規則困境的建議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所以能成為西方國家刑事審判的基石,和西方國家的法律理念、配套制度等密不可分。中國有自己的國情,完全照搬西方的法律制度,往往可能水土不服,達不到預期的效果。因此,必須結合我國的刑事司法傳統、刑事司法模式等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進行本土化的設計,以破解當前《非法證據排除規定》的實踐困境。
(一)建議在立法中規定只要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申請,即可以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
在英美法系國家,被告人只需要提出一項動議或反對,就可以啟動排除程序,甚至不需要提供任何線索。在大陸法系國家,法院可以依職權啟動排除程序,無需被告人主張。我國也應該向西方國家學習,在立法中明確規定只要被告人申請,即可以啟動排除程序,以保障被告人的權益。
當然這可能會帶來被告人濫用啟動權的隱憂。司法實踐中,也存在被告人不惜編造偵查機關(部門)工作人員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的事實和情節,企圖運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混淆視聽,達到排除合法證據,以逃避罪責的目的。建議立法中對于編造理由,濫用啟動權的行為給予處罰。
(二)完善被告人供述取證及同步錄音錄像制度
鑒于目前刑訊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主要發生在看守所以外,建議在立法中明確規定對于被羈押的被告人,必須在看守所提押室內進行訊問取證,看守所以外取得的被告人口供不得作為定罪的依據。
對于所有的案件是否都要進行同步錄音錄像,目前存在爭議,部分學者認為我國經濟條件差異較大,全部錄音錄像不現實。但是筆者認為,應該在全部的刑事案件中建立錄音錄像制度。據調查,全國的看守所基本上都建立視頻監控系統。實踐中,完全可以對提押室進行改造,建立遠程的錄音錄像監控系統。對于公安機關的訊問,由駐所檢察部門進行遠程監控并同步備份。對于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的錄音錄像,由上一級檢察機關進行監督并同步備份。通過引入外部監督機制,可以改變“打時不錄,錄時不打”等現象,最大程度的減少暴力、威脅等非法取證行為。
三、建立重大案件的律師在場制度
對于重大案件,偵查人員進行訊問時,要通知律師參加,保證被告人在審查程序中獲得有效的律師幫助。我國最新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第33條已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只能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這也為訊問時律師在場制度掃除了法律障礙。
四、完善考核指標
長期以來,我國刑事案件發案率始終居高不下,而公安機關的破案率卻一直不高。公安機關承擔巨大的社會公眾與輿論壓力。公安機關把破案率和檢察機關的逮捕率作為主要考核指標,而且公安部明確提出命案必破的要求。而對于案件的質量,比如退查率、不起訴率、無罪率等沒有列入考核指標。所以大部分偵查人員認為只要突破嫌疑人的口供,一逮捕就萬事大吉。長期以來,偵查人員形成了對口供的依賴,一旦嫌疑人拒絕提供口供,就會對嫌疑人進行刑訊逼供[9]。建議偵查機關不再規定硬性的破案和逮捕指標,而是結合當地治安情況,制定出符合實際的彈性方案,減輕辦案人員的壓力,同時要將退查率、不起訴率、無罪率納入考核指標,扎扎實實提高辦案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