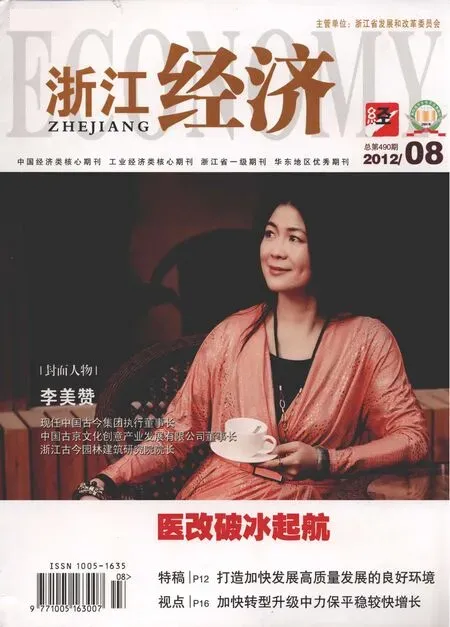用地緊缺正在損害浙江產業升級
浙江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遠未到達難以為繼地步,原有建設用地不可能大量調整出來用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用地緊缺也就等于掐住了產業結構增量調整途徑
樂清一家變壓器公司老總年前告訴我,他們2001年開始征用的一塊耕地,終于可在2012年初拿到。這種長達11年之久的拿地歷程,令人唏噓不已,典型反映了浙江的產業升級,正在遭遇用地緊缺的阻擊。
這家企業是當地納稅大戶。他們在柳市有兩個相距數公里的廠區,面積都很小,物流成本較高,嚴重影響企業生產經營。2001年,他們開始征用廠門前104國道邊上一塊70畝左右的耕地,當時處理好了與農民關系,地卻遲遲不能到手。
2009年,我去他們廠里調研,當時廠里開發出了干式、低耗等多種科技含量較高的變壓器,也拿到了多個重要訂單,但卻苦于場地狹小,不僅新產品難以量產,原有產品也受影響。萬不得已之下,他們在福建和蘇北等地買地,轉移了一部分生產能力,然而當地產業環境遠不如柳市,生產經營還是受到影響。
當前實施的“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按我的理解,可以有兩個含義。一是數量嚴格控制,浙江一個發達縣市一年的建設用地,大致只有1000畝左右,不到當地耕地面積的0.5%。類似于文成這樣的山區縣,只有500畝左右。二是征用嚴格控制,最大難點是占補平衡。即占用一畝農田,必須補上一畝農田,浙江寸土寸金,哪有地可補,一些地方已到了有指標也無地可用的境地。
這樣一個低水平的建設用地規模當然不敷使用。浙江正在向人均一萬美元以上的發展水平邁進,“半大小子,吃死老子”,這正是一個各方面均需用地的發展時期。浙江產業結構當前大致只相當于工業化中期水平,城市化率也僅62%,工業化和城市化都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然而,當前不要說企業和城市建設缺地,就連山區農民發展農家樂、鄉鎮建設幼兒園、民政部門建設敬老院等,也因缺地而受影響。
土地緊缺已影響到了浙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這是因為浙江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遠未到達難以為繼地步,原有建設用地不可能大量調整出來用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用地緊缺也就等于掐住了產業結構增量調整途徑。2004-2010年,浙江規模以上工業的機械電子電氣和儀表產值的比重合計,僅提高了2.9個百分點,平均一年僅0.41個百分點,進度明顯偏慢。這雖有多種原因,但長期來項目難以落地是一個重要因素。
蔡建平的工廠坐落在諸暨市店口社區五村。利用一棟租來的民宅,蔡建平2010年賣出了300萬套電熱、電容器銅配件,年產值6000萬元,占據全國40%,應該說已做到了極致。蔡建平打算進軍電容器行業,從二手市場以每畝120萬元購置了5畝土地,可是還缺20畝土地又在哪兒呢?蔡建平向政府打了報告,不過從柳市那家變壓器企業情況看,應該是不容樂觀的。
浙江確實存在著粗放和浪費用地狀況,如一些地方的馬路過寬、綠地面積過大、土地總體產出率較低等。不過,就當前階段而言,浙江集約用地水平也還是不能說較低,有些甚至已因集約用而影響了正常的生活生產。平陽、瑞安一帶農村,多戶農居聯排而建,相鄰兩家并用一堵山墻。浙江的大中城市,以及臺州、金華等地農村,相當多的建筑物間距小于1,光照條件很差;一些企業不得不在相鄰兩個車間之間蓋上頂棚,辟出車間,由此也出現了消防隱患。2007年,根據有關部門數據,全省人均建設用地0.295畝。日本在人均GDP與浙江大致相當的1990年,人均建設用地0.378畝,比浙江多28.1%。這或許有數據口徑問題,但至少可以認為,浙江與發展水平相同時期的日本比較,同時再考慮到有大量外來農民工的因素,人均建設用地或許不能算高。
土地不是一次性資源,是可以重復使用的。南宋皇城所在的杭州鳳凰山一帶,原先都應該算是建設用地,但現在局部是林業或園林綠化用地。從這個角度說,“但留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聽起來很煽情,實際并不完全確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