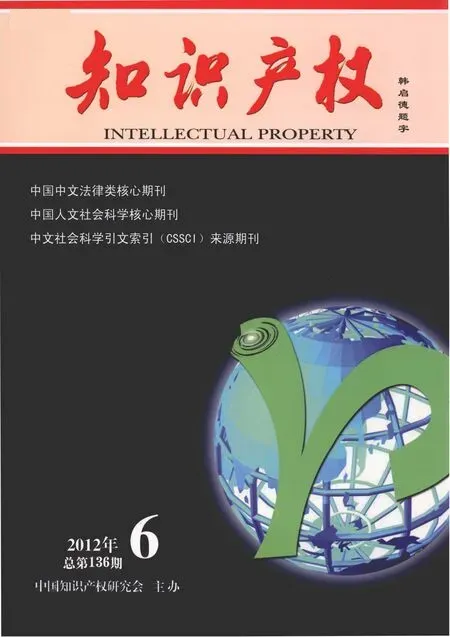試論我國禁止仿冒原則
劉 維
試論我國禁止仿冒原則
劉 維
禁止仿冒原則源于英美普通法上的欺詐侵權之訴,在英美商標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保護商業標識中的財產利益和消費者不受混淆的公共利益是禁止仿冒原則的正當性基礎。禁止仿冒原則的保護范圍在司法上不斷擴大,已涵蓋商業外觀保護,但應止于人格特征的盜用。禁止仿冒原則不要求行為人的主觀故意,財產利益的商業標識和混淆可能性是仿冒行為成立兩大要件。
禁止仿冒 正當性 欺詐故意 司法適用
《反不正當競爭法》第5條規定的仿冒糾紛有四種類型,分別為仿冒他人知名商品特有名稱、包裝、裝潢,仿冒他人企業名稱或姓名,偽造冒用質量標志和偽造產地。這四種類型仿冒行為的禁止均著眼于對商業標識的保護,經由多年司法判決的積累和發展,禁止仿冒原則在我國已經成為反不正當競爭法下保護商業標識和維護公平競爭的重要武器,成為我國商業標識法律體系中的主干。司法實踐中,仿冒糾紛案件在不正當競爭糾紛中的比例很高,以商業城市上海為例,2011年上海市人民法院一審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件受案94件,其中仿冒糾紛案件共27件,占到28.7%。然而,關于禁止仿冒原則的基礎研究、司法適用中的問題和發展現狀,目前還缺乏足夠關注。本文試對禁止仿冒原則的正當性基礎、禁止仿冒原則中的主觀要素、適用邊界以及構成要件進行探索。
一、禁止仿冒原則的正當性基礎
禁止仿冒原則是商業標識法律體系的一個分支,是反不正當競爭法在對未注冊商業標識提供保護過程中所發展出來的一個原則。禁止仿冒原則的正當性基礎提供了其存在的必要和價值,決定了其司法適用的范圍和構成要件。禁止仿冒原則的正當性基礎存在于兩個方面,一方面在于保護商業標識中的財產利益;一方面在于保護消費者不受混淆的公共利益。
(一)保護商業標識中的財產利益
標記本身并無價值,亦無受法律保護的理由。商業標識之所以受到法律保護,乃是基于其中所蘊含的財產利益。從本質上看,商業標識中的財產利益來源于商業標識的使用,商業標識的使用發揮了投資和勞動的功能。按照洛克的財產勞動理論,“只要他使任何東西脫離自然所提供的和那個東西所處的狀態,他就已經摻進他的勞動,在這上面參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東西,因而使它成為他的財產。”①洛克 :《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2月第1版,第18頁。經營者在某個標記上摻進投資和勞動,使該標記具有了識別商品來源的功能,脫離自然狀態,與此同時,消費者對該標記產生認可,形成商譽,此時的商業標識即具備了受法律保護的正當性,成為應受法律保護的商業成果。我國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對未注冊的商業標識提供保護,其正當性也在于此。
現代知識產權法的經濟刺激理論也為禁止仿冒原則提供了正當性。根據經濟刺激理論,法律通過授予創作人有限壟斷以作為創作人創作的經濟鼓勵。經濟刺激理論背后的哲學根據在于,個人經濟的改善和提高是刺激其投資和創作的根本途徑。體現在仿冒之訴中,反不正當競爭法對未注冊商業標識提供保護,是經營者在商業標識上進行投資的回報,同時激勵其繼續投資和經營。
最高人民法院在“三九釀與江口醇仿冒糾紛”案對上述理論進行了闡述:“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的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稱、包裝和裝潢,是知名商品的經營者在長期的經營中,投入資金、技術等進行管理和經營,逐漸積累形成的財產利益。如經營者主體發生變更,在權利繼受主體繼續經營的情況下,知名商品特有名稱、包裝和裝潢所形成的財產利益應由繼受主體享有。”②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申字第1084號民事判決書。
(二)保護消費者不受混淆的公共利益
禁止仿冒原則在現代法上的發展,呈現出與注冊商標保護相融合的趨勢,在這一意義上,商業標識保護的體系性已經愈發成熟,保護消費者不受混淆的公共利益成為這一領域的核心。識別性是商業標識的本質屬性,禁止仿冒原則為商業標識提供保護,其目的在于確保商業標識的識別力,由于識別性的主體是商品或服務的購買者,因此,保護商業標識的識別力實質上就是保護購買者對商品或服務來源的識別能力,換言之,就是保護消費者不受混淆的公共利益。我國商標法上判斷混淆可能性的主體標準和時空標準都體現了對這一公共利益的保護,混淆可能性的判斷主體并非施加特別注意力的群體或專家,而是在購買商品過程中施加一般注意力的普通消費群體,而且必須在隔離狀態下進行判斷。
這一正當性基礎使禁止仿冒原則(或廣義上的商業標識法律體系)成為一個特殊的法律領域。在訴訟上,消費者并非案件的當事人,但訴訟卻成為保護其利益的工具和手段,甚至在實體法律問題上,消費者的感知成為決定訴訟成敗的關鍵。“在有關商標侵權證據的考量過程中,法院必須擴大經常使用的、單對單、兩造爭辯的方法。作為第三方的消費公眾應在場且其利益甚巨。因此,當有證據證明對消費公眾存在混淆可能性、欺騙或誤導時,即可認定侵權成立。……所侵害的并非商標本身,而是公眾不受混淆及同等意義上商標所有人控制其商品聲譽的權利。……有利害關系的商人在保護其標識過程中可能提起訴訟。但是,所謂‘自由市場’機制(其正常運營時,也許稱之為‘消費者選擇’機制更為適合)的核心在于消費公眾和企業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公眾無需依賴政府制止混淆。”③Dallas Cowboys Cheerleaders, Inc. v. Pussycat Cinema, Ltd., 604 F.2d 200, p.205 (2d Cir. 1979).Dallas Cowboys Cheerleaders, Inc. v. Pussycat Cinema, Ltd., 604 F.2d 200, p.205 (2d Cir. 1979).
由此可以看到,商業標識上的財產利益與消費者不受混淆的公共利益同等重要,前者著眼于保護權利人的私人利益,后者關注保護消費者的公共利益,二者共同成為禁止仿冒原則為商業標識提供保護的正當性基礎。
二、禁止仿冒原則的主觀要件之辯
(一)我國司法判決的考證
搭車故意是否為仿冒之訴的構成要件,《反不正當競爭法》第5條持否定回答。但在仿冒之訴的司法判決中,搭車故意與仿冒之訴已經“形影不離”。如在“腸清茶仿冒糾紛”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康中源腸清茶產品裝潢在文字布局、圖案設計甚至色彩選擇方面均與御生堂腸清茶產品相似甚至相同,比如背景圖案,可選擇的素材范圍很廣,其卻采用了與御生堂腸清茶裝潢中基本相同的松樹、古代人物等素材,而且構圖方式也基本相同,并且采用了與御生堂腸清茶相同的三種底色,易造成相關公眾混淆。在御生堂腸清茶產品已構成在先知名商品且其裝潢為其特有裝潢的情況下,康士源公司作為同行業經營者,其采用上述相近似的裝潢,借靠他人知名商品聲譽以獲取不正當競爭優勢的意圖明顯,構成不正當競爭行為。”④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提字第60號民事判決書。
在商標侵權糾紛中判定混淆性近似時,被告的主觀故意可作為考慮因素。但我國仿冒之訴的司法判決中,法官顯然并非僅將搭車故意作為判斷混淆近似的一個考慮因素,在“腸清茶仿冒糾紛”案中,法官在得出混淆結論之后再考量搭車故意,進而認定不正當競爭行為,從中很容易得出“搭車故意”是仿冒之訴構成要件的結論。這種結論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011年十大案例“開心網仿冒糾紛”案中更為清晰:“千橡互聯公司作為互聯網業界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公司,在明知開心人公司通過‘開心網’(kaixin001.com)提供的社會性網絡服務已構成知名服務的情況下,自2008年10月開始使用該知名服務的特有名稱‘開心網’作為網站名稱,在相同行業和領域中向公眾提供社會性網絡服務,使網絡用戶對二者提供的服務產生混淆,其行為具有主觀過錯,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構成了不正當競爭,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⑤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9)二中民初字第10988號民事判決書。
在仿冒之訴的司法判決中,主觀上的搭車故意和客觀上的混淆誤認往往并列成為論述仿冒行為成立的兩大因素。在“九牧王仿冒糾紛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興達公司與九牧公司處于同一地區,其應當知曉九牧公司的注冊商標及其在衛浴潔具行業的知名度,本應誠實經營,但卻在被控與九牧公司注冊商標核定使用商品相同或類似的淋浴軟管、龍頭、花灑、沖洗閥等物品的包裝、合格證、保修卡、宣傳冊、購物袋、名片、公司網站網頁上等使用“香港九牧王衛浴潔具實業公司(監制)”文字,其利用九牧公司“九牧”、“九牧王”品牌聲譽的主觀故意明顯,違背了誠實信用原則和公認的商業道德,在九牧公司注冊商標具有較高知名度的情況下,客觀上容易誤導公眾,因此興達公司的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⑥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申字第123號民事判決書。
(二)禁止仿冒原則中主觀要素的歷史嬗變
1.禁止仿冒原則的起源
行為人的主觀故意是否為仿冒行為的構成要件,這還得從仿冒之訴的起源和發展中進行觀察。仿冒在英美普通法上的最初含義是冒充他人商品的魚目混珠行為,仿冒之訴源于欺詐之訴,欺詐故意是仿冒之訴的構成要件。“大概從1803年開始,英美普通法緩緩地發展出欺詐侵權之訴的一個分支并稱之為仿冒(passing off)或冒用(palming off)。簡單地說,作為侵權形態的仿冒,是指將自己的產品冒充他人產品。”⑦J. Thomas McCarthy, McCarthy on Trademark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Fourth Edition, §5:2.
在1842年發生的首個仿冒案件——Perry v.Truefitt案中,Langdale法官闡述了仿冒之訴的基本原則,從中也可見到行為人主觀故意的影子。“法院法和衡平法為該類案件(仿冒)提供救濟和保護的原則已經廣為人知。禁止一人將自己的商品偽裝成他人的商品予以銷售。禁止實施這種及任何其他方式達成此目的的行為。因此,禁止以可能引誘購買者誤認出售的商品乃其他人生產的方式使用姓名、商標、字母或其他標識。”⑧[1842] 6 Beav 66, p.73.
2.禁止仿冒原則的發展
如果說1842年發生的Perry案還只關注被告“偽裝商品”進行欺詐的故意,到20世紀早期,司法判決對仿冒之訴中的欺詐要素已經逐漸弱化,重心開始放在消費者的混淆后果上。在美國的不少司法判決中,甚至將仿冒作為混淆可能性的同義詞。有法院指出,仿冒與來源混淆之間的界限不是很分明,在效果上,仿冒僅是一種更為直接和明顯的誤導購買者對商品來源發生混淆的行為。仿冒與來源混淆在盜用競爭者財產或商譽上發生重疊。⑨Pezon et Michel v. Ernest R. Hewin Associates, Inc., 270 F. Supp. 423, p.427 (S.D.N.Y. 1967).
到現代英美法上,禁止仿冒的原理與制止商標侵權的基礎一致,保護消費者不受混淆的公共利益已經成為二者的共同原理。1990年奧利文法官在Reckitt and Coleman Properties Ltd v.Borden Inc案中的闡述清楚地表明英美普通法上仿冒之訴的構成:用一句話可以概括仿冒法的理論基礎——禁止用自己的產品冒充他人的產品,在此類訴訟中,原告若想勝訴必須完成三個方面的舉證。第一,原告必須已經在其商品或服務上建立起了商業信譽或知名度,相關公眾依靠印象中具有識別力的特征(無論是字號或名稱或者是標牌或包裝的顯著部分)與原告相聯系并購買其產品,因而此類特征被相關公眾認為是原告商品或服務具有區別其他人的顯著性特征。第二,原告必須證明被告對相關公眾作出不實陳述(不論是否對此有主觀故意),并引起或者可能引起公眾相信被告提供的產品或服務來自于原告……第三,他必須證明他因為被告的不實陳述所引發的誤解受到實際或可能的損害。⑩[1990] 1 All E.R. 873, p.880.
英國著名學者柯尼什論述禁止仿冒原則時,也認為行為人的主觀故意并非其構成要件,僅影響到損害賠償。“基于一般原則,被告即使不知道他的行為會引起欺騙,仍需負法律責任,然而他的無辜會影響損害賠償的判決。”?W.R. Cornish, Intellectual Property: Patent, Copyright, Trademark and Allied Rights, Sweet and Maxwell, 1981, p. 485.“除非被告成功造成必要程度上的混淆,否則,被告即使故意模仿、復制或假冒原告的產品,從而制造他自己的產品,也仍不需承擔法律責任。”?彭道敦、李雪菁著:《普通法視角下的知識產權》,謝琳譯,法律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第37頁。我國《商標法》第52條并未將行為人的主觀故意作為商標侵權的構成要件,《商標法》第56條將銷售者的過錯作為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條件,此一規定與英美法的規定為同一旨趣。
3.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視角
可見禁止仿冒原則在發展中已經拋棄了行為人主觀故意的要求,重心放在消費者混淆后果的考察上。在更為廣闊的反不正當競爭法視野下,也可看到主觀要件在禁止仿冒原則中的演變。
美國法上的反不正當競爭源于仿冒之訴,由于缺乏對不正當競爭的界定及系統理論的支撐,仿冒之訴一度成為美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下的唯一原則,仿冒之訴與不正當競爭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相互指代。由于仿冒之訴要求原告證明被告具有欺詐的主觀故意,為了在不正當競爭案件中勝訴,原告也被要求證明被告具有欺詐故意。然而,現代反不正當競爭法已經從傳統的禁止仿冒發展到涵括商業秘密保護、公開權保護、禁止虛假宣傳和商業毀謗、禁止盜用熱門新聞等一切違反公平交易和商業倫理行為的體系,其關注重心在于行為的正當性和行為的后果,盡管行為人的動機和主觀故意仍是判斷行為正當性的重要因素,但其早已不是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核心。
主觀故意并非仿冒行為的構成要件,還可從國際條約關于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規定中得到印證。《巴黎公約》第10條之2規定:任何違背工商業誠實慣例的競爭行為均構成不正當競爭行為。禁止任何對競爭者的營業機構、商品或工商業行為導致混淆的行為;禁止貶低競爭者營業機構、商品或工商業行為的虛假陳述;禁止導致公眾對商品性質、生產流程、特征、目的合適性或質量產生誤解的標識或陳述。由此可見,無論是仿冒行為、虛假陳述還是商業毀謗中,《巴黎公約》都未將主觀故意作為判斷不正當競爭行為是否成立的構成要件。《TRIPS協定》第16條第1款禁止以產生混淆的方式在相同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上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標,關注點僅在消費者的混淆后果。由于協定第15條第1款對商標采取了廣義的定義,應當認為仿冒商業標識行為的條件也是消費者的混淆后果,而沒有對行為人的主觀故意作出要求。
非常清楚,禁止仿冒原則在現代法上的發展已經放棄行為人主觀故意的要求。由此可觀,我國仿冒之訴的司法判決中強調惡意搭車為仿冒行為構成的條件,似有斟酌的必要。反不正當競爭法提倡正當競爭和維護商業道德,主觀故意是判斷行為正當性的重要考量因素。但現代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類型化程度已經越來越高,具體類型不正當競爭的構成要件已經逐漸精細化,在做司法判斷時應嚴格適用具體類型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構成要件。
三、禁止仿冒原則的保護范圍和適用邊界
(一)禁止仿冒原則的保護范圍
保護商業標識中的財產利益和消費者不受混淆的公共利益是禁止仿冒原則的正當性基礎,二者分別作為適用該原則的入口和出口,決定了禁止仿冒原則的適用范圍和構成要件。商業標識中的財產利益是進入禁止仿冒原則的入口,只有具有財產利益的商業標識方為該原則的關注對象,不具有財產利益的普通標記不能落入該原則的保護范圍。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5條規定的四種仿冒行為,均著眼于具有財產特征的商業標識,其法理基礎即在于此。其中,知名商品特有名稱、包裝、裝潢的保護已成為我國禁止仿冒原則最有生命力的適用場合,成為法律發展的試驗田,而“裝潢”的適用則成為禁止仿冒原則司法發展的主要陣地,使禁止仿冒原則在具有財產特征的商業標識的保護范圍內不斷擴張。
從語源上講,裝潢是指“裝裱”,即古代書畫用潢紙(以潢染的紙)裝裱。?劉春田主編:《知識產權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11月版,第333頁。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關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的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若干規定》第3條第5款對裝潢的定義為:為識別與美化商品而在商品或者其包裝上附加的文字、圖案、色彩及其排列組合。近幾年來,裝潢的內涵在司法上不斷擴張,早已突破其文義,當學者們還在爭論商業外觀的立法必要和保護體系時,禁止仿冒原則早已悄悄地將商業外觀納入其保護范圍之中。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認為“由經營者營業場所的裝飾、營業用具的式樣、營業人員的服飾等構成的具有獨特風格的整體營業形象”應作為裝潢保護,已經可以看到商業外觀保護的影子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態度。2009年上海市高級人民院審理的“三菱電機仿冒糾紛案”,表明司法界已經開始探索商業外觀保護的一般要件:“僅由商品自身的性質產生的形狀,為獲得技術效果而需有的商品形狀以及使商品具有實質性價值的形狀,人民法院不認定為知名商品特有的裝潢。商品外觀形狀如果符合最高人民法院該司法解釋關于商品裝潢的構成要件,并滿足受法律保護的其他要件,可以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第5條第2項獲得保護。”?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08)滬高民三(知)終字第17號民事判決書。2011年最高法院審理的“晨光筆仿冒糾紛案”則可標志商業外觀保護要件的確立:“對于文字圖案類裝潢而言,由于消費者幾乎總是習慣于利用它們來區分商品來源,除因為通用性、描述性或者其他原因而缺乏顯著性的情況外,它們通常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區別商品來源的作用。……內在于商品之中的形狀構造類裝潢構成知名商品的特有裝潢需要滿足更嚴格的條件。這些條件一般至少包括:1.該形狀構造應該具有區別于一般常見設計的顯著特征。2.通過在市場上的使用,相關公眾已經將該形狀構造與特定生產者、提供者聯系起來,即該形狀構造通過使用獲得了第二含義。”?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提字第16號民事判決書。
(二)禁止仿冒原則的適用邊界
禁止仿冒原則的保護范圍在不斷擴張,但其中心點始終恒定不變,即保護具有財產利益的商業標識,越過此范圍則無關仿冒,因此,禁止仿冒原則的邊界止于人格利益或具有人格特征的符號。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5條第3項禁止仿冒他人的企業名稱和姓名,立足點并非民事主體的人格利益,而在于企業名稱和姓名所具有的商業標識意義,制止仿冒他人企業名稱和姓名所可能帶來的市場混淆。因此,中外企業名稱或姓名只要在我國境內進行了商業使用并具有識別力,都可受到本項的保護,至于企業名稱是否在我國行政機關登記,則在所不問。
自然人姓名的商業標識意義,所體現的是姓名所具有的財產利益。“作為文化市場的經營者,作家通過署名的方式使自己的名字傳播,并使之成為消費者選擇作品的標識之一,這種標識作用可以指引其作出消費選擇。作家署名的這種標識功能,使其具備被他人借鑒、仿冒、攀附或淡化的可能性,故其有權要求禁止他人實施上述不正當競爭的行為。本案中,原告王躍文創作了以《國畫》為代表作的系列官場題材小說并在作品上以本名署名。該署名直接指向原告本人,明示作品的提供者身份;該署名在新作品上,能使人產生與原告創作的《國畫》等優秀作品相關的聯想;同樣,原告由于其先前的創作行為而享有聲譽,其署名作品也因此較為容易被消費者接受,有益于提高新作品的市場認同度。原告王躍文姓名的商業標識作用,應予認可。”?湖南省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2004)長中民三初字第221號民事判決書。
然而,姓名、肖像在本質上是具有人格利益的標記,民事主體也主要在人格意義上使用這些標記。在商業上,使用這些標記以區分商品或服務來源固然體現了其具有商業標識意義,但只要并非在來源識別意義上使用人格標記,禁止仿冒原則即不能適用。商業中對人格標記的使用更多是從人格意義的角度,為了借用他人聲望和名氣獲利,在這種場合下,由于缺乏適用禁止仿冒原則的正當性基礎,《反不正當競爭法》第5條第3項不可適用或類推適用。
四、禁止仿冒原則的構成要件
前已論及,禁止仿冒原則的正當性基礎決定著該原則的保護范圍和構成要件,商業標識中的財產利益是適用禁止仿冒原則的入口,只有具有財產利益的商業標識才能進入禁止仿冒原則的保護領地,至于是否成立仿冒行為,則還應受到混淆可能性的檢驗,因此,消費者不受混淆的公共利益是禁止仿冒原則的出口。
(一)商業標識中的財產利益
禁止仿冒原則所保護的財產利益,是通過經營者對標識的商業性使用來積累的,這與我國注冊商標的保護不同,在我國只要完成商標注冊,法律即賦予該注冊商標以財產權益,受到法律保護,注冊商標權利人因此享有商標專用權和排他權,甚至只要提起商標注冊申請,即使尚未完成注冊行為,法律仍然保護該申請注冊商標中的期待利益。
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5條第2項通過“知名商品”和“特有”來限定商業標識中的財產利益,成為認定財產利益的兩個門檻。前者是指商業標識的知名度,后者是指商業標識的顯著性,二者成為保護和認定商業標識(包括未注冊商標和注冊商標)的兩大要素。禁止仿冒原則保護的商業標識的知名度,并非全國知名,它與《商標法》第31條“有一定影響”的未注冊商標呼應,與馳名商標、注冊商標共同構成一個有層次感和立體感的商業標識保護體系。
從反面看,特有商品是相對于通用商品而言;從正面看,特有商品是指商業標識的顯著性,與注冊商標的顯著性認定并無二致,司法實踐中關于特有商品的認定,已經類型化為四種案件:(1)描述性標識只有通過“第二含義”獲得顯著性,才能受到法律保護。?同注釋④。(2)具有固有顯著性即可受保護。通常可借用版權法下的獨創性來判斷固有顯著性。?同注釋④。(3)具有固有顯著性,經過持續使用之后具有較強的顯著性。?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三監字第15-1號民事判決書。(4)經使用喪失顯著性,成為通用名稱后無法受到保護,最高人民法院在“84消毒液仿冒糾紛”案中對“84消毒液”的認定即為一例。?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02)民三終字第1號民事判決書。
(二)混淆可能性
基于商業標識的本質屬性,檢驗仿冒行為與商標侵權行為能否成立,均應通過混淆可能性理論。“我國法律保護注冊商標專用權和知名商標特有的名稱,目的之一在于保護交易秩序、制止混淆。在混淆的判斷標準上,兩者具有相同的規則。”?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0)湘高法民終字第11號民事判決書。
在我國現有的商業標識法律體系下,混淆分為來源混淆和關聯關系混淆兩種類型,在具體判斷混淆是否成立時,又要區分兩種案件類型,在相同商品或服務上使用相同商標的行為,可直接推定混淆可能性成立,構成商標侵權;除此之外的三種案件類型,如在類似商品或服務上使用近似商標的行為,則需完成商品類似和商標近似的法律判斷,以認定是否構成商標侵權。通過嵌入商品類似和商品近似的判斷中,混淆可能性在我國得到確立。
混淆可能性的判斷是一種法律判斷,需結合個案中的所有因素綜合進行認定,商業標識在物理意義上(音、形、義)的近似不等同于法律意義上的混淆性近似,實際混淆的證據不一定能得出法律意義上的混淆可能性,?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三終字第3號民事判決書。實際不混淆卻有可能成立法律意義上的混淆可能性。
s:The principle of preventing passing off has its root in the common law torts of deceit. It is of a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history of trademark and unfair competition law. Protecting the property interest in the business designation and protecting public interest from confusion as to source provide the philosophy basis for the principle of preventing passing off.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passing off expands. It encompasses the protection of trade dress, but shall not be applied to the misappropriation of personality. The business indication which has property interest and the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are the prerequisites of passing off, while fraudulent aspects of passing off were gradually deemphasized.
passing off ; philosophy basis; fraudulent; judicial application
劉維,華東政法大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