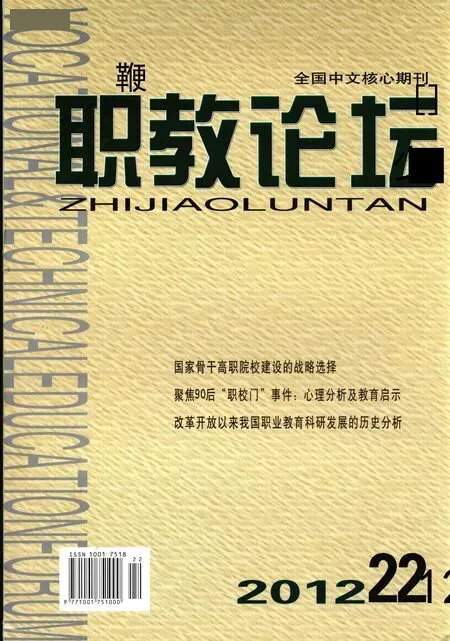民國初期成人女子教育研究
□胡若雪 邵曉楓
辛亥革命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統治,近代中國社會開始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急劇轉變,新的社會政治形態必然要求有與之相適應的教育形態,南京臨時政府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主張振興女學。他指出:“教育既興。然后男女可望平權。女界平權,然后可成此共和民國”[1],同時“教育上的平等為一切平等的淵源”的思想開啟了成人女子教育的新時期。五四運動開始后,女性問題得到關注,婦女解放成為這場運動的重要內容,女子教育成為這場運動的重要變革對象,成人女子教育也取得了突破性發展。目前,學術界對民國初期的女子教育做較多的研究,但總體上關注的是女子學校教育,對成人女子教育研究有所涉及但不多,更不夠系統。因此,本文擬對民國初期,即1912年到1927年間成人女子教育進行系統的梳理和總結,以利于人們了解和進一步研究這一時期成人女子教育的發展情況。
一、開始形成新的成人女子教育觀
民國時期,隨著民主革命的開展和西方先進文明的傳播,婦女解放問題被提上議程。而教育平等是解決婦女問題的根本淵源,只有形成了正確的成人女子教育觀,才能促進成人女子的解放。在這一時期,一方面,傳統的成人女子教育觀,即培養“賢妻良母”型的觀念還有很大的市場;另一方面,開始形成新的成人女子教育觀。
“賢妻良母”這個觀念作為中國傳統社會對女子身份、行為的要求,自母系社會結束男權文化的家族制度開始便深深扎根于中國文化中。在先秦時代,儒家思想十分重視女子對“婦道”的學習,孟子提出“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為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2]。要求女子溫順、孝順,以丈夫為依靠。漢代時“三綱五常”的提出形成了封建社會道德體系,在此基礎上發展的“三從四德”觀念則成了女子教育教條。之后劉向所著的《列女傳》和班昭所著的《女戒》更加系統闡述了男尊女卑的觀念和夫為妻綱的道理,進一步規定了女子的道德和行為準則,并將女子言行和思想困在這道德體系之中讓她們心甘情愿的成為男子的附庸品。至此,中國女性教育千年一制。直至清末時期,受西方“天賦人權”、“男女平等”等思想的傳播,中國的知識分子逐漸認識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女子教育開始走出閨閣。1819年中國第一所國人自辦女子學校——經正女學在上海創辦,確立女子教育的教育方針為“中西并重”強調自然科學和文化知識的學習。但教育宗旨仍是圍繞妻職和母職,以求達到“保國、保種、保教”的目的。正如《中國女學會書塾章程》中指出:“其教育宗旨,以彝倫為本,所以啟其智慧,養其德性,健其身體,以造就其將來為賢母,為賢婦之始基”[3]。
民國建立初期,雖然由于女權運動的開展,使女子教育得到了較大發展,女子教育的宗旨有所更新,但仍未脫離“賢妻良母”的模式。有學者指出:“女子生活的主要目的,是為人妻母,為人妻子的責任,就是社會道德的根本任務”[4]。“女子教育,尤需確認培養博大慈祥之健全的母性,實為救國保民之要圖,優生強種之基礎”[5]。這在當時的成人女子教育中也非常突出,如成人女子職業教育中女子所學的多為操持家政的知識和技能、成人女子留學教育傾向于選擇家政、教育等專業,成人女子社會教育的目的也是為女子學得知識以便更好的教育子女。可以說民初成人女子教育所遵循的還是一種“賢妻良母”教育模式,只不過將現代知識文化和先進科學技能與母職、妻職相聯系,以更好的服務丈夫、經營家庭、教育子女。但這樣片面宣揚女性為人妻母的職責以致教育不但忽略了女性的個體價值,而且低估了女性的社會意義。一方面使其仍未完全擺脫“夫為妻綱”的封建教條而不能成為擁有完整個性的人;另一方面將女性禁錮于丈夫和孩子組成的世界,只能體現其對于家庭的價值而無法體現其社會價值。
“五四”以后,以“賢妻良母主義”為宗旨的成人女子教育已經不能滿足社會的發展和女子自身解放的要求,廣大知識分子紛紛提出要促進女子自身經濟獨立和人格獨立。蔡元培認為女子教育的宗旨應與男子一樣“養成完全之人格”,即讓女子接受德、智、體等方面的訓練最后達到經濟上獨立、與男子在職業上平等、參政權同等,這樣女子才能擁有完全的人格取得真正的解放。胡適在考察美國后呼吁中國婦女向美國婦女學習并提出“超級賢母良妻觀”。胡適對“超級賢母良妻觀”的人生觀這樣解釋說:“這種超于良妻賢母的人生觀換言之,便是‘自立’的觀念……‘自立’的意義,只是要發展個人的才性,可以不依賴別人,自己能獨立生活,自己能替社會作事”[6]。所以成人女子教育的目的不是養成賢妻良母,而是成為比賢妻良母更重要的社會人,女子的責任不僅限于家庭而更應為社會服務。成人女子教育要讓女子以“自立”精神來輔助“依賴”性格,以“超級良妻賢母人生觀”來輔助“賢妻良母觀”以使女子自立自強。
無論是蔡元培提出的要求女子“養成完全之人格”,還是胡適提出的“超級賢母良妻觀”,相比于傳統的“賢妻良母觀”都更具有進步性。他們看到了女性作為“人”的個體的存在,看到了女性在促進社會發展中不可忽視的作用,強調培養女性的自立、獨立和完全人格更好的發揮其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
二、成人女子職業教育得到一定發展,開始走向平民化
女子職業教育始于清末,但由于對學生要求嚴格、收費標準高、學校數量極少并未普及。
1912年4月,民國建立后,蔡元培在《關于教育方針之意見》中系統地提出了五育并舉的思想,強調了實利主義教育的重要性。他認為“今之世界所恃以競爭者,不僅在武力而尤在財力”,“我國地寶不發,實業界之組織尚幼稚、人民失業者至多,而國甚貧,實利主義之教育,故亦當務之急者也”[7]。同時陶行知認為,職業教育不僅要在男性中開展,更要在女性中開展。“女性同為人類,自應有知識技能,去謀獨立生活”[8]。在此基礎上人們開始認識到對成人女子進行職業教育不僅能養成成人女子獨立人格和謀生的本領,而且能習得專門之技術提高自身的求生能力和社會地位。隨著五四運動開始,民族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和對新式職業人才的要求更進一步推動成人女子職業教育的發展,即成人女子職業教育開始走向平民化。
黃炎培曾說過:“如果辦職業教育而不是著眼于大多數平民身上,他的教育,無有是處”[9]。成人女子職業教育也絕不是為少數服務,要普及成人女子職業教育使其平民化就要做到兩點:一是成人女子職業教育形式多樣化;二是成人女子職業教育由城市走向農村,由貴族走向平民。1913年教育部公布的《實業學校令》第一次將女子職業教育納入學制。1919年教育部 《咨各省區為女子中學校可附設簡易職業科》中提出“各女子中學校自可酌量地方情形,附設女子簡易職業科,以資實用”[10]。許多省立中學紛紛響應號召開辦女子職業簡易科。如1920年黑龍江省立女子中學校提出:“現擬就女子中學校內添設簡易職業一班,擇上手工及其他科目,足以謀生活者,短期造就,俾貧寒女子均得養成應用知識技能或于前途不少裨益”[11]。該班以“教授女子實用之技術及必要之學科”為宗旨,招收十四歲以上二十二歲以下的家境貧寒女子。1921年江蘇省立女子職業學校增設甲、乙簡易科,其中乙種簡易科招收年齡在十五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的年大失學且略識文字之女子專習手工。除設置簡易科外,江蘇省立女子職業學校還設有冬季選科夜校以及貧女工廠對成人女子進行職業教育。除了公辦學校以外,很多民辦機構也為成人女子職業教育做出貢獻。蔡元培主張“擇地創立都市式、鄉村式女子職業學校,日、夜、星期職業補習學校,而又須有改良普通教育之準備”[12]。女子職業補習學校教育宗旨為“以補習其受義務教育未充之知識,及其所志愿職業之需要技能”,女子無論年齡大小、是否就業均可根據自己職業意愿選擇科目。女子職業補習學校的出現,由于其時間便利性和覆蓋地點廣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成人女子職業教育特別是鄉村成人女子職業教育的發展。
雖然這一時期成人女子職業教育取得了一定成就,有了一定創新,如重視教學與實踐相結合、重視校企合作解決成人女子生計問題。但其發展極不平衡且存在一定歧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政府對成人女子教育重視不夠。雖然教育部呼吁推進女子職業教育的發展,但實際上對成人女子職業教育的師資力量、教學設備、課程設置等重視仍不夠,真正獨立的成人女子職業學校甚少;第二,相比于女子職業學校的職業教育,成人女子職業教育科目設置單一、修業年限短、就業范圍窄。成人女子教育科目設置主要是以刺繡、紡織、縫紉、草編等簡易女紅為主,修學年限為一年至一年半、學成后多為女工或進行家政工作。造成這一系列原因主要是相比女子職業學校學生,傳統上認為成人女子文化程度較低,無法學習高深知識和從事高端職業。這不但低估了成人女子的繼續學習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成人女子的發展;第三,更多關注的是大齡失學婦女的成人女子入職和職后教育,而忽視了有一定學業基礎的從事高端職業的成人女子職后教育。
三、成人女子留學教育興起,并逐漸規范化
鴉片戰爭后中國大門被迫打開,國人在接受世界新事物的同時也認識到自身不足。于是清末年間一部分國人留學國外以期“師夷長技以制夷”,然由于封建觀念的束縛,女子留學的人數寥寥可數。直至民國成立后,留學熱逐漸興起,數以千萬的愛國青年為求國外高深之術已達到救國救民的目的紛紛踏出國門開始了留學之旅。在此思潮下,成人女子也積極參加到留學教育中,或為追求自身理想實現自我價值;或以期通過向其他國家學習改變中國女性面貌;或懷著“教育救國”思想,人們也逐漸意識到女子留學的重要性。當時有學者認為“誠以國內無教授女子高等學問之學校,必須遠涉重洋,然后能得相當之學問。或留學日本、或留學美國,蓋日本較近,資費較輕,美國雖遠,清華學校可以送往也”[13]。至此拉開了成人女子留學的序幕。清末時的女子留學主要集中在日本、美國,但到了民初由于政治原因成人女子留學國家主要集中于美國、法國和蘇聯。
留學美國始于“庚子賠款”,之后得到了一定發展。1914年起清華留美預備學校開始招收女生,“體質健全,品行端淑,天足且未訂婚,年在二十三歲以內,國學至少有中等畢業程度,英文及科學能直入美國大學校肄業者為合格”[14]。至此間年選派,均定額十名,到1929年為止選派的官費女子留美學生共五十三名。加上女子留學自費生“1914年,共有留美中國學生1300名,其中女生94名,至1916年,留美中國學生有女生159名,1917年增至近二百名”[15]。由梅貽琦、程其保所編的《百年來中國留美學生調查錄》(1854-1953)可知,1919—1926年留美人數共2370人,其中女性占278人,占總人數的11.7%。而在這其中,特別是留美自費生中,成人女子占了一定比例。如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教師楊蔭榆在“移家就學”的思想下被教育部派遣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于北京女子高師吳貽芳于1922年留學于美國密執安大學研究院。留法教育興起較晚,直至五四運動后才逐漸流行。從1919年到1920年8月止,留法人數共1200余人,其中女性只有21人。她們中大多數都是已就業的成人女子,抱著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的心情赴法。“而非勤工不能儉學者約有18人,他們都是國內女子師范學校或中學校畢業生,而又曾歷任小學教師,年齡在二十以上,對學術都有深切的希望”[16]。這其中就包括了蔡暢、向警予等,除此之外蔡暢的母親,年約五十歲的葛建豪也包含其中。此外,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和孫中山“以俄為師”的號召下形成留學蘇俄的熱潮。1920年2月,當時在北京的毛澤東在致友人信中即提出擬組織一只留學俄隊赴俄勤工儉學,并認為也可以組織女子留俄勤工儉學會[17]。作為留蘇的預備學校,中山大學共招收三期學生,第一、二期有300多人,其中女生約占3/10左右[18]。參與其中的大多為革命女干部,希望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以回國投入革命斗爭的實踐。
雖然這一時期的成人女子留學教育有了一定發展,但總體人數較少且發展速度緩慢,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由于女學才興、婦女解放運動才拉開序幕,社會觀念未能轉化,許多人對女子留學抱有懷疑態度;第二,由于時代原因,當時大部分成人女子文化程度較低、外語水平差,難以達到留學預備學校的標準;第三,留學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作為后盾,而女子留學的官費名額較少、對女子要求較高,一般的中產階級無法支付自費留學的巨額費用。雖然“五四”后“工讀主義”盛行,勤工儉學運動得到大力發展,使一部分貧困女子得以自食其力邁出國門,但也只有少數的成人女子參與,第四,一部分成人女子受家庭羈絆,婚姻、孩子成為其留學阻力。
四、成人女子社會教育取得較大發展,教育目的與內容多元豐富
民國初期,教育發展極不平衡,女子學校數量有限,能接受教育的女子比例極小,這造成女子文盲比例大、素質低,從而阻礙了國家發展。為了促進教育平等,達到教育普及的目的,蔡元培主張大力開展社會教育。他認為“必有極廣之社會教育,而后無人不可以受教育,乃可謂教育普及”[19]。1919年在杜威的民主主義教育思潮的影響下,國民教育促進團在上海成立。主張“培養國民道德、愛國精神,實施通俗教育代以學校教育”[20]。由此平民教育引起社會重視,在此背景下女子社會教育也得到大力發展。向警予批判了以前平民教育的籠統性,認為要特地推行“女子平民教育”,即將女子平民教育從籠統的平民教育中劃分出來以保證女子受教育的權利。她在《平民教育中劃分女子平民教育之我見》中指出:“所謂平民教育運動,平民一字的意義,當然包含占平民半數的婦女在內”[21]。在此呼吁下,女界聯合會、平民女校、女工傳習所等各種女子平民教育機構和團體紛紛成立,從而將成人女子社會教育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其發展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教育目的多元。民國初期成人女子社會教育得到廣泛關注,在不同思潮的影響下,成人女子社會教育的目的呈現出多樣化。以胡適等為代表的一部分知識分子認為成人女子社會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女子獨立自主。胡適指出,“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種能自由、能獨立之女子”[22]。他重視培養女子的“自立”精神,讓女子成為獨立的“人”,即成人女子能脫離家庭和丈夫的束縛做到思想獨立和經濟獨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主義者則認為成人女子社會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婦女革命干部,如其創辦的婦女工讀學校就是要求學生半工半讀,在解決生活問題的同時接受革命思想教育。另一部分以晏陽初為代表的平民教育派懷著“教育救國”的宗旨,把成人女子社會教育作為促進社會改良的工具。晏陽初抱著“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儒家思想,提出“人民是國家的根本,要建國,先要建民,要強國,先要強民,要富國,先要富民”[23]。認為到鄉村中去為農民辦教育關系到本固邦寧的根本問題。因此,他在鄉村創辦了男女高級平民學校及生計巡回學校等專為失學成年男女補習,以攻克農民愚、窮、弱、私等問題讓農民擺脫貧困落后進而達到興復農村、拯救國家的目的。教育與政治總是相互影響的。總的來說,這一時期的成人女子社會教育目的更多的是體現了建國初期不同派別對國家發展和走向的期望以及實現目標的方法,具體有很強的政治性。
第二,教育內容開始變得豐富。清末民初的成人女子社會教育內容主要限于識字,民國以后,在各種教育思潮的影響下,成人女子社會教育內容開始變得豐富多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學科設置多樣化。如上海平民女校“高級班設有國文、數學、英語、經濟學、教育學、社會學、理化、講演等課程”[24],學科的多樣化促進女性的全面發展[25];第二,重視女子生計教育。如天津女界組織的義務平民女校開設了婦女識字班,教育內容包括掃除婦女文盲和授以簡單的手工藝,以幫助女性獲得謀生能力。再如1919年在北京成立的女子工讀互助團。“要求學員每日學習四小時、工作四小時,工作主要從事織襪、小工藝品(制墨水、信箋、信封、帽子等)、縫紉、刺繡、販賣書籍”[26],以期能通過自身努力而達到經濟獨立;第三,加強女子的思想教育。為了加強婦女的思想教育促進其思想解放,知識女性組織了各種婦女團體,主要包括教育研究團體、促進男女平權團體、爭取女子參政權團體等。這些婦女團體在推進女子教育發展,宣傳男女平等思想,普及女子學識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并定期舉行講演通過對婦女日常生活問題進行討論,進而提高其對自身價值的認識,從而轉變思想。除此之外,一些報刊雜志如《婦女雜志》、《新婦女》、《婦女聲》等為宣傳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等做出了巨大貢獻。
這一時期的成人女子社會教育內容雖然開始變得豐富,但識字仍是其教育的主要內容,生計教育、思想教育、科學教育僅僅是掃盲教育的衍生物,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雖然這是根據當時國情制定的,但要成人女子獲得自身解放、取得男女平等僅依靠識字教育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讓識字教育、生計教育、思想教育、科學教育齊頭并進。識字教育是基礎,有了一定文化知識的保障才能更好的追求自我解放;生計教育是前提,女子獨立的關鍵是經濟獨立,只有經濟獨立、自力更生才能真正脫離父權、夫權的束縛;思想教育是關鍵,只有思想上的解放才能帶動行動上的解放;科學教育是升華,是女子突破自身束縛獲取新人生的武器。
綜上所述,民國初期的成人女子教育得到了較大發展:教育宗旨開始突破“賢妻良母觀”而更加強調女性的自立自強和社會價值;成人女子職業教育得到一定發展,開始走向平民化和更加重視女子個性的發展;成人女子留學教育逐漸興起并逐漸規范化;成人女子社會教育得到較大發展,教育目的多元,辦學形式多樣、教學內容豐富。雖然從總體上看當時社會對成人女子教育仍不夠重視,且在成人女子教育宗旨、成人女子職業教育、留學及社會教育等方面都還存在不少問題,但這畢竟是一個好的開端,也為以后的成人女子教育發展打下了必要的基礎。
[1]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孫中山全集:第二卷[C].北京:中華書局,1982∶357.
[2]楊伯峻譯注.孟子譯注(上)[M].北京:中華書局,1960∶140-141.
[3][22]熊賢君.中國女子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189∶299.
[4]姜偉堂,劉寧元.北京婦女報刊考 1905-1949[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618.
[5][16][20][25][26]杜學元.中國女子教育通史[M].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1995∶494∶476∶478∶479∶480.
[6]胡適.美國的婦人,新青年(第 5 卷第 3 號)[J].上海:群益書社,1918(9).
[7]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教育[G].江蘇: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第1版,1991∶16-17.
[8]陶行知.陶行知全集卷一[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257.
[9]黃炎培.黃炎培教育文選[M].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154.
[10][11]居鑫,童福勇,張守智.中國近代教育史匯編—實業教育師范教育[G].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200.
[12]宋學勤.簡論蔡元培職業教育思想[J].河北職業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01(5).
[13]張承蔭.論北京宜速設立女子高等師范學校之必要.都市教育[J].1915(21).
[14]劉真,王煥琛.留學教育——中國留學教育史料.第三冊[M].臺北國立編譯館,1980∶1045.
[15]留美中國學生小史.東方雜志第14卷12號[J].北京:商務印書管,1917.
[16][20][25][26]杜學元.中國女子教育通史[M].貴陽:貴州教育出版史,1995∶476∶478∶479∶480.
[17][18]黃新憲.中國留學教育的歷史反思[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163∶170.
[19]北京大學新潮社編.蔡孑民先生言行錄(上)[M].北京:新潮社,1920∶24.
[21]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253—254.
[23]姜榮耀.試論晏陽初平民教育思想的特點[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1995(1).
[24]李寧寧.民國時期女子社會教育發展歷程研究[D].陜西師范大學,2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