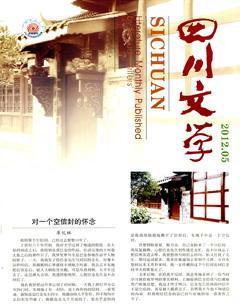母親的結(jié)繩記事
袁立生
一個(gè)夏日之夜
具體年月,我已記不清了。只記得那是“文革”中期,全國(guó)“派別”林立,“武斗”不斷。
那是一個(gè)夏日的夜晚,月明星稀。母親把我從睡夢(mèng)中搖醒,說(shuō),“幺兒,快起來(lái),來(lái)了幾個(gè)叔叔,要給你換個(gè)鋪位”。
借著昏黃的油燈,我清楚地看見(jiàn)家里來(lái)了四五個(gè)陌生人。其中一個(gè)是傷員,已躺在母親鋪好的地鋪上,頭、腳和腿上都纏著白色的繃帶,有的地方還浸著血。旁邊是一副擔(dān)架,分明是抬那個(gè)傷員用的;另外幾個(gè)人已圍坐在桌旁,正在吃著母親煮出的飯菜,狼吞虎咽的。
母親小心翼翼地解開(kāi)傷員腳上的繃帶,敷了點(diǎn)什么藥水后,又重新輕輕包上。母親把他慢慢扶起,拿過(guò)枕頭墊在他的背后,讓他靠著坐定。隨即,母親端來(lái)一碗飯菜,用勺子慢慢喂到他嘴里。
母親做的是干飯,用南瓜墊的底,菜是青菜,和了臘肉炒的,后來(lái)還上了湯。這樣好的飯菜,在那個(gè)年月,我們家除了過(guò)年時(shí)節(jié),平日里是斷然吃不上的。
母親把剩下的一點(diǎn)點(diǎn)飯菜,連同鍋巴,端給我,用非常輕微的聲音對(duì)我說(shuō):“幺兒乖,快吃,吃了就睡。”
母親又鋪了一個(gè)地鋪。母親安排兩個(gè)叔叔睡到床上,我睡在剛鋪的地鋪邊,中間是另兩個(gè)叔叔。小孩的瞌睡總是很香很甜。但那一晚,我分明感覺(jué)到自己的身體始終被壓著,動(dòng)蕩不得,周身骨頭都是疼的。
迷迷糊糊中,我感覺(jué)母親又起床了。
一陣斷斷續(xù)續(xù)細(xì)微的說(shuō)話聲之后,有一陣小小的響動(dòng),之后,一切又很快恢復(fù)了寧?kù)o。
最后的響聲,是母親在關(guān)后院的門(mén)。
不知何時(shí),我睜開(kāi)雙眼,天已大亮。我發(fā)現(xiàn)自己依然還是睡在床上。瞧瞧地面,什么地鋪、擔(dān)架、叔叔,全都沒(méi)有了,全都消失得無(wú)影無(wú)蹤了。昨晚的事,像是一個(gè)夢(mèng)。
屋內(nèi),除了幾束陽(yáng)光斜斜地射進(jìn)來(lái),一切都是寂靜。
母親,早已外出勞動(dòng)了。
母親 · 地主婆 · 羅嬸
距我們家院子約500米遠(yuǎn)處,住著一個(gè)地主婆。
這地主婆很老了,據(jù)說(shuō)其丈夫是解放時(shí)被人民政府槍決了的。在我兒時(shí)的記憶里,她差不多都是閉門(mén)不出,只偶爾從門(mén)縫里露出半個(gè)臉來(lái),極少的時(shí)候,弓著背在門(mén)口蠕動(dòng)——遠(yuǎn)觀像一個(gè)蟲(chóng)子,近看像一個(gè)鬼影。這時(shí),如果碰巧被我們一群玩耍中的孩子撞見(jiàn)了,我們立即被嚇得四下里逃竄。
但我多次看見(jiàn):母親給她送飯去,給她捉虱子,幫她洗被褥……
我們姓袁,老祖宗是袁家山的,從爺爺這一輩開(kāi)始才搬到了高家方的。
袁家山和高家方,相距六七里路程,中間隔著一個(gè)不大不小的山梁。
袁家山有一個(gè)女人,姓羅,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我也從未見(jiàn)過(guò),母親只說(shuō)我該稱她為羅嬸。這個(gè)羅嬸得了一種怪病:四肢無(wú)力,終年昏睡。開(kāi)始睡在床上,由于怕冷,后來(lái)就干脆睡到了柜子里,屎尿都在柜子里拉,吃喝則全靠著別人可憐,給一點(diǎn)吃一點(diǎn)。
對(duì)于羅嬸的病,有不同的說(shuō)法。傾向性的是:她本沒(méi)有病,只是不想干活,好吃懶做,久而久之就成了病,故稱為“懶病”。
正因?yàn)橛羞@樣的看法,所以那羅嬸就很難獲得別人的同情和照顧,包括她的家人和親戚。
母親是怎么看待她的病的呢?我不知道。因?yàn)槲覐奈绰?tīng)母親評(píng)說(shuō)過(guò)。在我有印象的時(shí)候,羅嬸的病已經(jīng)很重了,已經(jīng)睡在柜子里了。
羅嬸的丈夫早就死了;她有個(gè)兒子(1994年左右,聽(tīng)說(shuō)患同樣的病也死了),中專畢業(yè),在外省工作,也許覺(jué)得羅嬸這個(gè)母親有失他的臉面,所以別說(shuō)管,終年也問(wèn)都不問(wèn)一句;同院里,也還住著她丈夫的哥哥嫂子一家人;同一個(gè)生產(chǎn)隊(duì)里還有她自己的親妹妹。聽(tīng)母親說(shuō),開(kāi)始這兩家人還給點(diǎn)吃的,后來(lái)大概也嫌她太臟,言語(yǔ)又招人恨,終于也不管了。
大家都不管,怎么辦呢?我母親竟去了。
常常,早晨、中午或是晚上,母親從外干活回來(lái),做好飯,給我們留下一句話:“飯都好了,在鍋里,等你爹回來(lái),你們就先吃,別管我,我去看看你們羅嬸。”說(shuō)完,母親就取出預(yù)先準(zhǔn)備好的物品,提著一個(gè)口袋或是背著一個(gè)背篼,迅速走向那道山梁。
母親的腳步急促而堅(jiān)定。
我曾許多次目睹過(guò)母親離去的背影……
母親的背影越來(lái)越小,越來(lái)越小,不多大一會(huì)兒,就跟那山梁上的幾棵樹(shù)融為一體,難于分辨,幾閃,忽的就不見(jiàn)了……
母親說(shuō)是去“看”羅嬸。其實(shí),哪是一個(gè)“看”字就能了結(jié)的?實(shí)際上,母親是要完成兩件事:一是要把羅嬸拉了屎尿的床單(準(zhǔn)確地說(shuō)是柜單)和被子拆下來(lái)洗了并換上干凈的;二是要給她送去幾天的食物。由于她不能起身,母親就做了餅子,切成塊狀,穿上線線,一塊一塊的掛在柜子里,她餓了,就伸手去取來(lái)吃。后來(lái),羅嬸手也伸不動(dòng)了,母親就掛在她的脖子上。
一次,母親去“看”羅嬸回來(lái),母親惡心得吃不下飯。母親對(duì)父親說(shuō),她推門(mén)就是一股惡臭沖了出來(lái),像一股浪,直把母親沖得踉踉蹌蹌倒退了好幾步,母親當(dāng)時(shí)就嘔吐不止。
父親勸母親以后不要再去了,可母親卻對(duì)父親說(shuō):“遭孽哦。我不去又怎么辦呢?我以后去勤一點(diǎn)就是了。”
后來(lái),羅嬸死了。后事也是母親去料理的。
母親把羅嬸連同她睡的柜子,一把火,燒了!母親說(shuō):
“燒了,一來(lái)干凈;二來(lái)她活著時(shí)總覺(jué)得冷,死了,讓她熱個(gè)夠。”
一只白鴿
1970年初春,一個(gè)夜幕降臨的時(shí)候。我們家飛來(lái)了一只鴿子,白色的。
我們那里的說(shuō)法是:豬來(lái)窮,狗來(lái)富,鳥(niǎo)兒飛來(lái)是禍。因此,許多人都勸母親把這只鴿子趕走。可母親不管這些,收留了它。
母親還特意叫父親給它編了個(gè)籠子。
對(duì)于年幼的我而言,有一只鳥(niǎo)兒,自然是愛(ài)不釋手。
養(yǎng)了沒(méi)幾天,母親卻叫我把它放出來(lái)。母親說(shuō):“籠子小,它在里面不自由。”我說(shuō):“媽媽,放出來(lái),它不就飛了么?”我哪里舍得讓它飛走呢?
母親卻說(shuō):“幺兒,飛來(lái)是它自愿的。放出來(lái),它想走就走,想留就留,別強(qiáng)它之難。說(shuō)不準(zhǔn),它還不愿走哩。”
我覺(jué)得母親說(shuō)的有道理,于是就同意放了。
一放,那鴿子就一飛沖天,直入云端。
我想,完了。
哪知,那鴿子在天空穿過(guò)幾個(gè)云朵,越過(guò)幾個(gè)山頭,遠(yuǎn)遠(yuǎn)地翱翔了一個(gè)大圈后,幾個(gè)盤(pán)旋,又滑落了下來(lái)。
滑落下來(lái),還穩(wěn)穩(wěn)地就歇在了母親的肩上。
從此,那只鴿子就跟母親形影不離。除了偶爾去天空練練翅膀或是玩玩風(fēng)雨外,整日里都圍著母親飛前飛后。
遇著母親在家里做針線活兒,它就依偎在母親腳跟前或是其他地方,偏著個(gè)腦殼,眼亮亮地看著母親。
有好幾次,母親趕集,它也跟著去。
第一次,母親把它往回趕,母親對(duì)它說(shuō):“你不能去。去了,那么多人,你認(rèn)得么?如果別人逮了你或是傷了你,怎么辦?”
可當(dāng)母親走了好長(zhǎng)一段路程后,它又跟了去,而且還歇在了母親的前頭,它等著母親,仿佛它倒成了主人,母親成了隨從似的。
母親也直覺(jué)得這鴿子好笑而可愛(ài),拿它沒(méi)辦法,只好讓它跟著了。
那鴿子還真的聰明。到了集鎮(zhèn)上,母親在街上人群中走,它就在房檐上飛,母親走哪,它就飛哪,一一對(duì)應(yīng)。遇著母親進(jìn)店子買(mǎi)東西,它就在那房檐上等待。
一次意外,這只鴿子,死了。
母親用一塊白布,把它裹了。
母親把它埋在了一個(gè)高高的山頭,母親說(shuō):“讓它飛……”
寫(xiě)在懸崖上的標(biāo)語(yǔ)
父親對(duì)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很是不滿。因?yàn)椤拔母铩辈粌H使父親挨了批、遭了斗,吃盡了苦頭,受盡了侮辱,更重要的是紅衛(wèi)兵把父親心愛(ài)的一柜子的書(shū)全部背去燒了。
紅衛(wèi)兵來(lái)搜書(shū)的時(shí)候,父親不在家。慌亂中,母親只把一部《西游記》和《四書(shū)五經(jīng)》埋在苞谷柜里藏了下來(lái),其余的全被紅衛(wèi)兵背去燒了。
由此,父親特別反感“毛主席萬(wàn)歲”這個(gè)口號(hào),父親說(shuō):“人,是不可能萬(wàn)歲的!”
在一旁做活兒的母親,顯然理解父親的苦悶和不滿,只輕輕對(duì)父親說(shuō):“小聲點(diǎn),小聲點(diǎn)。”
父親是個(gè)讀書(shū)人,寫(xiě)得一筆好字。我們那個(gè)隊(duì)的所有標(biāo)語(yǔ)口號(hào),包括“文革”中的“毛主席語(yǔ)錄碑”都是父親寫(xiě)的。
一次,生產(chǎn)隊(duì)長(zhǎng)又給父親一個(gè)寫(xiě)標(biāo)語(yǔ)的任務(wù),地點(diǎn):西山坡上的一個(gè)絕崖石壁上;內(nèi)容:“毛主席萬(wàn)歲!”。
父親對(duì)寫(xiě)“毛主席語(yǔ)錄碑”還是樂(lè)意的,因?yàn)樗X(jué)得毛主席說(shuō)的話終究還是對(duì)的。但要他寫(xiě)“毛主席萬(wàn)歲”這個(gè)口號(hào),他就不愿意了。其次,那個(gè)石壁雖然非常適合寫(xiě)標(biāo)語(yǔ),但那絕崖陡峭直立,有二十五六米多高,下無(wú)攀援之路,上無(wú)落腳之坎,怎么去寫(xiě)呢?可父親迫于當(dāng)時(shí)的政治氣候,也不敢當(dāng)面拒絕。
回到家里,父親就把這個(gè)事和自己的不樂(lè)意說(shuō)給了母親。
母親略加思索后,對(duì)父親說(shuō):“是好事,去寫(xiě)吧。”
父親一臉的疑惑。母親又對(duì)父親說(shuō):“放心,我自有辦法,我給你當(dāng)助手。而且,保準(zhǔn)你寫(xiě)了都還想寫(xiě)。”父親聽(tīng)母親這么一說(shuō),知道母親心中一定有了好主意,所以也就高高興興地答應(yīng)了。
沒(méi)有那么高的梯子,母親就想到了用繩子往下吊。母親同父親一起,用稻草加上竹條,打了一條又粗又長(zhǎng)的繩子。
母親給父親做了一支筆,一支大筆,像掃帚那么大。
秋日的陽(yáng)光,溫暖而明亮。
西山坡,在陽(yáng)光的照射下也是層林盡染,楓葉紅透。
在那高高的石壁上,父親,就像是吊掛在一根蛛絲上的蜘蛛——只不過(guò),這“蛛絲”的另一頭是繞過(guò)一棵大樹(shù)后緊緊握在母親手上的——
“我可以寫(xiě)了,寫(xiě)啥子?”父親問(wèn)母親。
“說(shuō)啥子?大聲點(diǎn),聽(tīng)不見(jiàn)。”母親故意裝做聽(tīng)不見(jiàn),母親是要逗弄一下父親,母親笑出了聲。
“別開(kāi)玩笑了,快說(shuō),寫(xiě)啥子?”父親可不想逗了。
“就寫(xiě):人、民、萬(wàn)、歲 ”——母親說(shuō)。
父親一聽(tīng),一股熱浪涌上心頭!他無(wú)法不感嘆母親的智慧和高明!
“你真聰明!我怎么就沒(méi)有想到呢?”父親贊美著母親。
“少?gòu)U話,快寫(xiě)。否則,我就松繩子了。”母親還在逗弄父親。
父親高興勁一上來(lái),揮舞手中的大筆,撇、捺、橫折、橫……
人民萬(wàn)歲!
幾個(gè)金光閃閃的顏體大字就浸立在了那面石巖上了!遠(yuǎn)遠(yuǎn)的,三五公里以外,都可看見(jiàn)!
1980年我讀大學(xué)回家,都還看見(jiàn)那幅標(biāo)語(yǔ)。只可惜,后來(lái)因?yàn)猷l(xiāng)親們開(kāi)采石料給破壞了。
母親聽(tīng)書(shū)
一個(gè)大熱天的正午,整個(gè)村莊都浸泡在滾滾的熱浪和一片蟬鳴聲中。
我們家的前屋,門(mén)大開(kāi)著,風(fēng)正好可以穿堂而過(guò)。母親端坐在一個(gè)小凳上,靠著墻壁,手里做著針線活兒。父親盤(pán)腿席地而坐,坐在母親的腳跟前,面對(duì)著母親。父親沒(méi)穿衣服,光著背。一本書(shū),就放在母親的膝蓋上。父親正在給母親讀《西游記》哩。
母親一邊聽(tīng)著父親給她讀《西游記》,一邊依舊忙著自己手中的活兒,偶爾還向父親提出一點(diǎn)疑問(wèn)或是發(fā)出感嘆。
一章或是一回讀完了,父親故意考母親的記性。哪知,母親不僅能準(zhǔn)確說(shuō)出故事的情節(jié),而且還能整段整段地原文背誦,包括那吳承恩的詩(shī)句,母親都能一字不漏地背出來(lái)。
父親跟母親進(jìn)行交流,母親居然還能說(shuō)出一些道道來(lái)。
母親雖沒(méi)有上過(guò)學(xué)、不識(shí)字,但母親對(duì)文學(xué)作品的記憶和理解力,讓中師文化程度的父親常常自嘆不如。
父親是一個(gè)中師生,解放初先后在廣元的昭化和劍閣縣的碑埡(廟)教書(shū)。碑埡距我們家還有百多里的路程,由于那時(shí)條件太艱苦,加之有一年連續(xù)下了四十天的梅雨,父親得了痢疾,差點(diǎn)丟了性命,所以父親就不干了,自己回家跟著母親當(dāng)了農(nóng)民。雖說(shuō)是當(dāng)了農(nóng)民,但骨子里愛(ài)讀書(shū)的習(xí)性還是改不了的,尤其愛(ài)讀個(gè)《三國(guó)》、《水滸》和《西游記》之類的,加之母親又特喜歡聽(tīng)他讀,父親自然是樂(lè)此不疲了。
天不是太熱的時(shí)候,父親就在我們家房屋邊上的一個(gè)葡萄架下給母親讀書(shū)。父親坐在石凳上,母親坐在石凳上,中間是一個(gè)小石桌,正好可以供父親放書(shū)。父親讀著書(shū),這時(shí)候聽(tīng)書(shū)的就不僅僅只有母親,還有一串串的葡萄。
父親給母親讀書(shū)的時(shí)節(jié),要么是大熱天,要么是大冷天。春秋兩季,那一定是忙碌得上不沾天下不著地,哪有閑暇讀書(shū)呢? 若是大冷天,就必定有一盆火,父親、母親坐在火盆邊,母親決不會(huì)也決無(wú)可能只單單聽(tīng)父親讀書(shū),母親有做不完的活兒,或是紡線,或是納鞋,或是縫衣。
俗話說(shuō),一心不可二用。父親對(duì)母親這種聽(tīng)書(shū)、做事兩不誤的本領(lǐng)很是佩服,也很是不解。
一次,也是一個(gè)大冷的天,家里來(lái)了幾個(gè)客人。大家圍坐在火堆邊有說(shuō)有笑地?cái)[龍門(mén)陣,父親就拿“聽(tīng)書(shū)”這事給別人夸耀母親聰明,父親對(duì)母親說(shuō):“噯,你給我們大伙說(shuō)說(shuō),你是咋個(gè)做到一心二用的呢?”
母親并不正面回答父親的問(wèn)話,卻只調(diào)侃父親說(shuō):“你們男人家,就一個(gè)字,笨!我們女人,能有你們男人那么笨么?”
在場(chǎng)的人們,是一陣笑聲。
仲夏之夜 月亮升起來(lái)
母親一生不燒香,不磕頭,也不拜菩薩。母親說(shuō):“人死如燈滅。”
母親不封建,父親更是一個(gè)反封建主義的斗士。在這一點(diǎn)上,父親和母親可以說(shuō)是一拍即合。
距我們家屋后不遠(yuǎn)處的一個(gè)山坳里,有一口大池塘。
那池塘終年清澈見(jiàn)底,像是一面鏡子,水中有天,天中有云,白云朵朵,像是棉球;周?chē)L(zhǎng)滿了許多樹(shù),有柳樹(shù)、柏樹(shù)、松樹(shù)和楊槐之類的。特別的,在其入口處有兩棵古柏,樹(shù)干筆直,聳立參天,像是兩個(gè)守門(mén)的衛(wèi)士;一到仲夏時(shí)節(jié), 更是鳥(niǎo)兒弦歌,蟲(chóng)兒奏樂(lè),野花點(diǎn)點(diǎn),香氣撲鼻。
那口池塘,就是父親和母親天然的澡堂。
仲夏之夜,月亮升起來(lái)。父親和母親相互間一個(gè)媚眼,背著我們兒女,兩人就偷偷兒的溜向那口池塘了……
夢(mèng)或者是兆頭
母親的死,按封建迷信的說(shuō)法,還是有兆頭的。
1970年,萬(wàn)類霜天競(jìng)自由的時(shí)候,母親賣(mài)了一頭大肥豬,收入了五十多元錢(qián)。父親和母親帶著我和爺爺,我們四人玩了一趟“成都省”。在成都的人民照相館,我們照了像。可回家之后,照相館在寄來(lái)的信件中卻沒(méi)有照片,相館方面的解釋是照片壞了,怎么壞的沒(méi)有說(shuō),只是照價(jià)退了錢(qián)款。
這是母親生平第一次照相,居然壞了,母親自然是覺(jué)得有點(diǎn)遺憾。于是第二年的春天,母親就帶著我的小妹妹去集鎮(zhèn)上照了一張像。母親穿著一件滿大襟藍(lán)單布衣裳,留著齊肩的短發(fā),有點(diǎn)像劉海,母親的表情慈祥。妹妹把一本“紅寶書(shū)(毛主席語(yǔ)錄)”捧在胸口,是那個(gè)時(shí)代的印記。照片的背景,是一棵皂角樹(shù),樹(shù)枝上有稀稀落落的春天剛剛發(fā)出的嫩芽。
又是一個(gè)趕集天,風(fēng)和日麗的。母親算著自己不久就會(huì)坐月子了,于是母親就買(mǎi)了一個(gè)保溫水瓶。
母親提著水瓶高高興興往回趕。剛走出場(chǎng)鎮(zhèn)幾百米來(lái)遠(yuǎn),就突然聽(tīng)見(jiàn)砰的一聲炸響,差點(diǎn)把母親嚇了個(gè)趔趄,待母親回過(guò)神來(lái),才發(fā)現(xiàn)是自己手中的水瓶爆了,內(nèi)膽玻璃碎片散落了一地,手中只剩下一個(gè)空空的殼。母親只覺(jué)得好生奇怪,心想是不是自己提著瓶子摔動(dòng)不小心碰著哪兒了,但母親看看瓶殼卻沒(méi)有碰撞的痕跡,而母親此時(shí)正行走在平直的路上,周?chē)矡o(wú)障礙物之類的東西。母親就想,這一定是自己蓋瓶塞子時(shí)塞得太緊了,以至于里面的空氣膨脹,所以爆了。
一生不相信封建迷信只相信科學(xué)的母親,顯然認(rèn)為自己的解釋是正確的。
又過(guò)了幾日,母親做了一個(gè)夢(mèng):
母親和那只白鴿(前文中提過(guò)的)一起去趕集。走著走著,前面就沒(méi)有了路,母親正躊躇時(shí),那鴿子飛了來(lái),它說(shuō)它要馱著母親飛過(guò)去,母親覺(jué)得有趣,就說(shuō)那馱吧。于是那鴿子就帶著母親飛,越飛越高,越飛越高,后來(lái)竟在云中穿行,不知何時(shí),那鴿子也幻化成了一朵祥云。母親腳踩祥云,身披佛光。不知不覺(jué)中,就到了一個(gè)像是仙界的地方。湖光瀲滟,云蒸霞蔚。只見(jiàn)得:亭臺(tái)雕梁,樓角畫(huà)棟;奇花吐笑,異草展容……
遠(yuǎn)遠(yuǎn)地,還有兩個(gè)仙女姍姍而來(lái),說(shuō)是來(lái)侍候母親的。
待兩個(gè)仙女靠近母親欲帶母親走時(shí),母親這才猛然想起,自己今天是來(lái)趕集的,怎么卻到了這兒呢?
母親一急,夢(mèng)就醒了。
一個(gè)多月之后,即公元1971年農(nóng)歷潤(rùn)5月25日凌晨時(shí)分,母親由于產(chǎn)后大出血與世長(zhǎng)辭了……
母親,姓高名蓮青,字淑貞,小名春爾,享年44 歲。
責(zé)任編輯 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