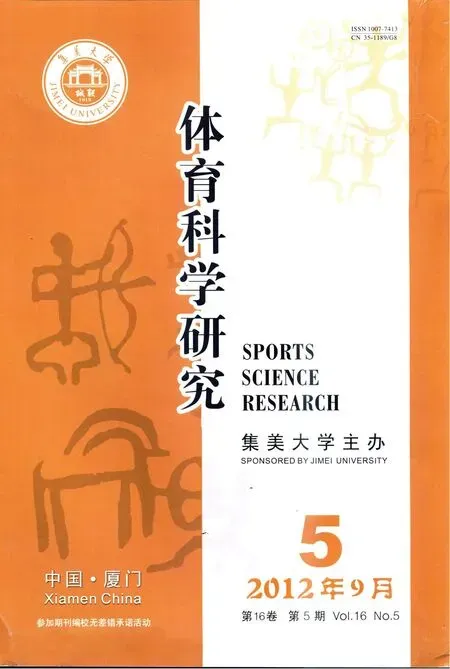美國、澳大利亞、南非、日本體育立法比較研究
程 蕉,袁古潔
(華南師范大學體育科學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1)
1995年頒布新中國第一部體育法頒布至今已經過去的17年里,中國體育法制化的道路仍在不斷發展中。要解決近年來體育體制轉軌時期不斷出現的新的體育改革問題,中國的體育法制化程度還遠遠不夠。因此,對其他國家體育立法的各個方面進行歷史分析和因素分析,比較不同國家體育法制化過程中形成的經驗和問題,有利于促進我國體育立法的進程。
國內對國外體育立法的研究成果不多,多為國別研究或者問題研究。本文綜合對比不同類型的國家體育立法特征,更能全面反觀對我國體育立法的現狀,望能對推進改革有所助益。本文在選擇研究對象上綜合考慮地域差異、經濟和體育發展程度差異、法系類別差異等因素,主張選擇有差異性的代表國家的體育立法為研究對象,最終選取美國、澳大利亞、南非、日本四個國家作為研究的對象,從各個國家體育立法的緣起、體育立法法系、體育管理體制對體育立法影響、體育“基本法”四個方面進行比較分析。
1 體育立法的緣起比較
縱觀美國、澳大利亞、南非、日本四國體育立法的歷史,比較其立法的緣起,從立法的內在動機和法制化道路來分析,四個國家的體育立法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社會演進型體育立法:是指一國的體育立法規制主要建立于社會發展綜合因素影響下體育發展的內在規律,為解決和規范體育發展中遇到的實際問題而產生相關法律依據。二是政府推進型體育立法:主要是指在一國體育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的基礎上,借助于政府的政策導向和主觀意向,通過移植和借鑒別國體育立法經驗的方式,逐步建立該國的體育立法體系。在本文的研究對象中,澳大利亞和美國體育立法屬于前者,南非和日本體育立法屬于后者。
1.1 社會演進型體育立法:美國、澳大利亞
美國的體育立法是隨著競技體育、群眾體育、體育市場的發展而逐步建立起來的。20世紀初,針對體育產業發展中的問題,美國開始了體育立法工作。最早出現法律糾紛并引起訴訟的運動項目是棒球。美國體育產業發展中的法律糾紛基本上都是圍繞著有關合同法、反托拉斯法和勞工法等問題展開的,并以經濟糾紛或刑事訴訟的程序來處理,而沒有用“體育法”來界定。[1]1950年9月21日,美國國會正式頒布了《奧林匹克協會組織法》,此后又進行了一些包括體育內容的公共立法和專門的體育立法,并相應地出現了系統化的體育法研究。[2]雖然美國體育單行法出現時間較晚,但是美國的體育立法一開始就是遵循著體育市場的發生發展內在規律而相應地產生和發展。
澳大利亞的體育立法也是隨著體育的自然發展而逐漸產生。20世紀初澳大利亞的經濟發展穩定,體育也得到穩步發展,尤其是1939年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成立后,拳擊和賽馬獲得高度商業化發展,足球、聯盟橄欖球、網球吸引了大量觀眾,高爾夫、橄欖球俱樂部等則吸引了很多參與者,擔起救援職責的沖浪運動協會興起,板球運動鞏固了其作為全國性運動的地位。在俱樂部和體育協會及其他體育市場蓬勃發展的基礎上,澳大利亞的體育立法活動開始起步。澳大利亞早期的體育立法主要集中在下列領域:1)地方政府的基礎設施。如1931年南澳大利亞州頒布《娛樂場地(規章)法》,促使總督制定娛樂場地管理及附帶目的相關條例。1933年維多利亞省頒布《墨爾本板球場法》,對墨爾本板球場進行立法管制。2)全民健身立法。二戰期間為了迎合當時“全民健身”的主導思想,澳大利亞政府1941年通過《全民健身法》。3)20世紀60年代,各州開始關注體育協會、體育俱樂部的規范性問題。如1967年新南威爾士州頒布《紐卡斯爾國際體育中心法》。1964年塔斯馬尼亞州頒布了《協會成立法團法》,該法規定了某些體育協會成立法團的條件及成立后的規定,后來各州紛紛效法,相繼頒布了各州的《協會成立法團法》。
美國和澳大利亞都是社會演進型體育立法國家,不論是聯邦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積極推動體育立法的發展,但是這種立法推動不是以政府的主觀導向為立法的出發點,而是充分考慮體育本身發展帶來的立法需求,進而及時地通過立法推動該國體育的積極發展。
1.2 政府推進型體育立法:南非、日本
日本政府對體育立法的推進始于20世紀中葉。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社會娛樂活動也隨之轉向軍事化目的。緊接著大戰結束,新的體育規劃需要產生。在這種情況下,政府于1949年建立國民娛樂活動協會,同年頒發了《社會教育法令》,以促進失學青年和成人的教育、運動競賽、以及娛樂活動。又于1958年修建國家體育場。到1961年頒發《體育振興法》,運動競賽的復活達到頂點。[3]隨著60年代后的日本經濟迅速崛起,成為亞洲“四小龍”中最早騰飛的國家,借1964年奧運會之機體育也在亞洲地域內呈現出龍首的姿態。日本的體育立法自此開始繁榮發展。由此可見,為軍事服務培養后備人才就成為早期日本體育立法的重要動機。
南非體育立法的歷史比較短暫,在1964至1992年間南非因國內嚴重的種族歧視而導致被各種國際體育賽事拒之門外,包括奧林匹克運動會、國際足聯的比賽。經歷了多年的封閉后,南非開始逐步撤銷種族歧視的相關法律,1992年南非重新恢復巴塞羅南奧運會的資格。[4]1993年11月,以“體育前景”(Vision for Sport)為主題的全國會議的召開奠定了南非體育未來發展的里程碑。會議上提出的幾項計劃為大眾體育和競技體育的發展打下了基礎。[5]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南非體育立法啟動。1996年南非新憲法的通過為體育立法提供了憲法基礎,特別是其中的權利法案使運動員獲得了廣泛平等地參與體育的權利。自此,體育立法開始從多個方面關注體育的管理和發展問題。
雖然都是政府推動型體育立法,但是日本和南非政府推動體育立法的目的有所不同。日本體育立法承載著軍事化、娛樂化、競技化的不同歷史階段的體育發展使命。南非體育立法則承載著恢復南非的國際交往和推動經濟建設的體育發展使命。
2 體育立法法系比較
從體育立法法系來看,主要分為成文法和判例法兩種類型。成文法是指經過立法機關按照一定程序制定并頒布的法律,具有較精確的條文化形式。判例法是產生于法官的判決,也構成司法判決的法律基礎。這四個國家體育立法類型分為以下兩種:
2.1 美、澳、日體育立法:成文法和判例法并存
美國的體育法規條例要求完全以憲法為依據,根據制定法和判例法的有關條款和程序實施裁決。美國體育法規條例主要由聯邦和州立法機關制定。除了成文法外,另外一部分是由法院判例形成的,成為體育的重要原則。[6]歐洲殖民者給澳大利亞帶來了英國的普通法,澳大利亞因此成為普通法國家之一。澳大利亞是英國普通法影響下的法系國家,因此在體育的法律中,也是成文法和判例法并存的國家。
日本法在其發展的不同歷史時期,移植和吸收了許多外來法律。封建時期以中國隋唐法律為基礎,明治維新后又先后以法國法和德國法為模式,二戰后英美法系對日本法的影響不斷加深,使當代日本法成為兼有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特征的“混合法”。[7]由于這個淵源,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在日本都得到相當的重視。當代日本體育立法已經形成了自身比較完善的成文法體系,同時日本的體育法學者也在不斷加強對判例的研究,出版了《體育事故判例總匯》等書。[8]
2.2 南非體育立法:單行成文法
幾個世紀以來,在南非占統治地位的是歐洲移民帶來的法律,先有羅馬—荷蘭法,后有英國普通法,二者相互競爭,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今天南非別具特色的混合型法律制度。[9]但在體育法律制度方面,南非更多的體現為成文立法,特別是在1994年正式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后。1996年通過的新憲法確立了國民議會是南非的最高立法機關,國民議會成為南非體育法的主要制定者。因此,成文立法成為目前南非體育法的主要淵源。
綜上所述,四個國家都有體育成文立法,只是南非體育領域僅僅為成文法。另外,審視四個國家的體育成文法,也有不同特點:1)體育成文法以單行法為主。澳大利亞、南非、日本這都是以體育單行成文法為主的國家。2)體育成文法由兩部分組成:體育單行法和涉及體育問題的部門法,前者為后者的補充。美國的體育成文立法很大一部分都是在部門法律中以條文的形式存在,也有針對特殊體育問題頒布的體育單行成文法。例如:在美國,體育合同的起草、終止合同以及終止合同的辯護和救濟都按照《合同法》的規定執行。在體育經紀的管理上,美國既有實行了幾百年的《經紀法》,規定體育經紀要履行忠誠、照顧、核算、扮演委托人監護人的角色等常規的法律職責。美國也有2000年全國體育委員會總干事會議通過的《統一體育經紀法》,對體育經紀的一些特殊內容進行規制。
3 體育管理體制對體育立法影響的比較
澳、美、南、日四個國家的體育管理體制可分為“政府分權型”和“政府管理型”兩種類型。
3.1 澳大利亞和美國:政府分權型體育管理體制對體育立法的影響
政府分權型體育管理體制下的立法活動表現為:一國的聯邦或中央政府參與宏觀體育立法、政策調控,同時州或省負責各州各省的具體體育立法和體育管理。各州或省在聯邦或中央政府重要立法基礎上制定各自的政策法規,并根據本州或省的體育發展自身特點制定本州或省的特殊體育立法。這種類型的代表國家為澳大利亞和美國。
從1994年起,澳大利亞環境、體育與國土資源部保留對1989年頒布的《澳大利亞體育委員會法》進行調整以及任命澳大利亞體育委員會董事會和澳大利亞反興奮劑總署董事會的權力,其余職能全部移交給澳大利亞體育委員會。作為澳大利亞最重要的體育管理結構,澳大利亞體育委員會采用董事會制,下設7個部門。其中最重要的是設立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亞體育學院,該學院配備了高水平的教練員、世界水平的體育設施和科研機構,為澳大利亞培養高水平運動員是其主要任務。澳大利亞體育聯合會和澳大利亞奧委會是澳大利亞最重要的體育社團組織,但它們在體育管理中的權力與作用遠不如其他西方發達國家。澳大利亞體育聯合會的作用主要是向政府提出體育發展的建議,并在議員和政府機構中游說,為澳大利亞體育組織爭取更多的利益與發展空間。同時,澳大利亞體育聯合會主要與澳大利亞體育委會員合作,承擔其委托的一些具體工作。由于澳大利亞行政管理體制采用聯邦制,因此各州政府體育管理機構不受轄于聯邦政府。盡管名稱不同,但澳大利亞各州政府均設立體育與休閑管理機構。[10]
上述澳大利亞的這種體育管理體制對體育立法產生了三個方面的影響:
1)聯邦政府不同執政黨派的政策導向對體育立法的影響重大。澳大利亞工黨和自由黨由于立場不同,分別代表了不同階層的利益,因此在體育政策、法規的制定上對體育的重視程度不同,尤其體現在對體育的撥款問題上,這直接導致了20世紀澳大利亞競技體育和大眾體育的政策重點不斷搖擺。以1972年至1996年澳大利亞體育進入摸索和快速發展階段為例,澳大利亞的體育發展和體育立法工作即受制于幾屆政府對待體育不同態度的影響。1972年Gough Whitlam工黨政府主張對經濟和文化事業包括體育有更多的管理權。聯邦政府采納了“澳大利亞娛樂的角色、范圍和發展”報告中73條建議中的大多數,增加了經費投入,并支持地方政府建立休閑中心。隨后,維多利亞州率先于1972年頒布了《體育和娛樂法》,1974年聯邦頒布了旨在促進競爭、貿易公平、保護消費者權益相關內容的《貿易實務法》,1975年聯邦頒布了反對種族歧視包括體育運動歧視的《種族歧視法案》。1975年自由黨掌權,新任首相Malcolm Fraser延續自由黨以往的觀點,認同體育應該自由發展,反對對體育的高額撥款。在Fraser自由黨上臺的前幾年,并不贊同政府對體育的高額經費支持,這引起了體育組織的抗議。迫于壓力,從1979年開始政府增加了對參加奧運會、水上項目救援、體育場館等多種體育發展項目的撥款。但是體育的發展還是受限,體育立法推進緩慢。直到1983年的政權更替,以Bob Hawke代表的工黨掌權,開始了澳大利亞體育發展黃金13年。從機構上,1985年成立了澳大利亞體育委員會(Australian Sports Commission),平衡大眾體育和競技體育成為該委員會的主要操作原則。1989年聯邦頒布了《澳大利亞體育委員會立法》,以立法的形式明確了澳大利亞體委的設立、目標、職能。從體育發展類別上,體育立法的范圍開始大范圍拓展,如從聯邦到地方一系列反對種族和性別歧視的法規頒布;在藥物濫用問題上新南威爾士州和維多利亞州都在1995分別頒布《體育藥品檢驗法》和《體育藥品檢測法》;1995年頒布增強體育教育的《體育學院法》;1992年針對煙草商對體育運動進行贊助行為規制的《聯邦煙草廣告管制法》;還有地方政府關于拳擊、運動場館等體育問題的大量立法也在這一時期展開。總體說來,20世紀70年代以來澳大利亞體育發展受執政黨影響頗大,工黨執政時期也是澳大利亞體育獲得較多撥款和關注,體育發展迅速,體育立法繁盛的時期。
2)州立法的協同性和特殊性。澳大利亞分權制的管理體制賦予了州政府體育立法的權利。20世紀中葉以來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在體育發展的大部分問題上都放權給各州,這就形成了州體育立法在極個別體育問題上響應聯邦立法,同時在各州體育發展具體問題上頒布地方特色體育立法的體育立法的格局。例如: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有代表性的立法《種族歧視法案》、《性別歧視法》、《殘疾歧視法》都影響了各州相關立法的發展。但是澳大利亞體育立法的繁榮更多依賴于州立法的繁榮。一類是各州政府普遍關注體育問題的立法如在體育協會成立法團問題上各州紛紛頒布《協會成立法團法》:1991澳大利亞首都地區、1984年新南威爾士州、2002北部地區、1981年昆士蘭州、1985年南澳大利亞州、1964年塔斯馬尼亞州、1981維多利亞州、1987西澳大利亞州。另一類是單個或者少數州關注的體育問題的立法,并非所有州都關注,也并非響應聯邦立法,以州體育立法最繁盛的維多利亞州為例,分別頒布了1933《墨爾本板球場法》、1972《體育和娛樂法》、1985《墨爾本和奧林匹克公園法》、1985《職業拳擊和武術法》、1994《墨爾本水上運動中心法》、1995《體育藥品檢測法》、2001《聯邦運動會管理法》、2002《職業拳擊和格斗體育法》、2002《體育賽事門票(公平進入)法》、2003《大型活動(人群管理)法》,這其中的多數法規都是維多利亞州地方的體育立法。
3)大眾休閑運動和高水平競技運動相關立法并重。澳大利亞市政府的市議會和鎮政府的鎮議會一般設有的綜合性的休閑委員會,在推動本地區的大眾體育發展過程中,委員會往往與州政府設立的地區辦公室密切合作。這一機構的設立和運行方式使得地方的體育管理機構以推動大眾體育發展為中心任務,而參加國際大賽的運動員選拔和訓練工作則歸屬于澳大利亞體育學院。這種體育管理類型的分工,不斷促成了20世紀以來澳大利亞體育決策及立法的兩大重點的平衡發展。
美國是聯邦制國家,政府沒有專門的體育主管部門,也沒有單一、垂直的權威機構來負責全面的體育協調工作。多個專門的社會組織和私人企業在體育運動中扮演著主要角色。這是美國體育體制最顯著的特點之一。美國國會1978年頒布《業余體育法》明確闡明,政府不介入競技體育的管理,不設置專門的體育管理機構,不進行直接的資金投入。因此,美國體育基本上不是由政府來掌管的,而是由經濟、社會和政治力量掌握,這些社會力量結合起來就產生了各種獨立的、不獨立的和半獨立的體育組織。
雖然美國聯邦政府在競技體育方面基本采取不直接介入的態度,但在大眾體育的管理方面卻承擔著重要的職能,如:美國聯邦政府成立了“體育與健身總統委員會”,這是一個負責美國大眾體育事業發展的重要的一個政府咨詢機構。此外,50個州都有“州總統健康與體育委員會”。[11]
上述體育管理體制對立法的影響體現在,首先《業余體育法》賦予了美國奧委會負責美國業余體育的管理權利,這奠定了《業余體育法》的在業余體育管理上的核心地位。其次,業余體育之外的職業體育不受《業余體育法》規制。
3.2 南非和日本:政府管理型體育管理體制對體育立法的影響
政府管理型體育管理體制下的立法活動表現為:由中央政府主導體育立法的政策和權力,通過設置專門的政府體育管理部門開展體育的管理和立法工作。這種類型的代表國家為日本和南非。
日本體協是日本業余體育界的中心組織,是全國性綜合體育團體,在道、市行政區均設地方協會,下屬單項協會40余個。日本是典型的政府管理型體育管理體制國家。這種管理體制的主要特點是由中央政府設置專門的體育管理機構,對全國的體育事業進行全面的監控和管理,在體育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以及體育資源的配置上起主導作用,事務性工作主要由社會團體承擔。政府管理型體育管理體制下,體育立法由政府決議,全國統一管理。這種管理體制對體育立法的不利影響是容易阻塞社會團體參與體育管理和立法的渠道。同時大量的事務性工作,容易削弱政府的宏觀管理職能。
在南非,由于種族歧視政策對20世紀后半期南非體育發展影響嚴重,南非體育的發展是在共和國建國后短期內發展起來的,因此南非的體育立法形成自身的獨特路徑。南非體育和娛樂部(SRSA)和南非體育委員會(SASC)共同制定體育政策、提供體育供給、促進體育和娛樂發展。SRSA負責發展實施國家體育和娛樂的政策和項目。[12]自2005年廢除南非體育委員會,體育和娛樂委員會的職能由南非體育和娛樂部(SRSA)和新成立的“南非體育聯盟和奧林匹克委員會”(SASCOC)共同承擔。SASCOC是南非所有高水平競技運動的管理主體。在這種政府管理型體育管理體制下,南非的體育立法屬于由國家統一領導的模式,各主管部門的部長在立法上享有很高的決定修改權。例如,根據1998年《國家體育和娛樂法》第14條規定“在與體育委員會磋商后,部長可以制定規章”。又如,2006年《2010國際足聯世界杯賽南非專門措施法》第9條規定“安全與保衛部部長可以就行政或者程序問題制定相應的規章”。南非體育立法的中央唯一性,有利于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
4 體育“基本法”的比較
體育的部門“基本法”是一種約定俗成的概念,是體育部門法的基礎,在其指導下,通過配套立法解決其貫徹實施問題。在這一點上,縱觀澳、美、南、日四個國家的體育“基本法”特點和經驗,對我國有借鑒參考的價值。
4.1 南非和日本:在體育“基本法”指導下展開立法
日本和南非都與我國的情況類似,賦予“基本法”核心地位。1998年《南非體育與娛樂法》作為體育“基本法”扮演了指導性的作用。在“基本法”的指引下,制定與其配套的相關體育立法,建立了比較完備的體育法律體系。南非除了《南非體育與娛樂法》這一體育基本法之外,還頒布了《體育領域反興奮劑機構法令》、《彩票法令》、《非盈利組織法令》、《體育與娛樂活動安全法令》、《拳擊法令》等一系列單行體育法,形成了一個比較齊全的體育法律體系。[13]不足之處在于體育“基本法”和憲法存在一定沖突,影響到立法的實際操作。南非1996年《憲法》申明了民主對人的尊重、平等和自由的價值。根據《憲法》第五章南非體育和娛樂部也承認“體育是各省和地方的權利”,但是“2005年《政府內部關系架構法》要求政府的三個領域必須互相協調共同制定計劃和提供服務。”由此可見,在體育和娛樂的問題上,南非的《憲法》和實際的體育娛樂管理架構存在沖突,需要做出調整。
日本1961年施行的《體育振興法》原本僅適用于業余體育,但為了實現促進體育運動事業發展的基本計劃,體育振興法進行了修改以便約束體育彩票機制。該法明確了振興日本體育的基本框架,為振興日本體育事業,成功地舉辦東京奧運會提供了法律保障,因此在日本該法相當于體育基本法的地位。
但是作為基本法,它存在下列問題:1)內容領域較狹窄,不能完全發揮體育基本法的作用。2)缺少關于國際體育交往、殘疾人體育以及法律責任等對于振興體育事業非常重要的條款。3)對競技體育的支持力度不夠。4)規定了太多的指導性、計劃性條文,且缺乏強行性致使政府并不必須履行任何的義務,以至于僅僅制定促進體育運動事業發展的基本計劃來配合體育振興法就用了38年的時間。[14]685)《體育振興法》已經頒布40多年,有些規定已經不適應目前日本體育的發展。不少學者提議修改體育振興法,盡快出臺一部日本《體育基本法》。1998年日本體育法學學會體育基本法研究委員會,已經起草并發表了《體育基本法綱要》。[15]
4.2 美國:《業余體育法》指導業余體育領域的立法
從1950年的《美國奧林匹克協會組織法》,到1978年修改為《業余體育法》,再到1998年修改為《特德?史蒂文斯奧林匹克和業余體育法》。不論如何修改,美國的體育“基本法”只能算是業余體育領域的基本法,職業體育不受其制約,而是受《反壟斷法》等法律的制約。
美國體育“基本法”《業余體育法》的不足在于賦予美國奧委會權力過大,也沒有相應的監督機制,使得其中的運作不太透明,產生了嚴重的腐敗問題。也最終導致美國幾任奧委會主要官員先后陷入腐敗的訴訟中,牽連引發許多奧委會高級官員先后辭職推出奧委會,美國奧委會2003年面臨土崩瓦解的局面。[16]33
4.3 澳大利亞:無體育“基本法”指導下的體育立法
澳大利亞雖然沒有體育“基本法”但是體育立法工作也開展得卓有成效。澳大利亞體育立法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發展,從一開始體育立法就是各州享有的權力。20世紀70年代開始澳大利亞體育立法進入繁盛時期,體育立法仍然沒有統一的體育“基本法”作為指導。盡管沒有體育“基本法”作為指導,但是在聯邦立法中,涉及在體育中禁止種族歧視、性別歧視、殘疾歧視這些體育公平的問題上,澳大利亞各州紛紛立法響應聯邦的上述法規。同時,在聯邦立法沒涉及的領域,各州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開展了更加多元化的體育立法。例如所有州都設立了《協會成立法團法》;大多數州都設立了體育藥品檢驗、體育場地場館管制相關的法規;少數州設立了《汽車運動法》、《職業拳擊和格斗體育法》、《體育中心信托法》、關于體育保險和大型活動的安全管理相關立法等。
從澳大利亞的經驗來看,雖然沒有體育“基本法”作為指導,但是各州有高度的立法自主權,有利于各州體育立法根據實際體育需求發展。澳大利亞的新南威爾士州和維多利亞州就形成體育立法的鮮明體系,成為地方體育法制化管理的代表。
5 對完善中國體育立法的借鑒
5.1 體育立法的去行政化和權力適度下放
中國的體育立法近十幾年來的發展同時受制于國際體育賽事交流的外力推動,和國內競技體育、職業體育、大眾休閑體育多重發展瓶頸的內力推動。這兩重力量推動下,要使我國的體育得到良性長遠發展,要適應和改變的地方很多,而體育法制化發展是必需的手段。但是體育立法的發展模式卻不得不受我國現代化模式的影響。
對于處于體育法制化初期的我國來說,澳大利亞、美國社會演進型的道路顯然不適合我國目前的體育發展現實,因此,我們只能走政府推進型體育立法的道路。然而,從南非和日本的體育立法存在的問題來看,政府推進型的體育立法有其優勢,容易對資源的集中調配,容易開展宏觀管理;政府推進型的體育立法也有其劣勢,就是立法的進程中,過于行政化導致立法的進程緩慢,體育法規的管理環節過于冗雜。
因此形成中國特色體育法制化道路,在中國現在的情況下,有兩條舉措:1)體育立法去行政化。行政的導向作用不可忽視,去行政化不是要完全消除行政的權利,這是不現實、也不符合我國基本國情的,而是指應減少行政的干預,讓體育法制化獲得更快發展,更好起到體育法規的規范作用。2)體育立法的權力適度下放。體育的各個領域有其自身的特點,中國現實體育環境下,如群眾體育、社區體育等具有更多地域性特征的體育領域,以及體育產業等可以在中央宏觀調控下地方性發展的體育領域,應賦予地方立法機構更大的立法權力。
5.2 體育“基本法”的定位和調整
在我國,體育“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1995年頒布至今,已經不能滿足體育的市場化、職業化、產業化和社會化帶來的體育新變革。有學者認為我國體育基本法修改的關鍵“并不在于《體育法》的規定是‘原則’還是‘具體’,而在于以《體育法》為核心的體育法體系的建立與完備。”因此,體育基本法應該從“管理法”到“服務法”,從“基本法”到“促進法”,[17]而非一部基本法就能囊括體育所有領域的所有細節。
比較四個國家的“基本法”情況,可以得出下列結論:1)體育“基本法”的有無不是體育法制化的必然因素。制定體育“基本法”并能在其指導下推進體育立法體系的發展形成才能體現“基本法”作用和價值。澳大利亞雖然沒有體育“基本法”,但是卻能在體育發展的方方面面,從聯邦到地方都“有法可依”,也是成功的體育法制體系。因此,目前我國加緊修改“基本法”之余,應花費更大氣力填補體育立法體系的欠缺,否則“基本法”就成了空架子。2)體育“基本法”更適合政府管理型國家的體育立法發展。南非、日本的體育法制歷史顯示,體育“基本法”在其相對短暫的體育立法歷史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中國目前各個體育社團發育先天不足的情況下,國家統一集中管理這種模式具有較為明顯的優點。“基本法”對中國體育發展來說就有宏觀調控和指導方面的意義。而政府放權型國家的代表美國雖然在業余體育領域有相當于“基本法”的《業余體育法》進行指引,但是其管轄的范圍未囊括體育全局,不包括職業體育。美國體育法的類型也多樹體現為成熟的法律體系中相關的體育條文,如《合同法》、《經紀法》、《憲法》、《反托拉斯法》、《勞工法》等等。
綜合上述分析,我國目前體育立法工作的重心,不僅僅是對“基本法”的修改,更要關注體育立法體系的完善,因此需要調整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的定位,調整對體育基本法修改目的和作用的認識。
5.3 體育立法應順應體育發展規律和社會需求
首先,體育運動本身的發展推動了體育領域新問題的出現、產生通過立法管制的必要性;其次,政府體育政策的工作重心也是和體育立法相輔相成的,體育立法成為政府宏觀調控體育活動的后盾。
澳大利亞體育立法的過程充分體現了這一特點。1920-1971年間,體育發展緩慢,體育的立法更多集中于大眾體育場地保障和體育協會的成立問題。1972-1982年是澳大利亞體育摸索發展時期,隨著對外交往增多,反對體育運動中的歧視,尊重體育公平成為這一時期體育發展的主流。體育立法也圍繞著這一主題開展。1983-1996年是澳大利亞體育高速發展時期,政府對體育的重視、澳大利亞國際體育形象地建立、體育傷害防護的關注、體育藥品管制的興起、反對體育運動歧視的白熱化,都推動了這一時期的體育立法呈現繁盛和多領域的特點。而1997年之后,澳大利亞體育的發展開始走向一體化平衡發展時期,體育風險防護、體育產業發展、體育知識產權保護以及體育藥品監管力度的加強,這些措施都越來越和國際體育發展的大趨勢接軌,這幾個方面的體育立法都體現出澳大利亞政府促進體育穩步發展的決心和力度。
澳、美、南、日四個國家的體育立法都不同程度體現了體育立法要適應體育內在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的特點。另外由于體育法制化發展的程度不同,社會背景不同,各國體育法制化繼續朝這個特點發展的路向也不盡相同。但是毋庸置疑的是,順應體育發展的實際需求必定是體育立法拓展和調整的宗旨。
5.4 注重體育立法的修改
通過修改使體育立法與時俱進,更好地規范體育發展是澳大利亞、美國、南非的共同舉措。以澳大利亞地方立法為例,1994年新南威爾士州《體育立法(修改)法1994年63號》,分別對1978《悉尼板球和運動場法》、1984《國家體育中心信托法》、1988《派拉馬特體育場信托法》進行了修改。美國的體育單項立法不多,但是針對體育發展,也不斷進行相關法律的調整。例如:在體育藥檢的問題上美國沒有專門的立法,受制于《憲法》的相關條款規制。因此在藥檢的問題上,美國經歷了公民以保護隱私為由進行抗議到通過不斷修改憲法達到民眾逐步認可的過程。體育藥檢的法制化經過了《憲法第四次修正案》、《憲法第五次修正案》、《憲法第十四次修正案》三次討論和修改的過程。[18]南非盡管體育立法時間非常短暫,但是從1998年至2005年僅南非體育委員會的相關立法頒布了四部,《國家體育和娛樂法》、《南非體育禁藥協會法》等都分別作了修改。日本在這一點略有不足,《體育振興法》頒布40多年來修改的呼聲日盛,而即便1998年日本體育法學學會體育基本法研究委員會已經起草并發表了《體育基本法綱要》,但是時至今日仍然未能正式修改出臺體育“基本法”。
5.5 借助國際比賽交流或特殊事件等時機推動體育立法
南非和我國的體育立法背景比較類似,體育立法的歷史短,經驗欠缺,而體育交流的增多等因素使政府推進體育立法成為必然道路。南非的體育立法很大程度上受外力的推動。例如借助國際賽事推動體育立法進程。2010年的南非國際足聯世界杯比賽是南非共和國建國后承辦的一項重要的國際賽事,為了申辦成功和舉辦成功,南非從2006年開始頒布了一系列的法規,引導和輔助賽事申辦和籌備工作。《2010國際足聯世界杯賽南非專門措施法》、《2010國際足聯世界杯賽南非專門措施法第二部》、《2010國際足聯世界杯賽委派外國醫療團及藥品、規定物品和醫療設備許可條例》。又如突發事件引發的立法:2001年南非足球慘案中43名球迷死亡事件,促使了《體育和娛樂比賽項目安全議案》出臺。借2010年足球世界杯的舉辦,比賽安全問題得到“南非體育和娛樂部”(SRSA)和“南非體育聯盟和奧林匹克委員會”(SASCOC)的尤其關注。2009《體育和娛樂比賽項目安全法》詳細擬訂了34條保障體育賽事安全的法規,涉及從場地到人員管理的方方面面。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期間使得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開始修改已經是一個很好的開端。
中國體育法有其特殊的歷史,在遵循本國國情研究制定中國體育法之外,為了促進其更好發展,也需要借鑒其他國家體育立法的經驗,讓法制為體育建設發展鋪設道路,為建設體育強國作出貢獻。美、澳、南、日四國體育立法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些規律性的特點,合理吸收其經驗,也是推動我國體育立法發展的助推器。
[1]凌平,馮宇超.略論美國體育管理法規的立法形式和司法程序對我國體育法制建設的借鑒價值[J].浙江體育科學,2003(6):4-6.
[2]黃世席.美國大學法學院體育法教學狀況及啟示[J].山東體育學院學報,2005,21(2):79-81.
[3][美]D.B.范達冷,B.L.本奈特.世界體育史[M].成都體育學院翻譯小組(譯)成都:成都體育學院.1976.
[4]South Africa banned from Olympics[EB/OL].(2010-04-24)[2012-05-20]http://news.bbc.co.uk/onthisday/hi/dates/stories/august/18/newsid_3547000/3547872.stm.
[5]Robert Chappell.Race,Gender and Sport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EB/OL].(2010-04-25)[2010-05-20].http://www.thesportjournal.org/article/race-gender-and-sport-postapartheid-south-africa.
[6]凌平,馮宇超.略論美國體育管理法規的立法形式和司法程序對我國體育法制建設的借鑒價值[J].浙江體育科學,2003(6):5-7.
[7]曾爾恕.外國法制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367.
[8]周愛光.日本體育法學的發展及研究動向[J].體育學刊,2006(5):4-6.
[9]洪永紅,夏新華.非洲法導論[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253.
[10]韋啟程,牛森.中日澳大眾體育管理體制模式的比較研究[J].山東體育科技,2005(9):50-52.
[11]國家體育總局《全民健身指導叢書》編委會.國外大眾體育[M]北京: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2003:40-41.
[12]South Africa Yearbook2007-0810.[R](2007-08-11)[2010-04-23].http://www.gcis.gov.za/resource_centre/sa_info/yearbook/index.html.
[13]郭樹理,周青山.南非法律制度初探[J].西亞非洲,2007(7):50-53.
[14]黃世席,陳華棟.日本體育法及其對我國相關體育立法的借鑒[J].體育與科學,2006(3):68-71.
[15]周愛光.日本體育法學的發展及研究動向[J].體育學刊,2006(5):3-5.
[16]郭樹理.外國體育法律制度專題研究[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11):33-35.
[17]田思源.我國《體育法》修改理念分析——兼論《體育事業促進法》的制定[J].法學雜志,2006(6):68-72.
[18]Adam Epstein.Sports Law[M].Thomson Learning,Inc,2003:164-165.
[19]蔣立山.法律現代化:中國法治道路問題研究[M].北京:法制出版社,2006.
[16]Bob Stewart,Matthew Nicholson,Aaron Smith,Hans Westerbeek.Australian Sport:Better by Design?The evolution of Australian sport policy.[M]Routledge,Taylor& Francis Group.2004.
[17]Adam Epstein.Sports Law[M].Thomson Learning,Inc.2003.
[18]Glenn M.Wong.Essentials Of Sports Law[M].Third Edition.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Inc.2002.
[19]Victoria University.Sports Law.[EB/OL].(2009-09-21)[2010-04-21]http://www.weblaw.edu.au/display_page.phtml?WebLaw_Page=Sports+Law.
[20]Legislation relevant to sport in South Africa.[EB/OL].(2008-07-24)[2010-04-21] http://www.srsa.gov.za/Legislation.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