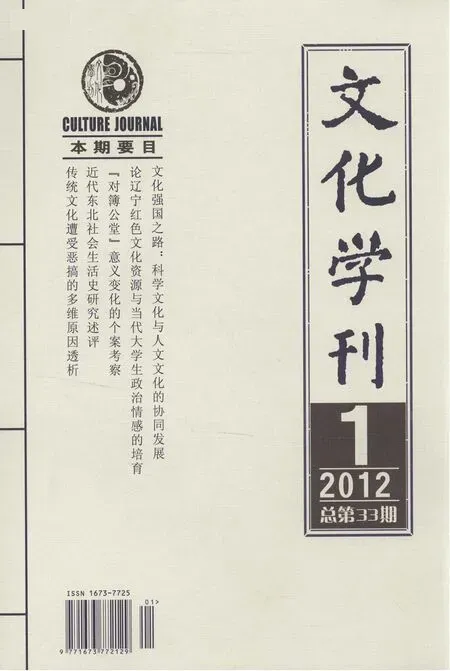傳統文化遭受惡搞的多維原因透析
鄒洪偉 張天明
(綿陽師范學院歷史文化與旅游管理學院,四川 綿陽 621000)
近年來,我國出現了一股惡搞傳統文化的不良風氣。一些人以電影電視、網絡隨筆、學術研究、文學創作、戲劇表演、商業廣告等方式對諸多的文化經典、歷史人物、詞語文字進行了重新的解讀和演繹。“文化新論”和“文化新品”猶如雨后春筍,令人目不暇接。如諸葛亮是分裂祖國的第一罪魁禍首;李清照乃“好酒、好賭、好色”之人;孫悟空去西天取經完全是由于愛上了唐僧;雷鋒是因為幫人太多而累死;黃繼光因小兒麻痹癥不慎發作才堵住了槍眼;《閃閃紅星》中的潘冬子是一個整日做明星夢的富家子弟;唐詩《春曉》變成了“春眠不覺曉,處處蚊子咬。打上敵敵畏,不知死多少”。《水滸傳》講述“3個女人和105個男人之間的感情糾葛”;“屈原”變成了豬飼料品牌;等等。諸如此類,使得大量的文化經典和歷史人物形象遭到篡改和顛覆。文化經典和歷史人物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載體。對其進行篡改,實際上是消解我們的文化根脈,否定我們的民族精神,去除青少年思想教育的基本食糧,將嚴重影響中華文化與民族精神的繼承和弘揚,危及我們民族和國家的興盛與繁榮。因此,消除惡搞文化之風,已迫在眉睫,勢在必行。如何消除?我們應首先透析傳統文化慘遭惡搞的主要原因。
一、道德教育的缺失
傳統文化蘊含著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其中的某些事件和人物往往是某種精神的符號和代表。惡搞傳統文化必然造成道德教育養料的不斷流失。究其原因,我們可以看出,傳統文化遭受惡搞也反映出我國過去相關道德教育的缺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逐步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知識、信息的占有、更新和創造的競爭在全社會逐漸展開。科學技術的作用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然而,國家對道德教育研究與實踐的支持力度遠遠不及理工科的某些項目,學校、團體和個人為了適應社會的發展不得不忙于應付智育與業務學習,于是,人文道德教育在不知不覺之中走向社會的邊緣。作為社會道德教育的制高點,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學術研究之風呈現下滑趨勢。很多學者為獲得更多的研究成果,篡改、剽竊、抄襲他人成果,將學術道德置之度外,對整個社會產生了極壞影響。
就道德教育自身評價來說,我國應試型的德育評價方式向學生灌輸了一種道德理念:為了自己的前途,就必須好好學習,獲得好成績。這種功利性的思維方式不但使學生難以習得道德教育的真正內涵,甚至有可能使德育課堂面臨不道德的抄襲風險。
就道德教育的方法來說,長期以來,我們學校德育課堂中,教師經常采用的講授法、榜樣法、宣講法等強行灌輸等方式。家庭教育中,家長也采取是類似的“規勸法”或“勸告法”。這樣的德育方式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受教育者的厭煩,于是打瞌睡、頂嘴、不理不睬抑或惡搞教育內容就自然成了他們對老師和家長的“回報”。
在這樣道德教育過程中,許多受教育者將難以做到客觀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和特性,也難以真正習得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尤其是很難認識到傳統文化的重要作用,養成捍衛民族文化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
如果人們沒有認識到傳統文化對于國家和民族發展的重要性,沒有意識到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世界地位,沒有認識到傳統文化很多因子的不可變更性,沒有樹立起對傳統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那么,他們必然會喪失對中國傳統文化最起碼的尊重和敬畏。而尊重和敬畏的喪失加上社會責任感的缺乏必然導致惡搞的上演。
二、不良心理的支配
人的行為是心理活動的產物。一些人惡搞傳統文化是有其心理上的動因的。每個人在潛意識里都有多種心理。這些心理本身并無絕對的好壞之分,只是在特定的環境中才能對其作出價值上的判斷。面對文化經典和歷史人物,在網絡、課堂等環境中,很多人的逆反心理、好奇心理、表現心理、放松心理和發泄心理紛紛顯現,行為矛頭直指傳統文化。
逆反心理是一個人普遍存在的心理現象,尤其在青少年中表現明顯。他們對于現存事物喜歡質疑,喜歡將原有的東西改頭換面,喜歡將神圣莊嚴當成游戲。作為權威的傳統文化也就自然成為青少年攻擊的對象。教科書將戚繼光、林則徐作為愛國主義的代表呈現在學生面前,有的學生偏偏非要說他們另有私心,經常賣國;“管鮑之交”令世人稱道,有人非得發表高論,稱兩者各懷鬼胎,相互利用,根本算不上什么偉大友誼。
好奇心理的驅使使得人們對于不為熟知的事物常常心懷向往,對于既有事物往往持否定批判態度。對傳統文化的熟悉也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部分人對傳統文化的遠離甚至背離。于是,正統學校教育中得來的文化知識和信息經常成為一些人惡搞的對象。
表現心理是人的一大天性,它能使人產生成功和備受他人尊重的感覺。有很多人為滿足自己的表現欲,常常通過嘩眾取寵或標新立異的方式來顯現自己,希望通過自己“獨特”的觀點理論和行為方式來引起別人的注意,從而出名。如老師和大部分同學們都認為李白是唐朝最偉大的詩人,已經不再評論李白地位,正準備學習李白詩歌時,一位同學突然站起,大聲說:“老師,李白是大唐第一古惑仔!”又如,“國學辣妹”在孔廟內袒露肚臍、濃裝艷抹、擺弄風騷的姿態,來“慰籍孔子千年寂寞”,以拯救國學。這些顯然是表現欲在作祟。甚至有些浮躁的專家、學者、演藝界名流,也想以惡搞的方式,吸引社會的關注,來展示他們的存在。
社會的快速發展必然導致問題叢生。當人們的不滿情緒不能通過正常的渠道來發泄的時候,于是,惡搞就成了一個極好的借助手段。惡搞并非是不滿的事物本身,而是泄憤心理的一種投射。比如《詩選刊》編輯部主任趙麗華和著名學者于丹在網上被人惡搞,其原因就在于人們對詩歌創作和文化解讀長期以來被功利和強勢的文化意識形態扭曲變形的不滿找到了發泄的出口。[1]
此外,“惡搞”文化中許多信息是對日常生活經驗的直接表達和描述,它以感性文化的形式實現了對現實生活零距離的復制,消除了長久以來因為所謂永恒和真理而產生的心理焦慮,[2]同時,“惡搞”為很多學習工作壓力較大的人們提供和塑造一個休閑娛樂的心理空間。這樣,放松心理就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人們惡搞傳統文化。
三、多元文化的沖擊
現代社會的便利交通和發達通訊使得世界變得越來越小。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推進,我國與各國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日漸頻繁。在這樣過程中,西方和港臺大量文化因子涌入中國,給中國文化的發展提供了許多新鮮的血液,同時也給中國傳統文化帶來了巨大沖擊。
在計劃經濟時期,文化傳播的形式、渠道和主體都是單一的,傳播的內容也相對穩定,這導致了人們對傳統文化的審美疲勞和心理壓抑。而西方和港臺多元文化的涌入,打破了我國原有傳統文化的單一發展的局面,使得國人驚喜地看到了不同于傳統文化的美好景象。在接觸、吸收各種混合性多元文化的過程中,極容易滋生出借西方文化模型和思想內核來惡搞中華傳統文化的心理。同時,改革開放以來相對寬松的社會環境也使得部分人士敢于通過惡搞的形式外化曾經掩藏的文化信息。
更需指出的是,西方和港臺多元文化中包含著一些重要的元素,可以直接催生“惡搞”行為。這些重要的元素有后現代文化、“無厘頭”文化、歷史虛無主義、達達主義、意識流、荒誕派、泛性論、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魔幻現實主義、波普藝術、行動藝術、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等。后現代文化具有后現代結構、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共生、否定權威等典型特征,惡搞文化與后現代理論所倡導的思想不謀而合,其選材的“碎片化”、作品風格的“荒誕化”都體現了強烈的后現代主義色彩。“無厘頭”是廣東佛山的一句俗話,大概意思是說一個人做事、說話都令人費解,其語言和行為沒有明確的目的,粗俗隨意,亂發牢騷,但并非完全沒有道理。[3]“香港“無厘頭”以周星馳的喜劇電影是最為顯著的代表。而西方的達達主義利用現存文化元素進行再創造從而顛覆傳統藝術的創作范例。所有這些文化和主義都具有顛覆文化經典、張揚個性、嘲諷社會的特點,對國人惡搞傳統文化提供了思想支持和直接樣板。
四、經濟利益的誘惑
影視、報刊和雜志對文化的傳播發揮了巨大作用。網絡的到來,更是讓文化信息能夠大面積、高強度傳播。如果這些傳媒沒有得到有效監管,勢必會成為傳播不良文化的溫床和推助器。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很多文藝工作者和軟件開發商以經濟利益為驅動,較多地考慮作品的商業價值,盡量去捕捉和迎合大眾的口味。“惡搞”類作品顯然符合這一條件,于是,大量荒誕的惡搞式的文藝作品和網絡游戲應運而生。什么 “戲說乾隆”、“水煮三國”,比比皆是。很多歷史劇在新的“人性化”解讀下紛紛閃亮登場,如《走向共和》里的李鴻章形象塑造完全拋開了歷史公論,看后甚至還讓人為之欽佩之至和感動得熱淚盈眶。
對很多媒體人來說,經濟效益最為重要。他們考慮最多的是讀者和觀眾的眼球,關心的是報紙的發行量、廣播電視的收聽(視)率以及網絡的點擊率。因此,這些媒體不可避免地會選擇那些能吸引“眼球”的信息加以傳播,。而“惡搞”文化以其特有的幽默詼諧、搞笑反諷、新鮮刺激、挑戰權威有著廣大的受眾基礎,這對媒體來說無疑有著極大的吸引力。
為追求最大的經濟效益,吸引受眾感官,很多文藝工作者、軟件開發商、媒體等文化生產者和傳播者喪失了最起碼的是非榮辱觀念和最基本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責任,想方設法地去創造、尋找和大力傳播另類、搞笑、搞怪、刺激、粗俗不堪的文化產品,為“惡搞”提供了生長的土壤。而相關法律、制度、規范的普遍缺失則為“惡搞”提供了土壤。
五、創新思想的歪曲
創新是以新思維、新發明和新描述為特征的一種概念化過程,是人類特有的認識能力和實踐能力,是人類主觀能動性的高級表現形式。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創新”在我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指出,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4]《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明確地把培養學生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作為素質教育的重點。其他各行各業也紛紛提出要進行創新。可以說,創新在我國已成為社會的時尚,作為一種思想和理念已經完全深入人心,舉國上下,處談創新,時時談創新。在文化教育領域,人們更是高舉著創新大旗,為形成先進文化和培養創新性人才而努力奮斗。
但是,很多人只是從方法論的角度理解了創新的存在和實施,而沒有從價值觀的角度去審視創新的意義和路徑。如有的教師認為只要學生在課堂上發表不同于傳統的觀點,不管該觀點是否正確,只要打破了常規,突破原來的觀點和理論,就是創新,就應該予以鼓勵。以致于有的學生在歷史課堂上完全不顧歷史事實,拋出了很多奇談怪論,如“譚嗣同在變法失敗后不逃走就是傻蛋”、“曹操是個大英雄”等。在語文課堂上,有學生認為白毛女應該嫁給有錢有勢的黃世仁。所有這些看上去都對原有的歷史文化人物進行了創新,但同時我們可以看出,這樣的創新改變了歷史人物的原有形象,模糊了很多學生的是非判斷。很多學生不禁要問:譚嗣同喋血菜市口的舍身取義怎么變成了愚蠢行為?不擇手段取得成功的曹操是個英雄?白毛女應該選擇金錢和權勢而放棄愛情嗎?如果教師對這些創新予以肯定的話,那學生所有的疑問將變成肯定的答案,由此,不擇手段、見利忘義將會在潛移默化中深入學生的骨髓,舍身取義、情義無價等寶貴品質在嘲笑聲中將蕩然無存。創新不是單純方法上的變化。任何有益的行為都應該堅持方法論和價值觀的統一。文化創新必須走在一定道德的軌道內。以上所謂“創新”是對創新的曲解,實際上是一種“惡搞”,違背了培養德才兼備人才的創新初衷。
惡搞中國傳統文化不利于我國傳統文化與中華民族精神的繼承和弘揚,影響著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危及我們民族和國家的生存與發展。制止惡搞,已經是刻不容緩。基于以上原因的分析,我們應該加強全民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國民道德素質,使人們深刻認識到傳統文化的重要價值,形成保護傳統文化的神圣使命感和歷史責任感,從而自覺地保護和傳承中華傳統文化;在建立創新型國家的過程中,應將創新與惡搞區分開來,開展真正的文化創新;整頓文化市場,建立、健全相關的法律法規;在學術領域尤其要杜絕抄襲現象,維護學術尊嚴,發揮道德教育至高點的作用。當然,惡搞的原因不只是以上幾項,我們還應從更多的角度和層面對其進行深入探討,以期為該問題的有效解決提供參考。
[1]文建平.芙蓉姐姐、趙麗華、于丹:墮落的三個代表[EB/OL].g.163.com/blog/static/24277317200792535454241/2007-10-25.
[2]左偉清,劉尚明.“惡搞”文化流行的原因及影響[J].當代傳播,2008,(2).
[3]郭玉秀,趙保峰.“惡搞”文藝作品盛行原因的探析[J].文學界(理論版),2011,(3).
[4]林其屏.江澤民對創新理論的新貢獻[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