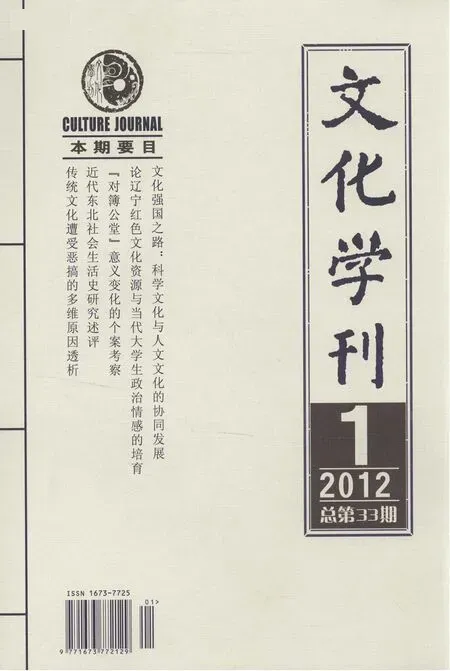俄國的黑龍江流域人類學調查對于我國人類學東北研究的意義
張 松
(黑龍江省民族研究所,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1)
東北地區是人類學資源較為豐富的地區,然而,與其他地區近年來人類學調查研究的長足進展相比,東北無疑處于落后的境地。我們要展開人類學的東北研究,最主要的工作當然是要對這一地區的世居民族,尤其是通古斯語各族進行長期、深入、細致的田野調查。與此同時,我們還應了解、吸收、借鑒我國前輩學者和國外學者關于這一地區的人類學調查研究成果。國外的調查以俄、日兩國為主,本文所要談的,便是俄國(包括蘇聯時期)的黑龍江流域人類學調查對于我國人類學東北研究的意義。
一、主要的調查和著作
(一)機構、刊物
中俄雅克薩之戰及1689年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后,沙俄的侵略勢力被阻擋在了外興安嶺以北。19世紀中葉,由于中國國內局勢動蕩,東北邊防空虛,沙俄開始有計劃地重又入侵我黑龍江流域。這一時期建立的一些學術機構和組織的科學考察便是為其侵略目的服務的。
1851年,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在伊爾庫茨克成立了 “俄國皇家地理學會西伯利亞分會”,并創辦會刊《俄國皇家地理學會西伯利亞分會學志》。該學會派遣馬克率領考察隊對黑龍江和烏蘇里江進行考察,馬克后來出版了《阿穆爾河旅行記》(圣彼得堡,1859年)和《烏蘇里江谷地旅行記》(圣彼得堡,1861年)。后來,又在伯力成立了“俄國皇家地理學會阿穆爾分會”,并出版會刊《俄國皇家地理學會阿穆爾分會學志》。1884年,在海參崴成立了 “阿穆爾邊區研究會”,1884—1888年,委員會主席為布謝,1888—1895年為馬爾加里托夫,他們都是著名的民族學家和考古學家。1921—1924年,研究會由著名旅行家和民族學家阿爾謝尼耶夫主持。1888—1922年,共出版了17卷《阿穆爾邊區研究會學志》。蘇維埃政權在遠東建立后,該會停止活動。近年來,該研究會及會刊得到恢復。俄國還在圣彼得堡成立了“東亞和中亞研究委員會”。1918—1920年和1921—1922年史祿國分別在遠東大學的歷史—語文系、東方系開設民族志學課程講座。沙俄時期經常發表關于黑龍江流域各民族的人類學論著的刊物還有 《民族學評論》、《古風今存》、《西伯利亞古風今存》、《皇家科學院人種志學和民族志學博物館集刊》等。另外,1922年,俄國人在哈爾濱成立了“滿洲邊區研究協會”,出版《滿洲邊區研究協會通報》,俄國人還在哈爾濱創辦了《滿洲通報》。上述機構中有些還建立了自己的博物館。
蘇聯早期,培養民族學人才的最重要機構是“列寧格勒國立大學地理系民族學分部”,博戈拉茲和施滕貝格曾在那里主持教學工作。1930—1941年,在列寧格勒設立“北方民族學院”。1962年,根據阿夫羅林的建議,在新西伯利亞國立大學設立了人文學系,培養西伯利亞各土著民族語以及考古學、民族學、歷史學等方面的專家。1966年,在伊爾庫茨克成立了“蘇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歷史學、語文學、哲學研究所”,第一任所長是奧克拉德尼科夫;1991年,該所更名為“考古學與民族學研究所”。1970年,在海參崴組建了“遠東諸民族歷史學、考古學、民族學研究所”,1992年,該所創辦了學術季刊《俄羅斯和亞太》。
(二)學者、著作
1854—1856年,施倫克在黑龍江下游和庫頁島進行民族學考察,在此基礎上,完成了他的三卷本巨著 《阿穆爾邊區的異族人》(圣彼得堡,1883年,1889年,1903年)。這是關于整個黑龍江流域(重點是下游和庫頁島)各民族的百科全書式著作,除了重點記述吉利雅克人、通古斯語各族、愛努人外,還涉及了滿人、達斡爾人、漢人、日本人、俄羅斯人。1886年,阿穆爾邊區研究會派遣馬爾加里托夫對奧羅奇人進行民族志學考察,這是施倫克沒有親自調查的民族。以這次田野考察所收集到的資料為基礎,馬爾加里托夫寫出了第一部關于奧羅奇人的專題學術著作 《皇帝港的奧羅奇人》(圣彼得堡,1888年)。該書為12開本,正文56頁,另附有1幅奧羅奇人分布圖和11幅手繪圖版。1890—1897年及1910年,施滕貝格對庫頁島和黑龍江下游諸民族進行了調查,大部分相關著作收入《吉利雅克人、奧羅奇人、果爾特人、涅吉達爾人、愛努人》(伯力,1933年)一書中。1912—1918年,史祿國對俄國的后貝加爾和阿穆爾地區及我國東北地區進行了調查,著有《通古斯人薩滿教基礎的初步研究》(《歷史—語文系學志》第1卷,海參崴,1919年)、《北中國人種志學》(上海,1923 年)、《滿洲人的社會組織》(上海,1924 年)、《北通古斯人的社會組織》(上海,1933年)、《通古斯人的心理情狀》(倫敦,1935年)。1913—1920年,洛帕京對黑龍江下游和烏蘇里江以東地區進行調查,著有《阿穆爾河、烏蘇里江、松花江的果爾特人》(海參崴,1925年)。 1934—1936年,佐洛塔廖夫對黑龍江下游地區進行了兩次考察,著有《烏爾奇人的氏族制度與宗教》(伯力,1939年)。20世紀50—80年代中期,斯莫莉亞克對黑龍江下游的那乃人、烏爾奇人及尼夫赫人進行了長期而深入的考察,發表了大量論著,其中最重要的是《薩滿:身份、功能、世界觀》(莫斯科,1991 年)。
俄國學者從19世紀中葉開始,在黑龍江流域進行了持續不斷的民族學考察活動,發表了大量論著,以上只是舉出其中最重要的。還有許多調查資料至今沒有刊布。
二、對東北研究的意義
(一)對凌純聲的影響
凌純聲先生是我國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第一次民族學調查是1930年在松花江下游地區的赫哲族中進行的,后來,以這次調查所獲得的資料為基礎,出版了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南京,1934年)。這是我國現代學術史上第一部科學的民族志,是中國人類學誕生的標志性著作。那么凌純聲的第一次田野調查為選擇東北赫哲族的原因,首先是從歷史背景上看,1930年前后,日本侵略者欲占領全東北的意圖已是昭然若揭,這樣的調查具有“搶救”性質。可供參照的是梁思永等人同一時期在東北進行的考古發掘。其次,再從他的學術知識背景來推斷。從《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書所列的參考文獻可以看出,凌純聲對施倫克、博戈拉茲、約赫爾松、洛帕京、史祿國等人在西伯利亞和遠東以及我國東北地區的調查成果是相當了解的。中國應該參予國際通古斯學的調查研究,并為自己在國際學術界爭得一席之地,這應是凌純聲先生當年的想法。凌純聲的調查是當時中央研究院整體學術計劃的一部分,并不是他的個人行為。至于凌純聲之所以首先選擇赫哲族,而不是鄂溫族和鄂倫春族,這應與他對史祿國和洛帕京的學術調查的清楚了解有關。在當時,東北的鄂溫克族和鄂倫春族已經過了史祿國的調查,洛帕京調查的是俄國境內的赫哲族(果爾特人),而對于中國境內的赫哲族是從來沒有進行過科學調查的,是學術上的空白。
凌純聲先生雖然早年留學法國,接受的是歐洲的學術訓練,但在他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呈現出的卻是典型的俄國西伯利亞民族志風格。全書的結構安排和平實的敘述與施倫克的《阿穆爾邊區的異族人》和洛帕京的《阿穆爾河、烏蘇里江、松花江的果爾特人》非常類似,甚至書名也相仿佛,可以說,這3部著作都是在客觀地呈現社會事實。另外,《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的赫哲族分布圖及多幅插圖均采自《阿穆爾河、烏蘇里江、松花江的果爾特人》。凌純聲先生將中外的民族學調查資料與中國古籍的記載相結合,來探討東胡和東夷的問題,是極具啟發性的,這一點為俄國學者所不及。
(二)基礎、規范、參照
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某一學科建立的標志是出現幾部具有深遠影響力的典范著作。這些著作能夠為本學科打下基礎并建立一定的學術范式,確立學術高度,使后來的調查研究者有所憑藉、有所遵循、有所參照、有所追求(追求卓越),形成一種優良的學術傳統。對于人類學的東北研究來說,我認為這樣的中國著作有3部或2部:《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秋浦的《鄂溫克人的原始社會形態》[1]及其續篇《鄂倫春社會的發展》[2]。而對于俄國的黑龍江流域(包括庫頁島)諸民族的調查研究者來說,必讀的著作大概有4部:《阿穆爾邊區的異族人》、《吉利雅克人、奧羅奇人、果爾特人、涅吉達爾人、愛努人》、《阿穆爾河、烏蘇里江、松花江的果爾特人》、《烏爾奇人的氏族制度與宗教》。在學術上,我們不妨實行拿來主義,將俄國的典范著作作為我們自己的基礎。這就要重視翻譯工作了。俄國著作大多有專業制圖人員繪制的詳細的民族分布地圖、藝術家繪制的精美圖版和插圖、大量的優質照片、詳盡的參考文獻,且紙墨精良、印刷裝訂考究,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中國的東北與俄國的阿穆爾地區大體上是同一個地理區域、氣候區域、生態區域、民族—文化區域和歷史區域(它的改變只是在1860年之后)。自近代以來。這兩個地區又經歷了類似社會、文化變遷:俄國貧民大量涌入阿穆爾地區,關內漢族貧民大量涌入東北,使這兩個地區的民族構成和社會文化徹底改觀;20世紀20年代和50年代以來在相同意識形態背景下和相近的民族政策指導下的社會和精神(思想)改造;中國改革開放和蘇聯解體后民族文化的復蘇和更加深刻的社會文化變遷。因此,俄國各個不同時期的著作便構成了我們的重要參照系。例如,《阿穆爾邊區的異族人》記述了各民族社會生活的原始面貌,正可彌補早期漢文史料(包括朝鮮、日本史料)記載的不足;謝姆的《那乃人的氏族組織及其解體》(海參崴,1959年)、 拉里金的 《烏德蓋人》(海參崴,1959年)和《奧羅奇人》(莫斯科,1964年)、斯莫莉亞克的《烏爾奇人》(莫斯科,1966年)等反映了社會主義制度下通古斯語各族的社會文化變遷;薩瑪爾的《在氏族樹的蔭庇下》(伯力,2003年)反映了蘇聯解體后,那乃人薩馬爾氏族的氏族制度恢復情況。
(三)理論、方法、敬業精神
史祿國的《族體:民族和民族志現象變化的基本原理研究》(上海,1923年)一書,是他在西伯利亞及我國東北地區長期調查的理論總結。在書中,他提出應將“族體”這樣一個“民族單位”作為民族學調查研究的對象。“族體是說著同一種語言,認為自己有著共同起源,擁有自己的風俗復合和生活方式,保持和尊崇傳統,并以這些同其他群體區別開來的人的群體。”[3]費孝通先生在《人不知而不慍》[4]一文中認為,曾為我國民族學界所普遍遵循的斯大林關于“民族”的經典定義正來源于這里。施滕貝格有著極為豐富的田野調查經驗,他的《西伯利亞諸民族民族志資料收集指要》[5]一文便是對其多年經驗的總結,他的指導思想和種種具體的調查、記錄方法極值得我們借鑒。
俄國學者取得的輝煌成就無疑與他們高度的事業心和敬業精神密不可分。在艱苦的條件下堅持長期調查,沒有一種為學術事業的獻身精神是不可想象的。比如施滕貝格,他是在被沙皇政府流放到庫頁島之后開始民族學調查的。
三、體質人類學、考古學、語言學
前面談的是民族學或文化人類學,這是人類學的核心內容。亞洲東北部的各種民族群體在漫長的歷史中經歷了復雜的遷移、混合、分化,民族文化也隨之傳播、交融、變異。許多問題單單依靠文化人類學是無法解決的,還要借助于體質人類學、考古學和語言學。人類學的東北研究也只有這樣才能形成一個完備的人類學學科體系。國內的相關成果我們自己要充分利用,同時,我們也需要了解和借鑒國外學者的論著。
體質人類學,早期稱為人種志學。在俄國,人種志學的研究起步較早。施倫克和施滕貝格對東北亞洲各民族進行過專門的人種志學調查,成果見于他們的前述名著中。史祿國還出版了主要針對我國東北各族的體質人類學專著。這方面的論著還有:龍切夫斯基《17個奧羅奇人顱骨的測量和關于這一部族的幾條札記》[6]、波克羅夫斯基《奧羅奇人的人種志學類型》[7]、馬尼澤爾《關于吉利雅克人的人種志學資料》[8]、列文《西伯利亞和遠東的人種學類型》[9],重要的論文集有《遠東諸民族的體質人類學與起源問題》(莫斯科,1958)、《西伯利亞土著的族源和人種史問題》(克麥羅沃,1986)等。近年來,基因學的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俄羅斯學者的相關研究值得我們關注。
俄國學者在遠東考古學領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涌現出了奧克拉德尼科夫、沙弗庫諾夫、杰列維揚科這樣一批著名學者。在俄國的西伯利亞語言學著作中,有大量用音標精確記錄的各民族的民間文學文本,它們同時也是珍貴的民族學資料。這樣的著作主要有:阿夫羅林的《那乃人的語言和民間文學資料》(莫斯科,1986)、《奧羅奇人的故事和神話》(新西伯利亞,1966)、《奧羅奇語原文和詞典》(列寧格勒,1978),謝姆《那乃語方言概要——比金(烏蘇里)方言》(列寧格勒,1976)、蘇尼克的《庫爾—烏爾米方言——那乃語研究和資料》(列寧格勒,1958)、《烏爾奇語》(列寧格勒,1985),科爾穆申《烏德蓋語》(莫斯科,1998)、彼得羅娃《奧羅克語》(列寧格勒,1967)欽奇烏斯《涅吉達爾語》(列寧格勒,1982)等。
總之,俄國學者對黑龍江流域各民族的科學的人類學調查,在時間上比我們早得多,在規模上比我們大得多。在學術上我們應該做到“知彼”,這是凌純聲先生在幾十年前早就達到了的,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應當做什么,怎樣去做。俄國的黑龍江流域人類學調查又是其西伯利亞人類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進行人類學的東北研究還要關注俄國的西伯利亞研究,那是一更加廣闊的學術領域。
[1]秋浦.鄂溫克人的原始社會形態[M].北京:中華書局,1963.
[2]秋浦.鄂倫春社會的發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3]史祿國.族體:民族和民族志現象變化的基本原理研究 [J].國立遠東大學東方系學報》,1923.第57期增刊.
[4]費孝通.人不知而不慍[A].滿族的社會組織[C].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5]施滕貝格.西伯利亞諸民族民族志資料收集指要[A].吉利雅克人、奧羅奇人、果爾特人、涅吉達爾人、愛努人[C].
[6]龍切夫斯基.17個奧羅奇人顱骨的測量和關于這一部族的幾條札記[A].海洋文集[C].
[7]波克羅夫斯基.奧羅奇人的人種志學類型[A].1927年全蘇動物學家、解剖學家和生物組織學家代表大會論集[C].
[8]馬尼澤爾.關于吉利雅克人的人種志學資料[J].圣彼得堡大學人種志學研究會年刊:卷6[C].1916.
[9]列文.西伯利亞和遠東的人種學類型[J].蘇聯民族學,19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