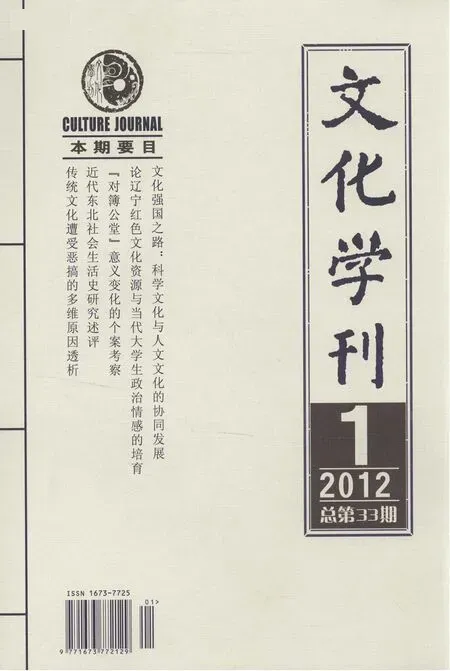何為通古斯——從比較視野看史祿國、凌純聲的通古斯人歷史研究
李金花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 100732)
回顧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界早期對于東北地區人群的研究,史祿國和凌純聲無疑是其中占有重要篇幅的兩個人。前者作為俄羅斯學者,1905-1910年留學于法國巴黎大學,獲得語文學博士學位,其后回國任職于俄國皇家科學院人類學和民族學博物館,在1912-1917年間對包括俄羅斯后貝加爾、蒙古、滿洲在內的西伯利亞、遠東地區被稱之為“通古斯人”的人群進行了多次田野調查[1],之后因為俄國政治變革被迫滯留中國,參與到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的早期進程中。后者作為中國學者,1926-1929年間同樣留學于法國巴黎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后于1930年左右前往中國東北的赫哲族進行民族志調查,成為早期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的代表人物。這兩位先后從法國巴黎大學畢業的人類學先驅,若從田野調查方面成果來說,則分別以《北方通古斯的社會組織》和《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最為典型,前者是史祿國對于通古斯人調查最為詳細而全面的著作,而后者則被中國人類學界奉為中國民族學史上破天荒之著作。[2]盡管史祿國的《北方通古斯的社會組織》一書主要著重于對于被他稱之為“北方通古斯”的通古斯人的社會組織的書寫,而凌純聲則意圖于對于赫哲族整體文化面貌的關注,但是兩人卻不約而同在兩書之前對于通古斯人的歷史起源問題有著重要篇幅的探討,兩人的不約而同并非偶然,而是有著其背后各自的原因。本文試圖以兩書中有關通古斯歷史的討論為橋梁,對于史、凌兩人的通古斯研究作一番考察。①在此處,我將赫哲族納入到通古斯人群當中,盡管史祿國認為稱之為Goldi的人群可以視為是通古斯人的近鄰,但是他亦不否認其同樣有著通古斯人的來源。見史祿國:《北方通古斯的社會組織》,“作者序言”,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124頁。
一、史祿國有關通古斯人及赫哲族歷史的思考
1929年史祿國的 《北方通古斯的社會組織》一書以英文版形式在中國上海出版之后,同樣亦為通古斯研究專家的I.A.Lopatin在當時的 《美國人類學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有關此書的簡短書評。在評論中,Lopatin說:
這本書中最引人入勝而同時又最具爭議的章節是史祿國對于通古斯人的分類以及其形成及遷徙歷史的分析。在通古斯人的起源問題上,存在著兩種假設,其中一種為大多數學者所公認的:即將滿洲視為是其發源地。然而,Drs.P.P.Schmidt和J.D.Talko-Hryncewicz這兩位通古斯專家則主張蒙古西北部為其發源地的假設,Dr.Schmidt的理論極具價值,因為他將阿爾泰南部地區視為是突厥-蒙古-通古斯的共同發源之地。史祿國不同意以上兩種觀點,他主張最初的通古斯人是在更南部地區:如中國北部和中部,黃河及長江之間……[3]
Lopatin的這段話將史祿國對于通古斯人的歷史起源及形成問題的主張鮮明地呈現出來,正是此一主張,成為了史祿國《北方通古斯的社會組織》前三章得以形成的基礎。在該書共八章的內容中,前面三章內容,分別是通古斯人對自然環境的適應、北方通古斯各集團的地理分布和分類及他們與鄰族的關系、通古斯的氏族和通古斯的歷史概述,后面五章則是如題目所言對于通古斯人包括氏族、家庭、婚姻、財產、社會習俗等社會組織的分析。前三章內容雖然包括有關自然環境的描述、北方通古斯地理分布現狀等這些非歷史的內容,然而實際上,卻可以從后來史祿國對于這些材料的處理中看出,無論是自然環境、還是地理分布、乃至于后五章中所談及的氏族、社會習俗等,都成為了他論證通古斯人歷史的材料的一部分,這其中甚至還不包括他所擅長的體質測量以及語言學材料的運用。縱觀史祿國一生有關通古斯人的研究,其主要可以分為三個部分①需要說明的是,對于史祿國這樣出身于歐陸傳統人類學學科思想熏陶和訓練背景的人類學家來說,他同樣對于體質、語言、考古等方面都有著深入的考察,尤其是體質人類學的研究,成為他后來在中國從事人類學研究的最為重要的田野工作,并因此寫出了一系列的相關專著。對于通古斯語言研究,他同樣在深諳通古斯語之時寫出了有關通古斯語的專門文獻。然而,就其影響來說,其對后來學者產生較大影響力的無疑是這三個方面。,社會組織研究②以其《北方通古斯的社會組織》、《滿族的社會組織》為代表。;薩滿研究③以其《通古斯人的心理-心靈情結》(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he Tungus)為代表。;歷史研究④以《北方通古斯的社會組織》及文章“遠東北方通古斯的遷移”為代表。。這同樣可以從他在《北方通古斯的社會組織》中所寫的“序言”當中看出:
本書沒有附上應有的結論,是出于以下考慮:即本書只是我的民族志學觀察的一部分。如前所述,社會現象同其他文化現象有著密切關系,如果對通古斯民族志,其中包括通古斯人的思想體系和通常所謂的“宗教”,不做一般的全面論述的話,許多社會現象是不可能正確理解的。這個問題將在我的另幾本書中探討。至于通古斯人的形成及其歷史,情況也是同樣地,因此我決定在今后的著作中再對通古斯人的社會組織及其歷史,作出一般結論。[4]
就如后來的眾多學者所公認的,史祿國在上文中所說的有關結論的思考最后引申出了他首創出“ethnos”一詞,開始了對于“民族”以及“民族性”等問題的思考。很明顯的是,對于“ethnos”其內涵的思考,則不得不說是包含在他對于通古斯人歷史、社會組織以及薩滿的研究當中。
對于在西伯利亞、中國東北這片廣闊地域上分布著的通古斯人來說,史祿國主張從語言學上來分成兩類,北方通古斯和南方通古斯,前者以分布在后貝加爾、阿穆爾州、賓海洲以及呼倫貝爾等地方的通古斯人為代表,后者以滿族為代表。前者按照其生計方式分類,又可分為飼養馴鹿的通古斯和游牧的通古斯,而后者則普遍以農業為主。夾雜在俄羅斯、蒙古、布里亞特、漢族之間的通古斯人,不管是生計方式、語言、體質還是文化特征,都呈現出紛繁多樣的局面,從史祿國的觀點看來,這種復雜多樣性一方面是通古斯人為了適應自然環境的需要,另一方面則是為了適應民族間外部關系的需要。正是此兩種環境的影響,才使得通古斯人出現了二十世紀初期史祿國民族志調查時所反映出來的特征。
要如何理解所謂的通古斯人,也即他所說的“ethnos”,則需要建立在他的民族志調查基礎之上。受俄羅斯、蒙古、漢三大強勢勢力擠壓下的通古斯人,其生計方式逐漸在拋棄傳統的馴鹿飼養,而納入別的生計模式當中,其語言及風俗,亦在不斷地忘舊納新當中,乃至于其活動的地理范圍,也日漸縮小。正是這一不斷變化的通古斯人,才成為了史祿國所說的 “ethnos”:我在本書中所使用的“民族單位”一詞,是指這樣一種單位,在這個單位中民族志要素的變化過程及其向下一代的傳遞和生物學的過程正在進行。這些單位永遠處于變化的過程中……[5]正是基于此一有關“ethnos”的論述,他對于通古斯人的歷史所作的一番考察,將其重心放置在通古斯人的遷徙當中。由此而來的起源地的討論,他反駁了施密特的北蒙古起源說和另外一種滿洲起源說。首先,他反對北蒙古起源說,因為從他對于通古斯人的民族志調查中可以表明北方通古斯是起源于南方。這包括通古斯人的服飾不適宜西伯利亞寒冷氣候、身體上的如眼睛對于雪地的不適應、以及心理上的如通古斯人不熟悉海洋。[6]其次,他反對滿洲起源說,因為滿洲地方氣候寒冷、地域狹小,不適宜民族單位的形成。而只有華北和華中的低地和高原所形成的谷地、即黃河和長江的中游和部分下游地區,有著適宜的氣候和寬廣的地域。隨后是中國漢人從西北部向黃河谷地的擴展,使得早期通古斯人開始向南或向北遷移。這在體質人類學上能夠得到證據:北方通古斯人最普遍的伽瑪型同樣在華東、華北、甚至是華南能夠看到。向北的通古斯人一方面與滿洲的古亞細亞人相遇,發生融合,同時另一部分人繼續向北遷移,直至西伯利亞。其后,通古斯人又發生了四次遷徙浪潮,史祿國以調查到的通古斯人的氏族名稱以及傳說故事為依據,對此四次遷徙波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由此可以看出,史祿國心中所勾畫的 “通古斯”,并非是一個靜態的民族體,而是一個動態的變化體,在不斷的外部環境的變化當中,其社會內部的社會組織、宗教心理、風俗習慣等不斷改變以得以協調,達到平衡,似乎可以說,二十世紀上半期人類學界從拉德克利夫-布朗等結構功能論到后來利奇等人所不斷完善的歷史視野中的結構功能的努力早已經在史祿國的通古斯人研究中實現。史祿國的歷史研究一方面應對了傳統漢學研究中對于歷史問題的關懷,更重要的是它成為了解釋何謂“ethnos”的一部分。
如果說《北方通古斯的社會組織》仍然是史祿國對于通古斯人社會組織關心的一個作品,那么,有關歷史問題的論述他在另一篇長文中則表達得更為清楚。早在《北方通古斯的社會組織》一書出版之前的1926年,史祿國在《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 會 雜 志 》 (theJournalof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發表了《遠東北方通古斯的遷移》(Norther Tungus Migration in the Far East)一文,該文副標題是“果爾德和他們的民族關系”(GoldiandTheirEthnical Affinities),這里所說的“果爾德”,也即是凌純聲所調查的赫哲族。史祿國在文章前言中談及,他的此篇文章本是為了回應Lopatin有關果爾德人的民族志研究而寫,但是文章寫成后卻不僅僅成為了回應Lopatin的文章,反倒成為史祿國對于果爾德人乃至通古斯人歷史研究思想的完整表達。[7]
Goldi在漢人的稱呼中,經常被稱之為“魚皮韃子”,而他們自稱為“浩占”或“浩津”,在其鄰近的比拉爾千及滿族人中,他們被稱呼為“赫哲”。史祿國認為雖然赫哲人與滿族人這一南方通古斯有著親密的關系,然而,他們的起源并不同,并且赫哲語言以及文化上都呈現出北方通古斯的一些特征。赫哲人主要聚集于黑龍江、烏蘇里江、松花江三大區域,因為地域的差異,其各自也呈現出不同的民族志特征。黑龍江流域的赫哲人受到了古亞細亞人、北方通古斯以及蒙古人的影響,烏蘇里江流域的赫哲人主要受到了漢人的影響,松花江流域的赫哲人被認為是最具典型性的,甚至被認為是滿族人的發源地。[8]盡管從文章標題看來其目的在于討論北方通古斯人的遷移問題,然而,全篇卻并未著眼于對歷史遷移問題的回顧,史祿國更傾向于從赫哲人的民族志調查的材料中去比較在夾雜在北方通古斯、南方通古斯之間的赫哲族是怎樣的民族志特征。他從赫哲人的生計方式——漁獵、善于用狗、主食為魚肉、捕魚方法、魚皮服飾、定居生活、雪橇、氏族組織、婚俗、生育習俗、薩滿、喪葬儀式等諸多方面,與北方通古斯人及滿族人相比較,描繪一幅赫哲人與其他人群之間的文化關系圖,與此同時,他還考察了赫哲人的語言、體質方面,從這些民族志特征,史祿國歸納出了北方通古斯人的四次遷徙波,在四次遷徙波之下的赫哲人,原初早期是北方的通古斯人群,甚至還飼養馴鹿,自稱為鄂溫克,其后受漢族以及俄羅斯人的強烈影響,到現今他們成為了包含漢、俄羅斯等文化特征在內的人群。
從比較起源于同一古老民族的不同人群的民族志特征,到根據這一比較來看民族志特征的地域分布,從而進行歷史遷移過程的回溯,這一帶有文化傳播論傾向的解釋在后來被一些學者所批評。史祿國的通古斯人的歷史研究是從民族志調查為起點,去尋找歷史的證據,而在歷史證據之后,再思考研究對象本身的問題,盡管為后人所批評,但是不容置疑的是,他的這種大區域的視角無疑為我們今天的人類學研究提供了極好的反思。[9]
二、凌純聲有關通古斯人及赫哲族歷史的思考
相較于史祿國對于整個西伯利亞、遠東地區以及中國東北地區的通古斯人人群的整體關注,凌純聲的通古斯人研究則集中于居住在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這一人群之上。對于赫哲族人的研究,他主要分為幾個部分:歷史;包括物質、精神、家庭、社會四方面在內的赫哲文化;語言以及傳說故事。歷史部分作為他開篇之章節,無疑有著重要的地位。
在《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的歷史部分,凌純聲主要辨析了以下六個方面的內容:通古斯非東胡民族,通古斯為東夷的一種,東北各民族名稱的起源及其轉變,赫哲與Goldi名稱的來源,中國文獻中記載的赫哲,現代的赫哲族及其地理的分布。凌純聲對于東北民族及赫哲族歷史的考察,主要基于中國史書之記載。他并不關心如史祿國所作的南北通古斯之類的區分,他更在意的是:曾經在中國東北部存在過、在中國史籍當中記載著的各民族,到底應該歸入哪個集團、或者說哪類人群當中。中國史籍當中曾明確區分了東夷、東胡的名稱,他通過梳理史籍當中出現的被稱為通古斯的各集團,認為通古斯人應該是“東夷”,而并非是如歐洲漢學家以及中國一些史學家所認為的 “東胡”,因為東胡應該與匈奴同種,是不吃豬肉的民族。而在中國東北地區,曾存在的古老人群有三類:古亞洲人、通古斯人、東胡人。盡管通古斯人為中國史籍當中的東夷人,但東夷人并不盡然全是通古斯人。凌純聲指出從古代到漢魏時期,中國東北地區的東夷應該是古亞洲族,而到隋唐之后,其主要民族才為通古斯人。有關通古斯人的起源,他亦提及了現存的三種說法,即滿洲地起源說,中國北方起源說,蒙古起源說。他駁斥了史祿國的中國起源說,認為其分析并不可靠,更加認為從史祿國的研究中所推演出來的通古斯人或許和中國南方的部分人群如苗瑤在文化上有相似之處錯誤百出,不可相信。盡管他沒有明確提出通古斯起源地在哪,但他推測認為通古斯人不可能是從中國本土向北遷徙而行,他認為通古斯人應該是從北部地區向南遷移的,這些北部地區可能包括史祿國所談到的馴鹿通古斯所居住的后貝加爾地區,或者是蒙古北部地區。他的理由有三:其一是中國東北部及滿洲地區已經有中國古籍上所記載的古亞洲族居住,其二是后來位于滿洲地區的女真亦是北方而來,其三是北通古斯人的遷移方向同樣是由北方而來。[10]有關赫哲族人歷史的分析,凌純聲依據中國古籍文獻梳理了從隋唐時期黑水靺鞨歷經遼金以及明清時期的演變過程,很明顯可以看出,他的這一做法就是眾多后來學者所說帶有“國族主義”觀念色彩,將赫哲族納入到中華民族的譜系當中,以此給這一人群以定位。而這一思想同樣影響了他在對赫哲族其他方面研究時的取向。盡管《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的大量篇幅都是在對于他所調查到的赫哲族人的現狀進行描述,然而,不然看出,在描述之后,他同樣會將之與中國古籍當中記載的其他風俗相比較,尤其關注與漢人之間的異同,如赫哲人的飲酒方法,就與中國古代的飲酒法相似等。[11]盡管他不同意史祿國有關通古斯人起源中國本部說,但是他也借用了很多史祿國所談及的通古斯人在中國東北受古亞洲人之影響的觀點,如赫哲族的夏帽與日本人、漢人甚至馬來群島人的相似,認為是起源于古亞洲族,并受其影響。[12]
如果將凌純聲的赫哲族研究納入到中國早期民族學、人類學的源流當中去思考,可以看到就如后人對他的評論一樣,他的赫哲族研究是當時中國民族學研究當中“中央研究院”的“歷史學派”的代表。[13]而這一流派后來直接進入臺灣,影響了臺灣很長一段時間內民族學人類學的發展。
有關凌純聲的民族學與歷史學的結合問題,我們一方面可以追溯到凌純聲本身在法國所受的歐陸傳統的人類學的訓練,另一方面,我們需要將之與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的學術流派聯系起來。正如諸多臺灣學者早已關注[14],早期作為中國民族學南派代表的中央研究院,形成了用民族學理論與方法來運用歷史的文獻與材料以試圖解決中國民族文化歷史難題的傾向。[15]凌純聲即是其中重要代表之一,他融合了法國人類學莫斯以來的注重民族志材料細節的特征以及中央研究院關注歷史以構建中華民族這一國族的目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就是建立在他自身扎實的田野調查以及蔡元培、傅斯年、李濟等人的指導之下[16],而此三人正是當時中國民族學、歷史學、考古學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們關注的正是如何在這些學科學術研究之下構建中華民族的問題。在此之下,對于凌純聲來說,“何為通古斯”的問題則迎刃而解:對于正在建構中的中華民族來說,作為通古斯人的赫哲人正是其中之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凌純聲在其后期的民族學人類學研究當中,似乎轉向了一種更為跨區域的尤其是對環太平洋文化的關注之上。他試圖利用各地各人群的文化特質來證明其中國起源問題。他的這一傾向遭到了后人的詬病,認為是帶有國族主義及傳播論色彩的民族學研究。[17]然而,應該看到,凌純聲的環太平洋文化的研究已經與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時的赫哲族研究存在差異,如果說后者有著國族主義的視角,那么前者更應該是一種文明的視野。他也似乎偏向了一種更為類似于史祿國所研究的路徑。盡管史祿國在其后期主要側重于從體質人類學上來解決這一問題,但兩人卻都是基于人群的遷移傳播觀點之上,試圖將起源、族群文化以及歷史過程聯系起來,進行一種跨區域的研究,盡管凌純聲的落腳點在文明,而史祿國落腳點在他所說的“ethnos”。
時至今日,中國的民族學、人類學界研究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重新開始,早已經拋棄了如史祿國和凌純聲似的研究路徑。尤其是結構主義的興起,對歷史問題的關注也開始從傳統的史學方式的探討走向結構與歷史這樣的主題,類如史祿國的“ethnos”的關注其重要性放置在族群、民族等詞匯之上,或者與國族相關,或者與單個視為“文化孤島”的族群有關,其已經大大偏離史祿國關注的意義。而跨區域的研究,則更加絕跡,社區研究方法已經深入中國人類學界。“何為通古斯”或者“何為赫哲族”的問題則已經失去了史、凌兩人曾經賦予他們的視角和意義,或者說,凌純聲式的國族意義仍然在延續,然而卻已轉變得更為狹隘。
[1][4][5][6]史祿國.北方通古斯的社會組織[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1-11.8-9.11.223-224.
[2][14][15]王建民.中國民族學史(上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169.145-160.153.
[3]羅帕廷(I.A.Lopatin).書評,美國人類學家(33),1931.637-639.
[7][8]史祿國.遠東北方通古斯的遷移[J].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雜志,1926,(57).123-183.
[9]李金花.從史祿國的北方通古斯的社會組織看人類學[J].西北民族研究,2010,(1).
[10][11][12][16]凌純聲.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M].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4.43-44.71.74.1.
[13]杜正勝.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M].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285-316.
[17]黃應貴.人類學與歷史研究的結合:以臺灣南島民族研究為例[J].臺大文史哲學報,200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