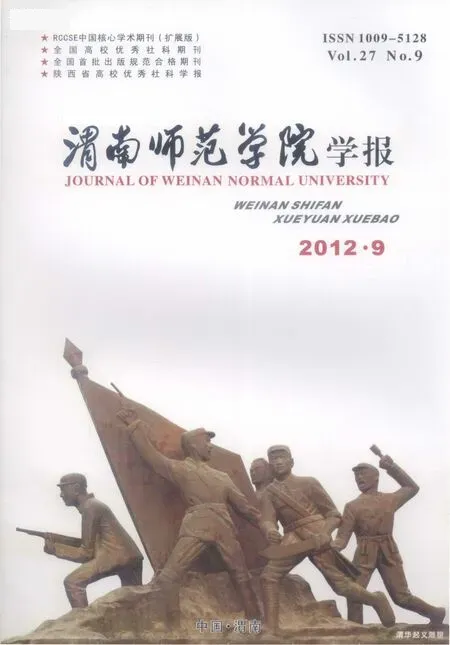論中國文學批評現狀與出路
——以“筆耕文學研究小組”為例
孫新峰
(寶雞文理學院中文系,陜西 寶雞721013)
論中國文學批評現狀與出路
——以“筆耕文學研究小組”為例
孫新峰
(寶雞文理學院中文系,陜西 寶雞721013)
當下中國文學批評深陷模仿和闡釋他人的舊語境中;全媒體時代及“編輯文學”、多模態文學等現實存在,淺批評風行;缺乏問題意識和清醒判斷力,無法克服刻板印象;精神低迷,狀態不佳。而同樣在中國文化沃土里成長起來的“筆耕組”卻很好地規避了中國文學批評的各種不足,堅持中國特色批評路線,得到了作家的認可和社會的肯定,成為中國文學批評領域有意味的品牌之一,為中國當下文學批評提供了思路,作出了示范。
中國文學批評;困境與出路;“筆耕組”;復制;創新
一、中國當下文學批評現狀
無可否認,中國當下的文學批評深陷傳播困境之中,批評的存在本來是為了播布中國的文學作品,卻沒有想到非但未把中國的文學推向世界,自己卻深陷泥淖,處在尷尬和無為的境地。近20多年來,從“失語”、“缺信”和“缺位”、“缺德(缺乏個性體溫、人文關懷)”到“真正透徹的批評為何總難出現?”“文藝批評的鋒芒哪去了?”“全媒體時代文學批評何為”“文學批評死了”等關鍵詞充分顯示了當下文藝批評的現實尷尬和危機。其實這并不只是一個地區的問題。概言之,當下文藝批評成就可觀,問題不少;雖有隊伍,但各自為戰,集體戰斗力不強;評論家和作家關系缺乏默契,批評缺乏有效性;一些評論家缺乏骨格和審美品格,人格依附比較嚴重,口碑不高;批評對象不集中,隨機性強,缺乏長期性、針對性;文人相輕在批評界仍有出現。批評無從用力、或用力不均、或力度高度效度不夠。在新的文學語境和倫理秩序下,文學批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之所以出現這么多不容樂觀的狀況,表面上看是方法論、審美品格或泛文化批評等問題,其實歸根結蒂是批評精神問題。對此,評論家雷達《真正透徹的批評為何總難出現?》、李揚《對新時期文學批評的回顧與反思》、饒先來《當代文學批評發展的困境與趨向》及中國作家網“今日批評家論壇”、近期《文藝報》等均有多文涉及。具體來說,處在當下中國文學批評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與挑戰。可以說,批評界已經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但暫時無力改變。漢語已成為國際語言,中國文學批評還深陷模仿和闡釋他人理論舊語境,無法突破;這種困境主要表現在“無根”的理論困境、“無方法”實踐困境、“無標準”評價困境、“無人”批評人格困境、“無群”批評隊伍分化等。主體缺席;批評明星化、庸俗化、商業化、浮躁化等傾向明顯;全媒體時代及“編輯文學”、多模態文學等現實存在,淺批評風行。缺乏問題意識和清醒判斷力,無法克服刻板印象;精神低迷,狀態不佳。呈現九多九少:名作家批評多,成長中作家關注少;男作家批評多,女作家批評少;表揚多,批評少;花樣批評多,切中肯綮批評少;宏觀印象批評多,精細文本批評少;自娛自樂多,責任批評少;知識搬家多,反思創新少;評論文章多,優質文章少;從業人員多,與大作家對等的大批評家少等。當下,國家品格、民族特色文學批評體系正在重建。“為何評?評什么?怎么評?”仍是學界普遍感到困惑和焦灼的問題,亟需固本培元,返本開新,砥礪創新批評精神。
二、“筆耕文學研究小組”:一個令人驚異的文學批評團體
30多年前,即1981年,全國第一個文學批評家團體——“筆耕文學研究小組”(以下簡稱“筆耕組”)在西安成立,由陜西當時一批中青年文藝評論家組成。組長是王愚、肖云儒,副組長兼秘書長為李星,其他成員有劉建軍、劉建勛、李健民、暢廣元、陳賢仲、蒙萬夫、薛迪之、孫豹隱等,顧問為胡采、王丕祥。1982年擴大吸收陳孝英、李國平等,并由李國平擔任秘書。“筆耕組”在陜西的文藝批評乃至全國的文藝批評中占有著重要的地位。“作為在全國成立最早的文學批評家團體,‘筆耕組’很快就在全國產生了重大影響,不但得到了時任中宣部副部長賀敬之的高度評價,更被相關媒體稱為‘集體的別林斯基’;《紅旗》雜志還專門刊發了經驗文章。”[1]30 年來,“筆耕組”筆耕不輟,直接促成《小說評論》誕生、全國第一個文藝評論家協會在陜西成立。一定意義上講,沒有“筆耕組”,就沒有后來中國文壇的路遙、陳忠實、賈平凹等,也就沒有今天陜西文學輝煌奪目的成就。2011年底,陜西省文聯為“筆耕組”頒發特別獎的授獎詞是:“‘筆耕組’以自覺的文化責任感和擔當意識,開創了陜西文藝批評‘精誠團結,辛勤筆耕,勇于探索,甘于奉獻’的全新傳統,其杰出的創新能力、追求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的精神,體現了批評家難得的才、膽、識、略。其必將成為陜西文藝批評薪火相傳的思想資源和精神動力,從而推動后世的文藝批評。”[1]
談到陜西文學批評,人們最先想到的就是1942年毛澤東“延安時期文藝講話精神”的啟蒙。而真正的開拓者,應該是鄭伯奇、胡采、李若冰等人。鄭伯奇,原名隆謹,陜西長安人。1926年畢業于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學哲學科。1919年參加同盟會,1921年參加創造社,后歷任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教授、黃埔軍事政治學校政治教官,上海創新社負責人,上海藝術大學文學系教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常委,爭自由大同盟成員,上海良友圖書公司編輯,《新小說》月刊主編,明星影片公司編輯,西安《救亡》周刊主編。陜西省立師范專科學校、西北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干部,西北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西北文學工作者協會主任,西北軍政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副主席,陜西省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副主席。中國文聯第二、三屆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第二屆理事。1920年開始發表作品。195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在十七年的秦地批評活動中,鄭伯奇作為五四時期的老作家,和許多老作家一樣,中止了創作而較多地從事文學批評和組織工作。他在本土常是以‘陜西新文藝’的先驅形象出現的,享有較高的威望。”[2]348有《鄭伯奇文集》三卷本行世。“在建國后十七年的文學批評活動中,胡采算得上是秦地批評界的權威。”[2]348胡采向來有“文壇巨匠”之譽。他從 20世紀40—90年代,就出版過《從生活到藝術》《胡采文學評論選》等十本評論集。他高舉“革命現實主義理論旗幟”,以“生活真實在創作中的作用”為準繩,對柳青、杜鵬程、王汶石、柯仲平、魏鋼焰、李若冰,包括后來的陳忠實、路遙、賈平凹等作家予以評論和鼓勵,極大地鼓舞了文學陜軍的士氣。1980年“筆耕組”成立時,胡采就是顧問。在胡采遺體告別儀式上,陳忠實說:“我認為胡采對文學、對作家的理解是深刻的,對青年作家的愛護是發自內心的。”賈平凹說:“我在文學上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不乏胡采的‘點化’之功。”中國西部作家研究中心主任劉衛平說:“無論從哪個角度講,胡采都是一個巨大的存在,在《講話》后的文學發展歷程中,胡采的投影是濃重而巨大的。杜鵬程曾寫過一篇《歷史的腳步》,而胡采的腳步也堪稱陜西文學的腳步。”[3]李若冰主持陜西文聯工作時期,文學陜軍和評論陜軍繼續向縱深發展,保持了相當可貴的銳氣和生氣。加之李若冰本人也是作家,他的文學作品尤其是散文很出色,“大氣清正,崇高堅實”。“自然、社會、生命糅合交織一起,構成李若冰散文的主題話語和精神向度”,其“以赤子情懷擁抱大自然、生活、生命的散文精神仍然是我們珍貴的思想財富,從‘寫什么’這個意義上來說,李若冰散文具有獨特的歷史價值和當代意義。”[4]可以說,從鄭伯奇到胡采再到李若冰,陜西文學批評組織圈始終保持良性健康發展局面,李若冰之后,陜西作家協會書記雷濤(包括省作協副主席、茅盾文學獎評委、小說評論現任主編李國平等)、一度擔任陜西文聯專職副主席的肖云儒(肖云儒期間或之后,陜西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孫豹隱、李震等)自覺成為文學批評活動組織圈的靈魂人物。陜西文學批評事業薪火相傳,自覺完成著“換代”和可持續發展的任務。
“筆耕組”成立伊始,其主要的評論對象便是陜西小說,這對陜西小說創作的促進作用是不可低估的。閻綱曾說:“陜西地面,人杰地靈,既有作家群,又有評論家群。少長咸集,群賢畢至,像筆耕小組這樣一支批評勁旅,全國能數出幾個!雖屬地方選手,卻打出了國家隊的水平……我讀過他們寫的好文章,他們代表陜西小說評論的希望。”[2]350常年浸淫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筆耕組”成員都奠定了自己獨特的理論批評地位。肖云儒有關西部文學的理論已經被學界廣泛接受,其關于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理論至今演繹著不敗神話;“敢言多思”的王愚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就堅持探索中國現實主義文學流變,始終挺立在潮頭浪尖;精警大氣、與時俱進的暢廣元對文學主體論深入細致的研究和探索,以及對中國文學批評文化轉向的相關理論和陳忠實個案研究,至今無人能出其右;陳孝英的喜劇美學理論建樹,開拓了喜劇批評的新的原野;“生拙老辣,意氣縱橫,有古君子之風”的費秉勛的《賈平凹論》,不僅成為新“賈學”研究的先聲,而且得到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廣泛認可。
30年的堅持,“筆耕組”成績輝煌,但是隨之也出現了一些圖解政策、知識結構陳舊、批評態度拘謹、視野不夠宏闊等負面聲音。如楊樂生在肯定肖云儒“對視”書系的價值時說:“從肖提出‘散文的形散神不散’起,中經為現實主義文學正名、審美理想等的有益探索,‘西部美’的理論建構,一直到近數年有關‘長安文化’的深入研究,加之他對幾乎所有藝術門類的探索的散文、隨筆及小說的藝術實踐,都使肖云儒成為研究當代文學、文化藝術乃至一部分當代學術領域繞不過去的一座山。……但是,其論著的缺陷和不足也明顯地存在著的,我以為,除了肖本人原因外(也是主要原因),我們千萬不可忽視時代、社會風氣對肖的影響和制約,這個個案,也完全可以以中國當代學術、理論和批評的縮影目之。”[5]72-75韓魯華也有相同認識:不論就“筆耕文藝評論小組”成員構成的理論素養,還是其文學批評實踐,客觀地講,都不可能是一種完全意義上的本體文學批評,最少,批評的意識形態化的痕跡還是非常明顯的。這是歷史時代所限定的。但是,它難能可貴的是,在國家權力意志和意識形態話語下,盡力向著文學批評本體靠攏。也正因為如此,“筆耕文藝評論小組”對于陜西文學創作的批評,是切合實際的,極大地促進了陜西文學創作的發展與提升。特別是對路遙、陳忠實、賈平凹他們那一代作家的文學創作,給予了引導和指導性的評價。可以說,他們那代作家的創作從中獲益頗多。當然,從今天來看,也有批評的不太妥的地方,比如對于賈平凹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廈屋婆”悼文》代表的一批作品的批評,就有失公允,最少是缺乏歷史發展的前瞻性和敏銳性。雖然如此,其批評的態度則是嚴肅而認真、坦蕩而真誠的[6]。不管怎么說,“筆耕組”建設性探索性批評對陜西文學繁榮做出了突出貢獻。
可以說,通過30年批評實踐,從中國文化沃土里誕生的“筆耕組”很好地解決了方法論等問題,得到了作家和社會的普遍認可,體現出了一定的中國精神和品格。已經成為中國文學批評領域一面旗幟,一個足金的品牌。“筆耕組”是中國文學批評的一面鏡子,其堅持審美個性和文化品格、堅持中西合璧、“別車杜”經驗中國化、創新批評理念,堅持中國特色,用一個聲音講話,不斷學習,積極跟進,重在建設,總結出了柳青道路、路遙經驗、陳忠實視角、賈平凹現象、紅柯筆墨等對全國都有借鑒意義的創作經驗;突破了舊語境的桎梏,為當下文學批評創新提供了思路,做出了示范。
三、“筆耕文學研究小組”批評特色和貢獻
“筆耕組”是在中國當代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領域都占有重要地位的一個作家和文藝家群體。“是當代中國文學批評領域一個極具意味的現象。甚至可以說是當代文學批評體制史上的一種特異現象。嚴格地講,這應當是一種帶有極強的同仁性質的文學批評團體,而非嚴格意義上的體制化的文學批評組織機構。今天的‘陜西文學藝術評論家協會’、陜西省作家協會評論委員會,方是體制下的文學批評組織。‘筆耕文藝評論小組’具有著歷史的超前性,更確切地講,應當是在當代文學批評歷史建構中,凸現著特異性。我甚至認為,這也是1980年初始全國思想解放,各種文化思想潮流所融會而成的改革大潮,所促成的文學批評上一個歷史的幸運”[6]。韓魯華此語可謂一語中的。
除了胡采、蒙萬夫、王愚等已經過世的之外,“筆耕組”核心成員暢廣元、李星、肖云儒、費秉勛等已經70多歲。一定意義上講,其批評經驗必須研究,而且研究就是搶救。眾所周知,“筆耕組”吸取原蘇聯經驗,走的卻是有中國特色的批評路線。他們本著尊重創作,對視作家作品,理解作家的態度,持續介入,跟蹤語境。開展認真的學理批評。其努力告訴我們:西方理論中國化的特色文學批評仍大有作為。與當下作家與評論家關系冷漠不同,“筆耕組”時期,確立了“文藝創作和理論批評相結合”的持續介入批評精神和原則,作家和評論家建立起了難得的良性互動的關系,如陳忠實說“我是被蒙萬夫老師罵出來的”;賈平凹也說“‘筆耕組’敢說實話,能點到穴位上”;作家葉廣芩也說“我之所以能成為一個作家,主要是李星等老師不斷地‘砸’的結果”[1]。“筆耕組”30年的努力直接為當下“創作評論兩張皮式”批評提供了啟發和借鑒。縱覽“筆耕組”30年批評實踐,可謂成就輝煌,經驗可貴。有一個事實已經引起大家的注意,也就是“筆耕組”成立時期,正是“西學東漸”之時。“筆耕組”的成功,一定意義上也是異域方法論在中國文學批評“軟著陸”的成功。陳孝英的喜劇美學批評,薛迪之的比較文學視野,暢廣元、李星、肖云儒等的文學文化批評都已經形成品牌。和中國當下活躍的老作家一樣,陜西這些老批評家更多地吸收了原蘇聯的批評傳統、批評精神。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的批評理念烙印極深,“集體的別林斯基”并非虛妄之言。總攬“筆耕組”30年批評實踐,堅持社會歷史批評傳統,堅持現實主義批評原則和人本主義、人道主義理念,高揚時代精神,以“尊重”、“對視”“理解”作家創作為關鍵詞,不猥瑣批評人格,從階級性、人性、人民性等角度體察中國文學,在批評的文學性方面做了大量“去魅”和“還原”的工作,鞭撻假惡丑,弘揚真善美,批評充滿著時代風格和個性體溫。肖云儒的靈氣,暢廣元的大氣,李星的率真深刻,都以鮮明的批評個性打開了局面。
20世紀80年代“筆耕組”才開始艱難起步,從陜西走向全國。1972年,陜西文藝創作研究室成立,以《延河》雜志1980—1981年連續兩期刊發的“陜西中青年作家專號”,以及配發的曾鎮南長篇評論文章為標志,全國第一個地域性作家群“陜西作家群”開始叫響文壇;同時,以《延河》《陜西文藝》等為平臺,“文學評論陜軍”初步形成;1981年“筆耕組”成立,集體向全國發出聲音,就“寫真實”等問題集中發表意見;1981年夏天,在秦嶺深處太白縣召開“太白會議”等,“筆耕組”成員集中向青年作家陳忠實、賈平凹、鄒志安、李鳳杰等對癥“開炮”,指出創作問題和不足,力促其克服調整創作弱點,向全國一流作家看齊,“筆耕組”聲名鵲起;從20世紀90年代,“筆耕組”成就杰出,這一階段的成就主要表現在,“筆耕組”直接促成了“陜軍東征”這個中國文壇重大事件,路遙、陳忠實、賈平凹、程海、京夫、高建群等作家的長篇作品在文壇集中亮相,引起中國文壇注意;同時,正是在胡采和“筆耕組”努力下,“文藝創作和理論批評相結合”成為陜西文藝工作的主要經驗之一。2011年底,筆耕組背負著沉重的使命光榮謝幕。“筆耕組”已經成為歷史的背影。
可以看到,“筆耕組”的魅力雖然是集體作戰,一個聲音講話,卻個性突出,10余人構成了十個人的文學批評史,形成了獨特的個人批評魅力。“筆耕組”之品牌之所以成功,完全是在科學批評精神指導下,積極規避中國文學批評進程不利因素、堅持投身批評實踐的結果;其不足亦是中國文學批評進程出現的不足;其成功經驗可互補、參照、推動當下文學批評積極調整,突出重圍,創新發展。地處陜西,自由、包容的學術環境和氛圍,是“筆耕組”出現的基本條件;自覺的社會擔當意識和主動獻身文學的精神,使其能在中國文壇發出自己的聲音,一堅持就是30年;“筆耕組”每個人的批評經歷都是一部個人的文學批評史。總體開看,“筆耕組”的文學貢獻主要在三方面:
其一是促成了“陜軍東征”事件,凝聚了陜西作家。
“構成‘陜軍東征’文學現象的代表性作品,除《白鹿原》和《廢都》外,還應包括《最后一個匈奴》《八里情仇》《騷土》《熱愛命運》《蘭袍先生》等作品”。其“出現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國社會處于轉型時期,市場經濟的確立和政治體制的改革對于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撞擊的結果,也是新時期文學發展進程中新舊交替不斷演化的結果”[7]16。盡管對“陜軍東征”這個提法還有爭議,但是陜西有一大批潛力雄厚、實力強勁的作家已經成為文壇公認的事實。自此,散兵游勇的陜西作家有了榜樣,有了歸屬感。商洛作家群、岐山籍作家群、陜北作家群、西安作家群,甚至出現“西北大學作家群”現象,可謂“異軍”突起,群峰鼎立。他們遙相呼應,構成了陜西地域作家群的基本底色。文聯和作協的凝聚力也顯著增強,得到了作家和藝術家們的普遍認同,他們視文聯和作協為“家”。如同李繼凱所說:“對秦地小說家來說,能有這樣一個‘家’,畢竟還是很幸運的,在這個‘家’的安慰鼓勵和幫助下,小說家們多少會快一些走出秦地。”[2]359陜西文學響亮文壇,突出重圍已指日可待。
其二是促成了《小說評論》雜志在陜西誕生。
正是在“筆耕組”努力下,1985年,全國唯一的《小說評論》雜志在陜西誕生,胡采、王愚、李星、李國平先后擔任主編。經過20多年發展,已經成為中國文學評論主要平臺;并一度入選全國中文核心期刊;2008年以來連續入選CSSCI核心數據庫,辦刊質量不斷提升,學術影響力不斷增強,實現了辦刊的歷史性突破。關于《小說評論》創刊,《小說評論》主編李國平這樣說:
《小說評論》是“筆耕文藝評論小組”發展的合乎歷史邏輯的一個結晶。也是進入后“筆耕文藝評論小組”時期的重要體征。就當時的情況看,“考慮到雖然有一支文學批評隊伍,但是,沒有陣地,難以鞏固,難以發展,從1982年起,就有不斷的呼吁創辦一個專門性的理論批評刊物。1984年全國當代文學年會在西安召開,創辦《小說評論》的欲望得到了與會專家、批評家的呼應和肯定。于是《小說評論》順乎時勢,應運而生”。[8]
韓魯華也指出:
進入后“筆耕文藝評論小組”時期,“筆耕文藝評論小組”的個體成員,對于陜西文學評論新人給予了提攜與培養,但是作為一種集體行為,其作用則是十分有限。這樣,《小說評論》就歷史地承擔起凝聚陜西以及全國文學批評力量的責任,發揮了它的陣地優勢。特別是,它以一個專門性的文學評論刊物,吸引了全國一大批從事文學評論,這里自然是指小說評論方面的專家學者,刊登了許多具有前沿性的探討性的學理性的小說批評文章。這不僅在促進陜西的文學創作與批評,發揮了積極作用,就是對于促進全國的小說創作與批評,以及文學理論建設和發展,亦是發揮了積極作用。可以說,系統性閱讀《小說評論》不僅可以看出新時期小說創作發展的歷史路向,亦可把握文學批評及其理論建構的歷史路向。[6]
李繼凱這樣評價:
多年的實踐證明,《小說評論》的確是小說家(尤其是秦地小說家)的益友和諍友,她為秦地小說家提供了一面鏡子,同時,在一定意義上講,她也成了秦地小說家與評論家密切合作的一種象征。[2]351
其三,形成了“陜西特色”的“青創會”等創作評論研討會議制度,鍛造了一支在全國有競爭力的創作和評論新軍。
和作家結朋友,“一對一”進行批評是“筆耕組”的傳統。陳忠實對此頗有體會:“《筆耕》文學評論組的幾位主筆,對陜西新時期冒出的幾位青年作家一直關注其創作發展動向,卻不知是有意分工或是各有偏愛,又都有各自研究的作家對象,關注并指點我的創作的是西北大學中文系的蒙萬夫教授,寫有專論。蒙老師不幸中年早逝,西安文理學院的王仲生教授又偏向于對我寫作的關注。”[9]“筆耕組”進行批評的主要方式就是開文學討論會。李繼凱曾就新時期以來的秦地文學“會議文化”進行過考察。他說:
1978年12月25日,作協、《延河》編輯部舉行座談會,為杜鵬程及《保衛延安》平反;1979年5月24日,《延河》編輯部召開文學專題座談會;1980年7月10日,《延河》編輯部召開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分析創作現狀;1981年11月12日,作協、西北大學、陜西師大、省現代文學學會、《延河》編輯部聯合召開《創業史》及農村題材創作研討會;1982年2月10日,“筆耕組”召開賈平凹創作討論會;1983年12月27日,“筆耕組”召開座談會,討論近年來的有影響的30余部中篇小說,包括路遙《人生》、賈平凹《二月杏》等;1984年3月22日,作協召開農村題材創作研討會;1985年8月20日,省作協召開長篇小說創作促進座談會。自1986年后,秦地文學界各類會議更有增加,僅長篇小說討論會每年都要召開一次或多次了。……在秦地,文學討論會大多是嚴肅的。……80年代的“筆耕組”成員大都深受傳統的三秦文化的影響,仍能保持嚴肅慎重的批評風格……[2]354
其中20世紀80年代初陜西作協在太白縣召開的“青年作家創作會議”可謂影響深遠。“會上,王愚、肖云儒、李星、劉建軍、蒙萬夫等作家評論家,針對陳忠實、賈平凹、京夫、鄒志安4位當時的青年作家進行了尖銳激烈的批評,這次會議讓陜西文藝界至今難忘,是劃時代的、里程碑式的會議。”[10]1984年,在陜西文聯舉辦的相關評獎會議上,“筆耕組”和《延河》獲得“陜西文藝開拓獎”中的“知音獎”;2011年12月30日,在陜西文聯“第二屆陜西文藝評論獎”頒獎會議上,“筆耕組”集體榮獲“特別貢獻獎”。在此,筆者還想強調有三次研討會也應該載入史冊。其一是1998年8月18日至20日,陜西省作家協會在秦嶺主峰太白山下的眉縣湯峪召開了專題研討會,對當時創作比較活躍的六位中青年作家及其作品進行了討論。這是繼1997年在延安召開的全省青年作家會議之后,陜西召開的又一個主要以青年作家為對象的創作研討會。50余名評論家、編輯參加,對王觀勝、葉廣岑、馮積歧、冷夢、紅柯、寇揮六位作家進行研討。其二是1999年9月2日,由陜西省作協、陜西省文聯、寶雞文理學院主辦的“紅柯作品研討會”在西安召開。陜西及來自京津的40余位評論家及有關人士參加了研討會。現在陜西文壇已經進入了“紅柯代”。其三是,“2008年12月8日,陜西召開賈平凹獲茅盾文學獎表彰暨陜西省青年文學創作會議,邀請了李星、梁向陽、周燕芬、常智奇、趙德利、暢廣元、段建軍、楊樂生、馮希哲、沈奇等十位評論家和賈平凹、馮積岐、張虹、紅柯、冷夢、王觀勝、朱虹、閆安等十位作家對寇揮、張金平、劉愛玲、林倫、黎峰、丁小村、高鴻、楊則偉、李小洛等十位青年作家進行了‘對文不對人’的認真細致的分析和評論”[10]。媒體稱與“太白會議”不同,這種“二對一”即每位青年作家對應一位評論家和資深作家式批評方式獨創,其實早在筆耕組主筆暢廣元編輯《神秘黑箱的透視》一書時就采用過“青年評論家先發言,作家回應,老評論家再批評”的模式。陜西已經形成了召開研討把脈診療作家創作的制度。可以說,陜西文學研討會已經走向成熟,其有效性不言而喻。各種各樣的研討會成為“筆耕組”展現自我個性,促進陜西文學爭先進位的當然的主要平臺。在“筆耕組”影響下,陜西文人民間雅集文學沙龍蔚然成風。
正是長期不斷地建設性批評,對陜西青年作家不間斷地幫助、推進,《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等先后獲得茅盾文學獎。可以說,“筆耕組”及其為主體的評論界為陜西文藝崛起做出了歷史性貢獻。正如暢廣元所說:“陜西文學評論界有兩個特點,一是團結;二是尊重作家。”[11]547尊重和團結并不是放棄原則,在“筆耕組”身上,找不到“月是故鄉明”的小家子批評意識。熱切關注不冷漠;實話實說不藏著;做作家知音,不做敵人;提前預警,雪中送炭;堅持思想的、歷史的、審美的、藝術的、文學的標準,重在建設,而不是亂棒打死,再踩上一腳。針對作品不對人,名家普通作者都關注。全程“介入”創作過程,及時進行幫扶指導。在30年的批評實踐中,“筆耕組”逐漸形成了鮮明的批評品牌:諸如“精誠協作、辛勤筆耕”的“筆耕組”共識;團結就是力量;骨氣形成品格;敢言形成風格;堅持形成性格;深度介入創作等。筆者也完全認同韓魯華教授指出的“筆耕文藝評論小組”的同仁性和本體性。他說:
“筆耕文藝評論小組”出現于80年代初,不可能脫離體制的約束,但是,就其發起的情形看,可以說,是陜西一批鐘愛于文學批評的同仁,為了促進陜西乃至全國文學創作的繁榮與發展,而走在了一起。或者說,它是“一個民間文學研究團體”,“聚集了一批文學批評力量,在全國也造成了相當影響”。這是一種文學批評的自覺地行為,而非完全的體制文學批評行為。因而,也就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去非文學功利性的意義。[6]
“筆耕文藝評論小組”的文學批評史的價值和意義,是不可忽視的。甚至它在這方面的探索,仍然對于我們今天文學批評體制的建構與變革,可以提供極富歷史意義的啟迪。筆耕組有自己的評價標準,主要堅持歷史的、審美的、文學的標準,針對作品不對人,全程介入。我以為筆耕組的批評關鍵詞主要是尊重、理解、對視,尊重作家創造;理解作家心理,是對視而不是俯視、仰視、斜視。2000年9月,中國文壇發生“博士直諫陜西文壇事件”,陜西籍評論家李建軍當面對陳忠實、賈平凹作品《白鹿原》《懷念狼》以及公認有成績的陜西文學和批評界發難,指出陜西文學創作和批評存在重大問題,此后以《三秦都市報》為平臺,學界、社會各界對此展開爭鳴討論,被稱為“博士直諫陜西文壇事件”。2007年,在陜西召開“新時期陜西文學三十年研討會”上,李建軍在陳忠實、賈平凹因故缺席的情況下,發表了長篇演講,主要指出陜西文學從創作到批評問題多多,不容原諒。其實面刺作家創作不足甚至失誤一直是“筆耕組”堅持的風格,從一定意義上講,從陜西文壇走向全國批評界的李建軍是未進入“筆耕組”的“筆耕組”成員,該事件可以看作是“筆耕組”批評風格歷史的回聲。
毋庸諱言,“筆耕組”對陜西文學批評力量的換代和交接做出了貢獻。韓魯華指出:
《小說評論》,在后“筆耕文藝評論小組”時期,一方面可能仍然延續著“筆耕文藝評論小組”文學批評的傳統或者歷史責任。一個有力的證明就是,《小說評論》的編委會構成的基本成員,絕大部分是原來“筆耕文藝評論小組”的主將,一直承續到今天。最近一期(2011年第6期)《小說評論》編委會11位編委,其中8位是原“筆耕文藝評論小組”成員。另一方面,《小說評論》發揚光大了陜西文學批評,包括“筆耕文藝評論小組”的優良傳統,并且經過20多年的不懈努力,進入全國文學批評刊物的前列,甚至可以說,在當代中國文學研究與評論領域,具有其不可替代性。特別是在發現培養文學批評新生力量方面,可以用功不可沒來評價。在陜西文學評論界,80年代的青年,今天已步入中年的文學評論家,很少沒有得到《小說評論》的扶持和提攜。就是從全國而言,亦有后來知名的文學批評家,或者得到了《小說評論》的大力扶持,或者就是從《小說評論》走向文學評壇的。[6]
可以看到,“筆耕組”筆耕不輟,度過了波瀾壯闊的30年。翻覽30年的《人民日報》和《陜西日報》,“筆耕組”批評活動報道此伏彼起,基本從無間斷。“筆耕小組的活動和聲名,在全國文壇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活躍時期,《陜西日報》逢會必報;《人民日報》文藝版詳細報道過如‘1982年賈平凹創作研討會’等主要觀點;中央報刊更是重點關注。約在1984年,時任中央研究室文藝組組長的陳涌來西安考察文藝工作時,在多種場合提到并肯定了筆耕小組。”[12]415在“筆耕組”示范帶動下,作家理論水平提升很快,許多作家創作評論雙豐收,如路遙的《早晨從中午開始》創作談已經成為路遙研究“不動產”;作家紅柯關于文學邊疆精神的創作談被《光明日報》發表,其《敬畏蒼天》文集中許多創作談也已成為研究西部文學不可或缺的資料;賈平凹的《平凹文論集》已經脫銷。啟發當下批評家,只要出于公心、大道,中國特色文學批評大有作為,路就在腳下;“筆耕組”相關創新批評經驗可以復制、推廣,其是陜西的,更是中國當下文學批評創新寶貴的民族經驗、國家經驗之一。
[1]筆耕組三十年筆談[N].陜西日報,2012-01-09(6).
[2]李繼凱.秦地小說與三秦文化[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3]王鋒.文壇慟別胡采[N].華商報,2003-09-25(1).
[4]馬平川.李若冰散文的當代意義[N].光明日報,2007-02-02(11).
[5]楊樂生.關于肖云儒“對視書系”答記者問[M]//選擇的尷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6]韓魯華.“筆耕文藝評論小組”與當代文學批評[EB/OL ]. http://blog. sina. com. cn/s/blog _4d34676601012cs2.html.
[7]陳傳才,周忠厚.文壇西北風過耳——“陜軍東征”文學現象透視與解讀[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
[8]李國平,姜廣平.本刊主編答姜廣平先生問[J].小說評論,2009,(1):4 -10.
[9]陳忠實.《白鹿原》創作手記(下)[N].陜西日報,2009-07-31(8).
[10]若星,等.文學重鎮春潮涌[N].文化藝術報,2008-12-27(7).
[11]暢廣元.神秘黑箱的窺視[M].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12]陜西省委宣傳部,等.陜西文藝三十年[M].西安:太白文藝出版社,2011.
【責任編輯 朱正平】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Outlet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Taking Writing Literature Research Group as the Example
SUN Xin-feng
(Chinese Department,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Baoji 721013,China)
the present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interpretation are in the context of imitation of others.The Media Age and Editing Literature and multi-modal literature exist,but lack of deepened criticism,such as shortage of problem awareness and sober judgment,incapability to overcome stereotypes,with low spirits and poor condition.But in the fertile soil of Chinese culture the Writing Group can well avoid the shortcomings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holding to Chinese characteristic criticism route,and has been recognized and affirmed by the community author.It becomes China’s literary criticism presenting the famous brand of being awareness,which offers the thinking way for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and sets a model for it.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predicament and outlet;Writing Group;replication;innovation
I206
A
1009—5128(2012)09—0064—07
2012—05—05
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當代文學的新鄉土敘事比較研究(11XZW019);陜西省教育廳科研計劃項目:陜西“大學作家群”現象研究(11JK0253)
孫新峰(1972—),男,陜西洛南人,寶雞文理學院中文系教授,文學碩士,主要從事陜西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