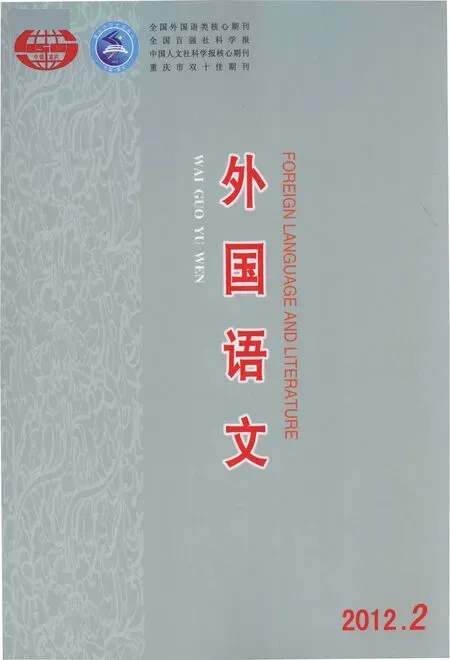抗戰歷史語境與重慶的文學翻譯
廖七一
(四川外語學院 翻譯研究所,重慶 400031)
1.抗戰時期重慶文學翻譯的特征與翻譯策略
作為戰時中國的首都,重慶成為全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中心。大批高校、出版機構、報刊雜志和文化團體西遷,無數文化精英匯聚重慶,為重慶的翻譯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在重慶翻譯、出版的文學翻譯作品從戰前的幾乎為零迅猛增加,到1944年超過全國翻譯出版總數的一半。
1939年,國民政府頒布了《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及《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辦法》。“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得到了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全國各個階層和全體國民的認同。1939年4月2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中央為開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告全黨同志書》中,重申了《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的正確性、權威性”,并指出:“國民精神總動員,應成為全國人民的廣大政治運動,精神動員即是政治動員。”(靳明全,2003:41)抗日民族解放的主流政治意識形態由此得到確立。
1938年,梁實秋在《中央日報》副刊的《編者的話》中說:“現在抗戰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筆就忘不了抗戰。我的意見稍為不同。于抗戰有關的材料,我們最為歡迎,但是與抗戰無關的材料,只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不必勉強把抗戰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戰八股’,那是對誰也沒有益處的。”(梁實秋,1938)梁實秋的言論雖然不乏合理之處,但立刻遭到羅蓀、茅盾、宋之的、胡風、沈起予、陳白塵、張恨水、黃芝崗等尖銳批評,認為“戰爭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主要樞紐”,“擴大到達于中國底每一個纖微。想令人緊閉了眼睛,裝做看不見,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羅蓀,1938)。主流政治話語的排他性和強制性可見一斑。
在抗戰民族解放的宏大敘事下,各個文學期刊的發刊詞,都將文學藝術視為抗戰的有效武器。《文藝陣地》稱本刊是“戰斗刊物”,任務是“如何構筑陣地,如何配備火力,如何洞明敵情而給以致命的打擊,如何搜尋后方的間諜與漢奸而加以肅清”(王大明、文天行、廖全京,1984:325)。《七月》和《希望》稱“在神圣的火線下面,文藝作家不應只是空洞的狂叫……[要]提高民眾底情緒和認識,趨向民族解放的總的路線”(同上,353-354)。《天下文章》稱“我們抗戰建國的偉業,需要有堅穩的物質的經濟基礎,也需要有充分的精神食糧”(同上,576)。《抗戰文藝》稱“首先強固起自己陣營的團結,掃清內部一切糾紛和磨擦……把大家的視線一致集注于當前的民族大敵”(唐沅,2010:2659)。《詩文學》稱“為了受難中的祖國,我們得獻出那一份熱情,那一點血汗,為了反映艱苦抗戰的最后階段的可歌可泣的史跡,我們得堅持我們詩的崗位”(唐沅,2010:3230)。
與當時主流的文化藝術活動一樣,重慶的翻譯文學“就其政治傾向而言,是抗日救亡的;就其思想特質而言,是民族解放意識”(靳明全,2003:55);因而其主體無可非議是為抗戰服務的。在戰時特殊的歷史語境下,重慶的文學翻譯呈現出如下突出的特征:關注翻譯作品的社會功能,強調主題的趨時性和形式的大眾化,在多元的翻譯策略中偏重節譯、編譯甚至改編。翻譯活動不僅僅是簡單的文化交流,同時也是中國戰時文學創作、世界反法西斯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重慶的文學翻譯為抗戰主流政治話語的建構、民族文學的發展,以及“民族人格精神的重塑”(靳明全,2003:24)都產生了不可估量的積極影響。
2.戰時文學翻譯的趨時性
戰時的翻譯活動最明顯的特征之一是趨時性,即文學翻譯為當下現實服務。也有學者將戰時重慶文學的特征表述為“戰時性”(靳明全,2003:45;徐驚奇,2009:172)。
文學翻譯的趨時性首先表現在待譯作品的主題選擇上。救亡、愛國、反抗法西斯侵略等文學作品被大量譯介,其比例之高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時期。戰時重慶文學翻譯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反法西斯戰爭文學、紀實性(報告文學)、經典名著和現代派作品,前兩類占了絕大多數。即便是經典名著和現代派作品,譯者或批評家通過譯序、譯跋或譯評,也將其中體現出的民主、自由、平等,甚至對愛情的向往或對黑暗的抨擊,都轉換成積極的精神資源,與當下的抗日戰爭產生了關聯。莎士比亞戲劇的翻譯與演出就雄辯地證明普世價值的弘揚同樣對中國人民的抗戰產生著積極和深遠的影響。
抗戰翻譯文學的趨時性還表現為翻譯的時效性,即文學翻譯家時刻關注國際文壇的動向,翻譯文學與國際文壇保持同步。翻譯家對國際反法西斯的文學作品非常敏感,許多作品一經出版立刻有翻譯家著手翻譯,很快在國內便有中文本出現。僅以《抗戰文藝》上發表的幾篇譯文為例:
《在特魯爾前線》(馬耳譯):原文發表于1938年2月5日;譯文發表于同年的第一卷第八期(1938年6月);
《第四十三師團》(戈寶權譯):原文發表于1938年6月;譯文發表于同年的《武漢特刊》(1938年9月17日);
《西班牙戰爭中的詩人們》(高寒譯):原文發表于1937年11月;譯文發表于第二卷第一期(1938年6月);
《巴塞龍那上空的“黑鳥”》(馬耳譯):原文發表于1938年5月;譯文發表于同年第二卷第四期(1938年8月13日);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八日》(戈寶權譯):原文發表于1938年7月19日;譯文發表于同年第三卷第二期(1938年12月);
《跟著碼頭工人前進》(王禮錫遺譯并跋):原文寫于1938年8月之后,譯文發表于第五卷第四、五期合刊(1940年1月)。
原文和譯文發表之間的時間差長的不到一年半,短的僅3個月。有學者對《時與潮文藝》上譯文的時差做過統計:
第1卷第1期,《月亮下落》是1942年春在美國出版的,重慶刊出時間是1943年3月15日,相隔一年;第2卷第4期,《不愿做奴隸的人》是英國1943年的最新作品,重慶刊出時間是1943年12月15日,同年刊出;第3卷第2期,《侵略》是1943年的獲獎作品,奧哈拉系列作品,是1943年紐約Avon書店出版的,兩文在重慶的刊出時間是1944年4月15日;第3卷第5期,《海的沉默》譯自1943年10月11日的美國《生活》雜志,重慶刊出時間是1944年7月15日,相隔九個月;第4卷第3期,參桑系列作品,是英國1944年出版的,重慶刊出時間是1944年4月15日,相隔時間更短;第5卷第1期,《亞達諾的鐘》,是1944年夏出版的,重慶刊出時間是1945年3月15日。(徐驚奇,2009:43-44)
更有意思的是,一些重要的作品還會有多個翻譯家搶譯,出現多個中文譯本同時出版或在短期內陸續出版的現象。如斯坦貝克的《月亮下落》在一年內就出現了5個不同的譯本:馬耳(葉君健)的譯本《月亮下落》(《時與潮文藝》創刊號,1943年3月15日);劉尊棋譯《月亮下去了》(重慶中外出版社,1943);趙家璧譯《月亮下去了》(桂林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1943);胡仲持譯《月落烏啼霜滿天》(開明書店,1943)、秦戈船[錢歌川]《月落烏啼霜滿天》(重慶中華書局,1943)。
威爾基的One World在美國出版之后,國內前后也出了5個譯本;最早的兩個是重慶中外出版社(1943年8月,劉尊棋譯)和重慶時代生活出版社(1943年9月,陳堯圣、錢能欣譯)的《四海一家》。其他譯本的書名還有《天下一家》、《自由中國》等。
美國飛行員勞森的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有三個譯本。重慶的兩個譯本分別為《我轟炸東京》(徐遲、錢能欣合譯,重慶時代生活出版社,1943年12月)和《東京上空三十妙》(白禾譯,重慶復旦大學文摘出版社,1943年12月)。一年以后,又有另一個譯本《轟炸東京記》。蘇聯劇本《蘇瓦洛夫將軍》也有四五種譯文。在戰時物質極端匱乏、生活條件極端惡劣的情況下,同一作品出現多個譯本非同尋常;只能說明翻譯家和文化界對相關資源認可的一致性和利用的迫切性。時效性在紀實性作品和報告文學的翻譯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3.戰時文學翻譯的大眾化
抗戰時期重慶翻譯文學的第二個特點是大眾化。大眾化主要體現在文學翻譯主題內容貼近普通軍民,形式通俗化,語言口語化;這是戰時文化運動的普遍要求。當時文藝界對大眾化和民族形式進行過廣泛的討論,并為推進通俗文化運動做出了種種努力:“‘文協’召開了怎樣編制士兵通俗讀物座談會,對通俗作品創作的原則和方法等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還于1938年舉辦了通俗文藝講習會,講解通俗文藝創作的理論與創作。”(靳明全,2003:81)文藝家必須以廣大抗戰軍民為對象,充分考慮大眾的理解與趣味,使文學藝術成為喚起大眾、組織大眾的武器。老舍(1938:34)提出要“出版一百種 供給士兵閱讀的通俗文藝讀物”,并強調“用詞造句,一定要注意。像有些新字新句實在為大眾所不懂”(同上,35)。姚雪垠認為,抗日民族解放戰爭中文藝工作者是文化戰士,“我們必須盡可能的用大眾口頭上活生生的語言寫作,并由此而發展嶄新的表現技巧,更發展嶄新的通俗文體”(姚雪垠,1938:42)。姚蓬子將文藝的功利性與大眾化聯系起來,稱“我們要以文藝的力量去提高廣大的落后民眾的抗戰情緒,首先要使我們的作品能夠接近民眾,不僅要使民眾看得懂,而且看了之后要有興趣”。如果在抗戰的炮火中文藝作品能“發生巨大的力量”,他就是“一個歷史上的最偉大的民族藝術家”(蓬子,1938:82)。夏衍(1938)甚至提出:“文藝不是少數人和文化人自賞的東西,而變成了組織和教育大眾的工具。同意這一新定義的人正在有效地發揚這一工具的功能,不同意這一定義的‘藝術至上主義者’,在大眾眼中也判定了是漢奸的一種了。”大眾化和藝術形式的通俗化被提升到空前的政治高度。
在民族危亡的緊迫關頭,翻譯的功利性日益得到強化。翻譯已經不再是翻譯家或藝術家手上的把玩,讀者對象、翻譯的功能、翻譯預期的社會效果都因歷史語境的變化而與其他時代有著非常大的差異。
首先,翻譯有明確的服務對象——預設的讀者。戰時所展開的文藝論爭,譯者所撰寫的譯序、譯跋,批評家所發表的譯評,都一致明確指出,讀者不是高高在上的精神貴族或封閉在象牙塔里的專家學者。只要與晚清翻譯家心目中的讀者——“出于舊學界而輸入新學者”(覺我,1997:336)比較,我們就會明白,戰時的讀者是全體抗戰的軍民。這樣的讀者定位直接決定了翻譯的內容和主題:戰爭和紀實類文學翻譯超過一半以上。有批評家就指出,要積極將西班牙“爭取他們的自由與獨立的反法西斯的斗爭”的作品翻譯過來,“西班牙的抗戰文學,是他們兩年來英勇斗爭的反映”(權,1938:35)。
為了達到激勵抗戰斗志、建立必勝信念,《抗戰文藝》還提出了“‘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口號,號召作家深入戰地和農村,寫通俗文藝,宣傳抗戰,反映抗戰,廣泛發動民眾參加抗日斗爭,直接為抗戰服務”(虞和平,2006:17)。文學翻譯也是如此,“不少譯本還紛紛出‘通俗版’,這種通俗版譯本直到戰后還在解放區廣泛流行,如蘇聯瓦希列夫斯卡婭的《虹》、戈巴托夫的《寧死不屈》等。1944年人文出版社還遵照戰時節約原則,創用袋納本形式,推出‘西洋最暢銷書叢刊’,多為原著凝縮譯本,其中有報告文學《東京上空三十秒》、《美國納粹黑幕》等。”(鄒振環,1994:91)
從更宏大的文化語境來觀察戰時的文學翻譯,其意義不僅對啟發、激勵人們投身于抗日民主斗爭意義深遠,同時對擴展我們的文學視野,提高我們的藝術表現力,從而推動民族新文藝的發展也有重要作用(柳岸,1984:18)。不僅如此,抗戰翻譯文學作為抗戰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其目標是抗戰“新啟蒙”。有學者就認為,抗戰新啟蒙運動的內容可以概括為“民主的愛國主義”和“反獨斷的自由主義”(鄒振環,1994:94)。從這樣的意義上看,抗戰文學翻譯不僅要為我們的抗戰文藝提供借鑒,提供新的視角、新的材料、新的表現形式,甚至也不僅僅是文化交流,而是中國偉大的民族解放和全世界發法西斯戰爭中國民人格精神的重塑與建設。正如創辦《西洋文學》的同人所表現出的遠見卓識:“我們認為文學不僅是表現人生,表現理想……它教我們怎樣做‘人’,做一個‘時代的人’……雖然是在非常時期,我們決不能忽視文學。相反地,同人以為現在正需要它的激發與感化的力量。”(程麻,1992:70)這樣的社會目標使戰爭文學、紀實類文學和經典名著的翻譯有機結合起來,從而也使確保抗戰的最后勝利與民族文化的長遠發展有機結合起來。
4.多元的翻譯策略
在抗戰特殊的歷史語境中,文學翻譯的文化使命使重慶的翻譯呈現出翻譯策略上的多元性。節譯與編譯在紀實類文學中比較普遍,改編和改譯在戲劇翻譯中特別明顯,而忠實原則和名著意識則在經典名著和現代派文學的翻譯中體現得尤為充分。如果要將翻譯家作粗略的分類,從事紀實類文學翻譯的多為政治活動家,從事戲劇翻譯或改編的多為藝術家,而從事經典名著翻譯的多為高等院校的學者專家。
戰爭與紀實類文學作品的翻譯注重社會功利和讀者反應,在翻譯策略上譯者主動適應文化水平不高的廣大抗日軍民,通常采用節譯或編譯策略。原作的藝術性通常讓位于作品的道德寓意或與中國抗戰的關聯性。與戰時國情不太相關的情節或描述通常被刪除,反之則可能被過度渲染,甚至增添與原文無關的道德宣教,故事情節簡潔明了,語言通俗、易懂是譯作表現形式上的首要追求。如徐遲選譯的《在掩蔽壕里——美國兵是這樣的》就是一例。文章選譯的是美國戰地記者恩尼·帕艾爾(Ernie Pyle)的小說。該書1943年4月出版之后風行一時。徐遲在《譯者小序》(1945:42)稱:“本名叫Here Is Your War,這是你的戰爭。因為這名字是給美國人看的,我譯到中國來給中國人看,改成今名,另外還加了一個小標題。我所選譯的,也是或多或少,順從了這個小標題,而在它的范圍之內抉擇段落的。因為我相信,我們做什么事情都得實用一點,登上一點文章也得求其切合實用。”為了給中國人看,徐遲不但改變了書名,選譯內容也要求“切合實用”;翻譯家自覺地承擔起宣傳家和政治家的責任。前面提到的“袋納本”、“通俗版”和“凝縮譯本”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節譯、編譯甚至改寫的翻譯策略。
戲劇類作品的改譯、編譯、改編是抗戰時期重慶文學翻譯中影響最為廣泛、也是最富有特點的翻譯類型。有學者在對山城戲劇節的感言中就說道:“戲劇在現階段的中國,是藝術之類里最受尊崇的驕子。這種現象可以從作家,民眾與政府三方面看。從作家方面說,抗戰以前寫戲劇的人仍然在寫,即不寫戲劇的人,因種種關系也寫劇,結果寫劇的人,較寫文學其他部門的人為多。從民眾方面看,每個劇的上演,都是轟動山城,足證明民眾對戲劇的愛好。再從政府一方面看,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曾特別規定戲劇不得援其他文藝書籍的例事后送審,而須事前送審……證明政府對戲劇的特別重視。”(冬,1945:2)這段話明白無誤地傳達出戲劇特有的社會性、宣傳性和教育性。外國劇本進入中國戰時語境,必然會發生一系列的變化;戲劇的直接性、廣泛性和直觀性客觀要求戲劇翻譯特別注重演出效果;因而劇情的簡潔明了、表演樸素流暢、動作直觀、布景簡單、語言對白通俗成為翻譯的重點考量,這也成為劇本演出成功與否的關鍵。如根據蘇聯劇本改譯的《人約黃昏》,其情節與對白就完全中國化:
他:璐璐!璐璐!
她:什么璐璐不璐璐!告訴你,我并不是什么璐璐小姐。我的姓名你以后自然會知道的。哼,真是個老實的家伙,你真的以為我跟你帶來了你母親的消息嗎?唔,時間不能再耽誤了,現在我們來談談正經事吧!你先聽我!
他:你瘋了嗎?
她:這現在已經明白了,你聽著:第一,我不是什么璐璐小姐,第二,我從來就沒有看見過你的母親,我只打聽到了一點關于他的情形,因為我要完成我的任務,要拿到你的文件跟你本人。
他:拿到我的文件跟我本人?
她:是的,你們這些文件!就是因為有了你們這些文件,這些軍事計劃,才使得東亞和平不能恢復,東亞新秩序,建立不起來,同時你們汪先生很好的主張也不能實現。這幾次大會戰,在湘北,粵北,在桂南,我們大日本皇軍死傷了成千成萬,還不是你們這些計劃在作怪,對不起,你的那些計劃已經在這兒了。至于你本人,又聰明又能干的你,我們也很需要你替我們工作。好了,連你本人今天也落在我們手里了……(孫施誼,1940:39)
翻譯家在譯序或譯跋中往往會不厭其煩地討論翻譯本土化的必要性。孫施誼曾撰文專門列舉了《人約黃昏》所做的改動:
首先,劇底內容——時間,人物及其身份完全改成了中國的,自不消說。
其次,原作中的女性,是蘇聯底內奸,——敵國底雇傭間諜。改作……漢奸,當然也并不失它在我國的政治意義,因為我們底抗戰陣營里,并不是找不出為敵人作間諜的“摩登女性”(劇壇正應該特別當心!);不過,我底改作,卻把“她”變成了一個正面的敵人——“在中國生長,說得一口好中國話”的日本女子了。這變更當然不是一點沒有來由的:第一,因為改成日本女性后,也并不致減損肅清內奸這一主題底任何方面;而且,因為將提線人抓出臺上來了之故,反可多提醒觀眾之政治的警覺。第二,因敵人之正面出現,不僅為的是更鼓起觀眾底同仇敵愾之心,而且還是想表現在這一種疆場上,也正有一場我敵底無形大會戰……和湘北,粵北,桂南諸役的會戰一樣,在這種蒙面的疆場,雖為斗智,然其緊張,其激烈,其為國之忠貞與智勇,亦正與沖鋒陷陣無殊?(孫施誼,1940:43)
劇本發表于1940年3月;劇本中提到的湘北、粵北和桂南的戰役正是剛剛結束的中日之間的戰斗。改譯或改編的意圖顯然是為了適應戰時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戰爭需要,符合“積極的主題,現實的題材,正確的啟迪,響亮的號召”(劉念渠,1944:107)。
改編的另一個原因是適應戰時的演出條件和觀眾的接受條件。在抗戰的中后期,大后方的經濟日益艱難,這也為戲劇演出造成很大的困難。《一九四三年重慶舞臺》一文就說明了經濟形勢與戲劇改譯之間的關系:“外國劇本的演出,要求著充分的人力,物力與時間,否則,那將是一種浪費;而這一年里,各個劇團所感到的經濟上的困難正與日俱增,心有余而力不足。《馬門教授》和《俄羅斯人》不是沒有人打算演出,卻不能輕易的冒險……從前希望多兩個布景的,現在倒希望少兩個了。這也是經濟困難中的要求。”(劉念渠,1944:106)孫施誼的改編正是為了適應戰時的演出條件,有利于“一切團體之采用”:(1)只需要兩個演員;(2)布景簡單,可以特制,也可以不要;(3)道具只要三件:一桌一椅一沙發;(4)音響用一個汽車上的喇叭就行;(5)光影有,自然最好,沒有也沒關系。(孫施誼,1940:44)
最后,改譯也是為了達到理想的舞臺效果。焦菊隱在《希德》的譯者附言中就說,已經有兩種譯本,但“兩種本子都僅適于誦讀。現在為了上演,不得不重譯一次,把其中辭藻雖美而意思重復的地方,一律縮短,以免舞臺上產生冗贅單調的效果”(張澤賢,2009:301)。在《狄四娘》改譯后記中,張道藩陳述了改譯的初衷:“因譯文對話不甚通俗,且以經濟關系,對于服裝布景等均不能按照意大利當時(15世紀)情景設備,故不能使觀眾得深切之了解。惟在現在之話劇界,經濟大都缺乏,莫謂不能照著者設計從事設備,即能,若由一般不慣西人(尤其古代人)生活,不懂西人風俗之演員演出,亦卻不易使人滿意。故不如改譯成一中國故事,不惟便于演出,而且使觀眾易于了解。”(張澤賢,2009:367-368)
類似的編譯或改譯劇本絕非個案。如王語今翻譯、徐昌霖改編的蘇聯烏利亞斯基的短劇《驛站》,易名為《兩位老粗跟一個女人》,發表于《戲劇崗位》(第三卷第五、六期合刊,1942年5月);陳治策改編蕭伯納的《斷頭臺》、夏衍改編的托爾斯泰的《復活》(重慶美學出版社,1943年5月)、李慶華根據奧尼爾《天外邊》改編的《遙望》(重慶天地出版社,1944年5月)、柯靈根據《飄》改編的同名劇本(重慶美學出版社,1944年)、王光鼎改編的《亂世佳人》(重慶大地出版社,1945年3月)等等。有學者曾做過統計:1937~1945年出版的改譯劇本的單行本就達79種,約占整個劇本總量(110種)的72%。(王建開,2003:234-235)
改編或改譯往往使故事完全中國化,翻譯與創作的界線已變得非常模糊。傳統的翻譯定義已經擴展,原來所接受的翻譯策略已不再適應戰爭期間的戲劇翻譯;刪減、增添、編譯,甚至取便發揮都成為特定時期為了特定目標進行特定文類翻譯所允許的翻譯策略或方法,有的戲劇家甚至將中西不同的劇本糅合成一體。如顧仲彝“把莎劇《李爾王》和中國戲曲《王寶釧》兩個故事糅合而成,形成一個中西結合的產物”(王建開,2003:237)。將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或歌劇改譯成話劇也不乏其例。
然而,抗戰期間仍然有一些翻譯家將翻譯作為一種藝術或者學術追求,希望發現翻譯或文學藝術本身的規律或原則,不愿將翻譯簡單地視為政治或戰爭工具。他們致力于經典名著或現代派文學的翻譯是他們相信名著中自由、平等、人道等普世價值,仍能服務于抗戰。梁實秋有關抗戰與文學關系的言論,實際上是他成熟的文學本位論的體現:
梁實秋的世界觀受古典思想(包括古希臘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中國的孔子)的影響甚大,追求一種中庸的人生境界,即在自然主義的縱欲與宗教的滅欲的兩極中,經理性的疏導和調節后求得精神與物質兩端的平衡,以達到一種和諧、適度的中庸境界。這一思想內核在梁實秋身上具體表現為:在政治上尊重作為國家象征的中央政府,主張漸進改良,反對暴力革命,在思想上崇尚自由主義,主張多元并立,反對專制獨裁;在倫理觀上講究尊卑秩序,推崇禮德儉讓,而表現在文學觀上便是信奉穩健、傳統、保守的古典主義,這在整體上基本是統一的。(徐靜波,1998:256)
梁實秋是愛國的自由派學者,二三十年代曾反對南京政府對自由的干預,30年代與左翼文學陣營論爭(包括與魯迅就“硬譯”進行的論爭),40年代反對張道藩有關文藝政策的言論都說明,“只要事關文學,就不論敵友,只論是非”;他對文學自身規律的堅守達到不僅“不怯”甚至“不智”的地步(余光中,1998:6)。他幾十年如一日堅持《莎士比亞全集》的翻譯,以及他的翻譯選擇和翻譯策略,其實都是他文學翻譯理念的體現。由于抗戰的特殊語境將文學翻譯的社會性、宣傳性和戰斗性提升到空前的高度,持中庸或為藝術而藝術的翻譯觀自然受到官方和左翼文學界的批評和質疑。其實,持類似觀念的翻譯家還有卞之琳、馮至、商章孫、柳無垢、柳無忌、施蟄存、戴鎦齡、戴望舒、梁宗岱、穆木天、方重、范存忠、楊憲益、俞大絪、朱光潛、孫大雨等。經典作品的翻譯家注重作品中人性的描寫和普世價值的展示,翻譯策略上精益求精,以忠實再現原作的精神思想和藝術風格為己任,不太注重作品的趨時性、社會性及宣傳功能。這就是張其春所謂的“唯美派翻譯”:“唯美派富創造于奢譯之中,奉藝術為至上,而于原文之靈思美感均能保持不墮,余所以認此為翻譯之正宗也。”他還認為,這樣的譯文“繪神傳聲,兼備眾美”,“信達且雅,神乎其技”因而“本身即為藝術,可與原著并傳不朽”(張其春,1945:16)。應該看到的是,這些翻譯家的翻譯盡管與當下的戰爭有些距離,但通過他們特有的言說方式,經典名著同樣轉化為戰時國民精神建構的寶貴資源,有利于民族文化的長遠發展。
5.結語
抗戰時期重慶的文學翻譯揭示了在特殊的戰爭環境下文學翻譯的特征與規律。文學翻譯不是簡單的語言轉換,甚至也不僅僅是文學的借鑒與交流,而是主流政治意識形態的順應、強化和建構。翻譯的政治性、宣教性和社會功能被提升到空前的高度,任何背離或對抗主流話語的翻譯活動都會受到質疑或批評,進而被邊緣化。文學翻譯的藝術性讓位于戰爭需要,翻譯文本、翻譯策略以及翻譯表現形式等的選擇,都必然受文化語境的制約,成為我們認識翻譯的文化屬性的有效案例。
*本文特為慶祝四川外語學院外國語文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而撰。
[1]程麻.抗戰文苑中的文學翻譯之花[J].江西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2).
[2]冬.三十四年戲劇節感言[J].文藝先鋒,1945,6(283).
[3]靳明全.重慶抗戰文學論稿[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3.
[4]覺我.余之小說觀[C]//陳平原,夏曉虹.20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987-191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5]老舍等.怎樣編制士兵通俗讀物[J].抗戰文藝,1938,1(5).
[6]梁實秋.編者的話[N].中央日報平明副刊,1938-12-01.
[7]劉念渠.一九四三年的重慶舞臺[J].時與潮文藝,1944,2(5).
[8]柳岸.抗戰時期外國文學翻譯淺議[J].重慶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1).
[9]羅蓀.與抗戰無關[N].大公報,1938-12-05.
[10]蓬子.文藝的“功利性”與抗戰文藝的大眾化[J].抗戰文藝,1938,1(8).
[11]權.加緊介紹外國文藝作品的工作[J].抗戰文藝,1938,3(3).
[12]孫施宜改編.人約黃昏[J].抗戰文藝,1940,6(1).
[13]孫施誼.關于人約黃昏(導演手記)[J].抗戰文藝,1940,6(1).
[14]唐沅.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匯編(第五卷)[Z].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
[15]王大明,文天行,廖全京.抗戰文藝報刊篇目匯編[Z].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4.
[16]王建開.五四以來我國英美文學作品譯介史[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3.
[17]夏衍.抗戰以來文藝的展望[J].自由中國,1938,5(10).
[18]徐遲.在掩蔽壕里·譯者小序[J].文哨,1945,1(1).
[19]徐驚奇.陪都譯介史話[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20]徐靜波.編后記[C]//梁實秋批評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21]姚雪垠.通俗文藝短論[J].抗戰文藝,1938,1(5).
[22]余光中.金燦燦的秋收(代序)[C]//徐靜波.梁實秋批評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23]虞和平.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新文化的新發展[C]//涂文學,鄧正兵.抗戰時期的中國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4]張其春.譯文之作風[J].文藝先鋒,1945,7(2).
[25]張澤賢.中國現代文學翻譯版本聞見錄(1934~1949)[C].上海:遠東出版社,2009.
[26]鄒振環.抗戰時期的翻譯與戰時文化[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