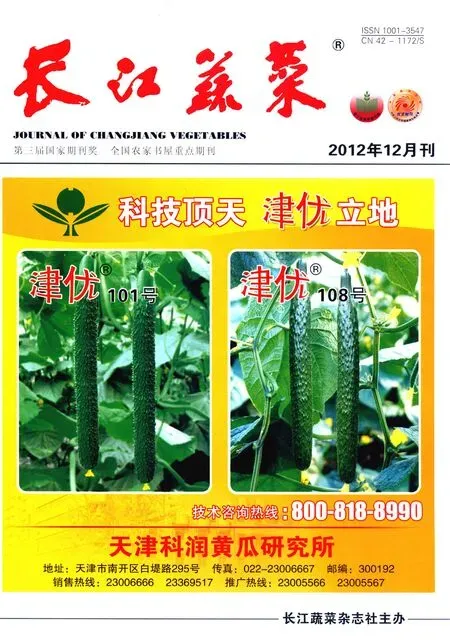種業問題的根源
——種權保護
何久春
種業問題的根源
——種權保護
何久春
營銷一百
特約欄目主持:何久春

美國威斯康 MBA工商管理碩士,經濟師,現任隆平高科蔬菜產業總監、湘研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同時擔任中國種子協會蔬菜種子分會副會長、湖南省園藝學會常務理事、長沙市蔬菜流通協會副會長等職務。
1996-1998年連續三年獲 “湖南農科院開發經營特等獎”、1998年獲 “湖南省科技金橋獎”、1999年獲 “湖南邵陽市三等功”、2003年獲“湖南省科學技術進步三等獎”、2005年獲長沙市高新區“優秀企業家”稱號。
導讀:近年來,植物新品種保護立法如空中樓閣,并沒有落到實處。政府對種權保護的不力,勢必會導致:一是企業放棄創新主體地位,課題組育種取而代之;二是生產同質化,產品同質化;三是行業小散亂以及市場惡性競爭。作者認為,政府作為品種權保護的實施主體,首先應立法保護,將種權納入國家強制性保護范疇;其次是執法,消弭潛在侵權因素,盡可能將侵權事件扼殺在萌芽狀態。
種權保護是政府對品種權人享有的對其被授權品種的排他性獨占權利的保護與維持。作者認為,政府作為品種權保護的實施主體,有兩個方面的工作,首先是立法保護,將種權納入國家強制性保護范疇;其次是執法,消弭潛在侵權因素,盡可能將侵權事件扼殺在萌芽狀態,充分建立起品種權人的信心。
1997年政府頒布 《中華人民共和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而“實施細則”則是2007年才出臺,在這十年之間,植物新品種保護立法如空中樓閣,并沒有落到實處。而“實施細則”出爐之后也未見有強有力的執法監督,滯后被動型保護執法嚴重打擊了育種家申請種權保護的積極性。政府對種權保護的不力,勢必會從以下三個角度攪渾種業市場。
1 企業放棄創新主體地位,課題組育種取而代之
種權保護的不得力一方面表現在種權保護申請期過長,新品種在其市場生命前期20%以上的時間是處于無保護狀態,而這個時期正是侵權行為高發期,反而之后被保護的80%的時間沒有太多必要,如果在前期沒有侵權行為發生,之后就鮮有發生,因為此時進行品種侵權,侵權者的市場風險極大,主要是品牌認可風險。另一方面是執法機構的被動滯后性執法,往往會令品種權人心寒,補救式的市場監管,以及自主舉證要求使得企業對申請品種權保護的期望值一跌再跌,企業便在申請品種權保護方面失去信心,使惡性侵權行為頻發,企業育種風險居高不下,因此企業便不愿意投資育種項目,那么便失去了創新育種主體地位。行業內育種創新能力不足,加上國外種企的壓力,政府便鼓勵民間育種,也就是常見的課題組育種,課題組育種的主體是科研院校。前隆平高科總裁劉石先生認為課題組育種存在三大弊端:①技術導向性育種,缺乏對市場需求的關注;②育種資源浪費嚴重,約50%的項目經費被用在項目研究以外的權力尋租方面;③育成的品種中看不中用,有市場開發價值的審定品種不到15%。盡管有以上種種弊端,但是課題組育種仍然能夠主導行業,原因就在于政府對該種育種形式的“大力支持”。種質資源和育種經費交給科研院校,并不能夠彌補種子行業育種能力的不足,科研院校技術導向型育種模式為行業帶來新的困擾,那就是研發與市場的對接錯位。
2 生產同質化,產品同質化
受國內種子生產基地限制,國內“三八線”式的種子生產格局屢見不鮮,在相同的制種環境下甚至會出現多家企業共享同一個制種戶,共用同一批制種臨時工的現象,這種生產模式無疑使得企業資源赤裸裸地暴露在競爭者面前,加之種權保護制度的軟弱無力,生產基地便成為行業侵權的溫床,套種、偷種情況嚴重。種權保護不力的背景下生產同質化必然導致產品同質化,繼續往下導致行業小散亂以及市場惡性競爭。
3 行業小散亂以及市場惡性競爭
既然能夠輕易竊取他人研發成果,行業準入門檻又那么低,可以想象種子經營主體便會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在行業內,大家拿著同樣的品種去經營同樣的市場,品種轟炸、品牌轟炸使得種植戶對市場供應品種的識別愈顯艱難,結果就是每個經營主體都可以分到一杯羹,但又都不多,也就是我們經常講的行業主體分散,單個企業規模不大。而大量同質化產品涌入市場,必然會打破原有的市場供需平衡,可以預見在市場無法消化行業所提供的種子產品時,種子企業就會回歸到最原始的市場競爭方式——價格戰。提供同質化產品的主體越多,價格戰就越混亂,沒有一家可以掌控整個市場走勢。而價格下跌又誘導種植戶產生錯誤的認知,他們會認為價格下跌的品種的商業化價值有待重新評估,在選擇品種時會慎之又慎。沒有耐心和對價格敏感的客戶就會立刻封殺該品種,那么新品種的市場需求會因其自降身份而下降。市場需求下降,市場供給增加,均衡市場供應量會比降價之前低很多,企業就會誤以為該品種已經走向市場衰退期,隨即將該品種列入待退行列,殊不知這種市場假象是由自己的價格戰帶來的。
歸納起來,政府對種權保護的不當是造成當前種子行業一系列問題的罪魁禍首,企業育種積極性下降,科研院校越俎代庖,選育的品種虛有其形,缺乏市場價值;而由于企業在生產環節無法進行資源保護,共享型生產基地便成為種業侵權的溫床,市場品種差異化程度越來越小;市場競爭呈現白熱化,無一家企業可以左右市場形勢,使得絕無僅有的優良品種提前終結了自己的生命。
4 政府到底應該怎么對新品種實施有效保護呢?
其實很簡單,首先是立法,將新品種權納入國家強制性保護范疇,給品種權一個清晰的身份,名正言順。在立法方面,我國基本上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品種權法律體系,幾乎在涉及種子行業的任何一部法律中,都有對品種權進行法律約定和保護的條款,而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及其實施細則則更專業和系統的對植物新品種進行了立法保護。其次就是提前保護原則。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在問題發生之后去尋找補救的辦法。這種滯后性的執法保護并不能給申請品種權保護的企業帶來安全感,因為企業申請種權保護是希望不發生侵權套種事件,而不是希望在權益遭損害后追索賠償。
最后就是政府應加強市場監管。如今的種權保護可以說非常消極,政府在種權保護執法過程中處于無作為狀態,侵權事件發生時,政府絕對不會是第一目擊者,法律追償時政府也不是舉證者,這些工作全都又還給了企業。所以,政府一定要發揮主觀能動性,持續主動地對種業市場實施監管,發現問題及時取證,并聯系相關責任企業,高效解決侵權糾紛。
政府要做的應該是企業做不了的事情,那樣才能使企業集中精力做市場。根據市場邏輯,一旦種權受到有效保護,其他的育種主體問題、行業門檻問題、市場競爭問題都會在“看不見的手”中得到解決。
何久春,湖南湘研種業有限公司,湖南省長沙經濟技術開發區壽昌路 17號,410100,電話:0731-82791278
2012-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