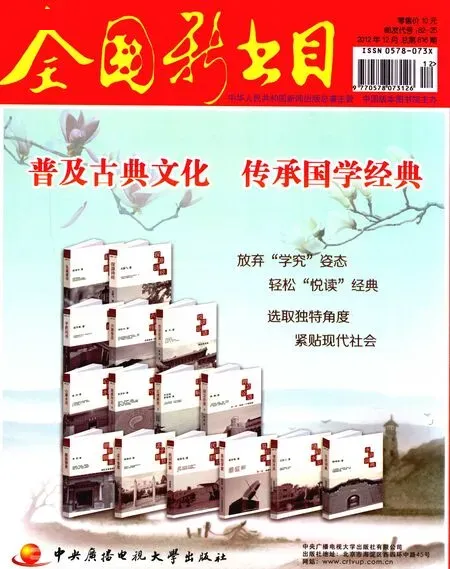一部情愛的萬花筒
——評《多元情愛—兩性關系史》
一部情愛的萬花筒
——評《多元情愛—兩性關系史》
無論從進化論的觀點,還是從神學的觀點來看,兩性原為一體,自從兩性相互獨立后,她們之間糾葛纏繞著,演繹著一曲沒有結尾的悲喜劇。兩性之間情愛關系,既是私密的不可言說的領地,也是統治與解放、自由與約束、欲望與理性、本能與道德等關系的多棱鏡。這本出自法國作家雅克·阿加利之手的《多元情愛—兩性關系史》,就給我們觀察人類情愛提供一個萬花筒,至少有三個方面值得關注。
對情愛形式寬容而客觀的記錄
說起人類情愛的內涵,如果換一個角度,以一顆包容的心和幽默的態度,將人類作為大自然的一部分,也許會為人類的表演而忍俊不禁。
作者站在星球上看人類,用歷史的長鏡頭記錄人類情愛萬象:“自然法則”下的民俗風化、群婚部落、一妻多夫、一夫多妻、同性戀儀式、后宮的女人、柏拉圖式戀愛……書中以圖畫式的描述營造出光怪陸離的片斷。初看起來匪夷所思,卻是人類真實的生活狀態。書中只陳述事實,不枉下結論,傳遞出作者寬容機智的態度,令人贊賞。
對本性與規訓矛盾的闡釋
人是由著本性支配行動,還是受道德秩序規訓,有時這一方占上風,有時那一方占上風,兩方面的戰爭永遠沒有結局。人類畢竟是自我馴服自己的高級動物,不斷地制造著規矩,也不斷地突破著規矩,如一臺在山路行駛的汽車,為自身安全前進,時刻調整方向、約束行為。
但是,人類本性自有沖破禁錮的力量。書中介紹,15世紀末,混亂的風氣助長梅毒在歐洲廣泛傳播。1459年,神圣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米利安一世頒布詔書,宣布梅毒是上帝對人類罪惡的懲罰。對疾病的恐慌,轉化為對疾病傳播途徑和異性的厭懼。禁欲思想盛行一時,性自由受到更嚴格的限制。面對縱欲可能帶來的可怕后果,人們對婚外性行為的憎惡感普遍化,轉化為節制和對享樂的排斥。
近代以來婚姻事務管理由教會逐漸轉入國家,一夫一妻制作為法律在多數國家得以確立。但是,在各個地方,在每一個時刻,都會出現脫離社會的反叛和抵制,出現瘋狂的愛情。特別是工業化生產的普及,人的自由受到限制,而自由的天性偏要從“性”這個窗口沖出來,性解放的呼聲曾一浪高過一浪。20世紀80年代中葉,艾滋病又成為性道德解放的攔路虎……本性與規訓的魔道之斗仍在繼續,作者對未來也作一番喜憂參半的展望,值得一讀。
對愛情與婚姻的追問
一,這一圣事有三重重大意義:靈魂的結合、肉體的結合、上帝與人類的結合,愛情也逐漸成為文學藝術的主題。女性愛情的意識覺醒,使男女情愛變得唯美,并且女性的愛情比男性的激情更勇敢,女性的愛情能夠不顧一切地推翻習俗的圍墻。至此,自由的愛情處處受到歌頌。但是,相對愛情的精彩,婚姻總顯得暗淡。
作者將19至20世紀一直到現代稱為婚姻的末日,婚外情的增多、離婚率的提高、避孕藥的出現、妓院的合法化等等都是重要原因。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身體史無前例作為一個消費商品,身體不再與內在愛、人格主體或類似的精神元素相關,以滿足所有人的選擇自由和自然欲望為承諾的消費文化導致人的主體的喪失,人成為物的符號與標簽,人與人的交流只能通過身體交換才能實現。作者對人類情愛的前景憂心仲仲,也值得我們深思。
電影《色·戒》中王佳芝面對碩大的鉆石感嘆:“這個人是真愛我的。”如果沒有鉆石,她會說什么呢?
作者囿于西方歷史的視野,將12世紀勇敢的騎士和游吟詩人當作風雅愛情的共同創造者,騎士是勇敢忠貞的主角,以詩人之口向外傳播。騎士往往被描述為在情人面前臉色蒼白,對她從不厭倦,忠心不二,隨時準備為她去死。這個時候愛情是一種病,如果相愛,只能期待死亡。騎士之愛是一個關于愛情和死亡的故事,沒有婚姻。
基督教將維護婚姻作為倫理的基石,宣傳結婚是教會的七件圣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