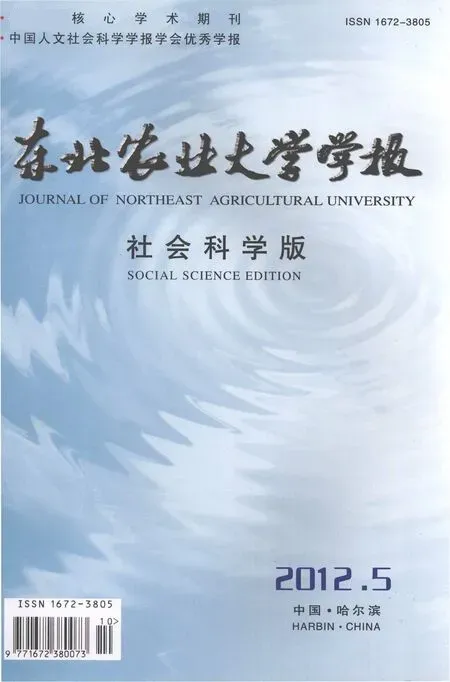從《寵兒》與《紫色》看黑人女性的身份重建
蔡 玥
(黑龍江科技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27)
托妮·莫里森和艾麗斯·沃克是黑人女性作家的杰出代表人物,肩負著民族與種族的雙重使命。她們在各自的文學創作中共同關注多重壓迫下黑人女性的悲慘生活,黑人女性的成長歷程,黑人文化傳統的傳承等主題。作為莫里森和沃克極具代表性的作品,《寵兒》與《紫色》分別以兩位作家不同的視角描繪了黑人女性塞絲和西麗從身份缺失到自我認知與覺醒,再到自我救贖與身份重建的成長歷程。盡管過程不同,但最終要實現黑人女性自我身份重建的目標卻是一致的。
一、黑人女性身份的缺失
在敘述黑人女性的身份缺失狀態時,莫里森和沃克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是,黑人女性的最終命運卻驚人相似,即都失去了人的獨立身份。
1.塞絲——奴隸制統治下,黑人女性的自我迷失
莫里森將《寵兒》的故事背景置于美國內戰后的重建時期(1865—1900年),講述南北戰爭后底層黑奴的苦難生活。盡管當時奴隸制已經廢除,但其影響依然深遠,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的奴隸性仍然存在,她們所受的創傷并沒有因為奴隸制的廢除而撫平,反而是歷歷在目。至1874年,奴隸制已經廢除整整10年,然而黑人仍然身處社會的最底層,白人的壓榨和迫害讓他們無法看到命運的改變和希望。在保羅·D的記憶中,大多數黑奴“眩暈、饑餓、疲倦或者被掠奪到了如此地步,讓他們重新喚起記憶或者說出任何事情都是個奇跡”,他們都“像他一樣,他們躺在山洞里,與貓頭鷹爭食;像他一樣,他們偷豬食吃;他們把身子埋進泥漿,跳到井里,躲開管理員、劊子手、退役兵、山民、武裝隊和尋歡作樂的人們”。黑人女奴的命運更加悲慘,她們沒有任何權力,只能極端地選擇死亡。塞絲從“甜蜜之家”農莊成功逃亡,但奴隸主“學校老師”隨即帶人追來,為了不使子女重蹈自己奴隸的命運,塞絲鋸斷了一歲多女兒的喉嚨,毅然決定以死亡終結她們成為黑奴的可能。弒嬰行為實質上是黑人女性對奴隸制的懼怕和無能為力,她們以死亡這種極端的方式阻止奴隸制向下一代傳遞。莫里森對奴隸制的血淚控訴真實地還原了黑人女性的生活狀態,揭示了其在奴隸制影響下作為獨立的人的身份缺失。
2.西麗——性別和階級歧視下,黑人女性的失語和隱形
在《紫色》中,沃克側重揭示黑人族群的內部矛盾,即在父權制和性別歧視的雙重壓迫下黑人女性的失語和隱形狀態。沃克筆下的黑人女性身受種族歧視、性別歧視、階級歧視等多重壓迫,她們是黑人族群中最悲慘的階層,完全喪失了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完整。
女主人公西麗長期忍受著父權制的摧殘:她14歲即被繼父奸污,還被威脅不得對“上帝”以外的其他人說,其兩個孩子也先后被繼父送人。對此,她不敢反抗,默默承受著繼父的欺辱和奴役;她沒有自己的意識,只能沉默并隱形。除此之外,西麗還長期遭受著自己丈夫的歧視和虐待:20歲時,西麗被繼父賣給了某某先生(阿爾伯特),但是她的生活沒有因此好轉,反而更加艱難。在某某先生眼中,西麗僅僅是勞力和發泄工具。她被自己的丈夫奴役和壓榨,卻仍然無聲地面對一切。西麗幫助妹妹逃跑,自己卻屈從于無愛的婚姻中。只要能夠生存,西麗可以忍受種種虐待和不幸,她的精神已變得麻木。即使有人鼓勵她反抗,但她仍選擇沉默和服從。西麗面對壓榨和迫害的順從與沉默,也預示著她的自我重建之路必將漫長而艱辛,她需要認識到的是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價值和尊嚴。
二、黑人女性的自我認知和覺醒
1.塞絲的母性與母愛
在白人奴隸主眼中,黑人奴隸只是他們的所有物而已,黑人女奴更如牲畜一樣。“學校老師”的兩個侄子獸性十足,他們強行按倒塞絲,吸走了她哺養嬰兒的奶水,瘋狂地踐踏她養兒育女的神圣母性,因此也激發了塞絲身為人的意識——保護自己兒女不重蹈覆轍的強烈母愛。
塞絲的母親在販奴船上多次被白人水手輪奸,她將和白人所生的孩子扔掉,只留下了和黑人所生的女兒塞絲。“嬰兒的心每跳一下,他就退后一步,直到最后心跳徹底停息……我止住了他……我把我的寶貝兒們帶到了安全的地方”。塞絲在逃亡途中鋸斷了年僅一歲多女兒的喉嚨,因為在她眼中死亡比成為奴隸更加安全。兩代黑人女性面對未來的抉擇時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結束自己孩子的生命,極端的弒嬰行為也使她們第一次真正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奴隸制統治下,黑人女性只有在決定自己孩子的生死時才有真正的身為人的權力,她們默默地、無奈地、卻又極其勇敢地想要去除白人強加的所有印記。她們滿腔的母愛和強烈的母性在弒嬰事件中得到了極度的抒發,這也正是黑人女性身為獨立的人而具有的合理身份。
保羅·D認為塞絲的愛“太濃了”,而塞絲的回應則是“要么是愛,要么不是。淡的愛根本就不是愛……‘學校老師’沒抓走他們。”塞絲被動悲慘的命運和她在選擇兒女命運時的主動出擊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她通過極端、悲愴的方式獲得了自己的聲音,贏得了孩子的命運,邁出了黑人女性自我重建的重要一步。
2.西麗的同性之愛
沃克筆下黑人女性的同性之愛往往超越肉體和情欲,她們彼此吸引,互相扶持,勇敢地表現愛與忠誠;她們的精神和人格獨立,不依附于任何人,不屈服于任何權威和壓迫。同性之愛已經成為黑人女性認識自我、發展自我、實現自我的有效途徑。
在西麗的意識中,男性的權威和女性的從屬都是必然要接受的,她麻木地忍受著一切痛苦和悲傷,只寫信給上帝來訴說苦悶。西麗與莎格的同性之愛為她麻木的生活注入活力,激發了她自我意識的覺醒。莎格的出現證明了西麗愛的能力:她嘗試著欣賞和享受自己的身體,體會到了愛的歡愉和滿足。莎格的引導讓西麗了解到了自己的懦弱和自卑,感受到了自己的麻木和無知,意識到了自己身為人的價值,“我窮,我是個黑人,我也許長得難看,還不會做飯,有一個聲音在對想聽的萬物說,不過我就在這里”。在莎格的幫助下,西麗逐步實現了精神、情感、經濟的獨立。她擺脫了“上帝”的精神束縛,在給妹妹耐蒂的信中寫道“我不再給上帝寫信了……我一直向他祈禱、給他寫信的那個上帝是個男人,他干的事和所有我認識的男人一樣,他無聊、健忘、卑鄙”。西麗曾過度沉迷于莎格的關愛,沒有莎格,她的生活空虛而失落,然而正是莎格的再次出走讓西麗完全掌控了自己,實現了情感的獨立;在莎格的幫助下,西麗開辦褲子工廠,并且有了不錯的收入,她還獲得了生父的遺產,實現了經濟上的獨立。
三、黑人女性的自我救贖和身份重建
在對塞絲和西麗自我救贖與身份重建的描述中,莫里森和沃克都強調黑人民族的集體力量。
談及《寵兒》的創作,莫里森一再表示反思過去、認識過去的重要意義:未來的幸福和平靜必然要與過去發生某種聯系,而要處理好現在和將來就必須要跨越難以啟齒的過去這道屏障。“寵兒”即代表了塞絲的過去,代表了黑人女性比死亡還痛苦的艱難境況——她們寧愿選擇死亡也不愿再做奴隸,她們能夠承受死亡之苦卻對終身為奴的命運無能為力。“寵兒”的陰魂不散破壞了平靜的生活,塞絲的精神和身體因此備受折磨;她內心的苦痛不可言說,而要實現自我重塑,就必須要正視現實,只有治愈了內心的傷痛才能真正地走向新生。最終塞絲最寵愛的女兒丹芙向黑人社區尋求幫助,以一首招魂曲驅除了陰魂。丹芙自我意識的覺醒幫助了塞絲的新生和重建,同時整個黑人社區也摒棄了嫌惡和歧視,在“集體行動”中增強了整個黑人民族的自我意識。
沃克認為,在充斥著性別和階級歧視的世界里,黑人女性的成長和覺醒離不開她們彼此的友愛和團結。姐妹情誼是《紫色》中西麗成長與獨立的關鍵性內容。在黑人族群內部,黑人女性不僅沒有得到男性同胞的幫助和扶持,還要忍受來自種族內部的性別歧視和虐待。面對種族、性別、階級等多重壓迫,姐妹情誼成為了黑人女性爭取自我救贖與身份重建的精神保證。情人兼好友的莎格啟發了西麗人性的復蘇,兒媳索菲亞和妹妹耐蒂激勵了西麗女性意識的覺醒。姐妹情誼使西麗的生命更加完整、健康。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互相友愛的姐妹情誼還迫使黑人男性必須更新觀念,摒棄性別和階級歧視,共同構建平等和諧的黑人民族。相互理解與和睦相處基礎上重建的兩性關系也標志著黑人民族意識發展的新階段,達成了兩性和諧與內部團結才能最終實現種族的平等和獨立。
[1] Morrison,Toni.Beloved[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13-15,35-38.
[2] 托妮·莫里森.寵兒[M].潘岳,雷格,譯.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8:25-30.
[3] 艾麗斯·沃克.紫色[M].陶潔,譯.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譯林出版社,2008:25-28,50-57.
[4] 常耀信.美國文學簡史[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0:230-235.
[5] 劉戈.革命的牽牛花——艾麗斯·沃克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5.
[6] 薛小惠.《紫色》中黑人女同性戀主義剖析[J].外語教學,2007(5):78-80.
[7] 高曉慧,宋寶梅,胡家英.論艾麗斯·沃克的生態婦女主義觀——以《父親的微笑之光》為例[J].學術交流,2011(7):187-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