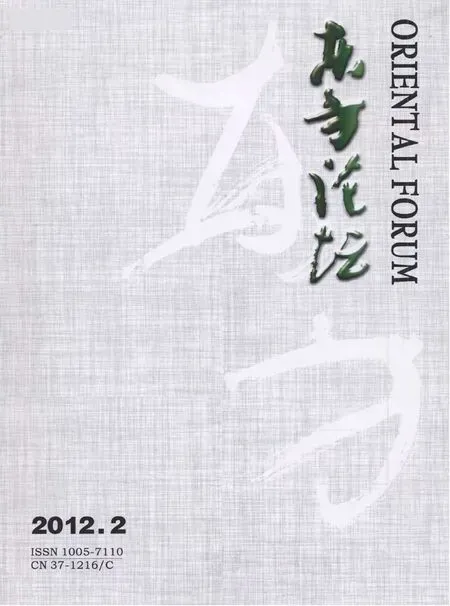《卡夫卡研究》的三重品格
《卡夫卡研究》的三重品格
宋 德 發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講到了三種觀察歷史的方式,即原始的歷史、反省的歷史和哲學的歷史。不妨借用這種說法,將文學研究的方法劃分為三種:“考證”、“論證”和“悟證”。一般而言,勤奮型學者偏愛“考證”,因此行文時“論證”得很嚴謹,但可能會顯得無趣,讓讀者不忍卒讀;才情型學者偏愛“悟證”,因此行文時“論證”得很有趣,但容易信口開河,漏洞百出,處處給人留下駁斥的把柄;功力型學者則努力將三種研究方法融會貫通,寫出既“嚴謹”又“靈氣”、既“規范”又“自由”的學術論著。
從學術追求和寫作風格來看,曾艷兵先生無疑是一位功力型學者,他的新著《卡夫卡研究》(商務印書館2009年12月)很全面地體現了他的學術品格:讓“考證”、“論證”和“悟證”相生相克,取長補短,直至“三位一體”,從而實現“文學”與“研究”、“耐讀”與“可讀”的有機統一。
一、“考證”的品格。“文學研究”帶有“科學”的品質,講究言之有據,言之有物。在一次巴赫金學術討論會上,一位研究巴赫金的論文作家受到一位學院派學者的詰難,說他的立論所依據的文獻是簡單且不可靠的,只能算“評論”,不能算是“研究”,因為是“評論”,所以要求倒可以降低一點。這段會議花絮其實傳遞出一個信息:中國主流學者雖然不像前蘇聯學者那樣,追求論文的每一頁一定要有幾個注釋,但他們對“考證”同樣是非常在意和重視的。
在《卡夫卡研究》中,我們能夠處處感受到作者嚴肅和嚴謹的學風,甚至說,作者對“言之有據”的堅守有些讓人感動。比如說論著第二十三章在專論“卡夫卡與《聊齋志異》”的時候,便將“考證”的方法發揮到極致。作者從其他學者以及卡夫卡的作品中獲得這樣一條線索:卡夫卡掌握了一種中國式的“變成小動物”的方法。作者由此作出一個“大膽推測”:卡夫卡之所以對這種方法駕輕就熟,可能是受到了中國同類小說的影響。于是,作者開始了他的“小心求證”。
曾艷兵先生發現,1913年1月16日,卡夫卡在寫給菲莉斯的信中提到了布貝爾出版的《中國鬼怪和愛情故事》,還說這些故事“精妙絕倫”,也就是說,卡夫卡認真讀過這本書,而且做出了精準的評論。通過艱苦而曲折的尋找,曾艷兵先生終于找到了這部《中國鬼怪和愛情故事》,驚喜地發現,它就是《聊齋志異》的德譯本。這個德譯本參考了英國漢學家翟理斯的譯本,翟理斯從《聊齋志異》的455個故事中選擇了164個故事,而布貝爾則從翟理斯的譯本中選擇了10個故事,另外直接從中文翻譯了6個故事。
曾艷兵先生又通過卡夫卡的傳記獲取了一個很隱蔽的信息:卡夫卡手頭有一本衛禮賢翻譯的《中國民間故事》,后來還將這部書當作禮物送給了自己的妹妹奧特拉。通過“山窮水盡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式的尋尋覓覓,曾艷兵先生又獲得了德語版的《中國民間故事》,確證了它收錄的故事中有15個來自《聊齋志異》,這15個故事中有四個是動物故事:《小獵犬》、《嬌娜》、《嬰寧》、《青娃神》。這些有力的外部證據,再加上卡夫卡作品與《聊齋志異》諸多內在的相通性,讓《卡夫卡研究》水到渠成地得出一個觀點:“看來,卡夫卡的創作思想和創作方法顯然受到過《聊齋志異》的影響和啟發”(參見該書第388頁)。 在《卡夫卡研究》中,這種對任何蛛絲馬跡都不放過的“偵探式”精神可謂隨處可見,正因為如此,曾艷兵先生對卡夫卡先生及其作品的“論證”是令人信服的。
二、“論證”的品格。“考證”可以說是“論證”的一個邏輯起點,正因為如此,無論是卡夫卡與中國文學的事實關系,還是卡夫卡的作品與他的家庭、民族、宗教的關系等,曾艷兵先生都不吝筆墨,尋根溯源,力圖給讀者一個全方位的交代。當然,“知人”未必就可以“論事”,對卡夫卡前世今生的梳理只是為解讀卡夫卡提供諸多外部的參考,按照“作家死了”的說法,真正可靠的或許只是卡夫卡的作品。曾艷兵先生自然深諳作品對于作家的重要性,因此,《卡夫卡研究》的一個重點還是在于以“作品”的字里行間為證據,“論證”卡夫卡作品深藏的意蘊。當然,對于“論證”來說,上述的各式“考證”固然重要,但論證的邏輯、語言和層次更不能忽略,否則,學者的考證可能會變成繁瑣、枯燥和簡單的文獻堆砌,甚至會起到相反的作用:你不論證我還能懂點,經過你的論證我反而不懂了。
卡夫卡本人、卡夫卡的作品、卡夫卡的語言是充滿悖論和哲學意味的,如何清晰地傳達出對他作品的理解,確實是一件富有挑戰性的工作。正因為卡夫卡的作品處處充滿閱讀障礙,因此我更加欣賞和欽佩《卡夫卡研究》解讀作品的方式,比如它的很多標題是“卡夫卡式”的,即用卡夫卡式的悖論來描述卡夫卡的悖論,卡夫卡說,“殺了我吧,不然你就是兇手”,曾艷兵先生則用“無所歸屬”、“無處不歸屬”和“超越歸屬”來描述卡夫卡的“歸屬”;用“失重的悲劇與尷尬的喜劇”、“幻想的真實與真實的噩夢”、“形而上的疼痛與疼痛的游戲”來描述《城堡》的主題;用“K想要的只是‘想要’的欲望”、“K所走的路是無路可路”來描述K遭遇的困境。當然論著中的很多地方也是“曾艷兵式”的表達,即用清晰明了、層層推進的方式來剝開作品的重重迷霧,比如它認為《法門內外》包含著“自我控告”、“社會控告”和“宗教控告”三個層次;《一次戰斗紀實》包含著“遙望中國”、“描繪中國”和“跨越中國”三重意蘊;《往事一頁》包含了“源于中國”、“抹去中國”、“建構中國”三種內涵……可以說,經過曾艷兵先生充滿思辨和智慧的解讀,卡夫卡以及卡夫卡的作品變得更加豐富、飽滿,更人讀者回味無窮和充滿期待了。
三、“悟證”的品格。文學研究不可缺少“悟”的層次,只能說是低層次的文學研究,或者說只是“研究”,但絕不是“文學研究”。對“文學研究”來說,“考證”和“論證”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和基礎,但如果僅僅止步于此,那么這樣的“文學研究”也是無法贏得讀者人心的。
我很欣賞曾艷兵先生在后記中說的一句話:“從某種意義上說,研究卡夫卡,也就是研究我們自己。”這和《死亡詩社》中的臺詞“Now, when you read, don’t just consider what the author thinks, consider what you think”(“當你閱讀時,不要只在意作者的想法,要想一想你自己的見解。”)無疑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在我們看來,《卡夫卡研究》也正是曾艷兵先生結合自己的生命體驗,與卡夫卡進行心靈溝通,進而發現自我、展示自我的一個嘗試,其中的很多精妙的思想,與其說是曾艷兵先生在卡夫卡身上發現的,不如說是他自己對世界和人生的一種參悟。
《卡夫卡研究》對卡夫卡及其作品的“論證”之所以精彩不斷,很大程度上歸功于這些“論證”的過程融入了曾艷兵先生對作家和作品的“悟”,這可以說是《卡夫卡研究》運用“悟證”的第一個層次,同樣,它用平行研究來比較“卡夫卡與老莊哲學”、“《圍城》與《城堡》”、“卡夫卡與《聊齋志異》”、“卡夫卡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與弗洛伊德”、“卡夫卡與克爾愷郭爾”、“卡夫卡與尼采”時,也是對“悟證”第一個層次爐火純青、渾然天成的運用。可以說,《卡夫卡研究》的這些章節讓我們對“平行研究”這一古老而日漸衰落的研究方法重新充滿信心和希望。
《卡夫卡研究》中“悟證”的第二層次就是作者借助卡夫卡和他的作品,表達了自己對世界與人生的理解。比如,他通過解讀《饑餓藝術家》,發現了“藝術與生活”的三種關系:生活是生活,藝術是藝術;藝術是手段,生活是目的;生活就是藝術,藝術就是生活。或許是受到這一發現的啟發和感染,曾艷兵先生努力追求的正是“學術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學術”的境界,在研究卡夫卡的十幾年時光中,他對卡夫卡的一切都感興趣,甚至一看到“卡”字就激動,天長日久,他連思考方式和言語方式都像卡夫卡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所知道的越來越多,但這并不意味著我不知道的越來越少”、“我該和卡夫卡說聲再見了。但是,再見就是再次相見,不是不再見。”當然,他更像卡夫卡的地方在于,他用卡夫卡對待寫作的虔誠來對待他的卡夫卡研究。
《卡夫卡研究》的“題記”是曾艷兵先生自己創作的一首詩歌:“這是人類生存的最后一個城堡/這是沒有出口的迷宮/這是赤裸靈魂的舞蹈/這是市集閑人的冷眼旁觀/這就是卡夫卡的世界/卡夫卡在這里思想/卡夫卡在這里祈禱/讓我們走進卡夫卡/去聽聽他對我們所寫什么……”這種風情萬種的題記在其它學術論著中是極少見到的,它讓我們不僅對卡夫卡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也對研究卡夫卡的曾艷兵先生,以及他的《卡夫卡研究》產生了濃烈的好奇之心。
(作者單位: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