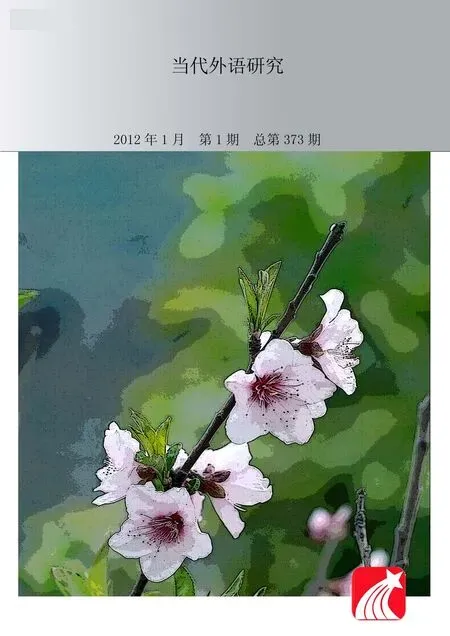以人為本從語言實踐出發對語言進行綜合研究
任紹曾
(浙江大學,杭州,310058)
1. 引子
語言研究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研究什么和怎么研究。不論怎么給語言下定義,說它是行為也好,知識也好,規則系統也好,選擇系統也好,語言總是人們用來交際的。日常聊天,撰寫專著,無不是傳遞信息。TheConciseColumbiaEncyclopedia把語言界定為“利用有聲語言的系統性交際,是人類的普遍特征”。這個言簡意賅的定義告訴我們:首先語言是交際,其次這種交際是建立在語言系統之上的。沒有語言,沒有群體共有的語言體系知識,人們就無法相互理解,進行交際。“有聲的”,是指口頭語言是第一性的,書面語言是第二性的。“利用”是指人利用語言進行交際,而這正是區分人與其他生靈的普遍性特征。用通俗的話說,語言就是說話。Humboldt,Jespersen,Bolinger,Halliday等語言學家都認為語言是一種活動。Humboldt說語言不是一個實體或已完成的事情,而是行動(Jespersen 1922:56)。Bolinger說語言實質上是一種思考和行為的方式(1981:2)。Humboldt、Bolinger說的行動(action)、行為(act),顯然和人的活動(human activity)同義。Halliday說語言學的目的在于說明語言怎樣起作用。為此他認為“最好把語言視為一種活動;具體地說是人們在社會上的一種活動”(1964:4)。
那么,語言究竟是怎樣一種活動呢?Jespersen(1924:17)指出,“語言的實質是人的活動——一個人使另一個人了解自己的活動和這個人了解前一個人想法的活動。要明白語言的性質,明白語法所研究的那一部分語言的性質,就絕對不可忽視語言的發出者和語言的接受者這兩個人,或者簡便地稱為說話人和聽話人,以及這兩者之間的關系”。這里Jespersen點明了語言的實質,也描述了交際過程。程雨民先生提出的人本語義學把語言交流理解為語言應用雙方不斷相互估量著對方的實際情況,說話方應用語言系統所提供的手段,試探著把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受話方則相應領會對方的想法并作出反應的一種過程(程雨民2011)。這個論述和Jespersen對語言的界定相比,共同點都是對語言活動、語言實踐的描述,但人本語義學凸出了說話雙方的智力活動,這表現在不斷相互估量著,試探著,相互領會…并作出反應。
人們的語言實踐過程就是人的智力起作用的過程,是語言的實質所在。所以語言研究就應該把語言實踐作為出發點,又作為研究的對象。由于語言實踐涉及說話雙方個人的認知過程,又涉及人們相互交際的社會過程,所以必須進行綜合研究。這可以看作研究方法。但是鑒于語言的實質,在這個研究方法中,中心是使用語言的人,是人的智力,人的意識。Jespersen是一位重視人在語言交流和語言發展中的作用的語言學家。他認為語言研究應該徹底而真誠地以人為中心(anthropocentric)。他說,在其他科學中這可能是個缺點,因為在這些科學領域里,研究者避免人的因素是個優點;相反,在語言學里,鑒于研究對象的性質,研究者必須考慮人的利益,而且從這個觀點,而不從任何其他觀點出發,判斷一切。否則,我們在各方面都有走上歧途的危險(1922:324)。那么語言研究怎樣以人為中心?怎樣從人的利益出發?從人的利益出發就是從說話人為某種目的而說話的實踐出發,從他說的話出發,從實際使用的語言出發,也就是從語篇出發。Jespersen(1933:177)說,如果我們不首先持續地考慮說和聽的活動,就根本無法了解語言是什么,了解語言如何發展。在功能主義的范圍里,語言學家們實際上都考慮到人。
Halliday重視語言的社會方面,在語言研究中考慮的是社會人。Langacker則重視語言的心理或認知方面,考慮的是“心理人”。所以他們的語言研究也都是從實際使用的語言出發。Halliday說他的語法是以語篇為研究對象又以語篇作為手段(2004:Preface)。Langacker說他的語法基于用法(usage-based)(1991:46)。Jespersen在語言研究中重視人的利益,重視人使用語言的方便,所以他提出了語言使用的簡易原則(1922;1960)以及語言演變中個人的作用(1925),但沒有認真考慮在交際過程中人的智力的作用,意識在形成語言系統和語言運用中的作用。他主張語言研究要堅持形式和意義的結合,對特定語境中詞句的意義有所說明,但沒有對語言意義和信息作理論上的區分。本文擬根據人本語義學(程雨民2010)的理論闡述,探討為什么語言研究要以人為本,從語言實踐出發,對語言進行綜合研究,以期探索語言研究的創新之路。
2. 雙重形義結合
2.1 語言系統的特點
從語言實踐出發對語言進行綜合研究,首先要弄清楚語言系統的特點以及語言系統如何運作。2011年出的AnIntroductiontoLanguage第九版在第一章討論語言是什么,開宗明義,說“當人們聚在一起時,不管他們做什么,…他們總得說話”。這意味著語言就是說話。所以研究語言歸根結蒂應該是研究說話,研究操同一語言的人在交流的時候為什么能彼此理解?他們之所以可以交流,是因為語言或語言系統是語言群體通過實踐獲得的約定俗成的共有知識。沒有這種共同的知識系統,人們就無法相互理解。
可是語言是怎樣一個系統呢?Jespersen指出,沒有一種語言是完美無缺的(1922:320),沒有一種語言在所有方面都是合乎邏輯的(1905:11)。他說英語語法是在起伏、動搖之中,充滿生機而又不斷發展,基于過去又預示未來,并非盡美盡善,但正在前進,可以改善……一句話具有人的特點(1909-1949 Part Ⅰ:Ⅴ)。他還說,沒有一個語言系統是完全嚴格的或十分協調的,我們將看到英語語法里存在漏洞和缺陷(1933:16)。他還指出,在討論語言的時候我們絕不能忘記人只是部分理智的,而人的普遍因素大體上是不合理的和不合乎邏輯的(1925:191)。他說人不是機器(1909-1949 Part Ⅰ:Ⅴ)。他還進一步指出,情感的影響不同于有條不紊的理性思維,在語法的許多地方是顯著的(1933:17)。例如,英語時態系統有現在時、過去時,卻沒有將來時;代詞系統第三人稱單數有性的區別:he/she/it,但其他單數人稱和復數人稱就沒有這種性的對立。這說明觀察敏銳的Jespersen看清了語言的特點,但是他并沒有說清楚語言體系為什么不是象算法規則那樣的完全嚴格,語言又為什么具有人的特性。人本語義學認為,語言從結構到運作,無論理解或運用都少不了人的意識參與。語言系統由語音系統、語法系統和詞匯系統構成。它們的共同特點是:它們都是意識的產物。例如,語音系統就是說話人意識中起辨義作用的系統,辨義就是意識活動的結果,所以語音系統是意識的產物。
語言系統是約定俗成的,音位、語素、詞以及詞的組合都是約定俗成的,而語言系統中的對立賦予語言構成成分的值。語言系統的構成成分是“心理實體”,這心理實體在不同的語境中以各種“變體”出現。例如,英語語音系統中的音位/p/與音位/b/對立,所以有不同的值,因而可以區別意義,但是/p/在不同的語境里,可以是送氣的,也可以是不送氣的。在英語里它們是同一個音位的兩個變體,但在漢語里卻是兩個音位。這要依靠人的智力根據從實踐中獲得的約定俗成的知識加以區分。英語的語法語素/s/,/z/,/iz/在boy和boys,desk和desks,peach和peaches;boy和boy’s,cat和cat’s,coach和coach’s;I walk和the boy walks,I bid和the boy bids,I coach和Peter coaches中的對立賦予了它們不同的值。但是同一個語素如/kts/中的/s/究竟是體現單數和復數的對立,還是主格和所有格的對立,/kut?iz/中的/iz/究竟是體現復數和單數的對立,還是動詞第三人稱和第一、二人稱的對立,要依靠人的智力根據語境才能確定。
可見在一個語言系統里,對立所形成的聚合體是相對固定的,而不是一成不變的,怎么樣的對立決定怎么樣的求解途徑,需要意識參與才能清楚。詞匯也是一樣。漢語詞匯系統里的ping guo是“能指”,它的“所指”是蘋果,指向蘋果這一概念。蘋果是植物的果實,植物可以按門、綱、目、科、種進行分類。簡單地說蘋果樹是木本,與草本植物對立。作為木本植物果實的蘋果與作為草本植物果實的草莓、西瓜對立,當然也與其他木本植物的水果梨子、桃子對立,因此在詞匯系統中就有自己的位置。音系的音位與語法的語素代表一般,“變體”則體現個別。同樣,詞匯系統中的詞匯語素也是代表一般,它有許許多多的個別體現。蘋果作為音義結合的語素可以指各式各樣的蘋果:大蘋果、小蘋果、紅蘋果、青蘋果、有斑點的蘋果、有疤痕的蘋果等等,這些都是個別,而代表一般的蘋果的概念就寓于其中。如果這些各不相同的蘋果需要各自的名稱,那人的記憶就不堪重負了。語言體系體現了人認識一般與個別的的能力。也正是憑借這最基本的認識能力,人類從不同的表象中概括出共同概念,形成語言系統。可見語言系統是在人的智力參與下形成的,語言使用也需要意識參與。為了便于人們表達大千世界里復雜紛繁的個體和關系、無窮無盡的信息,語言必須模糊。人不是機器,在人的意識影響下形成的語言也不可能是機器。如果語言是由1+1=2式的數學規則構成,那人們就無法交際。人們之所以在交際時可以相互理解,是因為語言是適合于人類智能的工具,而人類憑借智能運用語言。
2.2 語言系統的運作
語言有它自己的形式,那就是符號的“能指”及其組合。語言也有它自己的內容,那就是“所指”所表達的意義。而具有自己形式和內容的語言在使用時又作為形式,與另一個內容結合,這個內容就是說話所傳達的信息(程雨民1997:4)。語言系統所體現的第一層音義結合系統,才是我們表達思想的工具。舉個例子:his book是詞的組合的發音/hiz buk/和‘他的書’的意義的音義結合體,它提供一般性的語言意義,在不同的語境里可以傳遞不同的信息,可以是“他寫的書”、“他剛買來的書”、“他借來的書”、“他借給別人的書”、“他提到過的書”、“他的藏書”、“他喜愛的書”、“他尋找的書”甚至‘他遺失的書’、“他失而復得的書”。這些都是從語言意義推導出來的信息。“所指”指向概念,所指的組合指向信息。語言符號中的“所指”要結合語境經過推理才能把語言符號兌現為說話人所指的概念或傳達的信息。所以我們說,語言是指向性的,而不是規定性。
區分語言的“所指”和實際理解的概念,區分語篇所表達的語言意義和它們所指向的信息,需要智力的參與,需要意識起作用,需要推理,這是人們表達思想的需要,是人們交際的需要。另一方面,語言是適應人類這種通過智力活動傳達信息需要的工具。區分“所指”和概念,區分“所指”組合和信息才能把形式和意義結合起來對語言這一音義結合體進行研究。區分“所指”和概念,區分語言意義和信息,就可以明了語言是個別和一般的辯證統一體,所以人們可以進行從一般到個別的推理,使語言具有了非精確無誤的靈活性、滿足具體語境條件下表達和理解的適應性、處理不合理語句的應變性。Fauconnier說,語言并不承載意義,語言引導意義。語言只是認知建構冰山的一角。隨著話語的展開,大多數的認知建構在語言形式的幕后進行……這些隱形和高度抽象的心理建構默默地支持著我們的日常談話和思維,語法不過起著引導作用”(1994:44-45)。他的觀點以及Halliday關于語言概然性的觀點都可以從“所指”指向概念、“所指”組合指向信息、語言適應人類智能的需要、言語交際需要人的智力參與的實踐加以解釋。
2.3 語言意義與信息
事實說明在語言使用中,由于意識的參與,由于推理,從相同的語言意義中可以得出不同的信息,也可以從不同的語言意義中得出相同的信息。不妨看一個實例:
(1) 下雨了。
這同一個語言意義在不同的語境里可以傳遞不同的信息。對參賽的網球運動員,它意味著這場比賽要推遲了;對在農田里收割的農民,它可能是催促大家趕緊把稻谷蓋好或運回屋內。也可能是防洪前線的指揮員要求搶險人員做好準備,也可能是抗旱前線人們的驚喜。而在家庭的語境里,它可能是母親要兒子帶傘,要女兒關窗。在朋友之間。它也可能是表示遲疑,不愿意參與某種活動,等等。同一個語言意義導出如此不同的信息。再看一例。
(2) A—我來看朋友了。
—誰是你朋友?
B—我來看朋友了。
—我是我,你是你,這要說清楚。
“我來看朋友了。”真正看朋友的時候不會講這句話。只是在雙方不友好的情況下,說話人出于某種原因主動示好,把對方看成朋友,才這樣說,所以這句話的意思是“我來看你了,我這是把你當朋友”。這應該是說話人希望聽話人理解的信息。再看聽話人答話:A答“誰是你朋友?”如果在場有幾個人,這意思是“誰都不是你朋友”。如果只有兩個人,那意思就是“我可不是你朋友”。B答“我是我,你是你”,不傳遞任何信息,因為我不可能是你,你也不可能是我。加上“這要說清楚”意思就明白了:你我沒有任何關系。朋友關系是一種友好關系,既然你我之間沒有任何關系,當然也就沒有朋友關系。所以這答話所傳遞的信息是“我可不是你的朋友”。這大體上是第一個說話人的理解,也是第二個說話人期望他這樣理解。這說明與“能指”不可分割地結合成符號的不是概念而是“所指”。“所指”在不同的語境中指向不同的概念,與不同“能指”結合的“所指”也可以指向同樣的概念。這兩個例句還說明:相同所指組合表達的語言意義可以指向不同的信息;不同所指組合表達的語言意義也可以指向同一個信息。對這些實際使用的語句的分析可以說明語言意義只指向信息,并不等于信息。語言的這種音義雙重結合的特征為語言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子,也就是從語言實踐出發研究語言的路子。
3. 從語言實踐出發
3.1 語言研究的兩個階段
語言系統的運作是建立在音義雙重結合的基礎之上,而對這音義雙重結合的語言的研究之所以可能,是因為語言研究的第一階段已經完成,人們可以進入第二個階段的研究了。這第一階段是Saussure開創的“形式研究”。他面臨的任務是要把語言形式和語言內容分開,以便能夠客觀地分析語言形式,所以他著眼于形式。但是他并沒有否定意識的參與,他主張符號是“概念”和“印象形象”的結合(程雨民2011:10),也就是語言符號的“能指”和“所指”的結合。在這個階段,Saussure和隨后的描寫語言學家理出了能指與所指結合的符號系統,建立起包含大小不同的音義結合的符號單位的語言系統和單句結構。這樣,語言研究有條件進入第二階段,即對第二個音義結合的研究,也就是以音義結合的語言作為形式與思想內容相結合。這說明語言研究已經從純形式的研究進入音義結合的階段。當Saussure已經從說話中分離出區別于“言語”的“語言”,而語言體系大致的面貌已經清楚,人們就有條件研究實際使用的語言,或研究語言實踐。語言體系中的語法單位進入語言使用之后就成了具體的語句,就成了話語或語篇,所以人們就進入了語篇的研究。
1927年Bloomfield對葉氏的《語法哲學》作了評論。他說,“對于Jespersen來說,語言是一種表達方式,其形式表達說話人的思想、感情,并將它們傳達給聽話人。這個過程作為人類生活的直接部分不斷持續,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類生活的種種要求和無常變化。對于我,正如對于Saussure,這一切都屬于言語(la parole),是我們的科學所無能為力的”(1927:444)。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Bloomfield等形式語言學家把“所指”和概念等同起來,把語言意義和信息混為一談,而信息又如此復雜多變,所以他們就感到無能為力,而把語言的內容撇在一邊,把實際使用的語言,即言語撇在一邊。第二,Bloomfield等形式語言學家只把抽象的語言體系作為研究對象,但是語言體系本身不足以完成它自己的任務,語言體系必須要進入語言使用,要依靠人的意識參與才能表達人的思想。
3.2 基于語言系統的研究
上世紀60年代開始的語篇轉向也可以說明語言研究的第二階段的開始。但是許多語言學家之所以轉向話語或語篇研究,是因為他們看到形式主義的研究無法全面說明語言的特征,也難以作進一步的探討。他們致力于功能的研究,或意義的研究,形成了作為形式主義語言學對立面的功能主義語言學。功能語言學作為一個學派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卻是在否定形式主義基礎上試圖用功能解釋語言和語言結構的語言學。與功能學派不同,人本主義語義學是在形式主義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行的語義研究,并沒有否定形式主義;另一方面,人本主義語義學也研究語義,研究人是怎樣用語言交流思想的,說得詳細點是:人怎樣利用他所掌握的語言系統,結合客觀方面的社會環境、文化因素,以及主觀方面的聽說雙方的知識系統、交流目的、思想、感情、意志來交流思想的。可見人本語義學既考慮語義,也考慮語境,所以也應該是功能的。這樣看來人本語義學把形式主義和功能主義結合了起來。這應該有利于語言研究。人本語義學和語用學有共同之處,都需要結合語境通過推理求得對于語句的理解,但是人本語義學認為語言系統不是一個界線分明、一清二楚的系統,這個系統進入使用以后每一個層次都需要人的智力參與,所以應該是語言學的一個必要部分。人們一般認為只有在按字面意義理解受阻時,才結合語境求得語用解釋;人本語義學認為即使是按字面理解的直義句,也同樣需要推理理解,如上文(1)的“下雨了”。
3.3 不合邏輯的用語
從語言實踐出發就是要從交際中的問題出發,有什么問題就研究什么問題,包括語言表達和語言理解的問題。Crystal雖然說語言學在對語言作出解釋時要與其他硬學科一樣要客觀、系統、始終如一和明晰,但是他也承認語言學領域包括科學和人學(David Crystal:TheCambridgeEncyclopediaofLanguageandLinguistics)。因此,語言學又不是硬科學。所以語言研究不應該也不可能從某一個理論、假設、模式或方法出發,而要從實踐出發。語言實踐中的問題往往是由于語言的“不精確”、“不合理”、“不符合邏輯”造成,表現為語句意義不確定,語句意義有歧義,語句意義與語境不相容,也就是說不通或者不連貫。人們說話都想簡略有效,因而給理解造成困難。請看下面兩個例子。
(3) —劉翔今天晚上要跑兩槍。
—他狀態很好。
我們理解這兩句話不會有困難。但字面上的意思卻是不符合邏輯的。運動員怎能“跑槍”?語法上講“跑”一般為不及物動詞,不能接賓語。我們理解該語句,是因為我們的知識告訴我們徑賽項目都以鳴槍起跑,鳴一次槍,就跑一次,所以“跑兩槍”是指參加兩次比賽。這實際上是轉喻,以動作的信號代替動作。一個晚上參加兩次比賽體力消耗很大,第一句話實際上是暗示:一個晚上跑兩次,劉翔吃得消嗎?跑得好嗎?對方這樣理解了,所以說了“他狀態很好”,結論留給對方下:“他狀態好,所以連續跑半決賽和決賽沒有問題。”通過推理,對話也連貫了。
(4) 汪總,我向你求婚。
一個年輕的建筑設計師當著許多人的面向設計公司年過半百的女老總單膝下跪說了這句話。當時這個小伙子正與汪總女兒熱戀。“求婚”本來的意義是要求聽話人嫁給說話人,但在這兒卻變成了要求聽話人汪總將女兒嫁給他。聽話人為什么理解而且也沒有感到十分詫異?這是因為結合直接語境和文化語境她推導出了小伙子的意愿、期望和語句所要傳遞的信息。按中國習俗,婚姻大事都得征得長輩同意。這個共同的文化知識賦予了“求婚”臨時性的語篇意義。
例(3)不符合邏輯,例(4)不合常理。從語言實踐出發就是要研究這類問題。當然也應該研究語言意義明確但與所指信息未必一致的語句。
3.4 語言的變化
語言實踐中的問題也可能是由于語言使用出現了變化。人們使用語言表達思想,一方面要受制于語言體系,而另一方面要滿足人們表達思想的需要。語言使用中隨著社會的發展、科學文化的進步就會有許多創新,包括新詞新義,新的語法構式。二三十年前中國人會說“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具有魅力的城市”、“具有相當規模的企業”,近年常用的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魅力城市”、“規模企業”。這新的形式的出現是因為人們力求表達簡潔、方便,把“具有……的”省略了。但是這省略并沒有造成人們理解上的困難,因為漢語修飾語在前被修飾語在后的規則幫助了聽話人。漢語本來就有名詞修飾另一個名詞的組合,然而這類表示特征的名詞作為定語修飾另一個具有這一特征的名詞究竟是臨時性的語篇組合,還是已成為常態化的漢語語法系統中名詞修飾名詞的組合?進入語言系統要通過語言實踐檢驗,要看這種組合是否為操漢語的人群所接受。英語也有類似的變化。如英語的介詞短語一般不能做小句主語,但是偶爾也可以聽到In the afternoon will be okay for me,聽話人也完全可以理解。即使By the fire is much warmer和Behind the dresser is all dirty (Langacker 1991:66),似乎也不會造成理解上的困難,因為第一句的介詞短語指時間,第二、三句的介詞短語指地點。如果第一句加上The time,第二、三句加上The place,介詞短語用作定語就明白無誤了。可是介詞短語的意義就是說明具體的時間和地點,省略掉這兩名詞詞組反倒符合說話人表達方便的要求了。
然而,碰到這樣的語句From gap to gain is very American(Mailer 1968:44),我們會不會感到理解困難呢?也不至于。這句話的意思可以理解為Conversion from gap to gain is very American。介詞from...to就提供了“轉化”的意義,所以人們完全可以理解。在實際使用的英語中我們接觸到了這些以介詞短語作主語的語句,這樣的組合是不是就進入了英語語言體系里呢?這要看人們在語言實踐中是否接納,從而成為約定俗成的系統的一部分。再看一個Salinger的名著TheCatcherinTheRye中的例子。這是敘事語篇中出現的語句:1. What I did, I started talking, sort of out loud, to Allie (p. 98). 2. What he did, instead of taking back what he said, he jumped out of the window (p. 170). 3. What he did, he carved his goddam stupid sad old initials in one of the can doors...(p. 168). 4. What I’ll do, I’ll probably stay at Mr. Antolini’s house till maybe Tuesday (p. 179). 5. What I may do, I may hate them for a little while (p. 187). 6. The thing he was afraid of, he was afraid somebody’d say something smarter than he had (p. 147).看到這類句子,覺得不那么規范,似乎缺了點什么,按規范的句法要求應該在第一小句之后出現was/is that,但是省略之后句子理解起來并不困難。這是因為前5句都以what開頭,第6句以The thing開頭,作為信息的出發點,what和the thing都代表語義籠統的概念,小句中的動詞do的語義也很籠統,這就引導讀者期待具體的說明,而這說明就在隨后的小句里。何以見得?這六個語句中,第二小句的主語與第一小句相同,動詞的時態、情態與第一小句的動詞相同,如第4句中的’ll,第5句中的may,而且都是表示具體動作的動詞,如第1句的started,第2句的jumped都對did作出說明;第6句雖然沒有do,但was afraid 在第二小句中重復。
借助這些語言上的線索,聽話人可以結合語境,通過推理理解句子。這說明語言不是數學算法那樣的機械規則。如果那樣,上面這幾句話語我們就無法理解。這個例子還說明,在語言使用中語言會出現新的變化。就這個實例而言,這些變化究竟是Salinger的個人語言特點(idiolect),是否已被語言群體廣泛采用,是否會影響到語言體系,都是我們在語言實踐中應加以關注的問題。Bolinger說語言的特點之一是,“語言以變應變”,每一個語言都是處在動態的平衡狀態(1981:4)。他的意思是語言體系隨著言語中出現的變化而變化,語言在使用過程中的變化最終會影響語言體系。但是,正如我們上面討論到的漢語和英語的變化,并不是所有實際出現的變化都會立即導致語言體系的變化,但是只有從語言實踐出發才能察覺到這種變化。要進入約定俗成的語言體系,語言變化要經過語言使用的淬火長期鑄煉。
4. 綜合研究
對語言進行綜合研究包括對語言和言語的研究、形式和意義結合體的研究、多學科的整體研究(這涉及到心理學、邏輯學、哲學、社會學等)。切實的做法是從語言研究的需要出發利用這些學科的某些方面,而不拘泥于這些學科的任務和目的本身。這里我們只討論心理學和邏輯學在語言研究中的應用。
4.1 語言研究的心理方面
語言研究要以人為本,所以必須考慮意識的作用。意識是心理學的研究對象,但即使在心理學領域里,意識長期被置于邊緣地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直至上世紀70年代才有人指出:雖然行為主義認為意識太主觀,不值得認真研究,但是意識還是得到科學的關注,有關意識的討論已經在心理學文獻中處于完全體面的位置(Chafe 1980)。對于語言研究來說,我們只要承認意識的存在。其實,意識的存在并不難理解。我們中國有句老話:心不在焉,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禮記·大學》。原來這句話是為了說明正心。心不在焉的意思是心思不在這里,思想不集中。思想不集中是指意識沒有聚焦在這里。心之官則思。意識的活動產生思想。這符合思想和語言是意識活動產物的現代認識。至于對意識的深入研究,那是心理學的任務。
在語言學界重視意識在語言運用中起作用的當推Chafe。他重視意識,重視意識對語言的影響。他指出人們如何使用語言很大程度上依靠他們在時間推移中意識到什么,依靠他們內在注意的焦點,同時關注聽話人意識中的活動。他研究的中心是意識流如何形成語篇流,所以他致力于研究意識的種類:意識焦點和邊緣意識特征:意識有焦點,焦點處于邊緣意識的包圍之中,意識是動態的,意識有觀點和取向,意識單位大小不等,有準主題、基本主題和超主題。Chafe說,概念可以處于三種不同的狀態:活性的、半活性的和非活性的。完全激活的是已知信息,處于邊緣區域的信息是半激活的可及信息,未激活的信息是非活性的新信息,也就是長期記憶中的信息。但是Chafe不考慮體現信息結構的語句,只把信息局限于單個概念(Chafe 1994)。更令人費解的是Chafe雖關注意識,卻把意識和意義割裂開來,直到回應Jackendoff的批評時才說:事實上我們思考、說話和寫話的時候經常意識到意義(Chafe 1996),而且他也沒有區分語句所表達的語言意義與其指向的信息。人本語義學認為在語言運用中意識的參與必不可缺,而且重視語篇表達和理解整個過程中意識的作用。
4.2 語言研究的邏輯推理
語言學和哲學都研究意義,但著眼點不同。語言學首先關心語言意義的理解和表達,哲學是從已經理解的句子出發探討句子是否具有真值,即是否符合事實。所以兩個學科處理的材料相同,但階段不同,任務不同。邏輯研究思維規律,語言應用研究思想的表達,涉及思維過程,所以語言研究要用到邏輯。但是,應用什么邏輯,要以獲得信息的需要為準。研究語言結構及其內部運作要用到辯證邏輯,主要是對立統一規律,也就是說對立面(個別與一般相對立)是統一的,個別一定與一般相連而存在。一般寓于個別之中,而個別體現一般。音位是一般,音位變體是個別,音位寓于音位變體之中。馬的概念是一般,具體的白馬是個別,白馬非馬,但又是馬(體現一般的馬)。語言意義是一般,信息是個別。句子結構是一般,實際的語句是個別。在上面的例句中,從語言意義到信息就是從一般到個別的推導。理解實際語句時,主要用歸納邏輯,特別是三段論,這是因為要獲得信息,不是根據論據推出結論,就是要補充前提、論據。例(3)是從論據推出結論。例(4)的推理是:任何青年求婚都要征得對方父母同意,小青年在追求她女兒,所以這里“求婚”必定是指“要求聽話人把女兒嫁給他”。當然這個結論還要接受語言實踐和生活實踐的進一步檢驗。
綜合研究涉及語言交流的整個過程,包括第一,語言表達;第二,非語言因素:狹義語境和廣義語境;第三,人的因素,也就是意識活動的過程:說話人的知識狀況、意圖、意愿、目的以及說話和聽話人相互的估量,主要涉及的是推理過程。為了說明對語言問題的行綜合研究,現舉一例。
(5) 甲:老王兩個兒子都是大學生。
乙:建國在哪所大學念書?(程雨民1997:141)
老王兩個兒子都是大學生,建邦和建國是老王的兩個兒子,所以建邦和建國都是大學生。這是三段論的推理,但也可以根據情景知識作直接推理。建邦和建國都是大學生,也就是說,建邦是大學生,建國也是大學生,所以建國是大學生。這是聯言推理。如果是大學生,就肯定在大學里學習。建國是大學生,所以建國在大學里學習。這是肯定前件式假言推理。
由于乙不知道建國在哪個大學讀書,所以提出問題。這里雙方都提取了讀大學這一框架里的知識,如大學生都在大學里學習;也提取了有關老王以及老王兒子的信息,比如,他們的名字。推理是建立在對語句分析的基礎上的,也就是說推理不是隨意的。它為推理劃定范圍。直接語境是兩個對老王家熟悉的人談老王和他兩個兒子,間接語境是有關教育體制,即高等教育的管理和制度。如果我們設想兩個不熟悉老王家情況的人,對中國大學教育絲毫不了解的人,這兩句話就不連貫,就沒有辦法交流。之所以在現實中這兩句話是連貫的,就因為聽說雙方估量到對方有這些知識,而且可以毫不費力地應用直接推理、聯言推理和假言推理推導出結論。
這個例子可以說明我們要從語句的語言分析開始,這就涉及到語言單位以及語言單位的成分按一定順序的組合,比如第一句是按主語+動詞+表語的順序組合,是陳述句;第二句是按主語+疑問副詞+動詞的順序組合,是疑問句。但是為了要達到交際的目的,我們的分析不能到此為止,還要結合意義進行研究。語句的分析使我們得到語句的語言意義或命題,但我們還得進一步考察語言意義所指向的信息。結果發現兩句話似乎互不關聯,既不銜接也不連貫。而甲肯定乙的話是遵守合作原則的,而乙的話是符合合作原則的,應該是有關聯的。于是雙方調動世界知識,相互琢磨、估量,應用上述邏輯推理使得兩個語句連貫,從而理解對方講話,交際得以實現。這樣一個簡單的例子就可以說明:語句分析是說話人調用語言體系中的規則,根據交際的需要遣詞造句,而這個分析是基于形式語言學的;結合意義的分析涉及功能語言學對語句分析的理論,又涉及認知語言學中的認知框架或圖式、語用學中的關聯、話語分析中的銜接連貫。對意識參與的考察涉及心理學,推理的過程又利用到邏輯學。所有這些學科中有用的理論都被用來認識語句的表達和理解的問題,而這些理論又同時在語言實踐中經受檢驗。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是對語言進行綜合研究。
5. “相互估量”
本文開頭提到在語言交流中聽說雙方要相互估量。從語言意義推導信息的過程中我們需要語言知識給我們確定推理的基礎和范圍,世界知識給我們提供推理的條件,邏輯推理使我們得出必要的結論。這世界知識既包括話語發生的客觀的社會語境和文化語境,也包括聽說雙方主觀的信仰系統、價值系統和知識系統。這兩個方面都必須估量。請看一例:
(6)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這是Steve Jobs 2005年在Stanford大學畢業典禮上講話的結束語。對這兩句話作分析,要估量說話人的知識狀況、信念系統以及由此引出的說這句話的意圖、意愿,以及Jobs對聽眾的估量。關于此句,有三個譯文:一個是“保持饑餓,保持愚蠢”,另一個是“求知若饑,謙虛若愚”,還有一個是“常保饑渴求知,長存虛懷若愚”。這是Jobs引用的一句話。原話出現在一本叫做“全球目錄”雜志最后一期的封底上。Jobs簡單地介紹了一下雜志,接著他說這期雜志的“封底上是清晨時光一條鄉村公路的照片”。照片之下就是這兩句話:Stay Hungry. Stay Foolish.這是這本雜志在終刊時給讀者的告別語。他接著就說,“我總是希望自己能夠那樣,現在你們即將畢業,開始新的旅程的時候,我也希望你們做到這樣。”這說明Jobs把這兩句話作為自己的座右銘,也借來作為給Stanford畢業生的忠告。應該怎么理解這兩句話?這雜志封底的照片和它下方的文字說明構成了視覺下的多模態語篇。
這語篇的意義不僅以語言體現,而且還以照片體現。請注意Jobs是用語言在聽眾的腦子里呈現一張晨曦中一條鄉村公路的圖像。所以這里有兩個層次上的語篇。封底的多模態語篇的語言表述是Jobs演講語篇的一個部分。在描述這張照片之后,他立即說,“如果你們有冒險精神,你們就會發現自己徒步行進在這樣一條路上。”這句話連接了照片和它下方的說明,使得這多模態語篇獲得連貫,而且凸出了語篇的主旨。同時也將這多模態語篇主旨和他的演講意圖有機地聯系了起來。要了解這兩句話必須結合上下文,參考照片,要考量說話人的目的和意圖。既然這兩句話是出自這期雜志,那就要看雜志編者的原意。
Jobs對這個雜志作了介紹,說這是70年代一本具有創新精神的雜志,并把它與現在的Google相比擬,說它“充滿了便捷靈巧的工具和了不起的思路”。這樣一份具有創新精神、充滿創新內容的雜志在它發表終刊告別辭的時候,一定本著推動創新的宗旨,用一條大路的照片和兩句話指引它的讀者走上創新之路。既然Jobs說I have always wished that for myself,that用于反指那多模態語篇傳遞的信息,always說明他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希望如此。這樣他就現身說法為這多模態語篇做了詮釋。這就要求我們了解Jobs行事的準則、信念和希冀,從而了解他給這個忠告的目的。Jobs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物,從他的行,可以看他的言。他迷于創新,追求完美。他說“活著就是為了給世界帶來變化,難道還有其他原因嗎?”,“創新無極限,只要想象得到,就能做到”,“引領者與追隨者的區別在于創新。”為了創新,他主張“不要為別人活著”,“不要為別人的言行所束縛。”他可能渴望求知,但他更希望獲得智慧。他希望從蘇格拉底那里得到靈感,他從佛教教義里知道了“初始心態”(beginner’s mind),也就是空空如也,不受各種習性羈絆之心。有了這樣的心態才有可能找到創新的靈感。
Jobs的思想和行動說明他孜孜以求的是創新。他借用這雜志的多模態語篇的信息,同樣是為了鼓勵Stanford的畢業生走上創新之路。再看聽眾,Jobs知道這是一批經過富有創新傳統的Stanford大學教育與熏陶的年輕人,他們將馬上走進生活,一定躊躇滿志,希望做一番事業,也希望從他的演講中得到啟迪,所以Jobs借“清晨時光”比喻他們即將起步,“鄉村公路”比喻他們的人生道路,利用這兩句話鼓勵他們尋找并踏上創新之路。Jobs這樣說,符合他們的心理訴求,所以他們不可能不這樣理解。經過對說聽雙方的這番估量,我們知道封底語篇以及Jobs的演講語篇的最終信息是激勵讀者/聽眾勇于創新。現在我們可以看一看幾個譯文。第一個譯法是直白理解,但這意義就違反常規。人不能保持饑餓,人一般也不愿保持愚蠢,直義說不通,所以一定是用于隱喻意義。如何理解還是個問題。直義也只是表述了語言意義,它傳達什么信息不得而知。第二個譯法把第一句話理解為“求知”,所以用“饑渴”;把第二句話理解為“為人”,所以用“若愚”。第三個譯法與第二個譯法基本相同,只是為了把stay譯出來,加了“常保”和“長存”。讓我們來看一看這些譯法是否是Jobs希望傳達的信息,是否符合Jobs的信仰體系和行事的準則。如果Jobs“求知若饑”,那他就不會剛進大學就中途退學;如果他“謙虛若愚”,他就不會提倡冒險精神,不會為創新而活著,而他自己也只能跟在別人后面做追隨者,絕對不可能成為引領潮流、改變人們生活、改變世界的人物。從他卓越的事跡看,他所追求的不是一般的知識,而是創新、突破。由于矢志創新,他的所作所為只是在別人看來是愚蠢而已。這樣就可以了解這兩句話所表達的信息,大體上是:求索如饑,創新如癡。說白了就是:敢于獨創,走自己的路,莫管他人議論是非。這是聽說雙方估量的結果。作為讀者,要弄懂語篇的信息也必須站在聽話人和說話人的立場上對對方作充分估量。上面提到的后兩個譯法大概是以中國文化中“如饑似渴”、“大智若愚”的思想來理解原文,也就是說結合了中國的文化語境而不是結合Jobs自身的意識形態和他所處的文化語境來理解這兩句英語語句。“求知若饑,謙虛若愚”能給那清晨公路作說明嗎?能在讀者的腦海里喚起象Jobs那樣的創新者的形象嗎?
6. 結語
Jespersen說Saussure區分語言和言語,是抓住了真理,但他又批評說Saussure在語言和言語之間制造了鴻溝(1925:14)。人本語義學提出語言研究有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Saussure面臨的任務是把語言形式分離出來,但他不否定意識的參與,主張符號是“概念”和“印象形式”的結合。Saussure之后的語言學家繼續在音義結合體的分析上做工作,從而理清了語言系統和單句結構。在這個基礎上語言研究進入了第二階段,就是在第二個音義結合層次上的研究,也就是存在于人們意識中的作為音義結合體的語言與思想結合的研究。這樣就解決了語言和言語分裂的問題,因而也就將形式主義和功能主義統一了起來,并確立了對實際語言的研究在語言學中的中心地位。這必將為語言研究開辟廣闊空間和新的路子。
Bloomfield, L. 1927. Review of Jespersen’sPhilosophyofGrammar[J].TheJournalofEnglishandGermanicPhilology(26): 444-446.
Bolinger, D & D. A. Sears. 1981.AspectsofLanguage[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Chafe, W. 1994.Discourse:ConsciousnessandTime[M].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afe, W. 1980. The Deployment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Production of a Narrative [A]. In Wallace Chafe (ed.).ThePearStories[C]. Norwood: Ablex. 9-48.
Chafe, W. 1996. Comments on Jackendoff, Nuyts, and Allwood [J].PragmaticsandCognition(4): 181-196.
Fauconnier, G. 1994.MentalSpaces—AspectsofMeaningConstructioninNaturalLanguag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romkin, V., Rodman, R. & N. Hyams. 2011.AnIntroductiomtoLangauge(Ninth Edition) [M]. War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Halliday, M. A. K., McIntosh, A., & P. Strevens. 1964.TheLinguisticSciencesandlanguageTeachng[M]. London: Longman.
Halliday, M. A. K, 2004.AnIntroductiontoFunctionalGrammar(Third Edition) [M]. London: Edward Arnold.
Jespersen, O. 1924.ThePhilosophyofGrammar[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Jespersen, O. 1933.EssentialsofEnglishGrammar[M]. New York: Holt.
Jespersen, O. 1905.GrowthandStructureoftheEnglishLanguage[M]. Leipzig: Teubner.
Jespersen, O. 1909-1949.AModernEnglishGrammaronHistoricalPrinciples(7 volumes) [M]. Heidelberg: Winter.
Jespersen, O. 1922.Language,ItsNature,DevelopmentandOrigin[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Jespersen, O. 1925.Mankind,NationandIndividualFromaLinguisticPointofView[M]. Oslo: Aschehoug.
Jespersen, O. 1960.SelectedWritingsofOttoJespersen[M]. London: Allen & Unwin.
Langacker, R. W. 1991.FoundationsofCognitiveGrammar[M]. Stand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ailer, N. 1968.TheArmiesoftheNight[M]. New York: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程雨民.1997.語言體系及其運作[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程雨民.2010.“人本語義學”十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程雨民.2011.二十年來說話研究[R].程雨民先生85歲誕辰學術研討會.復旦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