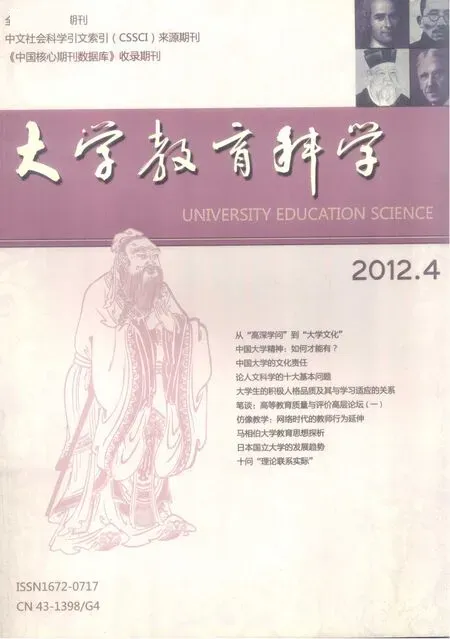教學質量只能靠教師內心來維護
□ 周 川
教學質量只能靠教師內心來維護
□ 周 川
高等教育質量,歸根到底是培養人才的質量,而人才的培養質量,需要高質量的教學來實現。質量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教授上不上本科生的課程,而是以什么態度、什么方式來上本科生的課。不管你是教授,還是副教授,抑或是講師,你站在講臺上,在教學過程中,你的態度如何,你教些什么,你如何去教,這些才是影響教學質量的最重要的因素。只要你心目中有學生,態度認真,備課充分,以學生易于接受的方式去傳授,如果還能與學生有交流和互動,讓學生學有所獲,總是受學生歡迎的,職稱高低并不重要。現在最令人擔憂的,恰恰是在這方面出了嚴重的問題。越來越多的教師不安心于教學,在教學上投入的精力和時間嚴重不足,缺乏基本的責任心,甚至于對教學敷衍塞責,搗漿糊。至于個別的將教學視同兒戲、忽悠學生的極端惡例,在媒體上也時有披露,高等教育內外的輿論往往為之大嘩。
教師不安于教學,不好好上課,肯定是錯誤的。但是,如果僅僅將板子打在教師身上,似乎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教學是一項良心的工作,它要靠教師的自覺來維持,靠基本的責任心來維持。到底是什么因素導致我們的教師不安心于教學?是什么因素導致教師失去了教學工作的基本責任心?影響因素肯定是多方面的,社會的因素,學校的因素,個人的因素,可能都有。但是,在這種種影響因素中,最主要、最直接的影響因素,無疑是高校普遍盛行的、不合理的教師業績評價制度。現在普遍盛行的這種教師業績評價制度,重科研輕教學,重數量輕質量,重名份輕實效,對大學教師的價值取向和精力投向產生了嚴重的誤導。不合理的教師業績評價制度,是當前教師普遍不安心于教學的始作俑者,是導致高校教學質量嚴重下滑的直接禍首。
人都是趨利的,大學教師也不例外。教師業績評價制度是一根有力的指揮棒。當前我國高校教師業績評價制度,普遍地采用計量指標的方式,偏重于科研項目的多少、發表的數量和刊物的級別,以及花樣百出的各種“名分”。只要科研項目多而不管其教學工作如何,只要發表得多且刊物級別高而不管其真實內容和水平如何,只要有種種“名分”而不管其實際效果如何,當這些指標有助于教師在職稱、津貼體系中明顯勝出時,那么,業績評價的指揮棒就必定會有力地將教師的追求和精力引導到有助于他獲得這些實利的方向上去。當一個教師將自己的目標完全定位于這些指標,并且將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滿足這些指標中去的時候,那么,他能夠犧牲的就只有教學了。因為教學在現有的各種業績評價體系中,幾乎沒有得到最低限度的體現,它是一項軟的指標,主要是一個良心活兒。按照教育的規律來看,教學本來就是很難用外在指標去衡量和評價的,除非采用學生的評價,特別是學生畢業以后對教師的評價,而這無論在技術上還是在當下的誠信體系上,又是難上加難的。
我曾指導研究生做過一個案例分析,很能說明問題。一位執著于教學且不失學術水平的副教授,是如何在職稱評審中處于明顯不利地位的。這位副教授任教于某“211大學”,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晉升副教授,21世紀初留學美國,三年后獲博士學位回國。十多年來,這位副教授擔任從本科生到博士生的各種主干課程教學,教學工作量飽滿,對學生要求嚴格,教學效果在師生中有口皆碑。更感人的是,這位老師對學生每份作業都能花大量時間和精力認真批改,其每年在學生作業上批改的文字,匯總起來足可出版一兩本著作(當然,這些文字都隨著作業一起還給學生了)。這位副教授的博士論文,以典型的質的研究方法研究美國中小學教師在城市學校和郊區學校的任教意向問題,達到很高的學術水平。博士論文以中文出版后曾獲得該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但是這位副教授三四年前在該校的兩次職稱評審中,均未能達到教授職稱的“科研指標門坎”,因為該校規定,晉升文科教授必須至少有一篇論文發表在所謂“權威核心”期刊上(該校“權威核心”期刊目錄每個一級學科一般只有一份)。這個案例向其同行們昭示了這樣一個無情的“鐵律”:無論你的教學如何認真、如何負責,但是這在該校現行的“業績指標”中卻得不到任何反映;無論你的教學怎樣優秀(且不失學術水平),但這對于晉升該校職稱毫無用處。這個案例分析后來在《大學》雜志上也刊登出來了。
現行的“業績指標”,重科研輕教學,重數量輕質量,重名份輕實效,其荒謬性和粗暴性,可謂登峰造極。到底是誰喜歡這些計量化的“業績指標”呢?教師顯然不喜歡,學生也不喜歡,說穿了,就是行政管理者最喜歡。首先,有了這樣一種計量化的“業績指標”,管理者就能夠輕而易舉地將這些“業績”數據轉化成自己的“政績”分數;越是追求GDP式“政績”的高校管理者,越是喜歡這種“業績指標”。其次,有了這樣一種計量化的“業績指標”,管理者就有了“外行領導內行”的尚方寶劍,充當起了評判者的角色;管理者再怎么不懂專業,但是他只要會數數字,只要會對照“權威核心”目錄按圖索驥,就能隨心所欲地臧否任何一位教師的學術水平和學術成就。再者,有了這樣一種計量化的“業績指標”,管理者就從教師的服務者搖身一變成為教師命運的主宰者,他能憑借著這些指標把教師整得團團轉,并且最終決定教師的升降和進退。荒謬粗暴的“業績指標”,是高校行政化的惡果,也是高校行政化的權杖。
此類“業績指標”的盛行,勢必將教師誤導入歧途。他們為了達到這些“指標”,整天忙著炮制有益或無益的文章,忙著填表、申報、公關,整天為這些忙得團團轉,哪還能安心于課堂,哪還有心思去“誨人不倦”,哪還有精力去關注學生到底學到了什么。如果就事論事去責備教師,沒有意義,但后果肯定是嚴重的。荒謬粗暴的“業績指標”在大學里盛行,付出的必將是科研和教育的代價,還有道德的代價。它既嚴重地戕害了科研,又更加嚴重地戕害了教學,褻瀆了高等教育事業的尊嚴。
至于那些“教學名師”、“教學成果獎”、“精品課程”等等獎項,其效果也是值得憂慮的。設立這些獎項,初衷也許是為了提高教學質量,但實際后果卻往往相反。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這些獎項有悖于“名師”成長的規律,有悖于教學工作的常識。第一,何謂“教學名師”?何謂“教學成果”?對此雖說眾說紛紜,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教學名師”和“教學成果”,是萬萬不能通過填寫表格來自己證明自己的。如果有不上課或不好好上課的人,由于表格功夫好或“詩外功夫”好而被評為“名師”或“教學獎”,那么這些獎項的負面作用對絕大多數教師的教學態度會產生極大的殺傷力。第二,獎項本來只是手段,但是現在卻堂而皇之成了目的。教育主管部門自上而下對大學教學水平的認定,都是簡單地以“名師”、“教學獎”、“精品”之類的級別和數量來標識。如此這般變手段為目的,必然驅使學校和當事人在各類申報表格上絞盡腦汁,做足花樣,甚至弄虛作假。那么這些獎項的負教育效應也就同樣在所難免了。
教學質量歸根結底要靠教師內在的責任心來維持,任何外在的直接針對教學的激勵措施,效果都必定是有限的,激勵不當甚至會起到完全相反的作用。在當前,只有徹底廢止荒謬粗暴的“業績指標”,最大限度地減少各種人造名分和獎項的誘惑,讓校園安靜下來,讓教師從名韁利鎖中解脫出來,負責任的教學才有可能真正地回歸大學校園。
book=48,ebook=64
周川(1957-),男,江蘇南通人,教育學博士,蘇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論及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研究。
- 大學教育科學的其它文章
- 從經驗到科學:中國大學教學質量外部評估的走向與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