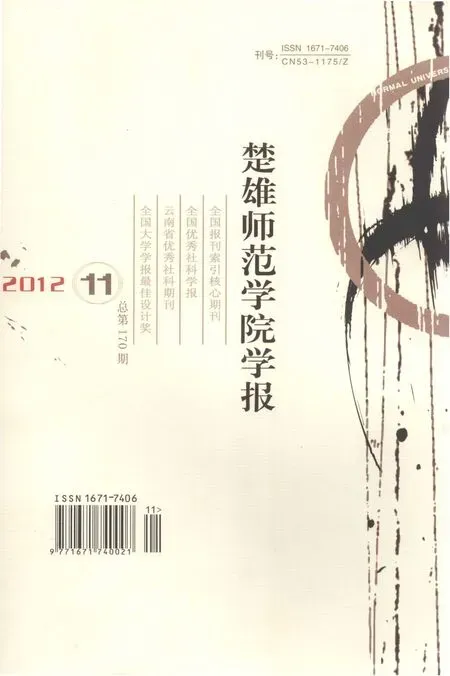興:審美人格的詩意構建*
楊曉雯
(云南大學,云南 昆明 650031)
一、興致——“興”美學意蘊的新呈現
“興”是中國古典美學中最富于爭議也是最有魅力的概念之一,它復雜、游動、多變,朱自清先生早已有“你說你的,我說我的,越說越糊涂”[1](P38)的感嘆。其纏夾的原因,很大程度源于“興”是一個歷史的、動態發展的理論范疇,其內涵隨時代背景、詩歌創作、文學思潮變化而變化。
“興”后來和《詩經》相連,漸漸衍生出詩學、美學意義上的內涵及用法,主要是隱喻和美刺之意。
彭鋒認為,隨著魏晉以來審美意識的不斷自覺,“興”有了第三個主要內涵:“即純美學意義上的情感的興發和興發的情感,我們把它稱作‘審美的存在狀態’。”[2]這種審美的存在狀態在袁濟喜看來,應該是隨著人的覺醒而逐漸自覺的,在魏晉六朝時代得到了最輝煌的展現。[3]
內涵的變化,首先表現為符號的改變。先秦文獻中的“興”,有美學意義上使用之“興”,也有日常語境中使用之“興”。前者有如《周禮》之“六詩”說, 《毛詩序》之“六義”說以及《論語》“詩可以興”之“興”。這些“興”,有的是“起”義,如“六詩”之“興”,即為音樂“起奏”之意;有的是“引譬連類”之義,如“詩可以興”。日常語境中的“興”,主要是旺盛、興隆、興辦、起床、奮發之義。無論是美學意義還是日常語境中的“興”,都是作動詞用的。而在魏晉時期,“興”出現了名詞用法,最為典型的,如《世說新語》王子猷雪夜訪戴“乘興而來,興盡而歸”之“興”。這種興致、興趣意義上的“興”普遍流行于士大夫之間,是他們進行人物品藻或游山玩水時抒發感情、品評風物的詞匯,但在魏晉以前是極為少見的。
“興”于魏晉,變化的不僅是詞性,其發音亦隨之變化。早有學者注意到了“興”發音的改變,宋代的李冶說:“然興字仍有兩讀,讀從去聲,則為興起之情;讀平聲,則為興起之意。”(《敬齋古今·拾遺》)也即是“興”作為興起之意,如果是名詞讀作去聲,如果是動詞,則讀作平聲。
從李冶關于“興”的讀音的解釋來看,到魏晉之后,“興”更多地和“情”連屬而用。而在先秦文獻中,實際上很少提到興中含情,其一個重要原因是,情在先秦文獻中主要作情況、實情、本性等,很少用作情感。大約在魏晉時期,“興”與“情”已經對舉連屬,如沈約《謝靈運傳論》之“情興所會”,劉勰《文心雕龍》之“情往似贈,興來如答”,北朝楊衒之《洛陽伽藍記》之“山情野興”。唐以后,此類用例更多,殷璠講過“情幽興遠”,皎然《詩式》稱“語與興驅,勢逐情起”,又稱“以情為地,以興為經”,皆旨“情”、“興”對舉而意近。古人釋“情”,常常定義為“外物所感者”(《荀子·儒效》),大約在這個基礎上,賈島《二南密旨》明確以“情”釋“興”:
興者,情也。謂外感于物,內動于情,情不可遏,故曰興。
這與“感興”說并無二致,只是直接點出了外感內動的結果——情,從而使“興”具有了可把握性。以上語境中的“興”雖可大致理解為“情”,但與作為表述一般心理狀態的“情”并不相同。這是一種詩情、審美之情,是由即目所見的活生生的外物當下觸發的生動的情。這種興感與外物而起之情,是“喜悅之情”,相當于“興致”、“興趣”。如晉廬山道人《游石門詩并序》:
釋法師以隆安四年仲春之月,因詠山水,遂杖錫而游。于時,交徒同趣三十余人,咸拂衣晨征,悵然增興。……退而尋之,夫崖谷之間,會物無主,應不以情而開興。
這種“乘興而為”的過程,是彭鋒所謂的“審美的存在狀態”,也是袁濟喜所說的“藝術生命的激活”,二者通過對“興”含義的闡釋和把握,對完成了超越日常瑣碎生活的一種藝術升騰的存在方式進行了指認。
和作為純粹詩學概念的“興”相比,這種“興”多出現在日常語境中,具有日常語匯使用上的隨意性和廣泛性。可以說,在魏晉時期,日常語境的“興”與詩學語境中的“興”在運用上出現了部分重疊。兩者的重疊也多少反映了魏晉士大夫對詩化人生或藝術人生的追求及審美實踐。
興致之“興”始于魏晉,和魏晉士人重情有關。宗白華說:“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4](P215)這種深情的喚起或表達,是他們對人生、生命意識的感悟和思考,也是對個體情感、個體價值的充分體認和直覺追求,也直接鑄成了魏晉士人在文化史上以特立獨行、瀟灑自我、重情任性著稱的一道奪目的風景。
二、興感:審美人格構建的關鍵
“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這是李白對六朝詩人以逸興為美、激發藝術生命風范的嘆賞。“逸興”描述的是審美主體任從本性、任興逍遙、自由無待的生活態度。這種生活態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就是審美人生。“興”是審美追求與人生追求的契合點,也是能否構建一種魏晉人普遍認可的理想人格美的關鍵因素。
并非人人能“興”,面對自然山水,并非人人都能觸物起情,進入悟境,獲得感情的凈化和升華。“興”在魏晉,作為人物品評的重要標準之一,獲得了新的內涵:“興”不再是簡單的描述主與客、情與景、天與人之間主客契合、情景交融、天人合一的過程和狀態,而是將“興”視為在天人合一的哲學境界及情景交融的藝術境界中,主體是否具備的感悟能力及審美能力來看待的。這種內涵折射出了個體意識的自覺,對主體受眾的關注;或者說他關注的并非是“因景起興——觸物起情——情景交融”這個過程,而是這個過程中主體一方起著多大的作用。他對這個看似理所當然的過程是存質疑態度的,并且看到了主體感悟、審美的局限性。“能興”或“不興”成了能否欣賞自然、融情于景進而深入玄境的關鍵。由于“興”本身是一種超逸功利、利害、計較之外的審美直覺活動,因此“興”對審美主體也提出了較高的人格要求。“興”體現了藝術美與人格美的重合。
王夫之很直接地將“興”視為締造審美人格的關鍵,并從這個角度對“興”作了不同于前人的界定:
能興即謂之豪杰。興者,性之生乎氣者也。拖沓委順,當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終日勞而不能度越于祿位田宅妻子之中,數米計薪,日以挫其志氣,仰視天而不知其高,俯視地而不知其厚,雖覺如夢,雖視如盲,雖勤動其四體而心不靈,惟不興故也。[5](P376)
能興者,即為豪杰。“興”在這里,一方面指將審美主體從茶米油鹽、祿位田宅的日常生存中超越出來的心理基礎,所謂“興者,性之生乎氣者也”。“興”是人本性中“氣”之所由生的源泉,根據王夫之接下來的描述,可知此“氣”乃光明澄澈之心,也是圓滿完整的人格。此“氣”也是莊子所說的:“無聽之于耳,而聽之于心,無聽之于心,而聽之于氣”[6](P117)之“氣”。另一方面,“興”又是主體精神的超越與升華。它要超越的是那種“仰視天而不知其高,俯視地而不知其厚,雖覺如夢,雖視如盲,雖勤動其四體而心不靈”,渾渾噩噩、庸庸碌碌的生活狀態。不能“興”,導致的是“心不靈”。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 “興”成了熔鑄審美人格的本體性因素。
在王夫之之前,已有學人提出相似觀點。明代袁黃在《詩賦》中對“興”作如下界定:“感物觸情,緣情生鏡,物類易陳,衷腸莫罄,可以起愚頑,可以發聰聽……斯謂之興。”[7](P230)“興”可以“起愚頑,發聰聽”,這種“啟發”作用和孔子的“詩可以興”有相通之處,但顯然前者更具有美學意味。明代趙南星更是直言:“愚人無興”,他說:“詩也者,興之所為也。興生于情,人皆有之,唯愚人無興,俗人無興。天下唯俗人多,俗人之興在乎軒冕財賄,而不可發之于詩。”又說:“夫詩者,興也,緣人情而為之者也。庸人之情不揚,俗人之情不韻。詩不難言,人自難之耳。”[8](P253)
袁黃、趙南星之論和王夫之所言,既有相似之處,又有不同之點。相似之處如,首先,他們都認為“興”和人的本情、本性有關。王夫之說“性生乎氣者也”;趙南星言“興生于情,人皆有之”。人人都有提高人生境界、進入逍遙之境的可能。其次,由于“興”具有“起愚頑,發聰聽”的重要作用,相應地,他們都將“興”視為人格境界提升的關鍵因素。第三、人人有“興”的可能,但并非人人能“興”,能達到這種自由,領略這種高峰體驗。由于“俗人之興在乎軒冕財賄”,所以俗人、庸人、愚人無興。《世說新語·賞譽》中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
孫興公為庾公參軍,共游白石山,衛君長在坐,孫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近。”孫遂沐浴此言。
在孫綽看來,衛君長這種人雖有名氣,但在山水與做詩上沒有靈性,不能起興,因而根本無法領略與享受藝術自由之境。因此,能否在生活與藝術上起興成了名士風韻的標志。這種能力與對美及自然的敏感程度有關。在中國古典美學中,審美還原的發生不是由主體的自由意志決定的,而是在人與自然的巧遇中,一種自然而然的感通中才會發生。也就是說,還原不僅僅取決于主體的意愿,還取決于“感物興思”的能力。玄學家亦然。只有超逸世俗塵世,進入興發狀態中,才可能體驗“天人合一”境界物我兩忘的愉悅,從而實現從功利道德意義的人格向人格美的提升,超越那種“雖覺如夢,雖視如盲”的庸常狀態。
王夫之、袁黃和趙南星論“興”,一方面“興”是人格境界提升的關鍵,另一方面則是詩歌創作過程中寫出好詩的關鍵,所以說“詩不難言,人自難之耳。”這里人格決定了詩格。
王夫之雖然也從人格境界的角度對“興”作了界定,卻對如何超越庸碌的生存狀態,即如何“興”未加說明。聯系他在《古詩評選》中說的另一段話可以看出“興”發狀態是如何發生的:
天地之際,新故之跡,榮落之觀,流止之幾,欣厭之色,形于吾身以外者化也,生于吾身之內者心也;相值相取,一俯一仰之際,幾與為通,而勃然興矣。[9](P68)
兩者之固有者,自然之華,因流動生變而成綺麗。心目之所及,文情赴之,貌其本榮,如所存而顯之,即以華奕照耀,動人無際矣。[10](P752)
這兩段話可視為回答“興”如何度越庸碌的生存狀態的最好參照。在王夫之看來,人與自然之間有一種深層的聯系,“兩者之固有者,自然之華”。這種關聯在“拖沓委順,祿位田宅妻子、數米計薪”的庸碌生存境界中隱蔽不彰,只有通過自然感興超越各種物我對待關系之后,它才能生動地呈現出來。因此王夫之的“興”是一種對“祿位田宅妻子”的“度越”。這種“度越”不是某種抽象的、僵腐的、一成不變的說教,而是一種生動的情感升騰狀態:“流動生變而成綺麗。心目之所及,文情赴之,貌其本榮,如所存而顯之,即以華奕照耀,動人無際矣。”在這樣的境界中,非單一的某事某物觸興起情,而是整個廣闊的天地宇宙、新舊之跡、繁華落寞、動靜止息、悲歡喜樂的碰撞把詩人帶到了一個心物合一、內外無差、身與物化的境界。主體在這樣的境界將“勃然興矣”,遂獲得一顆靈透慧心,人與世界“相值相取,一俯一仰之際,幾與為通。”這種完全超越世俗功利計較的境界不再是“仰視天而不知其高,俯視地而不知其厚,雖覺如夢,雖視如盲,雖勤動其四體而心不靈”的生存境界,而是一種超越道德功利境界的最髙境界,它提倡對人生釆取純藝術、純審美的態度,表里澄澈,一片空明。
感興的結果是人生境界的提升,能“興”則意味著獲得圓滿、完整人格的可能,意味著審美追求與人生追求的統一。這種重“興”并以“興”為美的人生態度在魏晉時期得到了最輝煌的展現。“興”升華到人生的最高層次,它使文士將自然生命激活為藝術生命,形成了完整豐厚的結構與內涵。
三、乘興而為:藝術人生的實踐
魏晉時期的名士們強調一種任興的生活。這種以“興”為美的生活造成了一個時代的藝術人生,在《世說新語》中有著生動的表現。收入這部筆記中的大都是漢末以來名士沖決禮法、率真自得、狂誕任放的軼事。名士們以自己的生命意志來支配行為,通過偶發性的情節來組織行為,形成創作。最典型的是王子猷的軼事。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任誕》)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任誕》)
王子猷出都,賞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于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任誕》)
這些故事很能說明魏晉人生與文藝以“興”為美的特點。王子猷雪夜訪戴的興致在于本身的偶發性,并不以功利目的,即見不見戴為目的,故興發而性,興盡而歸。在這里,“興”就是目的與樂趣。宗白華先生說:“這截然地寄興趣于生活過程的本身價值而不拘泥于目的,顯示了晉人唯美生活的典型。”[4](P221)宗白華先生獨具慧眼地發現了這則軼事中蘊含的晉人唯美生活的意義。晉人對“興”的理解,早已超出漢儒從政教意義的解說,而與整個人生根本意義相結合。兩晉時代的思想界與文學界,在玄學影響下,人們廣泛開展了對人生意義的討論,而這種討論往往伴隨著對山水與自然的欣賞。在宇宙造化中,人們發現了自身的微末,在觀照自然時也反思了自身存在的意義。這種觀照并非靜觀,而是通過偶發興感而達到的生命體驗。
王子猷的“種竹”、“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以及他與桓子野“不交一言”的交往,乃和嵇康鍛鐵“不受直 (值)”,陶淵明的“好讀書,不求甚解” (《五柳先生傳》)一樣,看似任誕、古怪,但實則如馮友蘭先生所云,這些魏晉玄學名士和人格美思想家們是“具有玄心的人”。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他正是個真正的藝術家”,只不過和訴諸于某種媒介的藝術作品相比,王子猷“乘興而作”的乃是“行為藝術”。由此也可見,在中國古典美學中,“乘興而作”除了創作論上的含義之外,還有行為審美實踐含義。王子猷的“乘興而來”和方回所說的“乘興而作”不同,它是一種率性而為、任情放達的直接的行為審美實踐,不見得一定要訴諸于筆端。如果說前三者“乘興而作”的直接結果是物化形態的“作品”,那么,后者“乘興而來”的直接結果則是一種“行為藝術”——審美個性的滿足以及人格境界的提升。“乘興而來,興盡而返”強調的是對人本性的尊重和真情不可違背。
任興的生活就是唯美的生活。它是人的自覺帶來的世風解放以及對自由精神追求的表現,雖然其中不乏輕狂和荒誕,但它的總體精神是向上的。所謂“興”在魏晉人看來,就是一種自由無待的生活態度,這種生活態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就是審美人生,其特點是以個體的自由無待作為人生的目的,而作為最高的境界與形式,則是駘蕩山水,寄興藝術。在魏晉文士看來,人的自然生命是受制于塵俗社會,是不自由的,那么,只有自由的人格才能超越永恒的“道”與“無”,擺脫世俗事物的紛擾。這種自由人格即是理想的人格,它順從自己的心愿,不以外在的禮儀是非毀譽作為做人的標準,真正的君子神閑氣定,擺脫外界欲望的束縛,超離于是非評判之上,以人格的自然伸張為美。這種任從真性的觀念,奠定了以“興”為美的倫理基礎。宗白華認為“魏晉時代人的精神是最哲學的,因為是最解放、最自由的”,[4](P215)宗先生認為,晉人酷愛自己的精神自由,才能推己及物,也才會有這種“意義偉大的動作”,“這種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才能把我們的胸襟像一朵花似地展開,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義,體會它的深沉的境地。”[4](P216)
四、寄情山水:人格美的詩意呈現
從魏晉人言“興”的人生觀念與文藝觀念中,我們不難發現,重“興”并以“興”為美,是建立在當時普遍存在的自然情性論之上的。士人“以玄對山水”(孫綽《太尉庾亮碑》),他們關注山水景物本身所昭示的自然之理,并進而將自然之美看作一種無所依傍、獨立自足的存在。同時,對自然的觀照采取無我的態度,在身與物化中進入與道為一的境界。宗白華先生總結為:“晉人以虛靈的胸襟、玄學的意味體會自然,乃能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瑩的美的意境!”[4](P210)《世說新語》載東晉畫家顧愷之從會稽還,人問山水之美,顧云:“千巖競秀,完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云興霞蔚。”簡文帝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不必名山大川,即使是身邊的園林,便可得莊子濮水畔逍遙之意。日常的自然風物進入如此的審美境界,正是日常生活詩化的標志。以這樣的藝術心靈面對山水,可以“由實入虛,即實即虛,超入玄境。”晉宋人眼中的自然,有著“目送歸鴻,手揮五弦”,超然玄遠的意趣。宗炳云:“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何其生生不息、極虛極活的境界,這也即所謂“以玄對山水”,以湛然之心觀照山水,領略山水美和體味山水呈現出來的道的意蘊。以性統情,應物又無累于物,即有情而能將情感上升到宇宙人生的高度,追求逍遙無待的自由之境。魏晉六朝人論“興”,往往在“興”中注入了更為深邃浩博的宇宙精神,體現出一種悲天憫人的意識。
晉廬山道人所作的《游石門詩并序》中記錄了這樣的游覽經歷:
引人致深若此,豈不以虛明朗其照,閑邃篤其情耶?……俄而太陽告夕,所存已往。乃悟幽人之玄覽,達恒物之大情,其為神趣,豈山水而已哉!于是徘徊崇嶺,流目四矚;九江如帶,丘阜成垤。因此而推,形有巨細,智亦宜然。
可以看出,詩人不否認情感的升華與凈化和外物的觸發有關,但也不認為一般的山山水水能夠觸興。斯時,夕陽西沉,暮色四合,山水隱退,詩人于是獲得如斯體驗:乃悟幽人之玄覽,達恒物之大情,其為神趣,豈山水而已哉!于是再觀覽山水,則“九江如帶,丘阜成垤”,進入的則是心物合一、情景交融的天地境界。其回歸的方式是典型的審美還原,其基礎便是天人之間的某種同構關系:形有巨細,智亦宜然。
在這些言談中,莫不滲透著對山水之美的深刻體驗。說江山秀麗,不如說是心靈英發。從品藻人物之美,到品味山川之麗,這是審美視野的巨大轉向和拓寬。他們觀日出,玩月影,彈旋琴,飲美酒,作清音,是對超塵脫俗的內在精神的追求,無形中成就了一段藝術人生。宗白華指出,正是透過這種真情,“山水虛靈化了,也情致化了”。[4](P215)如此,人們觀察宇宙之三維——人、自然和社會,才第一次完善了起來;如此,老莊所謂天人之際的關系,才能進一步親和起來。這種基于應物而無累于物,無為而無不為的原則達成的天人關系,是一種超越道德功利境界的最高境界,這種境界“以玄對山水”,對生活、對人生采取的純藝術、純審美態度,表里澄澈,一片空明。
這種境界即是馮友蘭所說的“天地境界”和張世英的“忘我之境”,是一種泯滅是非、彼此、物我的界限,實現與道同一、“天地萬物與吾一體”的人格美境界。其內涵和最高形態便是魏晉玄學人格美,按馮友蘭的分析,則是指超越道德境界之后駐留在天地境界中的人格。馮友蘭將這種“人格”稱之為“風流”,同時,他認為“風流是一種所謂人格美”。[11](P364)馮友蘭之所以把風流稱作“美”,是因為風流同美一樣,都是只可直觀領悟而不可以言語傳達的。他提出了四個構成“真風流”的條件:玄心、洞見、妙賞和深情。其中兩點:一是真風流之人,必有妙賞。所謂妙賞就是對美的深切感受,也即是美學中所說的用審美的態度來對待整個世界。正是由于有這種妙賞,我們才可以說宇宙的人情化和人生的藝術化。二是真風流之人,必有深情。[11](P348—355)這種深情并不是個人的兒女私情,而是超越自我之后對宇宙人生的深切的同情。
根據以上分析,把風流當作一種人格美是十分貼切的。風流所依托的天地境界,與其理解為哲學境界,不如理解為審美境界。而張世英正是用天人合一來描述審美境界的。從前文對張氏“天人合一”的分析,可見在馮友蘭那里作為哲學境界的“天地境界”就成了張世英這里作為審美境界的“無我之境”。屬于這種最高審美境界中的人格美,就是一種“天人合一”的人格境界之美。它具有“自然主義”和“個性主義”,即精神的自由、超越和飄逸的特點,也具有重視人的性情的真誠和純凈透明的特點,更具有渴求達到人的內外、物我、形神、本末及名教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并最終達到與天地萬物同一的人格美境界的特點。
魏晉玄學人格美,就其內涵和最高形態而言,是一種玄學名士內在人格精神與宇宙本體同一的境界美。士人遵循“應物而不累于物”、“無為而無不為”的人格修養方式,率性而為,乘興而作,造就了一個以“無”為心,以“道”為心,以“玄”為心的虛靈、純凈、空明、和諧的靈府,也即是確立了一個作為“真正的藝術家”的審美主體。這樣的主體一旦置于自然山水中,極易為景物所感,并與之發生同情、共鳴,產生內外無別、物我同等之感,從而進入一種天地萬物渾然一體的更大的和諧,更高層次的美的境界中,并達到人格精神的飛躍。王羲之《蘭亭詩》云:“爭先非吾事,靜照在忘求。”又云:“仰觀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大哉造化,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孫綽《三月三日蘭亭詩序》云:“乃席芳草,鏡清流,覽卉木,觀魚鳥。具物同榮,資生咸暢。于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決然入矣……”就是這種審美還原之后的表現。
魏晉玄學的人格美,就其標準而言,是一種性情的至誠、至真、至純之美,是對生命的“一往情深”。嵇康與向秀、呂安“率爾相攜,觀原野,極游浪之勢,亦不近遠近,或經日乃歸,修復常業。”“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司馬道子賞天月明凈,都無纖翳,嘆以為佳。”王羲之說:“從山陰道行,如在鏡中游!”很顯然,觀原野,聞清歌,賞天月,游山陰,都是魏晉士人至真至純的性情得以進一步提純并具象化、人情化的審美還原途徑。魏晉玄學人格美中的這種性情心胸已不只是真誠,而是達到了一種最高的“真”。“如在鏡中游”是一個何其空靈、澄澈又物我兩忘的境界!
魏晉玄學家們乘興而作,率性而為的直接結果是人生境界的提高,這種境界歸根到底是一種審美境界,向這種境界還原的方式只能是審美還原。
魏晉玄學名士們從事或并不直接從事某種具體的藝術美的創作,但正如揚雄所言:“言,心聲也;書,心畫也。”魏晉時代那些真誠的玄學名士“乘興而作”,即以自己的一腔熱血和整個生命去實踐純粹藝術和審美的人格。在他們所達到的人格美境界里,個體原先所感到的性情的矛盾、生死的惶惑、名教與自然的沖突、理想與現實的緊張,以及個體與社會、出仕與歸隱等種種的隔膜,都仿佛是一場春夜的喜雨,清晨的鳥語花香,勃發一片清新、和諧與生機……
[1]朱自清.比興 [A].詩言志辨[C].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2]彭鋒.詩可以興——古代宗教、倫理、哲學與藝術的美學闡釋 [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3]袁濟喜.興——藝術生命的激活[M].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1.
[4]宗白華.論〈世說新語〉和普人的美 [A].美學散步 [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5]徐中玉主編.中國古代文藝理論專題資料叢刊.意境·典型·比興編[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6]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人間世[M].北京:中華書局,1983.
[7]袁黃.詩賦 [A].古今圖書集成[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8]趙南星.趙忠毅公文集:卷八[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9]王夫之.詩廣傳:卷二·論東山.北京:中華書局,2000.
[10]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M].長沙:岳麓書社,1998.
[11]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五卷[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