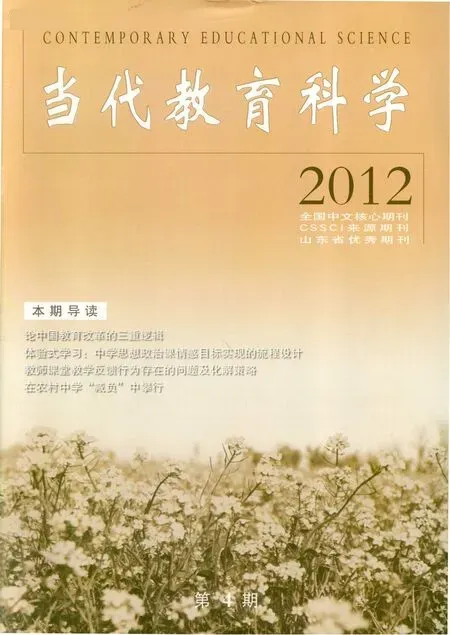“罰錢”的班規:基于德育視角的反思
● 趙春娟
“罰錢”的班規:基于德育視角的反思
● 趙春娟
近年來,當“體罰”、“變相體罰”被三令五申地禁止后,一些教師又開始采取“罰錢”這種方式來管理學生,于是有關學校對違反校紀和班規的學生以“罰錢”代替“教育”的新聞屢見報端。班級中用于約束和規范學生行為和習慣的規章制度具有管理和育人的雙重價值,但在班規實踐中,教師往往采取極端和強制的手段來實現班規的管理效能,如此簡單的“違規罰錢”能真正使我們的學生做到不再違紀了嗎?真正實現了紀律的功能了嗎?本文將闡述“罰錢”班規的特點,并從教育的本質、紀律的功能、懲罰的本義以及教師的懲戒權等方面來分析。
一、“罰錢”班規的特點
在產生方式上具有非民主性。“罰錢”的班規一般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產生,由教師來制定約束和規范本班學生行為習慣的規章制度并對違規學生處以罰款,以實現其班級管理的目標,保證班級正常的教學秩序。自上而下產生的班規往往摻雜著教師個人意志的表達,是教師對學生行為規范的強制性管理和約束,而不是出于對學生權利的尊重與維護。如此以來,“罰錢”的班規只是使學生更易于受教或是節省教師時間和精力的簡單程序,而不是一種道德教育的方式。
在實踐過程中具有外在強制性。“罰錢”班規在實施過程中,教師作為班規的制定者、執行者、監督者,其權利往往凌駕于班規之上的,規范只是用于約束學生,而不限定教師。教師通過對違規學生采取經濟制裁而賦予班規以外在權威,學生遵守班規并不是出于對規范的認可和尊重,而是出于對制裁的恐懼,兩者所體現的道德價值截然不同,外在強制力量支撐下的班規實踐已然喪失了德育的價值。
在功能上片面追求管理效能。“罰錢”是教師對尚未成年且沒有經濟收入的學生采取的經濟制裁的手段,這種帶有強制性質的手段唯一的目的就是使教師整齊劃一的實現其班級管理目標,維持其班級教學的秩序。道德教育從來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難以在短期內見效,加之應試的壓力,老師在班規實踐中便不看重甚至放棄這一教育的任務,轉而采取“罰錢”這種極端的管理手段而片面追求班規的管理效能。
二、為什么“罰錢”的班規缺失德育價值
首先,從教育的本質來看,“罰錢”的班規偏離了教育的根本目的。“學校教育是一種培養人的社會活動,其本質目的在于培養人、塑造人、發展人、完善人,舍棄‘育人’,就不能稱之為教育”。[1]紀律教育作為學校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是學校教育工作得以正常開展的手段,更重要的是,社會生活正常運行,需要使社會成員從小規范自己的行為,養成合乎社會需要的紀律性或紀律精神,在這個意義上,紀律是學校教育目標之一。教師為了創造更易于學生受教的班級環境,不惜采取各種極端的手段對擾亂和違背班級規章制度的學生進行處罰。當“體罰”、“變相體罰”等強制手段在學校被明令禁止后,老師們又在班規中采取“罰錢”這一新的班級管理辦法,在教師整齊劃一地完成教學任務的同時,班級的氣氛也因人人自危、謹言慎行而變得死氣沉沉。紀律不能為管制而管理,而應為教育而管理,在規范學生行為習慣的同時培養學生的紀律意識或紀律精神、成為一個有道德的公民才是學校紀律的教育目標。“罰錢”的班規不是在培養自由的人和創造思維,而是在維持一座座規模化批量化生產應試人才的專業工廠的秩序。
其次,“罰錢”的班規喪失了紀律的育人功能。我國通常把學校紀律納入德育的范疇,在其具有的多種價值所構成的價值體系中,育人價值具有主導地位。一個群體就是一個小社會,作為學生在校學習、生活的基本組織——班級社會是學生從家庭社會走向成人社會的中介組織,與富有感情的家庭生活相比,班級生活與更嚴格的社會公民生活的更接近。基于所有這些理由,班級規范便無法以像家庭規范那樣的靈活性來順應或提供各種各樣的環境,班級規范以其非個人的、更理性的特點培養兒童養成自我控制和約束的習慣,只有尊重班級乃至學校的規范,兒童才能學會尊重普遍的規范。這便是學校紀律的真正功能,它并不是旨在使兒童能夠從事工作、刺激他渴望受教導或節省教師精力的簡單程序,而是一種道德教育的工具。
“罰錢”的班規就是教師對違規學生采取的經濟制裁的班規,表面上看,“罰錢”的辦法在班級管理工作中一時半會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如此簡單的以“罰錢”代“教育”真的使學生懂得紀律的意義,真的做到不再違紀了嗎?“罰錢”手段是對學校德育的重磅一擊,它是教師為了實現其外顯的功利的目標,對紀律管理功能的片面乃至極端的追求,如此班規僅僅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操控了學生的行為,卻沒有使學生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和認可紀律的意義,沒有實現其育人的本質功能。
再者,從懲罰的本意來看,“罰錢”的班規扭曲了懲罰的本義。“懲罰的本質功能,不是使違規者通過身心的痛苦或者經濟的損失來贖罪,或者通過威脅去恐嚇可能出現的效仿者,而是維護體現良知的紀律的權威,如果允許違規行為不受到懲罰,必然會攪亂人們對于權威的信仰,紀律的權威就會逐漸被違規行為所侵蝕。懲罰就是向他們表明,紀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們的信仰仍然是正當的和值得的。”[2]學校教育中懲罰的本質亦是如此,懲罰是學校教育和班級管理中不可避免和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對于沒有經濟收入的尚未成年的學生進行經濟制裁實際上是在借家長的手打學生,而且還會在學生幼小的心靈上蒙上“金錢萬能”的陰影,有錢的學生不會把違紀罰錢放在眼里,沒錢的學生感受到金錢的無邊威力而去崇拜金錢。“罰錢”的辦法在實施的過程中還會造成班級成員人人自危、撒謊偽裝、告密成風等一系列班風敗壞的問題。“罰錢”的懲罰手段使學生對班規的尊重和信仰不是建立在班規的內在權威之上,而是建立在對金錢制裁的恐懼的基礎上,對制裁的恐懼與對規范的尊重截然不同,如此懲罰手段已經偏離其本質功能,走向了異化。
最后,從教師的懲戒權來看,“罰錢”的班規超出了教師的懲戒權限。“教師的懲戒權,是教師作為教育教學工作的承擔者和直接責任人員,對學生的失范性越軌行為進行管理權力范圍內的處理的權力,以懲罰違反學校紀律、規章者,戒除學生越軌行為的再次發生。”[3]規模化、制度化的教育及其活動的正常進行需要賦予教師特定的懲戒權力;尚未成年的學生在接受外在行為規范并將其內化為自身行為準則的過程中,也需要來自外來的尤其是教師的強制力量的影響。教師的懲戒權在現代學校教育中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教師需要的是合理行使其這一權力。教育行政主管部門賦予教師對學生懲罰的權限有:批評、勸告、指責、警告、記過、留校察看、勒令退學、開除等。在以上這些懲戒權限中沒有給予教師對學生實行“罰錢”的懲罰權力。教師對學生采取經濟制裁的辦法,已然超出了教師對學生的懲戒權限。教師的懲戒權是教師以社會代言人的身份對未成年學生進行引導與矯治的權力,教師不僅應合理行使這一權力,在班規實踐中更應用慈愛來調和,從而使嚴格堅決但不至于墮落為粗魯或嚴酷。
三、如何實現班規的德育價值
班規的產生方式要具有民主性。班規既可以自上而下的規定,更需通過學生集體的民主約定而形成。教師需要給予學生集體組織以足夠的支持和尊重,一個健全有效的學生集體組織將有助于學生從他律走向自律。
班規實踐中要體現師生的“共同遭遇”。班規是對班級學生約束和限制的規章和條文。但在班規實踐中,教師通常只是充當著班規的制定者和執行者,而不會與學生一起“共同遭遇”其約束和限制。正因為如此,學校紀律以及班級規章制度往往被視為教師個人意志的體現,而不能作為體現高于群體的道德訴求;往往被視為教師的特有的權利、學生必須的義務。“教師要把規范置于高出任何個體道德訴求的高度,教師必須使學生明白,規范不僅強加給他們,也同樣強加給他本人。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教師才能喚起一種感情。在倡導和實踐行民主精神的當今學校中,這種感情就會成為公共良知的基礎。”[4]
班規實踐中教師要合理實施獎懲。在學校紀律實踐中,獎賞和懲戒是一對常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它用肯定與否定的評價來鞏固和發展學生的優良行為,克服和改正學生不良行為。獎賞是一種陽性的強化;懲戒是一種陰性的調和。教師作為教育教學工作的承擔者和直接責任人員,對學生的行為規范有一定的制裁權力。教師要合理利用其獎懲的權力,避免對學生的獎懲超出其權限。由于與懲戒相比,獎賞在道德教育所起的作用明顯要少,教師在紀律實踐中應主要警惕對其懲戒權的濫用,避免對學生的懲戒超出其權限。與此同時,教師還要掌握獎懲的藝術,獎懲的方式比獎懲本身更為重要。
[1]吳洪偉.當代中國中小學紀律實踐價值取向研究[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06,(4).
[2][4][法]愛彌爾·涂爾干.道德教育[M].陳光金,沈杰,朱諧漢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62.152.
[3]王輝.論教師的懲戒權[J].教育研究與實驗,2001,(2).
趙春娟/山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院碩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張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