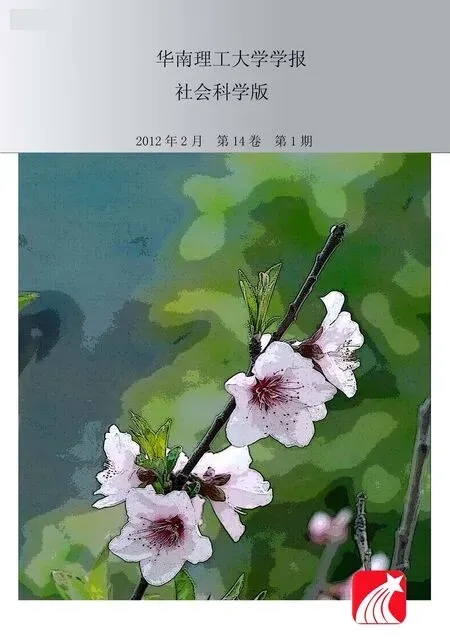論ICSID對涉中國投資條約仲裁的管轄權
——兼論ICSID涉中國第一案
沈 虹
(華南師范大學法學院, 廣東 廣州 510630)
在國際投資領域,存在多邊性的程序性公約,但是多邊性的實體公約缺失,國際投資領域的實體權利大量地體現于國家與國家之間締結的雙邊性投資保護和促進條約,全球現有雙邊投資條約已經超過3000個。數量眾多的雙邊投資條約導致國際投資法因國家和一國投資者的不同而存在差別和沖突。[1]關于投資爭議的解決方式既體現在雙邊投資條約中,也體現在《華盛頓公約》與大量的ICSID仲裁案例中。中國參與締結的雙邊投資條約數量躍居第二,僅次于德國。由于締約國之間個體的特殊性,中國在雙邊投資條約中所約定的爭議解決方式尤其是ICSID的仲裁范圍也各有差異,由此如何厘清各種沖突以確定ICSID對涉中國投資爭議的管轄權一直是學界關注的問題。但是中國在ICSID的實踐存在空白,直到2007年,中國香港居民謝業深根據《中國-秘魯雙邊投資條約(1994)》(下稱中國-秘魯BIT),以秘魯為被申請人,以秘魯違反了中國-秘魯BIT中的征收和國有化賠償,申請ICSID仲裁[2]。2009年6月19日,仲裁庭做出關于管轄權的裁決,認為仲裁庭對本案具有管轄權。本案是涉中國投資條約仲裁的第一案,該案的審理和裁決對中國具有深遠的影響,尤其是仲裁庭認為香港居民可以根據中國BIT將“征收和國有化賠償”提交給ICSID仲裁,必將打開ICSID對涉中國投資仲裁管轄范圍。本文試以該案為契機,探討ICSID對涉中國投資條約仲裁管轄權。
一、中國與ICSID管轄權的三種沖突
為了避免政治化的解決國際投資爭端,也為了給投資者在國際層面上提供爭端解決的途徑,在世界銀行的主持下制定了《解決國家和他國國民投資爭端公約》(下稱《華盛頓公約》),該公約開放簽字后于1966年10月開始生效。根據《華盛頓公約》的規定成立了爭端解決中心(下簡稱ICSID)。根據《華盛頓公約》的規定,ICSID是獨立的國際組織,享有和其他國際組織一樣的國際法上的權利和義務。ICSID的作用是為締約國與其他締約國私人投資者之間投資爭議的解決提供仲裁和調解的便利。但是國家批準《華盛頓公約》并不意味著ICSID對該國基于投資所產生的法律爭議具有當然的管轄權,ICSID對一國與他國國民投資爭端的管轄權以雙方自愿為基礎,對《華盛頓公約》的簽字和批準并不具有締約國同意將投資爭議提交給ICSID的法律效力。ICSID對爭議雙方書面同意提交給ICSID的基于投資而產生的法律爭議可以行使管轄權。換言之,《華盛頓公約》是設立ICSID的基礎,但是具體到ICSID對發生在某個締約國境內的投資爭議是否有管轄權還必須滿足其他的條件。
與其他締約國不同,中國同意ICSID管轄權的依據體現在中國和其他國家締結的雙邊投資條約中。根據中國參與的雙邊投資條約締結的實踐,中國在雙邊投資條約中對ICSID投資爭議的管轄權分成三種情況:第一種是沒有規定ICSID的管轄權,投資者和中國之間的爭議應提交給中國主管法院,對征收和國有化補償額的爭議可以在雙方同意的前提下提交給臨時仲裁程序。*見中國—挪威BIT, http://tfs.mofcom.gov.cn/aarticle/h/au/200212/20021200058415.html2010/12/23這種情況發生在1993年中國尚未批準《華盛頓公約》之前;第二種是規定了東道國和投資者關于征收補償數額的爭議,如果自當事任何一方要求友好解決之日起6個月內未能解決的,則根據該投資者的要求,可提交參考1965年3月18日在華盛頓簽訂的《關于解決國家和他國國民投資爭端公約》而組建的調解委員會和仲裁委員會,或者直接規定了提交給ICSID。一國政府和另一國投資者之間關于其他事項的爭端,可根據雙方的同意,提交如上所述的仲裁委員會。*中國—韓國BIT,http://tfs.mofcom.gov.cn/aarticle/Nocategory/201002/20100206791518.html.第三種是在雙邊投資條約中約定投資者可以單方面將投資爭議提交給ICSID,這一條款最早在1998年中國—巴巴多斯雙邊投資條約中出現,然后在后續的其他雙邊投資條約中也開始出現。有學者認為這一條款意味著中國在雙邊投資協定中全面承認ICSID的仲裁管轄權。[3]中國在1993年批準了《華盛頓公約》并成為公約的締約國,在中國批準《華盛頓公約》的時候,中國政府根據《華盛頓公約》第25(4)條提交給ICSID的英文聲明表述為:中國只考慮將因為征收和國有化而引起的賠償爭議提交給ICSID。*Text of Notification by China, http://icsid.worldbank.org/ICSID/FrontServlet .2011/01/26需要特別提出的是,中國全國人大批準《華盛頓公約》的批準書中表述為“征收和國有化賠償的數額”而不是“征收和國有化的賠償”,這兩者之間有差別。但是在上述的謝業深訴秘魯案之前,尚沒有涉中國的投資條約爭議在ICSID中出現,所以還沒有引發實踐中的爭議,但是這一中英文版本之間翻譯的差別,必將導致適用
上的問題。
簡言之,就目前中國參與的BITs和中國批準《華盛頓公約》的情況看,存在著幾種沖突:第一,是中國批準書中文版中的“征收和國有化賠償數額”和提交給ICSID的英文版“征收和國有化賠償”之間的沖突。第二是中國在BIT中與其他國家約定的“征收和國有化賠償數額,投資者可以單方面提交”和中國根據《華盛頓公約》第25(4)條所做出的“征收和國有化賠償”聲明之間的沖突;第三是中國在1998年之后簽訂的BIT中約定了“任何投資爭議可以提交ICSID”與“征收和國有化賠償可以提交ICSID”之間的沖突。
二、ICSID對涉中國投資爭議的管轄范圍之界定
學者們多數認為中國在雙邊投資條約中約定將投資爭議提交給ICSID將會導致ICSID對所有涉中國的投資爭議均有管轄權,導致“安全閥”的貿然拆除。[4]筆者認為,根據中國在加入《華盛頓公約》時的聲明,中國在雙邊投資中的約定并不能導致ICSID對涉中國投資爭議具有全面的管轄權。要對ICSID對涉中國投資爭議管轄權的界定首先必須要厘清締約國根據《華盛頓公約》第25(4)條所做聲明的效力。根據《華盛頓公約》第25(4)條的規定,締約國可以在批準或者在任何時候說明其準備或者不準備提交給ICSID管轄的投資爭議種類。包括中國在內的少數幾個國家援引了該條款對本國準備或者不準備提交給ICSID管轄的投資爭議種類提交了說明。
(一)締約國根據《華盛頓公約》第25(4)條所做說明的法律效力
由于《華盛頓公約》中對締約國根據第25(4)條所做說明的效力并沒有具體的規定,因此就締約國根據《華盛頓公約》第25(4)條所做說明的效力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說明構成對《華盛頓公約》的保留。一種認為說明只是構成一種意向,不具有法律拘束力。[5]
1.保留說不成立。筆者認為,保留說不成立。
根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中的規定,條約的保留是指的一國于簽署、批準、接受、贊同或加入條約時所作之片面聲明,無論措辭和名稱為何,其目的在于摒棄或更改條約中若干規定對該國適用時之法律效果。很明顯,中國根據《華盛頓公約》第25條(4)所做出的說明不構成保留。第一,保留是在相關條約的締約國之間導致某一個條款不能適用,而聲明并沒有導致《華盛頓條約》任何條款的不能適用,只是對管轄權的接受做出的限制。第二,條約的保留應向條約的保存機構做出。而ICSID的功能是在于為締約國和其他締約國的國民提供投資爭議解決的便利,并不是條約的保留機構和國家與國家之間就《華盛頓條約》爭議解決的機構,中國根據第25條(4)所做出的說明是對ICSID的管轄權的限定,并非向條約的保存機構做出的。第三,中國根據第25條(4)所做出的聲明只限于對中國有效,并不會在《華盛頓公約》的其他締約國之間產生對等的效力,也就是說在其他締約國沒有對ICSID的管轄權做出只限于“征收和國有化賠償”的聲明的情況下,如滿足ICSID的其他管轄權條件,則ICSID可以對中國國民針對該締約國提起投資條約仲裁的案件行使管轄權,例如秘魯并沒有對ICSID的管轄權做出聲明,而中國做出聲明了,這該聲明只對以中國政府為申請人的投資爭議有效,對以秘魯政府為申請人的投資爭議無效。
2.不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意向說不成立。意向說認為,締約國根據《華盛頓公約》第25條(4)同意提交中心仲裁的聲明只是該國單方面的聲明,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僅僅是構成一種意向。筆者認為,這種觀點無疑沒有注意到《華盛頓公約》的權威性和ICSID的國際法主體地位。第一,《華盛頓公約》是各國簽署的多邊性的重要的國際公約,需要各國通過國內法的程序予以批準才能對簽署國生效,締約國在批準和做出對ICSID管轄范圍的聲明時也是通過條約條款中的授權,是符合國內法中的憲法程序所做出的國家的行為,應具有國際法的效力。第二,從ICSID的國際法主體地位看,ICSID是根據《華盛頓公約》由各個締約國通過條約的形式授權成立的國際組織,具有獨立的國際法主體地位。中國根據《華盛頓公約》提交給ICSID的聲明其性質是國家與國際組織之間的行為,國家與國際組織之間的行為不具有法律拘束力無疑是很荒謬的推論。第三,無法律拘束力說與ICSID的實踐不符。早在牙買加案中,仲裁庭承認牙買加根據《華盛頓公約》第25條(4)所做出的說明對聲明做出后的同意具有拘束力。[6]締約國所做出的說明對ICSID是具有拘束力的。當然,締約國可以隨時更換或者撤銷說明的范圍,但是在說明生效期間,對締約國和ICSID均具有拘束力。第四,意向說的推理不合理。意向說認為《華盛頓公約》第25(4)條中規定了“聲明不構成同意”, 因此不能夠給投資者創設任何期待,由此推導出不具有法律拘束力。[7]實際上,《華盛頓公約》第25(4)的意思是指投資者不能由于締約國所做出的說明就主張締約國已經同意ICSID的管轄權,因此可以單方面將說明授權的爭端提交ICSID。換言之,在締約國根據《華盛頓公約》第25條(4)做出聲明的情況縮小管轄權的情況下,投資者提交屬于聲明范圍內的投資爭議的前提依然必須存在著其他書面的“雙方同意”。這一“聲明不構成同意”條款是為了回應在公約草擬的過程中,有談判國提出“在聲明的范圍內,投資者可以單方面將投資爭議提交給ICSID,聲明構成同意的一種方式”的主張。事實上是為了強調在締約國根據《華盛頓公約》做出聲明的情況下,投資者不能單憑聲明就主張“書面同意”的存在,而單方面將投資爭議提交給ICSID。
3.締約國的說明是對ICSID管轄權的限制。根據《華盛頓公約》第25條(4)的規定,締約國可以在加入和批準公約時對該國擬同意提交或者不同意提交給ICSID的類別予以說明,也就是說國家可以做出肯定的說明和否定的說明。對締約國做出肯定說明的,ICSID根據《華盛頓公約》的規定,可以對締約國同意的投資爭議行使管轄權;對締約國做出否定說明的,則ICSID可以對除否定說明外的其他投資爭議行使管轄權,其實質是締約國對ICSID對針對本國提起的投資爭議的限制。第一,從國際法的法理看,國際組織和國家作為國際法最重要的兩種主體,但是其獲得國際法主體的法律依據是不同的。國家是基于國家主權原則,國際組織獲得國際法上的人格是基于某些國家為了實現共同的目的賦予了常設性的機構有別于國家的功能,就如同在國內法中賦予非法人主體法律人格一樣。[8]國際組織的獨立法律人格已經在國際法院“關于聯合國國際求償案”中得到確認。根據《華盛頓公約》,ICSID具有獨立的職能,其職能是為國家和他國國民投資爭議提供爭端解決的途徑,這是《華盛頓公約》全體締約國對成立ICSID的授權。但是由于投資爭端發生于某一個締約國內,其本質為締約國主權管轄范圍內的事項,為了減輕發展中國家的擔憂,《華盛頓公約》還賦予了各國可以自愿的接受ICSID的管轄權,也就是說在《華盛頓公約》關于“投資的法律爭議”這一大的授權下,締約國還可以對某類“投資爭議”是否提交給ICSID個別授權,這一授權成為ICSID行使管轄權的條件之一。第二,根據《華盛頓公約》的規定,締約國根據《華盛頓公約》第25條(4)所做出的聲明不構成第25條(1)的同意,也就說ICSID在行使管轄權的時候,除了要滿足第25條(4)中的條件外,還需要滿足第25條(1)的規定。[9]這一點也可以從《華盛頓公約》第25條的名稱為“管轄權”得到驗證,換言之,ICSID在行使管轄權的時候要滿足第25(1)至25(4)的條件。第三,《華盛頓公約》這種安排是屬于國家經濟條約談判中“自上而下”的談判方式。[10]也就是說在締約國沒有做出聲明限制管轄權的情況下,ICSID對體現在其他書面法律文件中“同意”的投資爭議均有全面管轄權。[11]《華盛頓公約》這種安排事實上可以起到緩和發展中國家擔憂的作用。在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中,發展中國家往往處于弱勢,基于吸引外資的需要,不得不接受另一方發達國家高要求的保護標準,其中之一就是將所有的投資爭議都提交給國際仲裁庭(ICSID或者是臨時仲裁庭),而投資者與國家之間的爭議本質上為“一國內政”,所以《華盛頓公約》為處于弱勢的國家保留了做出聲明對管轄權予以限制的機會。
具體到中國在批準《華盛頓公約》的時候所做出聲明,其提交給ICSID的英文版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的批準書中有差別。根據中國提交給ICSID的聲明,中國同意將涉及“征收和國有化的賠償”這類投資爭議提交給ICSID。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批準書中表述為“征收和國有化的賠償數額”這類投資爭議提交給ICSID。其兩者的差別在于: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批準書,何種行為構成征收和國有化,以及該種行為是否需要賠償只能由中國的國內法院裁決的,只有在中國國內法院確定了征收和國有化行為已經存在并且需要賠償,投資者對賠償的數額有異議的,才能提交給ICSID。而根
據中國提交給ICSID的聲明,只要是征收和國有化賠償就可以提交給ICSID,其范圍要比“征收和國有化賠償數額”要廣泛很多。筆者認為,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差別,應是中國提交給ICSID的英文版具有法律拘束力。第一,從1993年中國批準《華盛頓公約》到現在,中國政府一直沒有對該差別予以補正,根據國際法中的“禁止反言”的原則,中國政府需要為其國家行為承擔后果。第二,《華盛頓公約》的締約國現有157個*http://icsid.worldbank.org/ICSID/FrontServlet?requestType=CasesRH&actionVal=ShowHome&pageName=MemberStates_Home.2011/02/14.,要求ICSID以各國國內程序中的批準書為準,無疑是強人所難,ICSID只對接收到的文本為準,而無法以締約國國內批準書為準。
但是中國在1998年以前所簽訂的BIT中提交給ICSID的投資爭議約定為“征收和國有化的賠償數額”條款并不直接限制ICSID的權限,其限制的是根據BIT提交ICSID的BIT另一國投資者的權利,也就是說。BIT是投資者提起仲裁的依據,其中對同意提交給ICSID的具體事項的約定是對仲裁的限制,就如同在國際商事仲裁中,爭議的雙方可以約定提交仲裁的事項,但是該約定并不會限制國際商事仲裁機構的權限,約束的只是仲裁協議中的雙方。簡言之,在涉中國的投資條約仲裁中,ICSID的管轄權既受到中國根據《華盛頓公約》第25(4)條做出的說明的限制,也需要審查投資者根據條約提起仲裁時其條約約定仲裁事項的限制。因此,在1998年之前所簽訂的BIT中,投資者不得將“征收和國有化賠償數額”之外的投資爭議提交ICSID,即使ICSID對“征收和國有化賠償數額”之外的其他涉及“征收和國有化賠償”的問題具有管轄權。
(二)“全部投資爭議”與“征收和國有化賠償”之沖突
在1998年后,中國所參與的BIT對可提交仲裁的事項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這一變化以中國——巴巴多斯BIT為分水嶺。在該BIT中,中國和巴巴多斯約定了“締約一方的投資者與締約另一方之間任何投資爭議,應首先協商,如在六個月內未能協商解決,可以提交ICSID或者根據《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仲裁規則》設立的仲裁庭”。*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巴巴多斯政府關于鼓勵和相互保護投資協定》第九條。http://tfs.mofcom.gov.cn/aarticle/h/bk/201002/20100206785125.html,2011/1/22中國之后與其他國家簽訂或者重新簽訂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中對投資者——國家之間的爭議解決表述為“投資者與締約另一國之間的投資爭議應協商解決,如在六個月內無法協商解決,應提交ICSID,除非爭議雙方同意依據《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仲裁規則》或其他仲裁規則設立專設仲裁庭”。*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關于促進和相互保護投資的協定》第九條。http://tfs.mofcom.gov.cn/aarticle/h/au/200405/20040500218063.html,2011/1/22.由此可見,中國開始在雙邊投資協定中接受了“任何投資爭議”可以提交給ICSID,毋庸置疑,任何投資爭議的范圍包含了中國在批準加入《華盛頓公約》中的“征收和國有化賠償”的爭議。由此產生兩個問題:第一是中國“全部投資爭議可以提交ICSID”條款對在1998年以前中國所締結的“征收和國有化賠償數額可以提交ICSID”條款的效力,也即是1998年前締結雙邊投資條約的國家投資者是否可以根據最惠國待遇條款主張“全部投資爭議提交ICSID”的權利;如果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話,則第二個問題是“全部投資爭議可以提交給ICSID”是否能夠擴大了ICSID對中國“征收和國有化賠償”管轄權的范圍。關于最惠國待遇條款是否能夠適用于程序性權利在ICSID的實踐中有不同的做法。在較早期的Maffezini案中,仲裁庭裁定最惠國待遇條款可以適用于爭端解決。*ICSID Case No.ARB/97/7.在晚近的Plasma訴保加利亞案中,仲裁庭拒絕了申請人根據最惠國條款啟動仲裁程序的主張。*ICSID Case No.ARB/03/24但是就ICSID的整體實踐看,仲裁庭傾向于認為最惠國待遇條款可以適用于爭端解決。[12]因此,就中國的雙邊投資條約實踐看,存在著1998年以后所簽訂的雙邊投資條約中約定的“基于投資所產生的爭議提交給ICSID”可以擴大適用于“征收和國有化賠償數額”的條約。
如上所述,ICSID在行使管轄權的時候,除了要滿足第25(1)條所規定的“雙方書面同意”的條件外,還必須要滿足締約國根據《華盛頓公約》第25(4)條所做出的授權聲明。也就說投資者可以根據最惠國待遇條款主張中國與該國雙邊投資條約中原有的“征收和國有化賠償數額”已經擴大為“全部投資爭議”可以提交給ICSID,但是ICSID對中國境內投資爭議除“征收和國有化賠償”之外的投資爭議不能行使管轄權。簡言之,ICSID對涉及中國投資條約仲裁的范圍可以分成幾種情況:第一,在BIT中約定“全部投資可以提交ICSID”的情況下,ICSID的管轄權也只限于“征收和國有化賠償”;第二,在BIT中約定“征收和國有化賠償數額提交給ICSID”的情況下,如果仲裁庭認為最惠國待遇條款可以適用于程序性權利,則ICSID對中國境內的投資爭議的管轄范圍限于“征收和國有化賠償”;如果仲裁庭認為最惠國待遇原則不能適用于程序性權利,則ICSID的管轄權只限于“征收和國有化賠償數額”的投資爭議。
但是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國-秘魯BIT中約定的是“征收和國有化賠償數額提交ICSID”。在謝業深訴秘魯案中,仲裁庭明確指出最惠國待遇原則不適用于爭議解決條款,[13]也就是說不能由于其他中國所締結的雙邊投資條約中約定提交給ICSID的范圍擴大而導致中國-秘魯BIT中的爭議條款適用范圍擴大。但依舊裁定仲裁庭對“征收和國有化賠償”具有管轄權,仲裁庭的依據有兩點:第一是認為中國-秘魯BIT中有“岔道口條款”,事實上使得投資者不可能將“征收和國有化賠償數額”提交給ICSID,第二認為根據中國-秘魯BIT的目的和宗旨,只有允許投資者將與“征收和國有化有關的事項”提交給ICSID才能保護投資者的利益。
三、ICSID對涉中國國民投資爭議的管轄權
根據《華盛頓公約》的規定,ICSID管轄的是一個締約國和另一個締約國國民基于投資所產生的法律爭議,其要素第一為投資發生于締約國的境內,第二為該投資者為投資條約定義中的“國民”。眾所周知,在國際經濟的領域中,中國是一個特殊的主體,在世界貿易組織中,中國具有“一國四席”的地位。由于歷史的原因,香港、澳門在1997年和1999年才陸續回歸。由于實行“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香港和澳門在國際經濟交往中具有獨立的地位,在某些國際經濟組織和條約中可以獨立于中國(大陸),甚至出現了香港、澳門加入的條約中國(大陸)沒有加入的情況。
根據中國(大陸)和其他國家締結的雙邊投資條約中對適用主體“國民”的定義,國民是指“具有該國國籍的自然人”。由此導致的問題就是中國(大陸)和其他國家締結的雙邊保護投資協定是否可以適用于香港、澳門的永久性居民。在謝業深訴秘魯案中,ICSID仲裁庭裁定對本案具有管轄權,香港居民謝業深可以作為中國國民援引中國-秘魯BIT。有學者主張該案關于管轄權的裁定為枉法裁判的先例,應予以撤銷。[14]
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香港和澳門居民的國籍問題,本文試探討香港居民的國籍,澳門居民的國籍則“同理可證”。筆者認為,香港居民和中國國民不能當然的畫上等號,但是大部分的香港居民具有中國國籍,在國際法意義上是中國的國民。第一,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政府從來沒有放棄對香港居民的國籍管理,只是限于香港為英國所實際控制而受到限制。從清朝末期、國民黨政府時期乃至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政府一直主張國籍法適用于香港地區。[15]第二,中國是單一制的國家,香港的回歸并沒有改變中國單一制的政治結構,中國在政治的意義上是單一主權的國家,在單一主權的語境下,不可能產生不同地區的居民有不同的國籍;雖然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權,但是并非所有的中國(大陸)的法律不能適用于香港地區。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其他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適用于香港地區。也就是說香港地區自然人的國籍應受中國法律的規范。第三,根據1996年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9次會議通過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幾個問題的解釋》中明確規定了:凡具有中國血統的香港居民,本人出生在中國領土者,以及其他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規定的具有中國國籍的條件者,都是中國公民。第四,國籍從國際法的角度看,國籍是一個人對國家的忠誠義務的體現,國籍本身是承載政治內容的法律概念,是國家對本國公民行使外交保護權的基礎,香港居民如無中國國籍,則中國政府將喪失對香港居民在外國的外交保護權,這無疑與中國的外交實踐不符。綜上所述,香港居民中除了已經明確取得外國國籍的,否則皆為中國公民。
當然,在謝業深訴秘魯案中,ICSID仲裁庭裁定香港居民謝業深可以作為中國國民援引中國—秘魯BIT也這一結論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中國-秘魯之間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簽訂于1994年,次年生效。而香港在1997年7月1日才正式回歸中國,也就是說在中國—秘魯BIT談判和生效的時候,當時的香港還沒有回歸,中國-秘魯BIT當然的不能適用于香港地區。但是對香港回歸之后所生效的中國締結的BIT,如果條約中還是約定該BIT適用于“具有該國國籍的自然人”,而又沒有明確排除適用于香港、澳門居民的話,則在國際層面上,把該BIT解讀為適用于香港、澳門居民是無可厚非的。但是鑒于香港和澳門實際上也與其他國家簽訂了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為了避免一個香港居民既可以適用香港和其他國家締結的BIT,也可以適用中國(大陸)以中國名義簽訂的BIT這一混亂的居民,中國(大陸)在以中國名義簽訂BIT的時候,應明確把香港、澳門居民排除適用該BIT。
四、結 論
基于投資條約和《華盛頓公約》所確定的ICSID對投資爭議的管轄權必須滿足三個條件:第一是投資條約中的“書面同意”;第二是符合《華盛頓公約》第25條的要求;第三是滿足東道國作為締約國一方根據《華盛頓公約》第25(4)所做聲明的范圍。
從1998年開始,中國政府呈現出全面接受ICSID管轄權的趨勢,這與中國的經濟實力日益增強有關,也有中國擴大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的投資活動有關。由于中國根據《華盛頓公約》第25(4)條說明范圍的存在,ICSID對以中國為被申請方的投資爭議只限于“征收和國有化賠償”。相應的,為維護中國投資者的利益,中國在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約定“全部投資爭議提交ICSID”時應關注該國對ICSID管轄權的授權,以避免“全部投資爭議提交ICSID”落空的結果。
由于香港、澳門的特殊問題,中國(大陸)在參與簽訂BIT時應對香港、澳門居民予以關注,明確香港、澳門居民是否適用該BIT。基于“一國兩制”的實際情況,中國應在BIT中明確該BIT不適用于香港和澳門地區,該條約中所涉“國民”不包括香港和澳門居民。
參考文獻:
[1] Calvin A.Hamilton&Paula I.Rochwerger, Trade and Investmen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rough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Treaties[J],New York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Vol.18,2005,p3.
[2] Tza Yap Shum v. Republic of Peru,ICSID Case No.ARB/07/6. http://icsid.worldbank.org/ICSID/FrontServlet.2011/01/12
[3] 魏艷茹.論我國晚近全盤接受ICSID仲裁管轄權之欠妥[J].國際經濟法學刊,2006(1):109-144.
[4] 陳安.中外雙邊投資協定中的四大“安全閥”不宜貿然拆除[J].國際經濟法學刊,2006(1):3-38.
[5] Monika.C.E.Heymann.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Settlel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Relating to China,[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Vol.11(3),2008.
[6] Kaiser company V. Jamaica, ICSID Case No.ARB/74/3,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and Competence(6 July 1975),1 ICSID Reports 296(1993).
[7] Monika.C.E.Heymann.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Settlel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Relating to China,[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Vol.11(3),2008.
[8] 伊恩·布朗利.國際公法原理[M].曾令良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753.
[9] Lucy Reed,Jan Paulsson,Nigel Blackaby, Guide to ICSID arbitration[M].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4(23).
[10] 徐崇利.經濟全球化與國際經濟條約談判方式的創新[J].比較法研究,2001(3):68-71.
[11] Carolyn B. Lamm. Jurisdi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J], ICSID Review.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 ,Vol.6.Number 2,Fall 1991,466.
[12] 徐崇利.從實體到程序:最惠國待遇適用范圍之爭[J].法商研究.2007(3).
[13] Latest Developments in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LA ISSUES NOTE NO.1(2010).P5
[14] 陳安.對香港居民謝業深訴秘魯政府案ICSID管轄權裁定的四項質疑——《中國—秘魯BIT》適用于“一國兩制”下的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嗎[J].國際經濟法學刊.2010(1).1-40.
[15] 張勇,陳玉田.香港居民的國籍問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35-63.13602866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