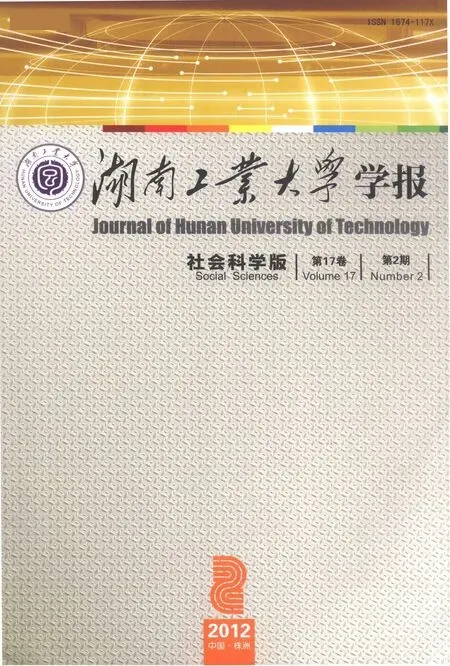邊緣生態·民間智慧·世道滄桑
——論《天眼》的境界獨特性和內蘊豐厚度*
劉起林
(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廣東廣州510006)
邊緣生態·民間智慧·世道滄桑
——論《天眼》的境界獨特性和內蘊豐厚度*
劉起林
(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廣東廣州510006)
彭見明的長篇小說《天眼》選擇湘楚民間的相術文化及相關社會生態正面寫實,既趣味盎然地描繪了一種底層社會的邊緣性風俗畫卷,又深刻地參悟和闡釋了民間相術所包含的處世境界和生存智慧,并以此為基礎洞察世事滄桑和人心善惡,其中體現出創作主體以民間智慧“拯世”“渡人”的精神意圖。小說由此顯示出既具境界獨特性又具內蘊豐厚度的藝術品質。
《天眼》;相術文化;邊緣生態;民間智慧;世道滄桑
一
早在20世紀80年代,彭見明即以《那山那人那狗》《大澤》等作品著稱于中國文壇,90年代后,他的創作明顯表現出以追求審美獨特性的創作主旨,堅持一部作品一個題材領域的創作思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正如他自己曾經明確談到的:“我孜孜以求的、苦苦尋找的是:我的作品中,有多少自己的聲音(能夠區別于他人的聲音)。”“在每一件新作中的眾多文學要素里多多少少提供一點更新自我(且不說超越)、給人耳目一亮的東西”。[1]繼90年代中期的《玩古》借玩古這一民間消閑文化時尚對世相民風的獨到體察、新世紀之初的《鳳來兮》由婚外情故事對人情冷暖的洞燭幽微之后,彭見明2008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天眼》又在追求審美獨特性方面令人耳目一新。
《天眼》竟然選擇了“相術”這一被長期視為“封建迷信”的社會生態作為創作題材。在當代中國,無論是社會文化整體格局還是民間社會,相術、巫鬼之類的“封建迷信”活動,都處于非主流的、被遮蔽和被摒棄的邊緣狀態。雖然新時期“尋根文學”的“復魅”敘事,曾使各類民間神秘文化的審美和精神意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展現,但在時代文化整體格局中,其邊緣性的定位并未發生根本改變。彭見明的《天眼》卻采用正面寫實的方式,來探尋湘楚民間的相術文化,題材選擇本身就顯示出巨大的審美獨特性和藝術探索性。更為難能可貴之處在于,作者不僅從底層社會邊緣性風俗畫卷的角度,趣味盎然地描繪了民間相術這一在當代中國鬼祟、乖戾卻始終頑強地存在、甚至也被社會各階層人士內心普遍認同和依賴的文化生態;還對民間相術所體現的處世境界和生存智慧,進行了精神文化層面深刻的參悟和闡釋;并以此為基礎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審美視角,既洞察世事滄桑和人心善惡,又包含著一種以民間智慧“拯世”“渡人”的精神企圖。
于是,《天眼》在從容平和、若巧若拙之中,顯出別致幽邃、鋒芒內聚的藝術風姿,審美意蘊超越了一般民俗小說就事論事或搜奇獵異的境界而變得豐富和深厚,作品的精神氣象也擺脫了因獨特而步入怪異的可能性,顯得穩健、正大起來。
二
《天眼》以民間相術為審美觀照對象,展現了一個隱秘、獨特而多姿多彩的邊緣性社會生存空間、一種別有意味的民間生存樣態。
作品以相術高人何了凡、何半音父子的人生軌跡和生存狀態為敘事中心和情節線索。作者廣泛地展示了他們的學藝過程、謀生方式、日常生態、江湖名聲、看相奇遇等各個側面,而其中著重突出的,當為何氏父子對于社會“主流”生態和“正統”人生模式的疏離。何了凡在那整個社會都認為干“革命工作”無比神圣和光榮的時代,卻覺得學算命來神而做工人乏味,懶散、敷衍到最后,只好辭職回鄉了事。何半音明明頭腦靈泛,但在似乎最應該規規矩矩地接受老師教育、熱熱鬧鬧地在學校里玩耍的年齡階段,卻是看閑書、跑江湖如魚得水而上學校總是心神不寧,最后也只好呆在家里,自己找舊書、破報紙悶頭鉆研。改革開放,時來運轉,他們由山鄉進縣城生活,卻拒絕有利于看相生意的繁華路段,偏要在老城區的流星巷深處找個出租屋來安頓,方覺“塘大水深好養魚”……凡此種種,均體現出何氏父子一副安樂于邊緣性社會生存空間,如《莊子·秋水》篇所說“曳尾于涂中”的“泥龜”式的人生姿態。
圍繞何了凡父子的看相測字生涯,小說還廣泛地展現了相術文化圈的群體生態。從“寅齋公”、慧覺、本寂等專業相術之士,到秀妹子、心宜等深諳相術之道的女流之輩,再到劉鐵、郭向陽、郭如玉等巫術的信奉、迷戀者,作者對他們的人生隱曲和命運真相,都進行了或正面或側面的點染和勾勒。其中的描述重心,也是相術對他們人生的意義和作用。于是,一種以相術文化為價值資源和立世根基的社會邊緣生態,以及其中所體現的“道中庸”但“實高明”的文化姿態,就被有力地展現了出來。“邊緣性文化資源立足于異質的共存、多樣的共生,社會與文化的‘他者’、‘底層’、‘弱勢’、‘沉默的大多數’之中,也確實埋藏著深厚的人文底蘊和道義光彩”,[2]因此,這種審美開拓實際上是作家深厚的人文情懷的藝術表現。
三
在此基礎之上,《天眼》以“相術”這種邊緣文化生態所包含的價值底蘊為基礎,參世道、悟人生,由此揭示出一種深具民間智慧的人生境界與處世哲學。
以原始宗教觀念為基礎的傳統巫文化及其相術之道堪稱源遠流長,而且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已經與儒、佛等文化的民間積淀相互交融,確實蘊藏著深刻的人生哲學意味。也正因如此,這種神秘文化至今尚在廣大的民間文化領域占有不可忽略的一席之地。從何氏父子謹守相術文化的處世法則,得以洞明世相而自得其樂,他們隱逸于鬧市、聞名于江湖,卻始終自甘邊緣,其中明顯體現出一種歷經世道滄桑而能獨立自足的生存境界。眾多相術圈人士,也均是依賴相術所隱含的價值觀來作為心理的支撐和行為的基點,才能既泯然眾人又獨具慧心。這種相術文化所體現的價值觀,諸多方面、種種元素凝聚到一點,就是作者借寅齋公給何半音取名所概括的“求半”。所謂“求半”,“是守本份,是知足,是隨緣,是戒貪念,是拒奢華,是甘居中游,是不偏不倚”。其中既明顯地積淀著道家文化知雌、守弱的處世哲學,又潛藏著佛家隨緣、舍得、戒貪念的思想觀念,還包含著草民百姓善良、知足、守本分的人生原則。
作者在《天眼》中張揚這種“求半”、“半音”的人生境界,無疑隱含著對人欲泛濫的商業化社會的深沉感慨,也帶有明顯的警示時尚性生存境界的審美意味。在作品中,即使是作者持基本認同態度的人物,當他們一味癡迷于放縱自己的欲望、“人心不足蛇吞象”時,也會出現“反誤了卿卿性命”的現象;當他們平和隨緣而又謹守做人的底線原則,踏踏實實地與人為善時,好運則遲早會降臨到善結“福緣”之人的身上。心宜盡管深通相術之道,但當她未能恰到好處控制自己的欲望分寸時,結果是間接地斷送了何了凡的性命。郭向陽過度地癡迷于對心宜的愛情,終瀕于瘋癲狀態,而他這種愛曾經以充分的善意和誠懇展示在心宜面前,最后也就換來了心宜在生活方面的照顧。劉鐵在險惡、詭異的仕途中維持自己為官、為人的本性,受過大老板的提攜,即不顧人事坎坷對大老板始終感恩守誠,從省城下放到了丁縣,也同樣本分做事、踏實為官,終因這世上畢竟需要認真做事之人而交得“好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還從眾多方面,將浮華奢靡的本寂和尚與低調本色的何氏父子進行了鮮明的對照,實際上是從相術文化人生哲學的持守者如何自我貫徹的高度,表達了自己的價值理念。
這樣,一種長期處于被遮蔽狀態的社會生態所包含的文化底蘊與民間智慧,也就被作者真切生動而準確深刻地揭示了出來。這種關注與揭示,既是作家精神理想的審美呈現,也使文本具備了一種“思考性”的品質。“強化思考性可能正是提升精神高度的途徑……許多優秀的小說都具有這種良好的品性。這是小說這一具象的、流動的、排斥邏輯方式的藝術的本性所決定的,同時也非常適宜于我們這個特定的處于文化價值重建的時代。”[3]于是,作家對于底層社會邊緣性人生樣態的表現,就不僅僅是基于溫厚的人文情懷,而且還具有一種獨特的精神深度。
四
《天眼》還更進一步,從這種民間的生存境界和處世智慧的角度來“天眼”觀人世,從而獨具意味和深度地展示了當代城鄉社會亦正亦邪的世道變遷和世態人情。
縱向審視歷史滄桑是小說的一個重要方面。主人公何了凡父子的算命生涯和相術的歷史命運,在這里成為了當代中國社會風云變幻的一面鏡子。何氏父子的相術曾經是偷偷摸摸地進行的“歪門邪道”,后來卻堂而皇之地成為了蕓蕓眾生裁決世事的心理依托;再到后來相術之風大盛,何氏父子雖隱匿陋巷卻名聲在外,以至守雌守弱、時刻防范,江湖險惡卻避之不及。他們這種種有關相術的復雜際遇中,蘊藏著當代中國文化觀念、人心善惡及其歷時性變遷的諸多意味。何氏父子與于長松一家的關系,也內蘊豐富地折射著當代社會的坎坷世道和歷史滄桑。在50年代初的剿匪戰斗中,何了凡舍命救回身負重傷的解放軍政委于長松,從此兩人互稱救命恩人,“成為一段流傳全縣以至更遠的佳話”,建國初期的時代風云和人際關系特征即隱含其中。文革時期,何了凡在于長松瀕臨絕望之際深夜探訪,作出了他“沒有完”、還會“官復原職”的預言;文革后,當于長松真的“一派得意的樣子”時,何了凡又大煞風景地斷言他“當個縣長也就到頭了”。這些流傳甚廣的“迷信段子”,實際上隱含著社會各方面對于長松等一代部隊轉業干部在不同時代環境里政治和人生必然處境的深刻洞察。進入新時期以后,于長松一家在了丁縣已舉足輕重,但每到面臨人生關鍵性選擇的時刻,他們卻屢屢跑到身為草民的何氏父子這里,來尋求神秘的暗示和心理的支持,其中又顯示出多少時代混亂與人心詭秘所導致的精神迷茫!這樣以一個性格和命運獨特的小人物來貫穿性地展示當代中國的歷史道路,本是20世紀80年代“反思文學”以來具有深厚審美傳統的創作思路,從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到陸文夫的《美食家》,從余華的《活著》到張宇的《活鬼》,堪稱名篇佳作迭出。彭見明的《天眼》,讓我們又一次體會到了這種敘事路徑的獨特藝術智慧和深厚審美潛能。
橫向觀照社會生態是小說更為濃墨重彩地表現的另一個方面。《天眼》廣泛地描述了當今社會千姿百態的風俗民情畫卷,并對其中光怪陸離的人際關系、人性欲望和人生價值觀,進行了切中肯綮的剖析。生活場域方面,從大紅山的十八里鋪到了丁縣城的流星巷;從名聲顯赫的陽山寺到落寞寂寥的陰山寺;從何了凡學藝的寅齋公那墻上貼滿了報紙和字紙的破茅屋,到何氏父子從廣州避兇回湖南的鄉村公路和集鎮,作者都以“浮世繪”式的筆法進行了豐富的展示。人際關系方面,作者描述了何了凡與于長松超越社會階層差異的朋友情誼,劉鐵與“大老板”擺脫成敗利害算計的僚屬忠義,郭向陽與心宜癡迷、信任和放縱兼而有之的男女情感,以及圍繞廣州的商場黑老大、省城的官場大老板和陽山寺的佛界大住持構成的商界、政界和宗教界諸多的人際矛盾糾葛。《天眼》以相術等神秘文化活動為線索,通過對這種種生活場域、人際矛盾的藝術反映,搖曳多姿而又意味深長地揭示了當今社會世態的豐富與復雜、人心的兇狠與質樸。
以小說對于陽山寺的描述為例,作者從名僧慧覺決定“重塑昔日大廟的輝煌”與縣領導尋找“振興貧困縣途徑”的想法一拍即合、陽山寺“項目”啟動寫起,錯落有致地展現了陽山寺從落成開光典禮、燒“頭炷香”給菩薩拜年,到慧覺圓寂、觀看慧覺“坐化升天”的錄像帶《佛光萬丈》之類的重大佛界活動。隨著這類情節的發展,小說對陽山寺的佛教人物也進行了精細的刻畫。慧覺聲名遠播江南數省而神龍見首不見尾,但“大慈大悲大善大德大徹大悟”中“亦曾有大惡”。本寂作為一個寺廟的大住持,個人生活竟豪華奢靡到于長松心生“縣長不如廟長”的感慨,還通過看相測字、送佛經書法、打造各種佛界活動等,為陽山寺和他本人賺取了俗界的廣泛知名度。一個“很有頭腦、很懂世情”,具有一整套功利算計和蒙世手段的佛家人物形象,就栩栩如生地表現了出來。妙云在陽山寺長久地精心服務后,突然卷款潛逃,而且她的住處與本寂的寢宮之間,竟然還有地道溝通,寺廟內部生活的本質也就暴露無遺。通過對相關人物生活的種種刻畫,作者入木三分地揭示了佛界復雜生態的內在真相。而一個“燒頭燭香”名額的競爭,竟然牽涉到大老板、于長松、關書記、劉鐵之間的暗斗與官運,官場中那“不動聲色的殺機和美好”,[4]也就通過與陽山寺的聯系,而得到了獨具特色的審美透視。
由此,佛界、俗界中亦正亦邪的各種生存景觀,就都圍繞相術文化活動這個軸心,在作品中得到了有聲有色的展現,文本的審美意蘊也因此變得豐富和深厚起來。
五
新時期以來的中國文壇,出現了不少描寫市井和鄉野細民人生的創作高手,涌現了大批描繪底層社會世態民俗畫卷的精品力作。如果從創作意圖和思想主題的角度區分,這類創作大致有如下幾種類型。劉心武、陸文夫等作家主要從社會政治角度命意。劉心武的《鐘鼓樓》《四牌樓》《棲鳳樓》等長篇小說著力表現時代政治生活影響所形成的世相與人生,作者試圖以對當代民眾群落生態的呈示,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提供借鑒和參考。陸文夫的《美食家》《小販世家》《井》等“小巷人物志”系列作品,則通過描述體現地域性風俗民情的人物在當代中國的命運變遷,來反思建國以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曲折道路及其得失,批判極“左”路線的危害和封建文化的痼疾。鄧友梅、林希、馮驥才的作品屬于另一種類型,他們繪聲繪色表現的是清末民初中國古老都市的怪世奇觀,觀照的是遺老遺少們那沒落腐朽者病態、畸形的人生,《那五》《丑末寅初》《蛐蛐四爺》《三寸金蓮》等作品即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劉紹棠與汪曾祺又有所不同,他們的作品以表現得頗為隱曲的人生況味為底色,而呈現一種贊賞謳歌性的價值與情感傾向。汪曾祺以行云流水般的筆致,詩化地表現往昔民間自在、和諧的人生形式和健康、美好的人性品質。劉紹棠則在運河灘爽朗、明快的風情畫卷中,展現傳統民間野俗的魅力及其道德的光輝。
湖南作家彭見明的創作自成一派。他的《玩古》《鳳來兮》《天眼》均是通過描述主人公在社會邊緣、幽暗處的人生命運,來顯示一種有關人生世道的民間智慧和底層品質,同時反觀各種時尚性的世相人生,其中既有人情世態審視,又有人生樣態展現,還有處世哲學闡釋。雖然“民間社會一向是以弱者的形態存在的,它以含垢忍辱的方式來延續和發展自身歷史”,但民間的理想和智慧“不是外在于現實生活的理想,它是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樂觀主義和對苦難的深刻理解聯系在一起”,[5]所以,民間的生命行進和生存境界,反而“意味著人類的原始生命力緊緊擁抱生活本身的過程”。“在一個生命力普遍受到壓抑的文明社會里”,[6]作者對此進行深入而透徹的審美展示,就使作品有力地建構起一種“道存于民間”“高手在民間”的世道感悟,進而有效地達成了創作主體悲憫當世、以邊緣文化資源“拯世”“渡人”的精神意圖,這正是長篇小說《天眼》既具審美獨特性又具內蘊豐厚度的根本原因。
[1]唐朝暉.我向往和追求平和的境界——彭見明訪談[J].紅豆,2004(7):1-9.
[2]劉起林.“邊緣敘事”得與失[N].人民日報,2010-07-27(24).
[3]雷達.日常性、思考性與精神資源[M]//雷達.雷達自選集·文論卷.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427.
[4]彭見明.與一本書有關的事情[J].理論與創作,1999(3):4-7.
[5]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365-367.
[6]陳思和.民間的沉浮:從抗戰到“文革”文學史的一個解釋[M]//陳思和.陳思和自選集.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207.
Ecological Edges,Folk Wisdom,Vicissitudes of Life and World——Comments on Peculiar State and Deep Connotation of Eye of Heaven
LIU Qilin
(School of Journalist and Communication;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510006,China)
Peng Jianming’s full-length novel of Eye of Heaven chooses physiognomy culture of Xiangchu and its positive realistic of the particular society,which not only describes the image of marginal custom with interest,but also deeply understands the state realm of dealing with affairs and survival wisdom in folk physiognomy field.Based on these,he observes changes in the world and human’s good or evil which reflect the creation subject of salvation and saving people with spiritual intention of folk wisdom.This novel shows both the quality of special realm and deep connotation.
Eye of Heaven;physiognomy culture;marginal ecology;folk wisdom;vicissitudes of life and world
I207.425
A
1674-117X(2012)02-0025-04
10.3969/j.issn.1674-117X.2012.02.005
2011-11-15
劉起林(1963-),男,湖南祁陽人,華南理工大學教授,文學博士,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責任編輯:黃聲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