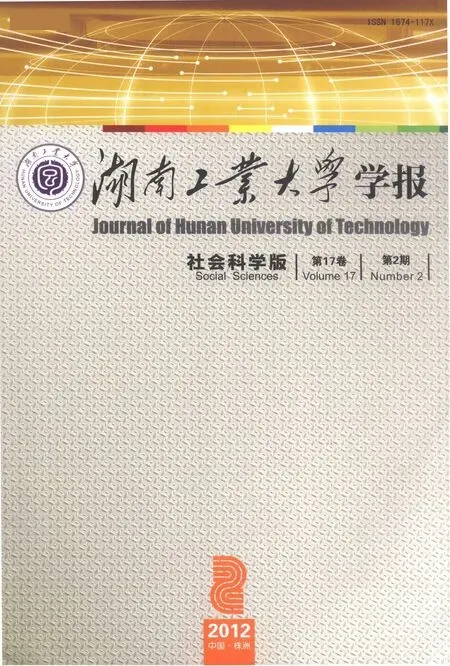家庭倫理視域里的魯迅進化論思想研究*
王麗萍
(湖南工業(yè)大學(xué)倫理學(xué)研究所,湖南株洲412007)
家庭倫理視域里的魯迅進化論思想研究*
王麗萍
(湖南工業(yè)大學(xué)倫理學(xué)研究所,湖南株洲412007)
魯迅家庭倫理思想產(chǎn)生的主要思想理論基礎(chǔ)是進化論、個人主義、人道主義。就進化論思想來說,魯迅的進化論思想可以說直接來源于嚴復(fù)的影響,但是通過在日留學(xué)其間對于進化論思想的相關(guān)文獻的直接研究以及章太炎“俱分進化”思想對其的影響,促使其形成了以重青年、重精神、重現(xiàn)在為特色的進化論思想,由此使得魯迅主張父母要解放了孩子,改變傳統(tǒng)家庭教育的方式。
魯迅;進化論;家庭倫理
魯迅是時代造就的偉大思想家。他的倫理思想深刻地根植于現(xiàn)代中國的土壤中,并有著鮮明的個性特色。通過對魯迅家庭倫理思想的整體研究,可以發(fā)現(xiàn)進化論思想對其思想的形成有著巨大的影響。在進化論思想的影響下,魯迅形成了以重青年、重精神、重現(xiàn)在為特色的進化論思想,由此促使魯迅主張父母要解放孩子,要改變傳統(tǒng)家庭教育的方式。
19世紀中后期生物學(xué)領(lǐng)域提出的進化論理論認為生物都遵循著由簡單到復(fù)雜、由低級到高級的發(fā)展規(guī)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更成為其思想的核心表達。出于富國強民的時代需要,近代文人學(xué)者普遍接受了進化論思想,可以說進化論思想影響著近代中國人思想的變革,其中康有為、孫中山、嚴復(fù)、章太炎等都是進化論思想的擁護者,嚴復(fù)更是結(jié)合當時社會的普遍需要,在系統(tǒng)介紹進化論思想的同時也對其進行了部分改造,擴大了進化論思想的影響,教育了一批仁人志士。
一 生物進化還是社會進化
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是根據(jù)對生物界的深入觀察而得出的理論,在當時打破了神造論以及物種不變論的唯心主張。恩格斯將其看作為19世紀自然科學(xué)的三大發(fā)現(xiàn)之一。正是因為其所具有的巨大影響,斯賓塞在其《社會靜力學(xué)》一書中將生物進化理論運用到了社會領(lǐng)域,認為社會也是不斷進化的,遵循著“適者生存”規(guī)律。這種將生物進化規(guī)律通約為社會規(guī)律的做法,遭到了赫胥黎的質(zhì)疑。在其《進化論與倫理學(xué)》一書中,赫胥黎就提出了反對意見,認為人類社會雖然也是不斷進化的,但是與生物進化所遵循的“適者生存,優(yōu)勝劣汰”不同,倫理規(guī)律在人類社會進化史上發(fā)揮著獨特的作用。
(一)達爾文的進化論
進化論源自達爾文對于生物進化的研究和發(fā)現(xiàn)。達爾文通過研究認為地球的生物都處在一種線性的進化過程之中。達爾文進化論認為,生物有一個緩慢的變化過程。達爾文進化論的核心在于指出了物種發(fā)展和演變的基本機制,就是自然選擇。達爾文觀察到,生物界普遍存在著繁殖過剩的現(xiàn)象,繁殖過剩必然導(dǎo)致生存斗爭。生存斗爭是每時每刻都存在的,所以不斷地有生物死亡,也有生物幸存。在這場生存與死亡的搏斗中,最基本的生存原則就是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在倫理學(xué)的意義上,達爾文的生物進化理論直接產(chǎn)生了達爾文主義。
達爾文主義以生物發(fā)展的自然規(guī)律看待人類社會。他們認為,首先,人類自身也是生物進化的結(jié)果,并且處在不斷的進化過程之中。這就意味著有些人可能處于進化的高級階段,而有的則處于低級階段。庸俗的達爾文進化論所產(chǎn)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全世界籠罩在黑暗之中的人種理論。這種理論的實踐所產(chǎn)生的令人恐懼的后果已經(jīng)充分展露在二戰(zhàn)法西斯的暴行之中。其次,生物進化論為人類社會和文化發(fā)展預(yù)設(shè)了方向。既然生物進化是呈線性發(fā)展的,那么人類社會和文化的發(fā)展也必定有一定的趨勢和模式。再次,達爾文主義認為自然選擇是合理的方式,因為這種機制促使了生物物種的發(fā)展。對于人類社會而言,強大的國家、民族和群體對于相對落后群體的侵略和打壓似乎也符合自然選擇。人類社會間的相互博弈,以及某些野蠻方式所進行的人類社會選擇也是自然原則的結(jié)果。
達爾文的生物進化理論對于近代中國產(chǎn)生過深遠的影響。當時中國處于深重的災(zāi)難之中。達爾文主義對于解釋當時的社會現(xiàn)象、激發(fā)民族自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從嚴復(fù)譯述《天演論》到馬君武翻譯出版《物種起源》,其中所介紹的進化學(xué)說,是在民族危機激化和深化的歷史背景下,出現(xiàn)的一種新型的、成體系的、有利于推動救亡和變革的理論形態(tài)。當時,進化論對于中國的影響主要在于,首先,進化論使中國開始認識自然科學(xué)的力量,并且改變傳統(tǒng)守舊的思想和思維習(xí)慣。中國傳統(tǒng)的歷史宇宙觀是以古代為楷模,效祖宗之法,強調(diào)“天不變,道亦不變”。這種傳統(tǒng)思維,是一個靜態(tài)的理論構(gòu)架,只能為傳統(tǒng)的綱常秩序提供依據(jù),而不可能帶來改變現(xiàn)實制度的觀念。西方進化論引進后所衍生的歷史進步觀念,則以不斷前進的社會趨勢為發(fā)展方向,為變法改制,以至為傳統(tǒng)的社會結(jié)構(gòu)和社會心理環(huán)境的根本變革提供了價值論證,并逐漸成為中國思想界的主流。其次,進化論為中國當時的革命提供了思想上的啟蒙依據(jù)。既然社會形態(tài)和政治體制也在進化過程之中,而且按照自然選擇法則,落后的國家和民族就會遭受淘汰,那么就必須改變當時中國落后的狀態(tài),政治的革命成為必然的考量。最后,進化論開啟了中國近代自由主義的大門。中國近代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基本受到了進化論的思想的教育和影響,魯迅便是代表人物之一。
(二)《進化論與倫理學(xué)》的進化思想
《進化論與倫理學(xué)》是英國博物學(xué)家赫胥黎的代表作之一。作為達爾文的朋友兼達爾文學(xué)說的忠誠擁護者,赫胥黎的著作簡要地向人們介紹了達爾文以自然選擇為核心的生物進化論,目的在于闡明進化論為其倫理學(xué)提供的“科學(xué)依據(jù)”。他表達的中心思想是:人性從惡到善的改變,以及社會美德的進展,關(guān)鍵在于消除生存斗爭。書中,赫胥黎闡發(fā)了達爾文的生物進化理論,肯定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一自然歷史演變的重要法則。然而赫胥黎寫作本書的目的卻不是單純表達對達爾文主義的贊美,而是要抨擊斯賓塞對達爾文進化思想的泛化。因為在赫胥黎看來,人類社會進化過程與自然歷史演化是不同的,人類社會的進化過程是一個倫理過程而自然歷史的演化則是一個生命過程,人類社會的進化所依據(jù)的是倫理,“社會進展意味著對宇宙過程每一步的抑制,并代之以另一種可稱為倫理的過程。”[1]而自然的生命進化過程卻不會考慮到倫理要求。雖然在人類社會也存在著競爭、適應(yīng),但是人類社會的競爭卻不是慘烈的你死我活,適應(yīng)也并不是純粹的“最適者”生存,因為在人類社會存在倫理法則,人們因為倫理法則的存在而可以以互助互敬、相親相愛的善行來抑制殘酷競爭的發(fā)生,即使是“不適者”在人類社會也會得到救助。
赫胥黎的這種主張具有對進化論自然主義的超越性,肯定了人類社會利他性的存在。而斯賓塞則堅持競爭法則在人類社會與自然領(lǐng)域的普遍適用性,認為競爭不但是自然生命過程的基本規(guī)律而且也是社會進化的動力,無論是在自然界還是在人類社會都遵循著“最適者”生存的原理,認為行為的善惡與否在于它對外在環(huán)境的適應(yīng)程度和它對個體保存以及種的繁衍與發(fā)展的意義。[2]只要是有利于個體生命保存以及種的繁衍的行為就是善的,反之則是惡的,這種善惡標準將自然界適者生存法則完全泛化到人類社會,因此可以說斯賓塞的主張不但“漠視了人類道德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xiàn)象的特質(zhì)”,[3]139而且對于“利己主義在發(fā)生學(xué)意義上的優(yōu)越性和超前性”[3]127的堅持,可以說將人類社會推向了“人對人像狼”的自然狀態(tài)。針對斯賓塞的自然主義主張,赫胥黎指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僅僅是自然歷史領(lǐng)域適用的法則,人類社會發(fā)展所應(yīng)當遵循的是人類自身所特有的倫理法則。
(三)嚴復(fù)對進化論的改造
進化論是通過資產(chǎn)階級改良派思想家嚴復(fù)譯述赫胥黎的《天演論》而傳入中國的。嚴復(fù)在其翻譯的過程中根據(jù)中國當時的實際需要作了些修改,闡發(fā)了自己的思想主張,將斯賓塞與赫胥黎的進化論思想進行了結(jié)合,突出了進化論的社會意義。
嚴復(fù)在留英期間,以自然科學(xué)的學(xué)習(xí)為主,同時接受了斯賓塞的社會進化思想,對赫胥黎維護人類社會的倫理法則,反對“任天為治”放任主義的宗旨并不十分贊賞,更反對赫胥黎對斯賓塞所鼓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批評。嚴復(fù)認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僅是自然界的普遍規(guī)律,也是人類社會歷史發(fā)展所應(yīng)遵循的法則,所以他在翻譯《進化論與倫理學(xué)》時,不但取其進化與倫理主題的一半將其譯為《天演論》,而且對于其內(nèi)容也進行了增刪,在原文中加入了大量的按語,以此來傳播斯賓塞的進化論思想。這主要體現(xiàn)在:一是將“物競天擇”的天之道推演到人類社會,認為人的行為也應(yīng)當遵循物競天擇的天演公例。認為“無異、無擇、無爭,有一然者,非吾人今者所居世界也”,[4]1329強調(diào)“變”、“異”、“擇和爭”對于社會發(fā)展的特有價值;二是接受了社會進化的樂觀主義態(tài)度。認為人類社會的進化是一個“由簡入繁,由微生著”,直線向前,日趨完善的單向發(fā)展過程,因此主張一種人類社會永恒進步論。“民群任天演之自然,則必日進善,不日趨惡,而那治必有時后臻者,其豎義至堅,殆難破也”。[4]1392如果說在《進化論與倫理學(xué)》中赫胥黎意欲將自然進化法則與人類倫理法則區(qū)別開來,那么在《天演論》中嚴復(fù)則是將兩者統(tǒng)一起來,以物競天擇的進化論作為人類社會倫理的基礎(chǔ),倡導(dǎo)一種富有競爭性的進化倫理觀念,并且指出人類競爭其勝負不在人數(shù)之多寡,而在其種其力之強弱。《天演論》中嚴復(fù)以《周易》《老子》中的思想來比附闡述進化論的思想,具體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宣傳了斯賓塞的社會進化思想,認為人類社會和生物界一樣,是不斷地演進的,按照此理則后一定勝于今。第二,進一步闡述了人類社會變化的根本原因是生存斗爭、自然選擇,而“優(yōu)勝劣敗”“弱肉強食”也自然是適用于人類社會的根本法則。第三,結(jié)合民族的危機狀況以及救亡圖存的理想認為“任天為治”、無所作為的態(tài)度是不足取的,而是應(yīng)該奮發(fā)圖強,“以人持天”求得個體的生存與民族的生存。
《天演論》對進化論的生物進化、生存競爭的觀點的詮釋,激起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危機意識,使他們覺得,在這個以適者生存、優(yōu)勝劣汰為原則的世界上,如果我們的民族仍按照傳統(tǒng)的社會發(fā)展模式,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因此提出了“自強保種”,以挽救危難之中國的要求,呼喚人們在“天演合例“的殘酷事實面前警覺起來,發(fā)憤圖強,保種進化。《天演論》中的進化主張也給了處于危難中的國人一種希望:現(xiàn)今的中國雖然孱弱多難,但不能說會一直處于孱弱狀態(tài),因為從進化論上來說,人類歷史的發(fā)展具有必然向上的趨勢,因此只要國人努力自救以自強就可以挽救自身的危難,變?yōu)閺娬摺U沁@種樂觀的進化史觀使《天演論》在1898年正式出版之后,就受到了仁人志士的熱烈歡迎。當然,他所宣揚的進化論帶有庸俗進化論的痕跡。
胡適以下的這段話最可說明《天演論》在當時的影響,他說:“《天演論》出版之后,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竟做了中學(xué)生的讀物了。讀這書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學(xué)史和思想史上的貢獻。他們能了解的只是那‘優(yōu)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在中國屢次戰(zhàn)敗之后,在庚子、辛丑大恥辱之后,這個‘優(yōu)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國人一種絕大的刺激。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燃燒著許多少年的心和血。‘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等術(shù)語,都漸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漸漸成了一班愛國志士的口頭禪。還有許多人愛用這種名詞做自己或兒女的名字,陳炯明不是號競存嗎?我有兩個同學(xué),一個叫孫競存,一個叫孫天擇。我的名字也是這種風氣底下的紀念品。”[5]
從鴉片戰(zhàn)爭到五四運動,中國始終處于內(nèi)憂外患的危機時代。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改良主義思想家、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舊民主主義者、以李大釗等為代表的新民主主義者都苦苦地探索救國之路。進化論中之“生存斗爭”、“適者生存”等思想迎合了當時中國人的危機意識和心理需求。他們把進化論看作為中國變法自強、保國保種和救亡啟蒙的理論武器。對于改造國人的世界觀,以“優(yōu)勝劣汰”促使國人覺醒,激勵國人奮發(fā),以圖自強、自立,保國保種,為傳統(tǒng)中國向現(xiàn)代中國的轉(zhuǎn)換起到了巨大的思想推動作用。但是,進化論畢竟有其自身的思想局限和消極影響,如果執(zhí)其一端,那么所引導(dǎo)的只能是一種盲目的樂觀,而且從當時實際情況來看,維新變法、社會改良也只是在保存現(xiàn)有社會制度層面上的救亡圖存,不能根本改變國家、國民的命運。
因此進化論思想也只不過成為一種盛極一時的政治運動,在《<進化與退化>小引》譯文中魯迅回憶指出:“進化學(xué)說之于中國,輸入是頗早的,遠在嚴復(fù)的譯述赫胥黎《天演論》。但終于也不過留下一個空泛的名詞,歐洲大戰(zhàn)時代,又大為論客所誤解,到了現(xiàn)在,連名目也奄奄一息了。”[6]255
二 魯迅進化論思想的形成
魯迅進化論思想的形成是一個過程,是在對嚴復(fù)、章太炎以及斯賓塞、赫胥黎進化論思想的綜合的基礎(chǔ)上形成的。魯迅首先接觸到的就是嚴復(fù)《天演論》中進化論思想,也就是“物競”、“天擇”等主張,以及社會進化、國家富強在于國民的不斷努力、自強不息等思想。還在南京路礦學(xué)堂時,抱持著對新事物新思想的學(xué)習(xí)熱情,魯迅就如饑似渴地拜讀了嚴復(fù)的《天演論》,并能背誦其中的段落,深受其中思想的鼓舞。他曾回憶說:“看新書的風氣便流行起來,我也知道了中國有一部書叫《天演論》。……哦!原來世界上竟還有一個赫胥黎坐在書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鮮?一口氣讀下去,‘物競’‘天擇’也出來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也出來了,斯多葛也出來了。學(xué)堂里又設(shè)了一個閱報處,《時務(wù)報》不待言,還有《譯學(xué)匯編》……。”[7]305-306讀《天演論》仿佛已經(jīng)成為他課余生活的一部分:“一有空閑,就照例地吃侉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7]306-306在《魯迅傳》中,林志浩寫道“《天演論》的有些章節(jié)熟到背誦如流的程度”[8]。
除了受嚴復(fù)《天演論》的激情鼓舞以外,魯迅還受到了章太炎先生的“俱分進化”思想的影響。1902年魯迅到日本后,通過讀《民報》、聽章太炎先生的講學(xué),較為系統(tǒng)地接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善惡并進的“俱分進化論”的觀點。這在《魯迅全集六》中《關(guān)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是有所記載的,在其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章太炎先生不但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都深深地影響了魯迅,促進了魯迅思想的成長。
從總體來看,章太炎的進化論思想是比較豐富的,有人總結(jié)出了“自然進化論”、“革命進化論”、“俱分進化論”等觀點,但能夠代表章先生思想深刻性的還是“俱分進化”思想。在“俱分進化”的思想中,章先生肯定了自然進化的思想“吾不謂進化之說非也”,但是針對當時嚴復(fù)、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對人類社會所持的進化發(fā)展觀提出了質(zhì)疑,指出僅以進化論為標準來判定人類社會歷史發(fā)展與否思想的局限性。
1906年他在《民報》第七號發(fā)表《俱分進化論》,提出了自己獨特的進化思想,表示了對進化論的質(zhì)疑與批判。章太炎對進化論的態(tài)度是有所承認亦有所批判的。章太炎并沒有否定進化這一理論,1897、1898年所著的《菌說》《原變》都肯定了自然界的進化規(guī)律。在章太炎看來,雖然人類也是自然界中的一份子,人類社會也在一定程度上遵循著生物進化的規(guī)律,但是人又不同于生物,因此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并不是簡單的直線過程。人類社會的發(fā)展不但包括以科學(xué)技術(shù)發(fā)展為標志的智識發(fā)展,也包括人類善惡道德發(fā)展和人類苦樂感受的心理發(fā)展。章太炎分析指出西方進化論學(xué)說本質(zhì)上是來源于黑格爾的理性哲學(xué),將進化的實質(zhì)等同于理性的發(fā)展,因此以人類智識的進化發(fā)展得出了人類社會必然進化發(fā)展的結(jié)論。章太炎認為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并不是單單以人類智識的進化而進化的,從善惡、苦樂這兩個層面的并進對人類社會必然進化發(fā)展的觀念提出了質(zhì)疑。“進化之所以為進化者,非由一方直進,而必由雙方并進,專舉一方,惟言智識進化可而。若以道德言,則善亦進化,惡亦進化;若以生計言,則樂亦進化,苦亦進化。雙方并進,如影之隨形”。[9]386從善與惡、苦與樂的并進具體闡述了“俱分進化”的思想。
章太炎從生物進化的角度指出:人較之于動物,無論是在行善、感受樂方面,還是在行惡、感受苦方面都要強出很多。人雖然可以做出很多善行,但也可以做出更大的惡行;人雖然可以感受到更多的快樂,卻也可以感受到更多的痛苦。
人類社會中的善惡苦樂并行兼進,其導(dǎo)致結(jié)果也必然是二者的相互抵消,由此得出結(jié)論說“進化之實不可非,而進化之用無所取。”[9]387章太炎認為,進化的事實不可否認,進化的結(jié)果卻不是人們所一心向往的善樂,而是善惡、苦樂的齊頭并進,因此進化對于社會的作用也就不足取了。社會的進化發(fā)展觀只是適用于智識的進化而在善惡、苦樂方面卻未必然,知識的進化也并不一定能夠?qū)⑷祟惿鐣w推向道德的理想王國,也不能必定將人們帶入至樂勝境。所以說,進化并不能使世界“達于盡美醇善之區(qū)”,這樣也就指出了這種樂觀進化論在人類社會問題上的局限性。章太炎的俱分進化論理論,對于當時的仁人志士來說,無疑會覺得無所取或者會降低人們的革命熱情,但是我們卻不能因此否定章太炎的批判精神、質(zhì)疑精神。可以說,“俱分進化”的思想為人們從價值層面辨證地認識進化史觀是有積極意義的。這種理論貢獻也被后來的后現(xiàn)代主義者們對理性、對進化史觀的批判所印證。
嚴復(fù)以及章太炎的進化思想、日文譯本《進化論與倫理學(xué)》、海克爾的人類種系發(fā)生學(xué),還有穆勒、斯賓塞和梅契尼珂夫的人類文明進化觀,均對魯迅產(chǎn)生了較大的影響。這樣魯迅對進化論思想的認識也就超越了早期所接受的《天演論》思想層面,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進化論思想。
三 魯迅進化論思想的特點
魯迅接受了生物進化的主張,他把進化論作為觀察社會的工具,由此形成了進化發(fā)展的歷史觀。他肯定人類社會是不斷發(fā)展、不斷進步而不是凝固或倒退的。魯迅所主張的社會發(fā)展變化的思想是同封建社會“天不變,道亦不變”的道德觀點針鋒相對的,與當時的封建頑固派“祖宗之法,莫敢言變”的僵化觀念是截然相反的,它不同于改良派折中調(diào)和的庸俗進化論。他把這種發(fā)展進化的觀點運用到倫理觀上,就形成倫理道德進化發(fā)展的思想。他不承認有永恒不變的道德信條,從來不用過時的封建倫理來衡量、限制新事物。恰恰相反,他正是在事物發(fā)展的必然歷史進程中看到舊道德的荒謬、腐朽、虛偽,堅信道德是隨社會發(fā)展的需要而變化發(fā)展的。魯迅在早期以至中期,就是以進化論為武器,對封建道德展開批判的。他依據(jù)生物進化的思想,指出青年是必勝于老年的:“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人。”[6]5獨樹一幟地提出了“救救孩子”、“青年必勝于老年”的生物進化主張。與當時的仁人志士大多將所接受的進化思想應(yīng)用于對社會歷史的整體考量不同,魯迅一反當時人們社會進化的整體論,將社會進化的可能指向了作為個體而存在的人,在社會進化論上表現(xiàn)出對人之精神的重視。同時在歷史進化論方面,也沒有因?qū)M化的盲目信念而樂觀地寄希望于將來,而是主張傾力于現(xiàn)在,以為唯有對現(xiàn)在對現(xiàn)實的逐步改變,才能實現(xiàn)發(fā)展進化的理想。魯迅形成了比較全面的而又非盲目樂觀的進化主張,正是因為抱著這種進化觀念,他提出了“立國首在立人”的思想,將“立人”作為其一生的追求。
(一)生命進化論——青年必勝于老年
魯迅在《人之歷史》中肯定了人及人類都是處在一個不斷由簡單到復(fù)雜的生物進化中的觀點。從生物進化的觀點看來人類與動物并無甚大區(qū)別,個體的進化也就是種族的進化,正是無數(shù)個體的進化匯成了種族的進化,因此肯定個體進化對于種族進化的意義,“我想種族的延長,——便是生命的連續(xù),——的確是生物界事業(yè)里的一大部分”。[10]354魯迅看到了在整個的進化過程中,新事物必然要代替舊事物的生物進化觀,指出青年是必勝于老年的。“凡是高等動物,倘沒有遇著意外的變故,總是從幼到壯,從壯到老,從老到死。”[10]354在魯迅看來,“生命的路是進步的,總是沿著無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自然賦予人們的不調(diào)和還很多,人們自己萎縮墮落退步的也還很多,然而生命決不因此回頭。無論什么悲慘來襲擊社會,什么罪惡來褻瀆人道,人類的渴仰完全的潛力,總是踏了這些鐵蒺藜向前進。人類總不會寂寞,因為生命是進步的,是樂天的。”[10]386只要是活著的人就都是有希望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長者,總有著希望的前途。”魯迅在1932年寫在《三閑集》序言中的這段文字可以說是其生物進化論思想的鮮明寫照:“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人。”[6]50人是生物之一種,所以適用于生物發(fā)展規(guī)律的自然也適用于人,既然生物是不斷進化與完善的,那么,人也應(yīng)當是如此的。從個體生命的成長過程來說,最為鼎盛的時期也就是青年時期,易于接受新鮮事物,具有突破一切障礙的勇氣與豪氣;從代際發(fā)展的角度來看,青年永遠是代表著將來代表著發(fā)展的,老年則代表著過去代表著保守。
魯迅主張青年就應(yīng)當歡歡喜喜地向前去,老的亦應(yīng)該歡歡喜喜的死去,“我想,凡是老的,舊的,實在倒不如高高興興的死去的好。”[11]321作為向死的老年更應(yīng)當為前進著的青年做出些奉獻與犧牲,“老的讓開道,催促著,獎勵著,讓他們走去。路上有深淵,便用那個死填平了,讓他們走去。”[10]355魯迅正是因為將青年看成是社會進化的真正力量所在,從而樂于犧牲自己,將自己奉獻于青年。
魯迅對于幫助青年采取了一種奉獻犧牲的態(tài)度,青年們提出的要求能幫的就幫,從不吝惜自己的金錢、時間與精力。正如他在寫給許廣平的信中所述:“我這三四年來,怎樣地為學(xué)生,為青年拼命,并無一點壞心思,只要可給與的便給與。”[12]他熱心支持學(xué)生運動,在北師大學(xué)生運動中支持學(xué)生與章士釗、楊蔭榆進行斗爭;支持青年木刻事業(yè),各處收集、幫忙展出等;支持文學(xué)青年,給人看稿子改稿子編書校字等等,甚至為青年的寢食操勞。
魯迅的進化論,不是把人類歷史看作如動物一樣是適應(yīng)環(huán)境的過程,其強調(diào)在社會的變革過程中,能夠真正改變社會的是社會中具有主體進化之精神的個體。在社會變革過程中只注力于社會整體的進化而忽視個體精神的進化,這種變革將是不徹底的或?qū)⒚媾R失敗的。如專注于器物的洋務(wù)運動與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其失敗的一個原因就是對人之精神進化的漠視。
(二)社會進化的“真源”——人之精神進化
受章太炎“俱分進化論”思想的影響,魯迅對嚴復(fù)等人的社會進化發(fā)展觀的片面性與盲目樂觀產(chǎn)生了質(zhì)疑。魯迅在個人與社會之間放棄了對社會整體發(fā)展規(guī)律的探討而將希望指向了個人,尤其是人之精神進化;在魯迅看來社會進化只能是個人進化的結(jié)果,但又不是少數(shù)個人進化所能代表的,與社會進化的英雄史觀不同,魯迅認為只有社會大眾的進化才能代表社會整體的進化,并因此以其犀利的解剖刀似的筆觸展開了對個人的剖解,開始了對人性的探討。這種探討不但包括“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的立新人主張,而且也包括針對中國國民的性格所展開的批判: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正如許壽裳在其著作《亡友魯迅印象記》中所說,魯迅一生所奮力去做的都是圍繞三個問題“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辦雜志、譯小說,主旨重在此;后半生的創(chuàng)作數(shù)百萬言,主旨也重在此。”[13]
魯迅在早期作品中,認為單單強調(diào)科學(xué)只能使人生枯寂,倡求人性于全的《科學(xué)史教篇》、提出立人觀點的《文化偏至論》、重個體精神之進化的《破惡聲論》、倡人文精神的《摩羅詩力說》等創(chuàng)作都表現(xiàn)出了對個體進化的強調(diào),而且這種強調(diào)所重點指出的是人之精神的進化。
《科學(xué)史教篇》中基于對西方科學(xué)演進過程的整體思考,認為個體進化不但包括智識進化而且也應(yīng)當包括人文精神的進化,個體進化是個人人性的全面進化過程。魯迅通過對科學(xué)史的分析指出,偏重于科學(xué)也只是近代以來的事,從科學(xué)史之演進,我們發(fā)現(xiàn),人文科學(xué)在其中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也正是人類探索未知的精神促動了科學(xué)史的演進,因此魯迅強調(diào)指出“故科學(xué),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顧猶有不可忽者,為當防社會入于偏,日趨而之一極,精神漸失,則破滅亦隨之。蓋使舉世惟知識之崇,人生必大歸于枯寂,如是既久,則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謂科學(xué),亦同趣于無有矣。故人群所當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已也,亦希詩人如莎士比亞;不惟波爾,亦希畫師如拉斐爾;既有康德,亦必有樂人如貝多芬;既有達爾文,亦必有文人如嘉來勒。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見今日之文明者也。嗟夫,彼人文史實之所垂示,固如是已!”[10]35他又提出了以求人性于全促人類文明,也即追求社會變革與進步,應(yīng)當以促進人性的進化為目的,主張科學(xué)與人文不可偏頗,培育具有健全人性的人,以此來促動社會的變革與進化。
《文化偏至論》則明確提出了“立人”的主張:“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wù),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若其道術(shù),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10]58以及“掊物質(zhì)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shù)”[10]47的主張。所立之人也就是尼采所主張的具有獨立意識、富有抗爭精神的“超人”,雖然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中“超人”的出現(xiàn)將遙遙無期,即使出現(xiàn)了也注定要成為孤獨者,“尼采式的超人,雖然太覺渺茫”,但魯迅沒有因此失卻希望,而是相信“就世界現(xiàn)有人種的事實看來,卻可以確信將來總有尤為高尚尤近圓滿的人類出現(xiàn)。”[10]341
正是因為看到了社會進化的“真源”所在——人之精神進化,魯迅在后來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展開了對國民性的批判。如1921年的《阿Q正傳》對國民性進行了整體的癥候式分析,“阿Q卻是一個民族中的類型。……實在是一副中國人壞的品性的‘混合照相’,……”[14]此種破舊而后立新的努力,也是出于對新人的切切期望。
(三)歷史進化論——傾力于現(xiàn)在
魯迅批評“心神所注,遼遠在唐”的復(fù)古主義者,“為無希望、為無上征、為無努力”的人物“非自殺以從古人”[10]69不可;他明確主張,社會的發(fā)展變化是有根源有規(guī)律的:“誠以人事連綿,深有根柢,如流水之必有源泉,卉木之茁于根茂……故茍為尋繹其條貫本末,大都蟬聯(lián)而不可離。”[10]48在他看來,進化的過程不是和平地進行,而是通過不斷的矛盾斗爭來實現(xiàn)的,“和平為物,不見人間。”“人類既出而后,無時無物不稟殺機”。[10]69他還認為,進化論的規(guī)律是從低級向高級發(fā)展并新陳代謝的,即“自卑而高,日進無既。”[10]8“吐故納新,敗果既落,新葩欲吐”[11]27。他強調(diào)事物的進化不可抗拒:“進化如飛矢,非墮落不止,非著物不止,祈逆飛而歸弦,為理勢所無有。”[10]70魯迅認為,既然事物矛盾著的雙方始終斗爭著,那么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是不可能的,矯往過正才是事物發(fā)展中的必然現(xiàn)象。他指出:“文明無不根舊跡而演來,亦以矯往事而生偏至。”“以改革為胎,反抗為本,則偏于一極,固理所當然。”[10]35
魯迅認為進化不但是一個生物過程也是一個時間過程,即是從過去、現(xiàn)在到將來的過程。因此進化論也就不但涉及到生物的進化也將涉及到時間的延續(xù)。關(guān)于時間也就是人們一般認識中的三維形式:過去、現(xiàn)在、將來。如果要在三者中進行選擇的話,人們會不約而同地選擇將來,因為將來是未知的,可以給予人們更多的好奇與希望。魯迅也是對將來充滿希望的,“世界決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將來的。”[6]56但是魯迅并沒有沉湎于對將來的美好希望中,為人們勾畫什么美好藍圖。魯迅所注重的不是TO DO而是DOING。
在魯迅看來,為人們勾畫美好藍圖確能得到人們的贊譽,但是如果只是單單地給出藍圖而沒有為著這藍圖去切實地做,這個藍圖也就如同“望梅止渴”、畫餅充饑”。魯迅力主人們要正視現(xiàn)在,以現(xiàn)在的努力抗爭來追求將來。1918年所發(fā)表的《人與時》中,魯迅就分析了人們對待過去、現(xiàn)在、將來的不同的態(tài)度,“一人說,將來勝過現(xiàn)在。一人說,現(xiàn)在遠不及從前。”而“時”卻說“你們都侮辱我的現(xiàn)在。”[11]35從詩中,我們可以看到,人們因憧憬而對將來持一種向往,因回憶而對過去持一種顧念,無論是向往將來還是顧念過去,人們都沒有賦予現(xiàn)在以價值,現(xiàn)在沒有將來好,現(xiàn)在不如從前。正如“時”所說,你們這樣是侮辱了我的現(xiàn)在,從三者之間的關(guān)系來說,過去、現(xiàn)在、將來三者是相繼的,過去會延續(xù)到現(xiàn)在直至滲入到將來;現(xiàn)在是不同于過去也不同于將來的,然而現(xiàn)在卻接續(xù)著過去與將來;將來既有對過去、現(xiàn)在的否定也有對過去、現(xiàn)在的延續(xù)。在這之中,我們否棄了現(xiàn)在也就阻斷了由過去到將來的路,也就否棄了將來。
魯迅更執(zhí)著于現(xiàn)在,而不是空寄希望于將來。在魯迅看來,現(xiàn)在的抗爭即是為了將來,只有現(xiàn)在的抗爭才會有不一樣的將來,否則將來亦只是過去的翻版,如封建家庭中的孩子,小的時候受家長的欺壓,到自己做爸爸時亦是去欺壓自己的孩子。有的明白希望在前,對待現(xiàn)在的態(tài)度卻不積極,總是一味地等待希望的到來,因此“但為現(xiàn)在抗爭,卻也正是為現(xiàn)在和未來的戰(zhàn)斗的作者,因為失掉了現(xiàn)在,也就沒有了未來。”[15]3魯迅發(fā)出“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xiàn)在中國的生存而奮斗……”[15]610的吶喊。魯迅的學(xué)醫(yī)、從文、支持青年、與論敵斗不都是積極要求改變現(xiàn)狀的舉動么,也就是足踏在地上為中國之將來而做的踏實努力。
在魯迅不懈努力的過程中也遇到過現(xiàn)實所給予的無情打擊,也有過后退頹唐的時候,在《自嘲》詩中對于自己的碰壁進行了自我解嘲,末句的“躲進小樓成一統(tǒng),管它春夏與秋冬”也可以說是魯迅當時的一種心境。自1909年魯迅留學(xué)歸來之后,與留日期間的大量創(chuàng)作問世相反,他將大量精力投入到輯錄校訂古籍,抄古碑,收拓片,鉆研佛經(jīng),搜集漢畫像,對古代的哲學(xué)、歷史、文學(xué)、藝術(shù)材料的進行分析和研究。這其中的原因,魯迅在《南腔北調(diào)集·<自選集>自序》中說的很清楚:“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fù)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于是失望,頹唐得很了。”[6]468可見,在過去、現(xiàn)在、將來永續(xù)的歷史過程中,魯迅體會到了個體的無助,但是他并沒有一直沉寂下去,“不過我卻又懷疑于自己的失望,因為我所見過的人們。事件,是有限得很的,這想頭,就給了我提筆的力量”,[6]468因而有了1918年的《狂人日記》,《狂人日記》不但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啟蒙主義”的第一聲怒吼,而且也揭露了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血淋淋的吃人史。自此,魯迅對封建傳統(tǒng)封建制度展開了全面的批判,為民族的存亡復(fù)興而執(zhí)筆,走到了啟蒙與救國的前沿。魯迅看到了將來決不是一兩個個體的將來而是我們整個民族的將來。只要有將來在,就有希望在。魯迅抱著對將來的希望,竭力去支持青年,展開對封建禮教、封建制度的批判,以期給將來的子孫一個新的開始,一個光明的未來,而不再是“黑屋子”、“人肉的筵席”。
傾力于現(xiàn)在的進化思想也就從一定程度上指出了進化的途徑只能是以現(xiàn)在的努力去爭取,而不應(yīng)該以過去來扼殺現(xiàn)在,也不應(yīng)以將來來抹殺現(xiàn)在,進化并不是可以等來也不是可以盼來的。這一點對當時進化論思想不但受到所謂“國粹派”的阻遏而且也受到反動勢力扼殺的情勢所提供的啟示尤其重要。中國的進化并不是可以自己完成了的,進化不但需要進化力量的切實努力,而且也更是惟有現(xiàn)在的切實努力與奮斗才是真實的,也才是獲取進化的主要途徑。魯迅的這種傾力于現(xiàn)在的進化論就與康有為、梁啟超等的寄希望于“大同”世界的夢想形成了明顯的不同。在現(xiàn)實中魯迅展開了對過去的批判,以及在現(xiàn)實中的各種論爭,這都是為了將來而做出的努力,魯迅立足于現(xiàn)實而寄希望于將來,始終相信“然人類者,有希望進步之生物也……”[16]
魯迅對進化論的吸取根據(jù)自己的智識進行了取舍,他堅決反對“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滿懷義憤抨擊“獸性愛國者”“執(zhí)進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異種悉如臣仆不慊也。[17]在《摩羅詩力說》中,他高度贊揚拜倫等援助弱小民族的行為,表達了他同情被壓迫者、弱小者的道德價值取向。
[1]赫胥黎.進化論與倫理學(xué)[M].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1973:57.
[2]赫伯特·斯賓塞著.張雄武譯.社會靜力學(xué)[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6:11-42.
[3]萬俊人.現(xiàn)代西方倫理思想史上卷[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0.
[4]嚴復(fù).嚴復(fù)集第五冊[C].北京:中華書局,1986.
[5]胡適.胡適作品集一[C].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54.
[6]魯迅.魯迅全集四[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
[7]魯迅.魯迅全集三[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
[8]林志浩.魯迅傳[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1:29.
[9]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四[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386,387.
[10]魯迅.魯迅全集一[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
[11]魯迅.魯迅全集七[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
[12]魯迅.魯迅全集十二[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11.
[13]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24.
[14]周作人,周建人.年少滄桑——兄弟憶魯迅(一)[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233.
[15]魯迅.魯迅全集六[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3,610.
[16]魯迅.魯迅全集十[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163.
[17]魯迅.魯迅全集八[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35.
Research of LuXun's Evolutionist Thoughts from the Family Ethics Perspective
WANG Liping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Hunan 412007 China)
Lu Xun’s family ethical thoughts owe much to such ideas as Evolution theory,individualism and humanism.His evolutionist thoughts originate directly from Yan Fu’s influence.The direct study of Evolution theory materials during his studying in Japan and the influence of Zhang Taiyan’s“The two-way Evolution”theory show that Lu Xun’s evolutionist thought of family ethics is featured with a focus on youth development,spiritual enhancement and present involvement.Therefore,Lu Xun holds that parents should change their traditional way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give freedom to their children.
Lu Xun;Evolution theory;family ethics
B821
A
1674-117X(2012)02-0098-08
10.3969/j.issn.1674-117X.2012.02.020
2012-01-06
收稿日期:湖南省社會科學(xué)院長沙市社科規(guī)劃辦2008年重點課題“魯迅家庭倫理思想研究”(2008030)
王麗萍(1975-),湖南醴陵人,湖南工業(yè)大學(xué)倫理學(xué)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應(yīng)用倫理學(xué)。
責任編輯:衛(wèi)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