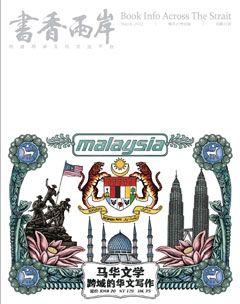賀淑芳:從成就自我,到面對自我
何永芳

馬來西亞華文作家賀淑芳,在今年年初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集《迷宮毯子》。書中收錄了她自2002年以來的12篇短篇小說,其明顯的多重時間性的“時空體”,讓有小說家和學者雙重身份的黃錦樹贊譽有加。
“我一直這么做:只要一覺得現實成了一堵墻,就會拼命從書里一字一字地吃掉,然后再一字一字地吐出來。”封面上的這句導語讓人很有深入窺探的欲望,細細讀完之后才明白,那“一字一字吐出來”的,不光是賀淑芳的寫作欲望,更是對現實里各種聲音的強烈回應,以及她塑造“自我”的艱辛。
文學啟蒙
賀淑芳出生在馬來西亞吉打州,小學二年級時,大姑媽來到賀淑芳的家中小住。大姑媽在新蓋好的廁所旁(“因為抽水馬桶的廁所很新,為了維護它,所以有好幾年的時間,整家人都舍不得使用。”),擺一張折疊椅,教賀淑芳看報章上的連載小說。她帶來一些小說,又發掘出家中不知哪位長輩保存的一大柜子的文學作品和刊物,甚至還有父親那輩人留下的課本。“都是已經過時的東西,我卻看得津津有味,”對于賀淑芳來說,無論是文學作品還是上一代人留下的課本,都是有趣的故事書。在廁所旁的小空地上,在狹小的樓梯上,她走進書中的紛繁世界而不自知,更不知道與文學的不解之緣已然萌發,何況日后還有盤根錯節的交集。
小時候的賀淑芳與其他女孩一樣在意自己的長相,經常問大人眼中的自己是怎樣的。大人有時候會回答道:“你的樣子最丑,無論搽什么都沒用。”這令她非常難過。此時的賀淑芳已看了不少言情小說,“最早看到一篇小說是敘述一個樣子長得很丑的女孩,長大后奇跡般地變成了美女,我就開始模仿所看到的小說文體來寫作。”于是,賀淑芳的小學作文也寫得像小說,第一次受到老師的稱贊,并在小學畢業時收到與其他同學不一樣的禮物——一本稿紙。這是賀淑芳的寫作初嘗試,對她來說,那既是一種出口,又賦予了自我想象,以及想象的樂趣。
上中學以后,因課業繁重,賀淑芳對文學的態度是“控制”,即便這樣,還是接觸到茅盾、梁實秋、郁達夫、張愛玲等的作品。而定期關注的文學雜志如《蕉風》和《椰子屋》,對賀淑芳的影響不容忽視,她從里面知道了外國文學,知道了西西——一位對她在文字和構想上都影響深遠的文學作家。年少的賀淑芳,每讀一本小說就會更喜歡文學一次,但對于寫作,一直不敢投入,因為幾乎每天都在為了應付考試而做準備,就連假期也不敢放松。賀淑芳的大學選擇理工,“因為大人告訴我,只有理工才有前途。拜馬哈蒂爾總統當時的政策所賜,我幾乎是全盤關注學數理,我怕如果沒有考上大學,就會像其他女人一樣永遠住在小鎮上的屋子里,操勞過一輩子……”由于寫得少,心里沒有信心,可又朦朧地有這樣的愿望,“覺得這或許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事情。起初我想如果幾年都不寫也沒有關系,只要還活著的話,總是有一天會寫點東西出來的。”
賀淑芳用“幸運”來總結大學生活。理工大學中有華文學會,這是當時大學中很重要的一個華文聚集地。賀淑芳參加了一個叫“思想探討組”的讀書小組,十幾個成員都是鐵桿書迷,從薩特到尼采,甚至有人讀馬克思主義。“我們的大學,本來沒有這些科系,這些成員的科系也都是理科,所以我們閱讀的困難可想而知,都是自己摸索和詮釋。小時候的寫作像是去試驗語言,看它可以組合成什么模式,然后組合成不同的閱讀經驗,但就是到此為止;而這些熱情的書友雖然沒有創作,但愛閱讀和思考的方式,讓我覺得跟他們相處就像是有了一種可以彌補和學習的標桿。”
大學畢業后賀淑芳在一家美資電子廠擔當工程師,這里對于理工生來說可能是理想的去處,卻是賀淑芳想極力逃脫的地方。工廠領域的原則就是要去除人性,隱形而深入地支配人的行為,每個步驟的設計都在于減低人為錯誤的可能性,工程師的任務就是想方設法贏過人的特性。印尼女工的性格溫順,視力卻多數因長期使用顯微鏡檢查晶片而損壞;而工程師們日常聊天的話題可以完全被晶體生產表現所占據,就像正常人討論蔬菜一斤多少錢一樣……她們使賀淑芳感到內疚。當時的經濟很景氣,這樣麻木的生活過了兩年多,“那時我經常幻想,死如何能夠自然地降臨。我跟自己說:這里沒有我。我把自己收在了別的地方。”
之后,賀淑芳選擇出國留學,前往臺灣政治大學修習中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