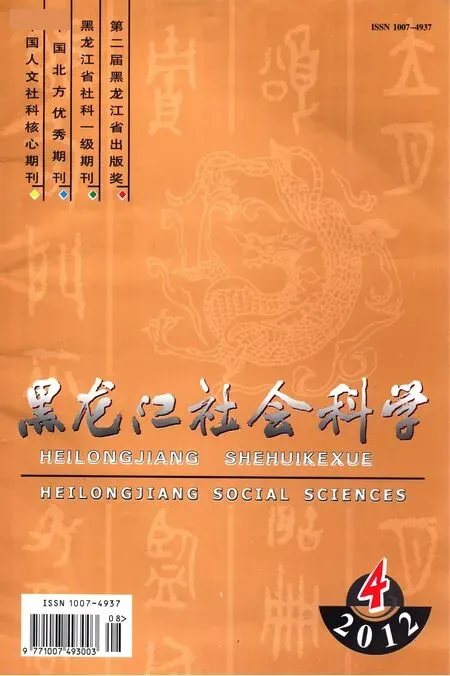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與身份危機
季廣茂
(北京師范大學a.文藝學研究中心;b.文學院,北京100875)
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與身份危機
季廣茂a,b
(北京師范大學a.文藝學研究中心;b.文學院,北京100875)
在研究對象的問題上,比較文學有必要擺脫“隨心所欲”的狀態,研究者有必要擺脫“隨遇而安”的心態。比較文學需要穩定的研究對象,至少是相對穩定的研究對象,無論這對象是單個的,還是由眾多對象構成的集合體。只有這樣,研究者才有可能投身于某個目標,投身于某項事業,比較文學才有可能擺脫身份的危機,結束在身份問題上長期忍受的煎熬和痛苦。
比較文學;研究對象;身份危機
從事比較文學教學和研究的人都知道,比較文學問題頗多,令初學者望而卻步。即使勇于面對,也常常不得其門而入。對比較文學的基本問題(包括比較文學研究的對象、方法、目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進行適當的清理和界說,是必不可少的。眾所周知,作為一個學科的比較文學形成于19世紀。但一種文學自誕生之日起,即有與其他文學相互融合和影響的沖動。美索不達米亞一帶出土的文物證明,當時那里的文學即已開始融合相鄰文化的英雄敘事[1]。文學創作如此,文學研究亦然。據說著有《論崇高》的朗吉努斯從“總是令所有人心花怒放的例證”中尋找真正的崇高,并考察來自古希臘、古羅馬和希伯來的諸多文學。中國人在長期接觸巴利語及引進佛經的過程中第一次意識到,漢語有著與其他語言不同的特征。這兩種語言的碰撞,不僅造成了實際的影響,而且使人意識到了差異,還為締結某種關系奠定了基礎。說得更具體些,兩種語言的碰撞帶來了混血現象,包括翻譯、混雜語言和雙語村的出現。可以說,比較的歷史與文學的歷史一樣漫長。
進入19世紀后,比較文學開始大行其道。比較文學曾經幾乎成為其他學科的典范。那是一個盛行“比較”的年代。任何一個學科,倘若沒有“比較”的視野,難免自慚形穢。就比較文學而言,精通本國語言,熟悉“外國語言”,將本國語言與“外國語言”兩相比較,是文學研究的基線。“跨國性”、“跨學科性”紅極一時。
但一般都承認,比較文學自從誕生之日起就危機重重,以至于談論“危機”成了談論比較文學的“序曲”。比較文學的危機有諸多表征,亦有諸多成因,但固定研究對象的缺失,既是比較文學危機的表征,也是它的成因。
在研究對象的問題上,比較文學界的認識不盡一致。最樸素的看法是:“每一個時代都有一些書、一些人在幫助人們了解別的國家和它的文學。這就是比較文學所要研究的主要對象。”[2]7馬里奧斯-法朗索瓦·基亞就是這樣看的。亞·迪馬與此是英雄所見略同。亞·迪馬在界定比較文學的范圍之前,先是界定了比較文學的地位。在他看來,毫無疑問,“比較文學是一個更為廣泛的學科——文學研究的組成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說,比較文學不僅要與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發生關系,而且要與本國文學史和外國文學史發生關系。“那么作為文學研究的一個分支的比較文學,它孜孜以求的研究對象是什么呢?這個對象是文學現象的一個方面,具體地說,它不是擷取某一個或某幾個文學現象在相應的歷史時期內進行研究,而是把這些現象放到另一個民族的領域里,和與之相類似的現象一起進行研究”[3]4。這無異于告訴我們,比較文學并不具有專門的研究對象——比較文學只是一種建立在“比較”這種廣泛和通用的研究方法上的學科。也就是說,比較文學之為比較文學,并不取決于它的研究對象,而是取決于它的研究方法,是方法派生了對象。這與其他學科大不相同:其他學科是先有研究對象,后有研究方法,方法是手段,對象是目標;在比較文學中,方法決定了對象,以至于只要使用比較的方法,選擇什么樣的研究對象都是可以的。一句話,方法先于對象,當然也比對象重要。
或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布呂奈爾等人承認,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與一般的文學的研究對象不同,“它的對象看起來像世界一樣復雜,而且時常不可捉摸”[4]。不僅確定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十分困難,甚至認定它的研究范圍同樣不易。“期望把它的范圍嚴格描述出來,也許僅只是徒勞”[2]3。應該說,在這個問題上,除去那些較為“極端”的看法,比較文學研究者達成的基本共識是,比較文學的對象是不同語言或不同文化間的文學現象。“不同語言或不同文化間的文學現象”意味著,作為比較文學研究對象的“文學現象”必須是兩種語言和文化共同具有的現象。從邏輯學的角度看,“共同具有的文學現象”的外延必定小于一般意義上的“文學現象”。因此可以說,這是對文學研究所做的“化約”。以此為研究對象,必定限制比較文學的視野,不利于比較文學的發展。此外,“不同語言間或不同文化間的文學現象”會隨著“語言”和“文化”的變化而具有不確定性,這也使得比較文學研究的對象變得游移不定。
如前所述,在某些人看來,比較文學之為比較文學,不是由“文學”來確定的,而是由“比較”來衡量的。這顯然有本末倒置之嫌。正如克羅齊所言:“恰恰因為比較的方法只是一種方法,它不足以圈定一個領域。”至少,比較文學之所以能夠成為比較文學,離不開它漫長的歷史。“我不理解,離開了比較文學的歷史,比較文學如何能夠建立起來”[5]。令克羅齊不理解的不只這一點。他還不理解:在“是否有生存權利”的問題上,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學科,像比較文學這樣受到如此長久的懷疑[6]。勒內·韋勒克在《比較文學的危機》中,查爾斯·伯恩海默在《引論:比較的焦慮》中,都表達了同樣的憂慮。作為一個學科,比較文學存在的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它的研究對象。人們難免要問:比較文學究竟研究什么?什么才有資格成為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
比較文學與文學史、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不同,因為文學史、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擁有固定的研究對象。幾乎從來無人對此表示異議。文學批評的對象是個別的文學現象,它要評判具體文本的藝術價值和獨創性。文學史的研究對象是世界各國文學的歷史發展進程,它要闡明不同時期文學的特點。文學理論的研究對象是不分歷史時期和國別的各類文學現象,旨在探討文學的一般規律和特點。
與它們不同,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是隨著比較文學的發展不斷變化的。比較文學的歷史告訴我們,作為一個學科的比較文學的確立,并不是持續不斷地深化理解某個研究對象的結果。比較文學的歷史就是一直在致力于“鎖定”自己的研究對象的歷史。
毫無疑問,比較文學研究的對象是文學文本。不過,它理解的文學文本不同于文學史、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理解的文本。或者說,比較文學在確定自己研究對象的過程中,不斷深化它對文學文本的認識。其實在文學的發展過程中,隨著地域的變化、時代的變遷和語言的演化,文學的定義在不斷革新,有關文學的假定也在不斷更替。難能可貴的是,比較文學樂于認可和接受這些變化,并時時調整自己的研究焦點。這是其他文學研究所不具備的品質。在這個意義上說,沒有確定的研究對象,未必純然是比較文學的短處。
眾所周知,比較文學不同于比較語文學和比較解剖學。在西方,比較語文學興盛于1885年前后至20世紀初。比較語文學主張采用比較的方法研究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言的關系,以探明它們各自的發展歷史,進而揭示它們之間可能具有的共同起源(或祖先)。它的興起是由威廉·瓊斯爵士于1786年的一項發現引發的——梵文與拉丁文、希臘文、德文有關。比較解剖學以比較的方法研究生物在結構特征上的相似與差異,從而了解生物進化的規律,確定不同的生物是否存在共同的起源(或祖先)。在這樣的比較研究中,研究者最后總是走向一個共同的因素,即共同的起源(或祖先)。如果達不到這個目的,無法在兩個或多個因素中找到共同的起源(祖先),“比較”即告失敗,研究必須終止。
比較文學顯然無法把比較語文學和比較生物學作為自己的模型,以之確立自己的研究目標和研究對象,因為不同國別的文學——特別是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顯然并不具有共同的起源(祖先),這是不需要研究的。也就是說,比較語文學和比較解剖學要達到的目的,對比較文學來說,完全是自明的。在比較語文學和比較解剖學那里,差異只是基于共同起源的變異,是“同”中之“異”;在比較文學這里,差異是實實在在的差異,是“異”中之“異”,而非變異。
如果比較文學以比較語文學和比較解剖學為模型,把不同國別的文學視為基于同一起源的成長與變異,認定這些文學具有共同的根基,甚至具有共同的“樹干”,差異只是“枝”“葉”問題,那么對于影響和翻譯的研究似乎也會變得多此一舉,比較文學也會變成某個國家之內的一門歷史科學,盡管它的研究范圍完全可能跨越國家的邊界,形成所謂的“印歐比較文學”、“烏拉爾—阿爾泰比較文學”。它的研究對象將局限于民間文學和神話,因為只有民間文學和神話才嚴格符合比較語文學和比較解剖學強調的擴散和變異的模型。
無論如何評價,這種現象值得我們關注:即使沒有明確、固定的研究對象,比較文學依然“我行我素”。自19世紀以來,文學生產和文學消費的世界性品格為“世界文學”的形成創造了成熟的條件,學者們對跨語言和跨國界的文學交流產生了濃厚興趣,直接促成了作為一個學科的比較文學的形成。雖然不同國家的文學并不具有共同的起源(祖先),但比較文學一直都在尋找不同國家的文學之間的共同點。
比較文學相信,文學之所以為文學,不論國別如何不同,必定存在著共同性。只有認可這一點,比較才有可能,比較文學才能成立。比較文學相信,不論形態如何不同,文學都揭示了人類經驗的普遍性,都呈現出人類共同的情感、欲望、意志、觀念、人格乃至共同的境遇。這是共同的主題。但僅僅執著于這一點——文學揭示了人類經驗的普遍性——是不夠的。“文學揭示了人類經驗的普遍性”是一個具有能產性的假設,卻不是堅實的普遍有效的結論。在實際研究中,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比較文學研究實際上只是對文學主題的研究。這時,對文學文本的解讀常常也是主題性解讀。如此研究和解讀極易流于瑣碎和任意。此外,研究者除了關注內容(主題),常常忽略形式方面的審美質素。
一味閱讀翻譯成本國語言的文學文本,會對這種類型的比較文學研究情有獨鐘,因為文學一經翻譯,主題可以“幸免于難”,形式方面的審美質素必定“損兵折將”。這不僅因為文學文本的形式方面的審美質素具有“不可譯性”,而且因為翻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具有“選擇偏見”,即注重內容,忽略形式。在這方面,對詩歌的翻譯表現得最為明顯。對詩歌進行主題學解讀,完全可能買櫝還珠,得不償失。我們雖然有所收獲,但應該有更大的收獲,兩者之差,即我們的損失。
正像蘇源熙指出的那樣,如果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并非文學文本的內容(特別是主題),那它可能是文本的某個維度,而文學文本的內容則只是這個維度的征兆而已[7]。如何理解蘇源熙所謂的“維度”?他所謂的“維度”類似于“積淀”了內容的形式:雖然“維度”屬于形式的范疇,但它又“積淀”了內容,同時又“征兆”著內容的存在。在這方面,俄國比較文學和比較詩學的研究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啟示。
俄國19世紀的亞歷山大·維謝洛夫斯基及其20世紀的傳人維克托·日爾蒙斯基認為,詩歌的韻律在無可阻擋地進化著。他們試圖在借助于歷史詩學的研究,確定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在此之后,芒羅·夏德維克與科肖·夏德維克合著了《文學的成長》。“文學的成長”頗具詩情畫意,仿佛文學是某種植物或動物。他們把當時民間文學和口頭文學研究取得的成果融入了自己的比較研究[8]。這種研究擬以比較語文學的方式,充分利用歷史分支研究和類型劃分方面的成果,追問對于比較文學來說至關重要的問題:文學最初的特征是什么?文學最初采用了何種文類?執著于怎樣的主題?文學又是如何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的?在他們看來,比較研究不能過多強調文學受到的側面影響,如希臘和拉丁的書面文化對文學的側面影響,否則比較研究就會受到干預,研究的行程就會改變。這與梵·第根的比較文學研究大異其趣,因為在梵·第根那里,研究比較文學就是研究文學的“進口”和“出口”。這是兩種完全相反的比較文學研究范式,但同時可以并行不悖,這本身表明,自1930年代以來,比較文學研究“大肚能容”,同時又缺乏連貫一致性。
蘇源熙告訴我們,以比較語文學為比較文學的模型,這樣做的不乏其人。詹姆遜就曾借助理查茲和奧格登的理論,把比較文學建立在語義學的基礎上。他們認為:“一個民族使用的語言就是一套極其復雜的手勢。國家借助于符號操縱一方天地,同時舒緩或刺激情緒……一個社群中存在著一系列的意義、感覺、語調和意圖,確定它們中哪些能用語言中的詞語來表達,哪些不能表達,實際上是展示這個社群的某些行為,隱藏另外的行為。”“如果對意義所做的這個粗略說明差強人意,那么文學的比較就會成為幾個種類的意義的比較,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都想運用詞語來激發這些意義”[9]。
由此可知,比較文學研究的對象應該是“意義”,比較文學實即比較不同種類的意義。當然,意義是由詞語等符號激發而來。依人類學之見,人類具有解釋符號的能力。這不僅為人類學介入比較文學的研究預留了空間,而且把符號這個人類學范疇視為所有文學的根基,視為比較文學研究的根基。在這個基礎上,研究者可以判斷歐洲各國的文學是如何“本是同根生”的,又是如何“相煎何太急”的,它們在各自采用了自己的民族語之后,究竟還有多少相似性。
當然,最重要的符號還是語言,語言的重要性無論如何不可小覷。俄國形式主義者追尋的“文學性”首先表現在語言上。維克托·什克羅夫斯基在1925年出版的著作《散文理論》中提出一個革命性觀念——“藝術即技巧”。在這里,形式主義批評家的知識取向與比較文學對研究對象的強烈渴望完全一致。可惜的是,什克羅夫斯基的著作被塵封了四十年之久。蒂尼亞諾夫后來把“文學性”視為所有文學傳統的“公分母”,即所有文學文本的共通因素,因此有資格成為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這對諸如比較文學之類的世界性學科而言,意義非同凡響。尋找并描述所有文學文本中的“文學性”,似乎成了比較文學的一項義不容辭的使命。雅克布遜專注于詩歌中的“文學性”,對什克羅夫斯基專注于散文中的“技巧”做了必要的補充。散文自然與詩歌不同:散文具有無可置疑的“可譯性”,詩歌在翻譯方面則大受限制。這似乎表明,“文學性”雖然是所有文本的共通因素,但共通不等于“可譯”。翻譯屬于世界文學的范疇,并不屬于比較文學的范疇。保羅·德曼重新界定了“文學性”的概念,將其視為“語言的修辭之維或譬喻之維……任何言辭性事件,只要把它當成文本來閱讀,文學性都會呼之欲出”[10]。即使蘇格拉底式對話,也可以作如是觀。
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對語言學的關注,對“文學性”的青睞,為比較文學追尋自己的研究對象確立了有效的框架,帶來了重新發現的機遇。任何一種人類文化都無法離開語言和語言藝術,任何語言藝術都不乏打破庸常語言交流的各類“技巧”。除此之外,俄國形式主義批評還帶來了一種“文學平等主義”,因為它消解文學經典:任何文學作品都有其“技巧”和“文學性”,這是它們共同的特征,只要把這些特征尋找出來,所有的作品都同樣優秀,并無高低之分、優劣之別。當然,它的不足之處也是顯而易見的。和語言學一樣,形式主義傳統中的其他學科(如敘事學、符號學甚至福科的“譜系學”)也催生了諸多專門術語。這些術語似乎使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遠遠離開了特定的文學傳統。學者們合作編纂文學術語辭典似乎使情形有所改觀,但正如蘇源熙警告的那樣,對此不要過于樂觀。學者們努力把當今術語與古代詞匯熔為一爐,但張冠李戴、亂點鴛鴦譜之類的事情始終無法徹底杜絕。
什克羅夫斯基、雅各布遜和保羅·德曼等人對“文學性”的迷戀,暗示了這個概念對比較文學的吸引力。有了“文學性”,不同語言的對峙、不同國家的僵持和形形色色的歷史分期,都不再重要,甚至無足掛齒;因為比較文學沒有固定的研究對象而反對比較文學的意見,頓時煙消云散。“文學性”派生了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盡管對“文學性”的認識并不完全一致,但大家在下列一點上已經達到共識:“文學性”語言與庸常語言不同,它關注的不是發話者、受話者、語境、接觸和代碼,而是信息。“文學性”可以脫離語境存在,這也是比較文學渴望已久、孜孜以求的品質。盡管有這么多的優點,比較文學還是無法把“文學性”的大旗高高掛在自己的城堡上,任其飄揚。這是因為,“文學性”雖然是文學的本質屬性之一,它的“出身”卻頗為可疑:它并非文學的一望便知的屬性,而是“閱讀”出來的屬性,即通過閱讀而概括出來的屬性。這顯然容易給人造成“相對主義”的錯覺。“相對主義”的高帽,是比較文學唯恐避之不及的。
進入1990年代以來,文化研究迅速崛起。相形之下,文學研究大有收縮之勢,以至于文學研究仿佛受到了致命的威脅,要對自己的疆界進行“嚴防死守”。但是,“在美國還出現了擴大比較文學研究領域的傾向,把人類的其他‘表現領域’,即其他藝術門類,甚至非藝術門類,都列作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3]43這對一直追尋自己研究對象的比較文學,產生了強烈的影響。文學文本的觀念與以前已經大不相同。有人把文學文本視為比較文學理所當然的研究對象,這似乎是老生常談,但論者又常常賦予它新的內涵。比較文學把文學文本視為“復雜多變和通常矛盾重重的文化生產領域中的一種話語實踐”[11],或者視為“處于不同的認識論語境、經濟語境和政治語境中的文化表達的物質可能性”[11]。這實際上是把文學視為文化,把文學研究活動視為文化研究活動。文本成了眾多話語模式之一。文學話語不再是比較文學的焦點,文化話語趁機異軍突起。這是比較文學的范式轉移,無論我們如何評論這次轉移的利弊,有一點無可否認,此舉對歐洲的文學經典和歐洲的“宏大理論”遺產帶來了巨大沖擊。它采用社會科學的范疇,瓦解了學科間的邊界,使比較文學喪失了自治,使比較文學失去公認的中心,以至于有人認為“在這個領域內其實是沒有核心活動的”[12]。不同的學者選擇不同的研究對象,使用不同的語體,表達不同的觀點,但對敘事類和紀實類文本情有獨鐘,對傳記類和歷史類文本刮目相看,詩歌、詩語及文學語言、“文學性”頗受冷落。有人認為,比較文學如有未來,就必須摒棄詩歌、語言和國家的觀念。雖然還有人力主堅守文學的特殊性,反對把文學文本投入其他話語的汪洋大海,但因為大勢已去,故而收效甚微。
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文學與文化之間的爭執,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對峙,通常暗示了研究者對西方文學經典和非西方文學經典的態度:選擇文學還是文化,選擇文學研究還是文化研究,意味著選擇西方經典還是非西方經典,意味著研究者對“西方中心論”的態度。在全球“后殖民”的語境之下,這固然令非西方的研究者欣喜,但拆解“西方中心論”的努力未必能夠成功:文化功能主義者相信,強勢文化之為強勢文化,弱勢文化之為弱勢文化,西方文化之穩居于中心,非西方文化之徘徊于邊緣,自有其道理在,也有其“功能”在。這道理和這功能,絕非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樣簡單,只要識者登高一呼,立即應者云集,然后揭竿而起,天地為之易色,乾坤為之扭轉。多元文化主義是一個令人渴求的夢想,也是一個難以真正實現的渴望。正如周蕾所言,把非西方的普通文本列為通常只有西方文本才能置身其間的“經典”之列,只能使一批新的“西方中心論”專家侵入非西方的文本。那些打著反對“西方中心論”的學者無法剔除其“西方中心論”的框架,只是把它隱藏起來而已[13]。周蕾認為,這為比較文學提出了新的課題:在以文化研究為主導的比較文學研究中,何種專家意見才有價值可言?比較文學要培養專屬于自己的未受“西方中心論”影響的專家嗎?無論如何,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是否引入歐洲傳統和歐洲經典之外的新傳統和新經典,而在于如何盡快擺脫那些沒有實際意義的幻覺性問題,從而面對具有實際意義的問題,采取徹底的實用主義態度。有人會說,不要再追問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了,能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吧。
這導致了比較文學研究對象的“離散化”,使研究者在比較文學研究對象的問題上茫然若失,也深化了比較文學面臨的危機,以至于對比較文學的界定既不是“比較文學”中的“文學”,也不是“比較文學”中的“比較”,而是其他莫名其妙的東西:“不是對文學的解讀”,而是“對隨便什么可讀之物從文學角度所做的解讀”。
在研究對象的問題上,比較文學有必要擺脫“隨心所欲”的狀態,研究者有必要擺脫“隨遇而安”的心態。比較文學需要穩定的研究對象,至少是相對穩定的研究對象,無論這對象是單個的,還是由眾多對象構成的集合體。只有這樣,研究者才有可能投身于某個目標,投身于某項事業,比較文學才有可能擺脫身份的危機,結束在身份問題上長期忍受的煎熬和痛苦。
[1]David Damrosch.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M].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39 -77.
[2]馬里奧斯·法朗索瓦·基亞.比較文學[M].顏保,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
[3]亞·迪馬.比較文學引論[M].謝天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
[4]布呂奈爾,等.什么是比較文學[M].葛雷,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226.
[5]János Riesz.in Sensus Communis:Contemporary Trend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ed.Tubingen:Gunter Narr Verlag,1986:104.
[6]See Henry H.H.Remak.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Crossroads:Diagnosis,Therapy,and Prognosis[J].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1960,(9):3.
[7]See Haun Saussy.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Terrorism[J].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6.
[8]H.Munro Chadwick and N.Kershaw Chadwick.The Growth of Literature[J].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2,(3):5,1.
[9]R.D.Jameson.A Comparison of Literatures[M].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1935:33 -35,29-30.
[10]Paul de Man.The Resistance to Theory[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6:17.
[11]Charles Bernheimer.The Bernheimer Report,1993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M].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1971:42.
[12]Haun Saussy.Comparative Literature? [M].Publicat 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18,2003:36 -41.
[13]See Rey Chow.In the Nam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C]//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116.
J4
A
1007-4937(2012)04-0115-05
2012-04-17
季廣茂(1963-),男,山東泗水人,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西方文論和比較文學研究。
〔責任編輯:王曉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