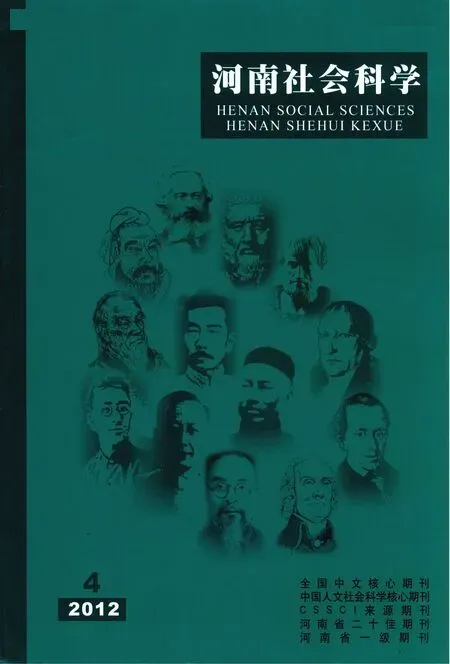弗羅斯特詩歌的悖論詩學
王曉俊
(河南工程學院,河南 鄭州 451191)
Xia Jixian(82)
弗羅斯特詩歌的悖論詩學
王曉俊
(河南工程學院,河南 鄭州 451191)
美國詩人弗羅斯特有著比較復雜的世界觀。他認為,世界是一個丑與美的復合體,人類是一個善與惡的組合體。這種悖論詩學在其詩歌中主要表現為四個方面:(1)熱愛自然,憎恨自然;(2)熱愛生活,厭倦生活;(3)熱愛人類,憎惡人類;(4)始于歡樂,終于憂傷。從新批評的視野出發,在精神分析與文化批評視閥下,解讀弗羅斯特“鄉村哲學家”的悖論詩學,有助于真正地感悟其詩歌中的智慧與真諦。
悖論;自然;生活;人類;歡樂;憂傷
弗羅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在美國詩壇的地位類似但丁,承前啟后,既沐浴在傳統詩歌的氤氳中又為現代派詩歌創作提供一塊肥沃的土地,留下了《林間空地》、《未曾選擇的路》、《雪夜林邊小駐》等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其詩以描寫新英格蘭的自然景色或風俗人情始,漸漸入哲理的境界樸實無華,卻又細致含蓄,耐人尋味。崛起于20世紀20年代的新批評,將文學批評的視角由傳統的作家生平研究轉向作品的語言、形式和藝術手法的研究,豐富了文學批評的內涵,沖破了傳統文學批評的樊籬。悖論這一文學批評術語由新批評派人物艾倫·泰特(Allen Tate)和I·A·瑞恰茲(I·A· Richards)提出,并由新批評派主要人物之一克林斯·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在其專著《精制的甕》中得到詳細闡釋。布魯克斯認為悖論是詩之“高峰”,中英詩歌中運用悖論的例子俯拾皆是。華茲華斯的那句名言是“兒童是成人的父親”看似矛盾,實則道出了深刻的哲理。中國古詩中運用悖論的例子也很多,如白居易的“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杜牧的“多情卻似總無情,惟覺尊前笑不成”以及魯迅的“于無聲處聽驚雷”等。被許多評論家冠名為“鄉村哲學家”的弗羅斯特,擁有豐富的哲學內涵,所創作的詩篇大都蘊含著深邃的哲理,發人深思。弗羅斯特的抒情詩格調低沉,詩人思想和性格中陰郁的因子表達得非常充分。世界觀比較復雜的弗羅斯特認為世界是一個丑與美、善與惡的組合體。因此,他一方面描寫自然美以及自然對人類的恩惠,同時也敘寫自然的破壞力,正是這種詩歌的悖論增強了每一首詩歌的張力。我們按照當代新批評的思想,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弗羅斯特詩歌進行探討,透視其悖論詩學。
一
萬物有靈且美,有緣得遇且珍惜。弗羅斯特在詩中呈現給讀者一幅幅美麗幽靜的畫面——遠離喧囂都市的鄉村,不曾被現代工業文明浸染的“凈土”。自然界的萬事萬物在他的作品中得以頌揚,山川湖泊自然流暢,日月星辰點綴空中,海浪沙灘涌動迭起,花木鳥蟲映入眼簾,以此來驚嘆造物主所締造的自然景觀。弗羅斯特在其成名詩集《少年的心愿》(A Boy’s Will)中,對大自然的情有獨鐘凸顯在字里行間,無比摯愛之情溢于言表:“我的心愿之一是那黑沉沉的樹林,/那古樸蒼勁、柔風難吹進的樹林。”[1](《進入自我》)詩人酷愛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在那一片小如寶石,形如太陽的圓形的草地上長滿了紅朱蘭,詩人為紅朱蘭免遭“毒手”而祈禱:“在離開那地方之前,/我們作了番短暫的祈禱,/愿每年割草的季節,/那地方能被人忘掉,/若得不到長久的恩寵,/也望博得一時的歡心,/當花與草分不清的時候,愿人人都能刀下留情。”(《紅朱蘭》)殘酷無情的現實——寒冷的冬天,凜冽的寒風,內心的孤獨憂傷,在大自然花木鳥蟲的光芒照耀下,黯然失色,痛苦也隨之消失。一只鳥、一只蜂仍然能給詩人帶來無限的希望和喜悅,使詩人歡欣鼓舞、精神振奮。在《致春風》中,在富有獨特生命力的春天里,春風使得萬物復蘇,生機盎然,詩人為之雀躍,油然歌唱起來。詩人行云流水,譜寫出美妙動人的詩歌:“攜雨一道來吧,喧囂的西南風!/帶來唱歌的鳥,送來筑巢的蜂;/為枯死的花兒帶來春夢一場,/讓路邊凍硬的雪堆融化流淌。/從白雪下面找回褐色的土地。”
山林中,萬籟俱寂,柔風輕輕拂過臉頰,雪花如同花絮徐徐落下。此時此刻,詩人不再孤單,他如同徐徐落下的雪花,融化在美麗如畫的大自然中。是夢終歸要醒來,履行諾言就意味著一諾千金,責任和義務令他不舍離去,心中充滿感傷。詩中所寫:“這樹林真美,迷蒙而幽深,/但我還有好多諾言要履行。”(《雪夜在林邊停留》)在夏日里,“抬頭仰望”及“一只小鳥放開美妙歌喉”都是真實寫照,詩人弗羅斯特駐足仰望樹上鳥兒棲息之地,欣賞著綻放美妙歌喉的歌聲,如癡如醉。如今樹上沒有“鳥兒鳴啾”,“惟有一片枯葉殘留枝端”,詩人為尋覓那只鳥“久久徘徊,繞樹三匝”。沒有鳥兒美妙的歌聲,生活似乎失去了意義,變得黯淡無光。貌不驚人的一塊小卵石激起詩人心中的千層浪,扣人心弦,語言表達中的一文不值并不代表詩人態度上的冷落,在精神層面上依然振奮不已。“我經營著一片遍地卵石的牧場,/卵石像滿滿一籃雞蛋令人動心,/雖說它們無人稀罕,一錢不值,/可我仍然想知道這是否有意思——”(《詠家鄉的卵石》),由此可見,使他為之動心、精神振奮的就是這塊“一錢不值”的卵石!
《踏葉人》以淺顯易懂的口語表達形式,語氣平緩、冷靜,采用人們熟悉的韻律,表達詩人對自然的情感,詩人從喜歡到厭倦的整個心理變化都展現在畫面中。“整個夏天我都覺得它們對我悄聲威脅”,因為大自然中的樹林對于我們人類生存的威脅悄然而至,厭惡感與抵觸感進一步加深;秋至冬來的落葉使詩人觸景生情,感受到生活瀕臨絕望,“它們似乎也希望拉著我一道去死”。而后,作者打算鼓起生活的勇氣,極力克服和戰勝內心愈發強烈的恐懼心理,準備迎接來年的新生活,“準備踏來年的積雪”,然而他的努力即將消失殆盡之時,開始懷疑人生,悲觀自棄,成功改變現狀成為當務之急,讀者對此卻疑慮重重,“厭倦了秋色”成為頹廢無奈之舉,詩人對樹林產生抵觸情緒,態度也變得憎恨起來。
詩人面對大自然的冷漠無情越來越感到厭惡。《荒野》中的大雪冷酷無情,吞沒一切生命,就連小動物也不放過。詩中:“大雪和夜一道降臨,那么迅捷,/壓向我路過時凝望的一片田野,/田野幾乎被雪蓋成白茫茫一片,/只有少數荒草和麥茬探出積雪。//這是它們的——周圍的樹林廣闊。/所有萬物都被埋進了藏身之所。”《星星》作品中,蒼穹中的星星成為會說話的心靈之窗,富有生機,時隱時現。夜晚,我們仰望蒼穹,孤獨感黯然消逝,似乎找到了依賴和傾訴的對象。星星“仿佛關注著我們的命運,/擔心我們會偶然失足”,冷漠無情讓我們倍感孤獨,精神支柱失去了平衡,“然而既無愛心也無仇恨,/星星就像彌涅瓦雕像/那些雪白的大理石眼睛,/有眼無珠,張目亦盲。”人類在冷漠的大自然中感受不到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渺小到幾乎為不存在,成為孤立無援的可憐蟲。
二
弗羅斯特采用傳統的詩歌形式表達其對現代生活的觀點,借自然描寫表達對社會的認識,向往理想而又腳踏實地,傳統與現代、自然與社會、理想與現實的雙重性在詩作中比比皆是。弗羅斯特對大自然的熱愛,進而使他熱愛生活。《生存考驗》一詩中,他寫道:“上帝把人世生存的短暫的夢/描繪得非常完滿,充滿溫情。”人生之路充滿荊棘,總是如此坎坷而短暫,但苦樂相伴,溫情常在,回味無窮,這就是追求生命的價值所在,詩句中流露出詩人對生活的無比熱愛,勾勒出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冰與火,這兩種相異沖突的角色,便是仇恨和欲望的象征。詩人情感的宣泄在《冰與火》一詩中一覽無余,對生活的滿腔熱愛之情,最終熔化為兩種可能導致毀滅人類的力量。原詩歌很短,此錄如下:“有人說世界將毀滅于火,/有人說毀滅于冰/根據我對于欲望的體驗,/我同意毀滅于火的觀點。/但如果它必須毀滅兩次,/則我想我對于恨有足夠的認識。/可以說在破壞一方面,/冰,也同樣偉大,且能夠勝任。”(余光中譯)詩中深刻地表露出詩人面對未來的憂慮,不難看出他對人類的眷戀之情。《白樺樹》借對自然景物的描寫,揭示出詩人復雜的內心世界,他把世界看做一個善與惡的混合體,悖論的人生觀基本形成。當他承受不住生活的壓力時,他想尋求一條通向天國的道路,短暫地離開人世一段時間,只是想短暫的逃遁,但生活的眷戀使他無法逃避現實:“我喜歡憑著爬一棵白樺樹離去,/攀著黑色樹枝沿雪白的樹干上天。/直到那棵樹沒法再承受我的體重,/低下頭把我重新送回地面。/那應該說是不錯的追求和歸來。”雖然現實生活丑陋而又殘酷,但只要我們活著,最終還須面對它,并且要選擇坦然地面對它。漫漫人生之路,中途的短暫休息是為了走更好更長遠的路,不辜負每天嶄新美好的晨光,及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悖論充斥在我們人類的現實生活中,矛盾無處不在,成為詩人思維方式的特定模式。詩人生與死的悖論詩學表現得淋漓盡致。
以弗洛伊德為代表的精神分析批評家認為,文學活動是一個復雜但又不是不可理解的精神現象,而要打開這個殿堂之門就應該努力去關注和了解文學中的無意識活動。他們在對作家的研究中,非常注重搜集作家的各種資料,進而進行分析,其中包括相關的傳記資料,如自傳、私人信件、講稿及其他文稿,尤其是對作家童年的生活記載[2]。采用這種文學批評方法,可以促進我們加深對作品的研究,逐一闡釋弗羅斯特的悖論詩學。生活的坎坷和苦難使得詩人形成復雜的世界觀,因此在詩歌創作中反映出他思想和性格中陰郁的一面:11歲喪父,后隨母親遷居美國東北部的新英格蘭,他與這塊土地結下不解之緣。幼年時期患有神經性胃病,其兒子埃利奧特死于霍亂,而女兒埃莉諾·貝蒂納剛出生幾天便夭折,母親又死于無法治愈的癌癥,妹妹珍妮飽受精神病的折磨而最終死于精神病,女兒瑪喬麗死于產褥熱,妻子心力衰竭而死,兒子卡羅爾自殺身亡。起初弗羅斯特的詩歌在美國并沒有引起注意,1912年遷往英國定居后,受到一些詩人的支持與鼓勵,出版了詩集《少年的意志》(1913)和《波士頓以北》(1914),好評如潮,得到了美國詩歌界的贊揚之聲。1915年回到美國經營農場,而后于1924、1931、1937、1943年四次獲得普利策獎,詩名日盛。成名后的弗羅斯特奔波于幾所著名大學,經常外出讀詩和進行演講,成為駐校詩人與詩歌顧問。“經常拖著病體疲憊不堪地回家。”[1]由于詩人過度疲憊,他希冀片刻的安寧,即使在干農活時,他也會干著干著打起“盹”來:“冬日睡眠的精華彌漫在夜空/蘋果的氣味使我昏昏欲睡。”(《摘蘋果后》)弗羅斯特詩歌中多處出現的睡眠,使人想到死亡。這條荒蕪之路,在他看來,如此這般痛苦,種種迷惘和惆悵不斷襲來,面對繁重的生活壓力,使他喘不過氣來,死亡與睡覺緊密聯系起來:“我拱起的腳背不僅還在疼痛,/而且還在承受梯子橫檔的頂壓。/我會感到梯子隨壓彎的樹枝晃動。/我會繼續聽到從地窟傳來/一堆堆蘋果滾進去的/轟隆隆的聲音。/因為我已經采摘了太多的/蘋果,我已非常厭倦/我曾期望的豐收。”詩人痛苦的經歷和生活的磨難使他既向往人生,憧憬未來,又厭惡生活,他的悖論人生哲學在其許多詩歌中都有書寫。
三
對大自然的熱愛,進而使詩人熱愛生活,熱愛人類。《仆人們的仆人》以女仆的口吻講述了她的家屬以及她自己的不幸遭遇,表現了詩人對普通百姓命運的關切,寄托著詩人對普通百姓命運的關切,寄托著詩人無限的同情和對普通人的真摯情感。《冰與火》描寫可能導致人類毀滅的冰與火——仇恨和欲望的象征。對未來世界的擔憂成為詩人在這首詩中的主旋律,充分表達了熱愛人類的真摯情感。同時,詩人還流露出對人類的懷疑和敵視,認為人與人之間的仇恨和人類永遠不能滿足的欲望將會給人類帶來痛苦和災難,甚至導致人類的毀滅。《熄滅吧,熄滅》通過描寫一個普通童工被電鋸奪去一只手,最后導致死亡的悲慘遭遇,展現了詩人對普通人命運的關注,對下層人的同情。
弗羅斯特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像“我們各長一只友愛與仇恨之手/友愛之手把彼此緊緊相拉,/仇恨之手讓我們苦苦爭斗”。現實生活和人類社會就是在愛與恨、親與疏,理解與隔閡的矛盾之中運動和發展。《補墻》就體現了這種矛盾的心理。詩人認為,在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都有一條不能互相跨越的墻,都要保持一定的距離,才能彼此友好相處。國與國之間互不侵犯,才能相安無事。該詩講的是“補墻”,實際上卻是“拆墻”的,因為“砌墻的地方我們本來用不著墻”。詩人告訴我們,人與人之間不應有一堵“墻”,無論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只要人與人之間坦誠相見,只要國與國之間和睦相處,平等互惠,那么“墻”則是多余的。只要拆除那堵阻隔人類溝通的“墻”,人類才能共同發展,人類才能避免戰爭,才能求得和平與安寧。因此那堵“墻”既需要修補,又不需要修補。此乃詩人的悖論詩學。
四
弗羅斯特宣稱一首詩應“始于歡樂,終于智慧”[3]。詩人運用質樸無華的語言給讀者展現出一幅幅幽靜美麗的自然畫卷,給讀者帶來無限的歡欣和鼓舞。他那簡單的語言中往往迸發智慧的火花。但是,弗羅斯特給讀者帶來無盡的歡樂之時,也帶來無限的憂傷。詩人為尋覓那蘭花遠道而來,那美麗的花朵不僅使詩人歡欣,也給讀者帶來無盡的歡樂。因為:“紫葉片亭亭玉立,在榿樹下,/在那漫長的一天里,/既無輕風也沒有莽撞的蜜蜂/來搖動它們完美的姿勢。”(《尋找紫邊蘭》)然而,詩人的歡樂似乎是短暫的,他發現那花蕾白得像幽靈,同時,隨著夏天的過去,秋天的到來,樹葉也會飄零,淡淡憂傷躍然紙上:“我只是跪下來拂開榿木樹枝/觀賞它們,或更多/數數它們在矮林深處的花蕾,/……秋天就要到來,樹葉會飄零,/因為夏天已過去。”(《尋找紫邊蘭》)
《白樺樹》一詩的開頭,詩人依托自然景色或風俗人情,將一幅優美的自然畫卷平鋪而徐,使讀者漸入哲理的境界:晴朗的冬日,壓滿了冰條的白樺樹在風中搖擺。詩人設想某個農家孩子攀爬白樺樹,這種快樂景象讓讀者展開遐想。這不禁使我們回想起那無憂無慮的童年時代。詩中寫道:“每當我看見白樺樹或左或右地彎下/與一排排的較直且較黑的樹木相交,/我都愛想到有位男孩在搖蕩復寫紙們。/但搖蕩不會像冰暴那樣使白樺樹/久久彎曲。在晴朗的冬日早晨,/在一場雨后,你肯定看見過它們/被冰凌壓彎。當晨風開始吹拂時,/當風力使它們表面的琺瑯裂開時,/它們會喀嚓作響并變得色澤斑駁。”詩人透過這些快樂的光景,試圖逃避殘酷的現實,不堪忍受精神肉體上的痛苦,復雜的內心世界使他產生了離開人世間的念頭。白樺樹上的雪是與死亡有關聯的意象特征,借爬白樺樹之力,來找尋一條通向天國的漫長之路,卑微和渺小的生命從而徹底擺脫了塵世的煩擾和憂傷。詩歌語言的感染力為讀者留下深刻的情感觸動,感傷憂愁無限放大。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弗羅斯特的悖論詩學還表現在他與傳統觀念的相悖上。詩人在《意志》(Design)中這樣寫道:“我發現只胖得起靨的白色蜘蛛/在白色方靈草上逮住一只飛蛾/一只宛如僵硬的白絲緞的飛蛾—/與死亡和枯萎相稱相配的特征/混合在一起正好準備迎接清晨,/就像一個女巫湯鍋里加的配料——/蜘蛛像雪花蓮,小花兒像浮沫,/飛蛾垂死的翅膀則像一紙風箏。”傳統意義上,白色往往象征純潔、忠貞、安寧。白色在這里卻被描寫成“浮沫”和“女巫湯鍋里的配料”,“萬靈草”完全是對美麗花朵的嘲諷。傳統的“白絲緞”往往使人想起女郎的裙袍,由于“韁硬”和“垂死的翅膀”它只能用作裹尸布。傳統的純潔之于詩人則是邪惡和死亡,這首詩不免使人對人類產生恐懼之感。但是,盡管與傳統存在悖論,弗羅斯特還是從其中尋找書寫詩歌的靈感。
弗羅斯特的詩歌富于象征和哲理,同時又有濃郁的鄉土色彩,那些看似互為矛盾的表述,往往飽含著深刻的思想,折射出真理的光輝。正是這種悖論哲學構筑起詩歌的有機結構,使其詩歌迸發出一種張力,閃耀著智慧之花,使詩歌耐人尋味,“雅俗共賞”,令讀者“流連忘返”;正是這種悖論詩學有效地表現了詩人復雜的內心世界,反映出復雜的社會生活。
[1]理查德·普瓦里耶,馬克·理查森.弗羅斯特集[M].曹明倫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其他詩歌的原文均選自本詩集,不再一一標注。)
[2]王先霈,等.文學批評原理[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
[3]Greenberg,Robert A,Hephburn,James G.Robert Frost:An Introduction[M].New York:Holt,Rinehartand Winston,1961.
責任編輯 宋淑芳
(E-mail:hnskssf@163.com)
Research into the Narration Structure in Chronicle of Zuo Zhuan
it’s well known that the narrative structure’importance for work and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zuozhuan has been analysed.But most of the analysis articles were restricted within narrow traditional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limits.According to the western narration theory,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zuozhuan has three characteristics:firstl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structure,it describes events based on the jing,that’s the historical sequence,secondly,its overall arrangement is graceful and of appropriate detail,finally,its recessive structure is planed carefully and farsighted.All the characters reflect zuozhuan’s originality,based on nerrative style of chunqiu,and is of genre distinct from it.
zuzhuan,describe events based on jing;“all the stars twinkled around the bright moon”;recessive structure;have a style of one’s own
Xia Jixian(82)
I106.2
A
1007-905X(2012)04-0091-03
2012-01-10
河南省高等學校青年骨干教師資助計劃項目(2009GGJS—126)
王曉俊(1976— ),女,河南商丘人,河南工程學院副教授,上海外國語大學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英語語言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