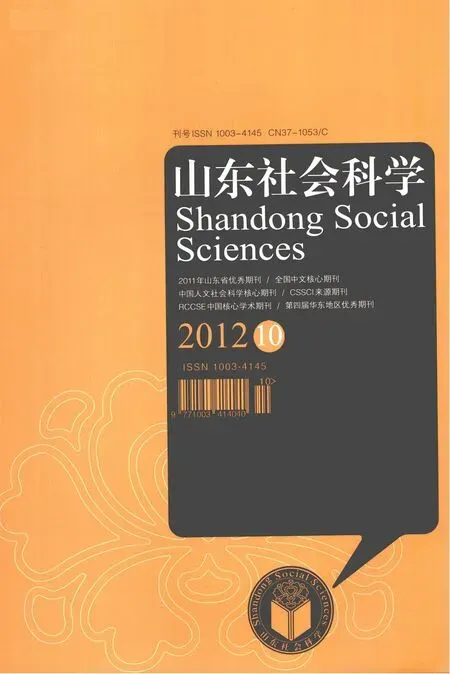新聞專業主義與中國史學傳統——文化視域下的新聞專業主義中國化問題
趙光懷
(臨沂大學傳媒學院,山東臨沂 276000)
近年來,在中國媒體迅速發展的同時,有關新聞真實性問題的事件不斷發生,新聞誠信受到公眾懷疑,媒體公信力下降呈現出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為了實現新聞的真實性,有效提高媒體公信力,有的學者開出了新聞專業主義的藥劑;有的學者則提出了從文化角度審視新聞專業主義的新思路,比單純的職業分析更能顯示出人的思維性和能動性特征,為研究中國新聞專業主義問題開辟了新的視角。本文擬從新聞學與史學傳統的關系出發,從文化層面對新聞專業主義中國化問題進行探討。
一、中國新聞專業主義的發展及與史學的淵源
西方新聞專業主義概念引入中國新聞界是晚近的事情,學術界一般將其界定于20世紀80年代。拋卻概念滋擾,作為一種新聞思想觀念,西方新聞專業主義對中國新聞業的影響也算久遠。20世紀初,在民族新聞業起步時期,一批報業人士在建立中國新聞學體系及其辦報實踐中,都多多少少沿用、借鑒甚至照搬過西方的新聞專業主義觀念。他們在當時動蕩不定的社會政治氛圍和救國救民成為時代主題的背景下,一方面從報業實踐中借鑒西方新聞專業主義,一方面高揚時代精神,其新聞專業主義精神體現出濃重的中國特色。
中國的新聞專業主義思想產生的背景迥異于西方。在民族新聞業發展過程中,一部分報人不滿足于將報業淪為政黨政治和政治宣傳附庸的狀態,開始反思報業定位問題,呼吁在客觀報道的基礎上建立獨立自主、職業化的新聞事業。中國以新聞為本位時代的序幕是由黃遠生拉開的,他主張新聞業擺脫政治羈絆,認為“從事新聞工作,一不是為謀職業生路以求安身立命;二不是追逐名利以求聞達于世;三不是百無聊賴暫以棲身,而是痛感中國政治之腐敗,人民苦難深重,愿為之奔走呼號,以求激勵民心,改善政治,改造國家和社會”。①《新聞界人物》編輯委員會編:《新聞界人物(1)》,新華出版社1983版,第36頁。新聞業者的職業意識、社會責任感與人文精神、時代聲音融為一體,這是中國新聞專業主義精神的內在要求。著名報人邵飄萍反對“有聞必錄”的傳統史書式報業模式,主張報業要體現現代新聞價值標準和選擇,引用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的警世之語,以勉勵其《京報》記者。如果說黃遠生、邵飄萍、徐寶璜、戈公振等新聞界先驅從理論上初步闡明了職業化報刊理念,并從實踐上作了初步嘗試的話,以張季鸞為代表的新記《大公報》人則可看作是廣泛實踐中國民族新聞業職業化的杰出代表。張季鸞在新記《大公報》續刊論評《本社同人之旨趣》一文中明確提出并系統闡明了“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主張,這也是張季鸞在政治立場、新聞言論、經營方針和報紙風格等方面對辦報思想的具體概括。①周雨:《大公報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頁。張季鸞的辦報思想,擺脫了康有為、梁啟超以來辦報者多以報紙為政治斗爭工具的傳統,以期保持辦報不受政爭的影響,將新聞專業主義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也是中國早期報人與西方新聞專業主義契合度最高的思想代表。在現代報刊發展過程中,新聞專業主義依然影響著中國新聞業的發展,鄒韜奮即為其中的代表。②從鄒韜奮的《人民的喉舌》一文中可以看出其作為現代報人的人民報刊理論和實踐思想,也深受新聞專業主義影響。
總體看來,新聞專業主義在中國新聞界產生的時間較晚,尤其是作為專用概念引入中國更晚。而且,黃遠生、邵飄萍等人的辦報思想,雖有受西方新聞專業主義影響之因素,但由于其社會背景及文化背景之不同,其內涵及意蘊亦頗不相同,其為民請命和兼濟天下的精神在境界上是高于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其中體現更多的是中國傳統士人堅持思想行為獨立的“士道”精神!實際上,新聞專業主義的早期影響主要局限于當時報界少量人士,產生的社會影響較小。與新聞專業主義相比,中國史學傳統與中國新聞界的淵源更深,影響也要大得多。
中國官報的歷史悠久,但中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新聞事業起步很晚,最早的近代報紙是由西方傳教士興辦的。由于新聞學與歷史學的內在邏輯聯系及中國發達的史學傳統,新聞報刊在中國發展之初,中國知識分子對新聞的認識與理解首先是從新聞與史學的契合開始的,產生了新聞與歷史同一說。近代闕名的《史學》一文稱:“泰西不立史館,蓋報館即其史館也。”并特別指出:“蓋今日之報章,即異日之史料。”③邵之棠:《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三·文教部三·史學》,文海出版有限公司(臺北)民國六十九年(1980年)版。其后,在中國近現代的新聞報刊事業發展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始終未斬斷將新聞學與中國傳統史學聯系在一起的文化情緣。隨著維新運動的開展,國內報業逐步發展起來,一些維新運動中的著名思想家,如譚嗣同、梁啟超等人,也認為二者具有相同或相似性。在中國現代報業發展過程中,仍有不少人堅持新聞、史學同源說,如李大釗、蔡元培等人。李大釗認為:“新聞是現在新的、活的社會狀況的寫真。歷史是過去、舊的社會狀況的寫真”④李大釗:《在北大新聞記者同志會成立會上的演說》,《新聞戰線》1980年第2期。。當時的報界人士不僅將新聞報學與史學精神和方法融為一體,在新聞實踐活動中也踐行這一理念。史量才曾提出“史家辦報”的思想,也認為報紙是“史家之別載,編年之一體”,“為修史者所取材”。“日報者,屬于史部……必評論之,剖析之,伴讀者懲前毖后,擇益而相從”。當時的《申報》就編過類似今日《年鑒》的各類冊子《申報月刊》、《申報年鑒》等。⑤徐培汀、裘正義:《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重慶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頁。新聞學與歷史學的聯系之密切,以至于今天新聞學界仍有將新聞學列入史學之支流的論斷,如新聞學界泰斗甘惜分先生到晚年仍堅持并多次論述新聞與歷史的同一論。如果說早期的新聞與史學關系更多的是從史料價值角度探索新聞與史學的關系,今天更多的學者和新聞業界專家則從新聞記者與史家職業道德、業務能力結構等操作層面探討新聞學與史學、新聞記者與史家之關系,足見二者聯系之密切,為我們從更深文化層次上探索二者之關聯提供了大量可資借鑒的資料和線索。
關于新聞與史學之關系,學界盡管有認識上的分歧,但對二者本質區別的認識上還是較為一致的。在本質完全不同的兩個事物上,中國人將新聞與史學聯系得如此緊密,在世界上是十分突出的,為什么會產生這種現象?僅僅從概念解讀的方式來分析是遠遠不夠的,既要從新聞學及新聞事業本身發展的角度考慮,更要從中國文化背景進行觀照。從文化角度而言,盡管中西方新聞專業主義有其職業共性方面的內容,但由于文化環境的差異,其內涵及表現方式有極大的不同,中國新聞專業主義對文化值的關懷和追求是遠遠高于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在中國的媒體文化生態系統中,新聞專業主義與其說是一種職業理想化的模式,不如說是中國文化傳統在現代新聞業中的映射。我們拋卻新聞學與歷史學的技術與操作層面的差異及學科之爭,從文化價值角度審視專業主義與史學傳統的關系,另有一番景象。
二、新聞專業主義與史學傳統文化內涵的一致性
新聞專業主義作為一套論述新聞實踐和新聞體制的話語系統,在職業實踐框架下闡述了媒體的社會功能、新聞從業者的角色及職業操守。新聞界通常將歷史學的時間拉近至當代史,將新聞記事追蹤至史學時段,并以此作為二者對接的契合點,這種觀點已經為大家所熟知,姑且不論。從文化價值觀念方面來看,二者具有高度的內在一致性。
真實是新聞的生命,追求真理是新聞的終極價值歸宿。關于新聞能否達到與客觀事實的完全統一問題歷來是新聞界爭論不休的話題,世界知名記者湯普森、莫耶斯等知名記者始終將新聞客觀性描述為一個神話,丹尼爾、布魯克等人則始終將客觀性作為新聞報道的基本要求來捍衛和堅守。盡管對客觀性的達成效度認識不同,但新聞對客觀真實性的價值追求是新聞的永恒話題和終極價值追求,這與中國史學傳統的價值追求是完全一致的。正如甘惜分先生所言:“客觀性和傾向性的統一,這是中外歷史學家公認而又爭論不休的重大原則問題,同時也是現代新聞學最困惑的間題之一。”①甘惜分:《再論新聞學與歷史學》,《新聞界》1996年第2期。
追求真實與真理的文化價值在中國史學傳統中源遠流長,史官忠于職守而秉筆直書的事例不勝枚數,最著名的當數《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的齊太史直書崔杼射殺齊莊公一事的故事:太史兄弟三人因“秉筆直書”先后被殺,但其后先后嗣書者仍堅持“實錄”其事,驕橫的崔杼最后不得不妥協。非獨有偶,《左傳·宣公二年》中記載了太史董狐堅持直書趙盾弒殺晉靈公一事。孔子著《春秋》,歷代史學家都稱頌其“善惡必書”的著史精神。司馬遷的《史記》更為人稱道,“其言直,其事核,不隱惡,不溢美”,將中國史學傳統的“實錄”手法和“秉筆直書”精神推向了一個高峰,成為中國史學優秀傳統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唐代著名的史學理論家劉知幾在他的《史通》一書中,大力提倡歷史“以實錄直書為貴”,“烈士循名,壯夫重氣,寧為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②劉知己:《史通·直書》,黃壽成校點,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頁。,將史學的“實錄”手法和“秉筆直書”精神提升到理論化水平,并成為中國傳統社會的主流文化價值觀念之一。
新聞盡管有報道、判斷、推理之寫作手法之區別,但與史學一樣,一切皆需以尊重客觀事實為基礎,任何虛構和主觀臆斷都是絕不允許的。新聞專業主義也將正確處理客觀性與傾向性的關系作為其主要內容,強調客觀性是第一位的,與史學的價值觀念和價值追求是一致的。中國新聞業長期無專業主義概念,但中國文化中的內在價值觀念中卻有與新聞專業主義一拍即合的精神,這也是中國早期新聞人士將史學與新聞相提并論的一個基本原因,在這一過程中,國人自覺不自覺地表現出的是新聞專業主義之文化觀。
新聞專業主義與史學傳統在社會責任與文化創造方面也表現出高度的一致性。從中國史學傳統來看,盡管有長期的政治“資鑒”和服務帝王將相的時代局限性,但絕沒有因此而掩蓋史學家在對客觀事實追求基礎上而堅守文化獨立性的光輝。中國傳統史學同時還具有反對依附于權威與政治的優良傳統,強調對事實負責,對社會負責。當然,這種文化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并沒有囿于史學一隅,而是彌散為中國傳統文化精神,是中國文化價值觀念的優秀傳統。從現代文化觀念來看,中國史學的這種悠久傳統也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終極價值追求,是中國古代文化自覺體系的重要表現。
史學家們一方面強調歷史是歷史事件的客觀記錄,必須真實、客觀和公正,達到主觀與客觀的統一,但另一方面,他們又不得不無可奈何地承認歷史是歷史學家寫的,而史家的立場、水平、思想傾向多種多樣,作為個人作品的歷史著作亦不可避免地帶有主觀傾向,歷史是由歷史學家制造的、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等說法就是這一思想的反映。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史家之主觀影響,在史學的編纂與敘事方法上,形成了“述而不作”傳統。“述而不作”語出孔子《論語·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意思是說,老彭這個人好述古事,孔子將自己比作老彭,說自己寫的《春秋》只是講述史事而已,沒有“作”,即沒有自己的創作。說得更通俗些,即不表達自己的觀點,只是“秉筆直書”歷史事實。盡管孔子所謂的“不作”原意是說自己議論國家禮儀制度資格,并非真正不“作”,但后世對于孔子提出的“述而不作”的涵義理解不盡相同,“述而不作”思想在中國文化中影響深遠,尤其在史學領域,進一步強化了早期史學傳統中“秉筆直書”的史學精神。
十分有趣的是,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對客觀性的追求與困惑在新聞專業主義發展過程中也遇到了。為了達成歷史記載與事實客觀性的統一,史學家在記錄事實時通過“述而不作”手法,形成了中國的史學敘事傳統。為了保證新聞的客觀公正,在新聞專業主義的影響下,新聞報道與敘事上“述而不作”的影響也是很明顯的。如果說史學家堅持“述而不作”是出于對史學主觀性的一種主動規避,新聞專業主義的“述而不作”則是為了擺脫影響新聞客觀性的社會現實的一種策略,其對立面是影響新聞報道的來自政府、黨派、財團及媒體自身利益的影響。盡管這兩種精神及其行為的動機與目的全然不同,然而其對事實客觀性的價值取向是一致的,這也是史學與新聞承擔社會責任的共同原則。
西方新聞專業主義并不是隨著新聞業的出現而出現的,是新聞業在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后才產生的,是與“職業化報刊樣式”和“新聞信息模式”相伴而出現的,是按照具體職業實踐層面構建起來的,具體體現在職業理念、職業態度、職業紀律和職業責任四個方面。新聞專業主義最早誕生于20世紀初的美國,是政黨報紙解體后基于“公共服務”信念而在新聞界發展起來的。其突出特點是相信媒介可以持獨立立場進行客觀的事實報道,并以此監督政府。其目標是使新聞服務于全體人民,而不是隸屬、依附某一利益集團。
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文化載體與產生背景不同,但從文化價值觀看,與中國史學精神的文化價值追求是完全一致的。當然,二者的區別也是很明顯的,西方新聞專業主義更多是從形而下的現實操作層面出發的,其關注的是新聞事業的現實問題。而中國古代史學“實錄”與“秉筆直書”文化傳統既有忠于事實的現實意義,更多的則是忠于文化理想,更為突出的特色是文化價值觀念和人文精神。因此中國史學傳統的文化精神和社會責任感與新聞專業主義相比,具有更深層次的意義,就其文化意義而言又是高于新聞專業主義的。
三、新聞專業主義中國化必須立足中國文化與社會現實
新聞專業主義概念在20世紀80年代傳入中國后,再次成為新聞界的熱議話題。新聞專業主義能夠在中國落地生根,能否成為推動中國新聞業發展的推動力等問題,如何更好地推動新聞專業主義中國化,使其義為我們的新聞事業服務,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要研究課題。
在新聞業快速發展的過程中,面對政治利益及經濟利益的誘惑和壓力,新聞界及傳播者普遍感覺到堅持新聞專業主義理念或真正實現新聞專業主義理想是難以實現的。近年來,隨著席卷全球的媒介兼并浪潮的逐步高漲,新聞客觀性和獨立性原則不斷受到侵蝕,新聞專業主義的價值觀念引起學者們的反思,正如丹尼爾·哈林所言:“很清楚,現代主義高峰期的專業主義,已經不再可取了,它需要在重要方面被重新思考。”①[加]羅伯特·哈克特、趙月枝:《維系民主?西方政治與新聞客觀性》,沈薈、周雨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74-175頁。近來發生的《世界新聞報》“竊聽丑聞”事件在新聞界再次引發軒然大波起,新聞專業主義神話再次被粉碎。
中國學者對西方傳入的新聞專業主義的態度也有很大分歧,不少學者持排斥或批判態度。如浙江大學徐亮教授堅持認為:“新聞專業主義只能是一個相對性理念,并不能免除對某些語言技術和某些類型文本的偏向,試圖以此慮構一種純粹的客觀新聞理想,就可能掩蓋另一些真相。因此,新聞專業主義決不能越界而成為普遍真理”②徐亮:《新聞文本的文學性與新聞專業主義的相對性》,《新聞與傳播研究》2008年第2期,第54-59頁。。僅從語言及敘事方面來看,這種認識是很深刻的。然而,這種觀點是僅僅就新聞實踐的具體操作層面而言的,我們不能以此否定新聞專業主義的精神價值。這些學者的觀點都是從新聞專業主義的消極面出發來進行闡釋的,都存在一個共同的立足點,即都是從新聞專業主義自身所蘊含的從業者職業定位的角度來進行,其結論并不能令人滿意。朱清河、張榮華在對國內新聞專業主義研究情況的基礎上進行了總結,將國內學界的觀點歸納為四種偏向:其一,專業化的技術挪用,抽離為新聞表達、制作的技術;其二,將專業化轉換為政治立場的判斷;其三,專業化“拿來”以后的本土化堅持;其四,專業化的普適價值教育。③朱 清河、張榮華:《新聞專業主義理論與實踐的中國近觀——兼論社會轉型期新聞專業主義的價值旨歸》,《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
在不同的社會和政治制度和新聞產業體制下,僅從職業道德和職業規范方面達成中西方新聞界共同認可的新聞專業主義明確不變的定義和標準是不現實的。研究這一問題,必須在西方新聞專業主義中國化路徑中進行解讀與闡釋。從精神文化和價值觀念層面上看,新聞專業主義完全可以突破其載體和技術層面的苑囿。美國威斯康辛-麥迪遜大學傳播系教授潘忠黨認為,新聞專業主義遠遠超過了職業的基本社會學特征。④陸嘩、潘忠黨:《成名的想象: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聞從業者的專業主義話語建構》,《新聞學研究》(臺)第71期(2002年4月),第20頁。潘忠黨為我們研究新聞專業主義進一步拓寬了思路,我們要在從更深層次上研究新聞專業主義問題,也唯有如此,才能為中國新聞專業主義的落地生根提供新的思路。
不管在西方還是在中國,也不管是新聞從業者自我認同的職業道德,還是官方所倡導的外部職業道德,兩者要想發揮效用,必須得共同作用于新聞從業者的精神文化心理層次之上,從文化價值觀的角度進行透視和建設。在此層面上,新聞專業主義在中國落地生根不僅是現實的,也是我們必須大力改造和發展的。
首先,新聞專業主義與中國文化傳統有高度一致的契合性,特別是與中國古代史學傳統精神內在價值觀念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其具有在中國落地生根的文化基礎。我們暫且拋開操作層面的問題,以真實、公正、客觀為核心立場的新聞專業主義精神,與中國傳統史學的“實錄”手法和“秉筆直書”精神具有文化價值觀念的高度契合性和內在一致性,二者具有嫁接的文化基礎。而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史學是影響中國文化傳統最深刻的學科之一,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說:“中國于各種學問中,惟史學最為發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惟中國最發達”。英國著名學者、著名漢學家李約瑟在《中國科技史》中也認為,中國的“科學之王”既不是神學,也不是物理,而是歷史。因此,通過史學傳統這一文化接口,西方新聞專業主義可以實現在中國落地生根,為我所用。
其次,西方新聞專業主義必須經過中國文化的改造才能真正為我所用。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產生于新聞事業尤其是報業大眾化時期,有其獨特的背景,在其發展過程中,往往被西方新聞商業模式運作所淹沒,沒有積極健康地向上發展,始終囿于新聞職業規范領域,沒有升華到精神和文化層面。而中國的新聞媒體發展,無論是從政治環境還是從文化背景上,都與西方全然不同,來自西方的新聞專業主義理念有與中國新聞業發展環境不適應的一些方面,完全照搬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概念和技術規范,不僅不能落地生根,還會遭到來自環境的排異。對此,要從兩個方面進行改造。一是在中國新聞體制環境下,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指導,從新聞實踐和操作技術層面進行改造,使其能夠成為我國新聞從業者的職業規范。二是從深層次的文化層面進行系統改造,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嫁接到新聞專業主義,構建中國特色的新聞專業。無論我們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如何,其構建的文化結構及文化價值觀點都是我們無法規避的現實環境。也唯有如此,才能將客觀、公正、真實等新聞價值觀念內化為新聞從業者的職業道德。
在中國政治與市場條件下,新聞從業人員的自覺和自律很容易遭受現實壓力的裹挾,新聞的人文屬性被經濟屬性所淹沒,從而形成新聞專業主義理想與新聞現實之間的背離。從中國新聞業發展情況看,一方面是新聞業的快速發展,一方面是日益突出的媒體公信力不斷呈現下降趨勢。誕生于西方新聞事業發展過程中的新聞專業主義精神,無論是從解決我們新聞業發展中的深層次問題,還是從今天的廣大新聞工作者的現實操作層面,都有其積極的意義,我們不能因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局限性而一味排斥之,對其進行改造和利用,是中國新聞業發展的迫切需要。尤其是在中國目前文化狀況及文化產業體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新聞專業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無疑對改進我們的新聞工作提供了職業規范框架和豐富的精神食糧。我們應該以客觀的態度對西方新聞專業主義在中國的落地機制開展積極研究,既要從職業操作層面進行借鑒和利用,更要立足中國新聞業發展實際,借助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對其進行深層次嫁接和改造,達到事半功倍之效。也唯有如此,才能夠將新聞專業主義提升到更高、更深的文化精神層面,使其真正成為推動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動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