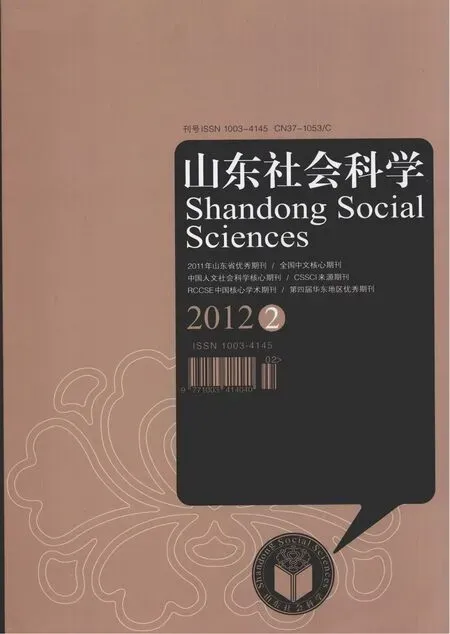現代化與民族認同的沖突與融合
——以幾部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為例
孫俊杰
(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山東濟南 250100)
現代化與民族認同的沖突與融合
——以幾部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為例
孫俊杰
(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山東濟南 250100)
現代化一方面是新時期改革開放以來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另一方面,它與構建我們民族認同的傳統文化又往往處于矛盾沖突之中。這種矛盾沖突造成了知識分子心理上的兩種焦慮:現代化的焦慮與民族認同的焦慮。這兩方面在不同題材的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中有著不同的表現。概括說,作家在改革文學中更多地表達了現代化的焦慮,并呈現出與傳統文化融合的認識趨向;而鄉村小說更多地附加了民族認同的情感。這使改革與鄉村的文學空間承載著不同的文化價值取向。
現代化;民族認同;改革文學;鄉村小說
現代化和民族認同問題是從中國近代以來一直延續至今的文化命題。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90年代的國學熱,追根溯源,除了政治、經濟、文化的因素,從精神層面來看,可以說它凸顯了知識分子心理上這樣的兩種焦慮:現代化的焦慮和民族認同的焦慮。一方面,新時期的改革開放,使我們再一次看到了與西方國家相比自身落后的狀況和危機,認識到現代化的迫切性,更明確地將工業經濟的發展、“四個現代化”的實現作為社會發展的目標;而另一方面,現代化與構建我們自我身份認同和民族認同的傳統文化又往往處于矛盾沖突之中。
民族認同感必然來自于在共同的民族歷史中承傳下來的傳統文化,其中主要是儒家文化,它的審美趣味、價值觀念、道德規范、思維方式、風俗習性等在幾千年的承傳過程中早已沉潛為我們的無意識,內化為一個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對民族文化的認同與對民族精神的體認,是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的深層基礎,它是中華民族認同的精神基石,也是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必不可少的要素。”①俞祖華:《近代國際視野下基于中華一體的民族認同、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人文雜志》2011年第1期。也正基于此,“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問題乃是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和90年代的國學熱的焦點,其他一切文化與文化史問題的討論都是以這一問題為中軸而展開的”②邵漢明主編:《中國文化研究二十年》,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2頁。。作家們以其創作參與著對這一問題的思考。由此,我們通過幾部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和認識,既可以看到伴隨現代化進程作家對傳統文化認識的不斷深化,也可見出由于文化立場的不同,作家以不同的題材空間承載的不同文化價值取向。
一、改革進程中對傳統文化認識的深化
最突出地表現了現代化在中國新時期的進程及其帶來的美好前景的莫過于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中幾部改革題材的長篇小說。無論《沉重的翅膀》、《都市風流》、《騷動之秋》、《抉擇》還是《英雄時代》、《湖光山色》,它們都與社會生活同步,反映了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曲折和必然性。其中,《沉重的翅膀》和《英雄時代》是兩個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文本。這種代表性就在于它們對傳統文化的表現和態度,映現了作家在與社會文化環境的相互促進中,對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化之間深刻關聯認識的不斷深化。
張潔的《沉重的翅膀》是反映新時期改革開放、中國進行史無前例的現代化建設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作家以磅礴的激情寫出了改革初始新與舊、文明與愚昧、改革與守舊、解放與僵化的種種沖突,在根本上演繹的是傳統文化對于現代化的阻滯力。柳建偉的《英雄時代》書寫的則是黨的十五大前后的社會、經濟、政治狀況。此時,市場經濟尚未健全,隨著現代化的發展,社會出現了很多新的問題:國企虧損,下崗,貧富差距,私營經濟成為富有活力的一支力量,其中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矛盾,它更多地看到了傳統文化中的優質因素對于現代化的補益作用。我們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除了借鑒西方現代化的有益經驗,也必然要汲取傳統文化中的精華作為現代化的精神基石,這是《英雄時代》中表現出的文化取向。《沉重的翅膀》中的鄭子云和《英雄時代》中的史天雄作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代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他們矢志不渝的目標。由于處于不同的改革階段,在他們身上充分體現出了中國現代化的時代特色,這種時代特色表現在,他們所面臨的生存困境、精神困境、文化困境與情感倫理困境已經有了根本的不同。
在《沉重的翅膀》中,現代化首先是經濟的現代化,提高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擺脫貧困、吃大鍋飯的狀態是彼時最緊迫的任務。作品通過“小”字輩的激情與活力,通過老一輩如李瑞林等人的思想轉變展現了現代化強大的感召力和歷史必然性。鄭子云作為“改革派的一個亡命徒”,面對的最大阻力就是傳統文化惰性造成的反對改革的僵化、守舊的觀念,如小說中所說的“鄭子云的對手早就有了,那便是這個社會里,雖說是殘存的、卻萬萬不可等閑視之的舊意識”。我們看到傳統文化中的“政治文化”對田守誠等人的深刻影響,他為保權、保位子,處心積慮,小心翼翼,無所作為,不敢作為,見風使舵,八面玲瓏;看到了傳統文化中的群體意識形成的反改革的“圈子”,他們視支持改革的人為異類而加以排擠。作為現代化代表的鄭子云,作家在描寫他與反改革派進行斗爭時,也寫出了他自身承襲的傳統倫理道德的重負,以及這種重負對他精神造成的戕害和痛苦。這一點主要表現在他的婚姻生活上。他雖然是個現代化的先鋒,卻沒有勇氣掙脫與妻子夏竹筠的沒有愛的婚姻,只能維持著虛無的“模范家庭”的稱號。雖然在小說中,作家也著力表現了鄭子云的憂患意識、擔當意識,寫了普通工人、群眾之間的友愛互助等傳統優秀品質,但在根本上,作品所傾力揭示的,依然是傳統文化對現代化的那種深重的阻滯力量,甚至作家在塑造這些人物的優秀品質時,也很難說從理性上意識到了它們和傳統文化有什么關聯。
時代發展到90年代后期,《英雄時代》中史天雄在其改革的探索過程中,已經不必去承受傳統婚姻倫理的枷鎖。小說中的主要矛盾沖突來自于他和陸承偉之間,這是以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品質——以國家集體的利益為重、奉獻的精神、仁愛的精神為精神基石的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之間的矛盾。陸承偉最后的自我救贖則表現了對民族文化精神的某種皈依。
在史天雄所探索的以馬克思主義信仰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道路的過程中,傳統文化的優秀品質成為他所秉持的重要精神價值。首先,史天雄本人是一個極富儒家文化精神品質的人。他和鄭子云一樣具有憂患意識、擔當意識、責任意識。王傳志說他“身在江湖,心系廟堂”的話語里雖然透著一絲涼意,卻也是對史天雄的一種懇切評價。“國家利益”是他一切行為的準則,無論是初始的想挽救紅太陽集團、加盟“都得利”,還是最終聽從黨的安排去領導合并后的紅太陽和天宇,他從未考慮絲毫個人的得失。史天雄所領導的“都得利”集團,作為他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一個樣板,也是充滿了仁愛精神的團體。它最初的創立就是為下崗工人提供一個再就業的機會,在這個集團里,不僅全體員工真心地為抗洪救災捐款,而且作為個人,還有王小麗、楊世光、江榕、毛小妹等人充滿純樸“仁義”精神的作為。“都得利”體現著一種集體的精神、一種“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精神,正如它的經營理念:“與全市人民共渡難關”。如果說,這就是史天雄所探尋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應具有的現代精神品質,那么這種現代精神品質是不是可以稱為儒家文化傳統在當代的傳承呢?
這種精神品質在《英雄時代》中可以說是作家有意加以表現的,這從史天雄對陸承業與陸承偉的不同態度即可見出。史天雄雖然對陸承業的頑固、剛愎自負以及家企同構觀念進行了批判,卻借梅豐之口對他以國有資產為重、不推卸責任的國家意識、奉獻意識表達了敬意。而作為史天雄主要的對手,陸承偉可說是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代表。陸承偉曾在美國哈佛工商學院讀MBA,受到西方的教育,回國后投身商界,“在美國學到了務實精神”,也接受了美國的價值觀念、道德倫理觀念。《英雄時代》中展示了陸承偉所代表的西方現代化對社會所造成的危害,如個人利益至上、金錢至上造成的道德墮落、自私自利、無國家意識,為私利挖社會主義墻角。這種現代化與史天雄所領導的“都得利”集團的價值信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種對比更顯示出對傳統文化中優秀價值品質的認同,也是對構成中國特色的民族文化的認同。
從《沉重的翅膀》到《英雄時代》,從單純的現代化建設到尋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勾畫出改革者篳路藍縷、不斷探索的改革實踐,既是現實的社會發展,也傳遞著對于傳統文化的再反思、再認識。
二、鄉村小說對傳統文化的流連和困惑
總體來看,在改革文學中,現代化具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尤其是在《沉重的翅膀》等80年代的改革題材的小說中。這與當時文化啟蒙者二元思維的影響有關,也就是把傳統與現代作為兩個對立的因素,西方現代的是改革的方向,值得肯定;中國傳統的則是保守的,應該否定。改革文學中所設置的改革者與保守勢力的矛盾沖突,就是在這種二元思維的制約下形成的。改革文學是以現代化作為總體價值旨歸,以之觀照傳統文化,取我所需,而一切阻礙現代化發展的都被毫不留情地批判和拋棄。他們的主人公精神靈魂的力量足夠強大、信仰足夠堅定,在現代化生活所展現的五光十色之中才不會自我迷失。鄭子云和史天雄及其他改革領導人物從來沒有過猶疑、徘徊,沒有過靈魂的上下求索,他們所做的只是站在現代化的基點上,認準了方向,向前、向前。然而,對于更多的普通人,現代化在帶給人豐富充裕的物質生活的同時,也使人感受到目迷五色的炫惑,傳統的維系精神家園的價值體系在現代化的沖擊下四分五裂,喪失終極意義,連同我們的民族認同的迷惑。于是,我們又到歷史中去追尋、去挖掘,在現實中仔細辨認那些構筑我們精神心靈的根系。鄉土、鄉村或者民間成為靈魂漂泊的最后錨地。
陳忠實的《白鹿原》和賈平凹的《秦腔》便是這樣的兩個文本。《白鹿原》問世于1993年,我們當然無法忘懷此時文化界對于傳統文化的各種再認識、再思考的成果。“與‘尋根’文學一樣,它也體現了發掘傳統資源以探求民族精神、重續文化命脈的努力:而與‘尋根’文學否定‘中原規范’的傾向不同,它要尋求的恰恰是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原規范’中隱藏的生命活力。”①張林杰:《〈白鹿原〉:歷史與道德的悖論》,《人文雜志》2000年第1期。《秦腔》是賈平凹有感于自己無奈的離根體驗,曾經魂牽夢繞的淳樸的故鄉的人與事、風土人情在現代化風卷殘葉般的進程中都已難覓其蹤,通過對傳統鄉土文化衰落過程中的各種現象的藝術把握為傳統文化譜寫的一曲挽歌。
如果敘事視角部分地決定了作家對于事件的態度和認識,講故事的方式也暗含了對故事的闡釋,那么,我們近乎可以說,改革文學是以現代化的視角來書寫的社會進程,因此更多地看到了傳統文化對于現代化的阻滯因素,而現代化是光明與美好的一種現實許諾。《白鹿原》和《秦腔》則更多地傾向于傳統文化的角度,書寫了傳統文化在現代化擠壓下的衰落、困惑以及它頑強的生命力。由于這種角度的不同、文化立場的不同,《白鹿原》與《秦腔》所看取的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都呈現出與改革文學中不同的另一番情景。對農業文明中的傳統倫理感情、對人際關系中脈脈含情的一面表現出更多的熱情,對于現代化,雖然理性上認識到它的必然趨勢,卻更多地傾向于它所帶來的弊端的書寫。
《白鹿原》和《秦腔》都書寫了儒家文化傳統所濡染的精神人格魅力。
《白鹿原》中貫穿始終并集聚了作家最多情感的人物白嘉軒,作為儒家文化傳統在民間民眾中的體現者,是儒家文化人格的化身,真誠地信仰并恪守儒家的行為規范準則。他以傳統宗法制度治理白鹿原,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等“三綱五常”組織家族世俗生活、規范行為、凝聚人心、解決爭端,擔負起為家族謀利益的責任。考察白嘉軒一生所為,修祠堂,辦學堂,為防白狼筑堡墻,刻《鄉約》,策動“交農”,率眾求雨,“刺刷”小娥和孝文,修鎮妖塔以及勇于承擔責任,多次以德報怨營救“仇人”(黑娃、鹿子霖及鬧農協時曾傷害過他的那些人等),體現了儒家文化傳統中重義輕利、仁愛謙恭、注重修身治家等傳統道德人格。正是這種人格力量使“白的一身,仿佛濃縮了的民族精神進化史的象征,他的頑健表明,封建社會維系幾千年之秘密,就在于有像他這樣的棟梁和柱石的支撐”②雷達:《一九九三年的“長篇現象”》,《當代作家評論》1994年第1期。。作家對于白嘉軒無疑傾注了深厚的愛敬感情。其他如朱先生是“白鹿原最好的一個先生”,黑娃對傳統文化的皈依等都表現了作家對傳統文化的認同與傾心。
同樣,《秦腔》通過引生的視角與講述也表達了賈平凹對儒家文化傳統的代表人物夏天義、夏天智及白雪等人的向往和愛。夏天義和夏天智是引生最為尊敬的兩個人,他們身上有著白嘉軒和朱先生的影子。他們都是執著于傳統耕讀文化的人,夏天義對土地的熱愛最突出地表現了傳統耕讀文化中人與土地的關系。雖然在夏天義和夏天智身上多了現代社會的因素。如夏天義把黨、集體、國家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夏天智也已不可能是私塾先生或者如朱先生置周圍的紛爭于身外,而是一個小學校長。但這種外在的現代因素并沒有改變他們在內在的思想情感、道德倫理方面的傳統文化特征。他們注重自身德性的完善,對于村人都表現出一種“仁義”之心:如夏天義的清廉自守、熱心村務,夏天智以其德望熱心解決鄰里家庭糾紛、樂善好施、資助貧困的學生上學、對病中的秦安給予關心與安慰。同時,他們還極為注重家庭倫理關系。夏天義與夏天智幾個兄弟妯娌之間一直其樂融融、相互幫扶,呈現著傳統家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這些都是傳統耕讀文化所孕育的道德倫理。這種道德倫理在現代鄉村無序的底色上顯得尤為可親與珍貴,而引生對于白雪的癡愛更是表現了他對傳統文化的那種精神皈依。
如果說《白鹿原》有意識地表現了儒家文化的生命活力的話,那么《秦腔》中“矛盾和痛苦”、“迷惘和辛酸”的復雜情感,則來自于賈平凹對傳統人倫情理和人格的流連,看到了它們在現代化的進程中不可避免地成為記憶中的陳跡。作者看到現代化在滿足著人們的物質需求、帶給鄉村新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同時,也在丟棄傳統文化中美好的東西。在引生所述說的清風街的生離死別、喜怒哀樂、吃喝拉撒睡中,幾乎沒有使人快慰的事,被人看做“十全十美”的婚姻中,有的只是不和諧、隔膜、爭吵,最后分手;唯一的新生,帶來的卻并非歡欣而是痛苦;能夠記起一年中發生的五大“惡”的案件,卻沒有述說一件喜樂之事。這種對事件的選擇本身就已表明了對現代化的立場、觀點和態度。
然而,無論白嘉軒所代表的傳統儒家文化具有怎樣使人敬慕或贊揚的品質,具有怎樣的凝聚力和生命活力,它卻始終處于歷史現代化進程的邊緣狀態,沒有成為歷史發展的動力。無論是鬧農協、國共合作、抗日戰爭,還是中國內戰,所有這些歷史的大事件對于白嘉軒并沒有產生什么影響,他所采取的都是一種“反身而誠求于己”的內斂、冷眼旁觀的姿態。甚至他也從未產生朱先生那樣的抗日情緒。他懲罰異己的方式更多地是將他們驅逐出去,卻不能夠審時度勢,使自身更具包容性。那么它的凝聚力和生命活力又體現在哪些方面呢?在歷史進程中又具有怎樣的作用呢?如果它并不能推動歷史的發展,那就必然被歷史和人民所淘汰。如雷達所說:“陳忠實《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場和價值觀念是充滿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贊賞;既在鞭撻,又在挽悼;他既看到傳統文化是現代文明的路障,又對傳統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戀不舍。”①雷達:《廢墟上的精魂》,《文學評論》1993年第6期。
同樣的困惑也表現在《秦腔》之中。“人是土命,土地是不虧人的,只要你下了功夫肯定會回報的”,但這種回報卻沒能使人擺脫貧窮,夏天義對現代化的拒絕與阻礙行為遭到了子孫輩的抱怨。當慶金只能賣血給父親治病、瞎瞎因無錢上交稅款被抓走時,夏天義的幾個兒子之間為了贍養老人而不斷發生的矛盾爭吵、錙銖必較,也許并非完全是道德的滑坡,更是緣于經濟的貧困。極度的貧困使人心胸狹隘、情感變異。夏天義與夏天智的“仁義”行為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現實的問題。如果“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牧民》),那么,“實”與“足”需要現代化,而現代化帶來的物質豐富卻并沒有必然地附帶著人情物理的美好,卻似乎是不可避免地帶來欲望的無限膨脹……如同年三十的團聚這一最具家族認同之感的傳統風俗,在后輩眼中也已失去了意義一樣,現代化以不可阻擋之勢在沖擊著傳統文化,消彌著民族認同的根基。
這種困惑矛盾正是由于作家無法找到解決現代化與民族認同之間矛盾的一種外在表現。
三、兩種題材小說不同的文化承載
改革小說中的現代化具有無可爭辯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它所表現的改革是激情的、振奮的、向上的,是全民投入的。在其中,大多數主人公都充滿了一種內心的躁動,很少有對日常生活瑣事的精雕細刻和品味。這種躁動是一種時代的情緒,驅使他們去把握機遇、拼搏進取,最大限度實現生命的價值,推動社會歷史的發展進步。因為改革正是民族強大的社會需求,可以說,改革小說最為充分地表現了作家的也是民族的現代化的焦慮。
而現代化焦慮和民族認同的焦慮必然內在地糾纏在一起。現代化依憑其強勢的西方文化和國家意識形態,使得中國傳統文化與它的對話一直處于不平等的狀態。西方文化以及現代化的現實需要一方面映照出傳統文化的諸多弊端,一方面又對形成我們民族文化—心理的傳統倫理道德、固有價值體系產生了巨大沖擊。以人為中心的啟蒙理性在重現人的價值、尊嚴之時,也給人的精神信仰帶來了危機,追求物質的享受給人帶來舒適也造成人與自然的失衡,拜金主義使社會道德墮落,工業社會的政治、經濟、科學文化以及人們的欲望都經歷了脫胎換骨式的轉變。面對這種社會現實,知識分子不能不問:構建我們精神、情感、心理,綿延幾千年的文化傳統該何去何從。賈平凹說:“在社會巨變時期,城市如果出現不好的東西,我還能回到家鄉去,那里好像是一塊凈土,但現在我不能回去了,回去后發現農村里發生的事情還不如城市。我的心情非常矛盾”,“這種現狀,就讓人想回家,卻回不去了”。①賈平凹、郜元寶:《關于〈秦腔〉和鄉土文化的對話》,郜元寶、張冉冉編:《賈平凹研究資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頁。精神上的無家可歸之感,正是曾經賴以安身立命的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面前無可挽回的衰落造成自我身份迷失的表現。
我們的傳統文化與鄉村有著天然的本質的聯系。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進行現代化建設之前,中國一直是一個農業大國。“鄉土中國”的概念隨著費孝通先生《鄉土中國生育制度》一書的出版,成為對中國傳統社會文化性質的一種經典概括。鄉土不僅指向幾千年來中國絕大多數人口賴以生存的環境,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農業本位思想和家族意識外化的精神坐標。在這片廣褒的鄉土上,誕生了中國古老而燦爛輝煌的人類文明。天人合一、農業本位、家族意識、仁義禮智信……它的核心觀念對于整合社會秩序、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我的關系起到了至為重要的作用,使得中華文明一直綿延下來。它曾經是我們的驕傲,曾幾何時,又被看做現代化的羈縻負累。而鄉土,作為誕生古老文明的母親,對于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卻始終具有“原鄉”的性質,是割不斷的根、擺不脫的夢魅。正如白嘉軒所說:“無論是誰,只要生在原上,他就得返回原上來。”盡管白孝文認為:“誰走不出這原誰一輩子都沒出息”,“回來是另外一碼事”,回來即意味著“原”在心底的存在,因為它所攜帶的文化是人們身份認同的憑依,它不僅使人更深地認識自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也認識到自身的歸屬——民族與國家。
正是因為這種鄉土所孕育的傳統文化是我們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是靈魂的“錨地”,是自我身份認同的依據,作家將民族認同與現代化的矛盾沖突突出地表現在鄉土文學敘事之中。
我們在《白鹿原》與《秦腔》中看到了這種沖突,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更借少數民族的山林文化,以山林文化與現代化相對照,以年屆九旬、鄂溫克民族最后一位酋長女人的講述,更為明顯地表現了現代化和民族認同的雙重焦慮。對這個民族歷史的回顧,也是對民族文化的審視和反思。眾多的死亡故事,嚴寒、瘟疫、猛獸侵害下舉步唯艱的傳統生活方式,舒緩而深情的講述、偏執的固守之間的矛盾張力彰顯的是現代化的合理性與民族認同的需求之間難以兩全的價值評價懸置,為了民族更好地生存,需要進行現代化,而現代化卻使傳統民族文化更趨式微,依蓮娜徘徊往返于城市與山林之間、痛苦與迷惘地游走于現代與民族文化之間、最終導致自殺的悲劇更顯示了這種雙重焦慮的無法偏至。
在潛在的現代化坐標中,作家對鄉村所代表的鄉土文化、傳統文化的追慕、批判或者哀悼,是民族認同的精神需要,更是作家在建設現代化進程中對本民族特性的反思和對其優質一面的弘揚,承擔著“舊邦”如何更好地“維新”的現實思考。“舊邦維新”暗合了民族認同與現代化的融合。
當白嘉軒充滿信心地宣稱:“無論是誰,只要生在原上,他就得返回原上來。”他又怎么可能意識到孝文的返回更是一種反叛者的挑戰呢。當孝文成了社會的主角,運用計謀將早已皈依儒家傳統、立志“學為好人”的黑娃押上歷史的審判臺并槍決時,白嘉軒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傳統與文化人格也被現代化宣判了死刑。而代表儒家傳統道德理想人格的朱先生與逃離封建家庭進行革命的白靈同樣都是白鹿精靈的啟示,是否又表現了作家認為只有將傳統儒家的優質因素與現代化的優秀品質相結合,才會產生真正的代表幸福、祥和的白鹿精魂呢?夏風與白雪所生的女孩具有先天的殘疾,必須經過大的手術才能夠成為一個正常人,也讓人想到傳統文化的美好因素能夠被現代化吸收、融合從而產生一個現代的“寧馨兒”還需要一個艱難的過程。夏天義和夏天智死去了,傳統文化似乎已隨著它的代表人物的死去而土崩瓦解,但毀滅也意味著新生。引生等待夏風回來,這又使人生出了一種期望。當夏風再次歸來概括自己父輩一生的是非功過,無疑就是一種對傳統文化再思考、再認識的過程,也許在這個過程中,他能夠對傳統的父輩更多一些“溫情的敬意”,更多地體認到父輩身上閃光的品格,體認到自己與腳下這塊土地傳承下來的傳統文化永遠無法割斷的精神聯系。
I206
A
1003-4145[2012]02-0089-05
2011-11-30
孫俊杰(1973—),女,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山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師。
(責任編輯:陸曉芳sdluxiaofa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