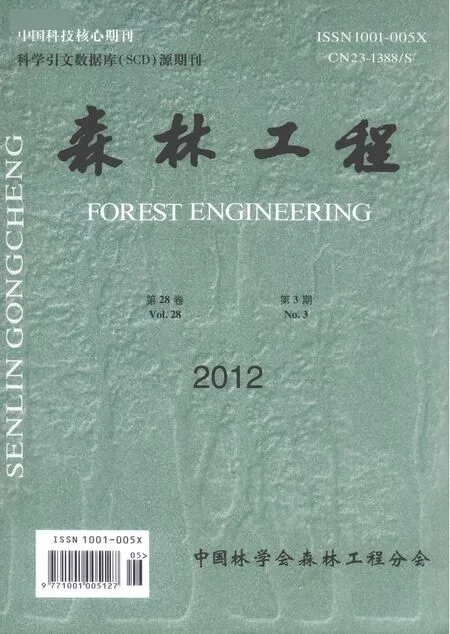浙江東陽木雕和黑龍江木雕特色比較研究
許雪梅,程 巖,張耀華
(黑龍江生態工程職業學院,哈爾濱150025)
木雕藝術以其特有的質感表達著溫和、質樸和神秘,是我國古老的特色工藝,是我國民間藝術的一種。木雕在我國的歷史源遠流長,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文明,并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到清代達到高峰,至今在許多古城里仍然保留著相當數量的木雕傳世精品[1]。隨著文化的發展、經濟的繁榮,這一古老的藝術形式又呈現出勃勃生機,在國人的生活中,承擔著實用、熏陶、 “成教化助人倫”的功能,融入人們的生活,影響著民族的性格,美化著人們的生活。
隨著對木雕藝術的關注越來越多,發現地方風格差異明顯,本文對東陽木雕和黑龍江木雕兩者之間風格的自然環境、社會文化等做了比較研究。
1 浙江東陽木雕分析
我國傳統四大名雕有浙江東陽木雕、廣東金漆木雕 (潮州木雕)、溫州黃楊木雕和福建龍眼木雕,東陽木雕為四大名雕之首,與蘇繡,石雕、磚雕、灰塑等藝術形式并稱為浙江民間文化藝術的瑰寶。2010年課題組成員南下浙江,在蘇杭一帶對以東陽木雕為代表的木雕藝術進行了一番考察,親眼見識了古建筑中的精美木雕和現代的一些木雕精品,感受工匠們的技藝之精湛。同時對東陽木雕的題材、風格和文化內涵進行了一番研究性學習。
1.1 題材特色
題材包括自然風光、建筑、歷史人物、動植物、經典故事、神話傳說和吉祥圖案,只要民間百姓喜聞樂見的內容都被當作雕刻題材。
(1)自然風光。江浙一帶的自然風光自古就是沒有爭議的美,“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道出了生活在蘇杭一帶人民的自豪感,湖光山色,奇花異草,旖旎的自然風光自然不光是畫家、詩人描繪和歌詠的對象,當然也反映在木雕作品中,經木雕藝人提煉、抽象、概括和夸張變形后再現的自然景觀更具有美感和藝術的感染力。
(2)建筑。杭州古民居受文化傳統和優美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響,形成獨具一格的以木結構為主的建筑風格。古民居以規模宏偉、結構合理、布局協調、風格清新典雅,亭臺樓榭、粉墻黛瓦、高脊飛檐、曲徑回廊和層樓疊院為典型特征,建筑是木雕裝飾的主體,尤其是裝飾在門罩、梁柱、窗楣、窗扇、牛腿和挑頭上的木雕,工藝精湛,造型逼真,栩栩如生。建筑更是木雕表現的主題。木雕作品中小橋流水、花窗洞門,表達著人在畫中游的境界。
(3)歷史人物。歷朝歷代造就了層出不窮的歷史人物,帝王將相、文人墨客、英雄豪杰、名士高人,如吳王錢穆、岳飛、蘇軾、白居易、張蒼水、于謙、阮元、胡雪巖、夏衍、梁實秋、蓋叫天、秋瑾、茅以升、郁達夫、李叔同、魯迅、茅盾、吳昌碩和徐志摩等。厚重的歷史積淀不僅為木雕創作提供了不盡的素材,更成為吳越大地上浩然正氣和永恒的精神傳承。
(4)動物。青龍、玄武、朱雀、白虎、游龍、鸞鳳、麒麟、仙鶴、喜鵲、獅和鹿等祥禽瑞獸為題材,這些圖案不僅造型夸張、生動活潑、栩栩如生、姿態各異、趣味盎然,更多的是將現實中的動物神話、理想化,承載了精神文化內涵,是一些信仰的標志和象征,成為了民族的圖騰。
(5)植物。西湖邊的奇花異草以及梅蘭竹菊、松柏、荷花等題材,經過藝術的提煉加工形成一定的圖案化、程式化,表現著文人化的審美取向。
(6)經典故事。民間流傳的歷史典故和傳統故事,比如“唐伯虎點秋香”、“西廂記”、“貍貓換太子” “劉備招親”、“二十四孝”和“忠孝節義”等,這些內容都反映了人們對愛情、善良、正義、公平的追求和對邪惡、霸權的憎惡。
(7)神話傳說。“布袋和尚得道”、“八仙過海” “、白蛇傳說”、 “豬八戒娶親”、 “秋翁遇仙”、“麻姑獻壽”等優美的神話傳說反映儒家禮教、道家風骨和佛家教義。
(8)吉祥圖案。反映主人的吉祥如意、財源廣進、人丁興旺和健康長壽等美好愿望的吉祥圖案。如“喜鵲登梅”、 “馬上封侯”、: “五福捧壽”、“早生貴子” “歡天喜地”、 “招財進寶”、“福壽雙全””等以諧音、比擬、象征和寓意等手法,體現了當地的民俗風情和審美習慣。
(9)抽象圖案。萬字、方勝、如意、回紋、水波紋、火紋、云紋、鎖紋、冰裂紋、八寶博古等抽象紋飾以重復的形式無限延展,形成了抽象的富有節奏變化的韻律之美。表現出民族文化的精神特質。
(10)詩文。以詩詞歌賦為內容,結合金石、書法等藝術形式,以楹聯匾額的形式,表現文人化典雅的審美取向。
(11)宗教信仰。宗教題材,大多是圓雕,主要是佛教、道教以及民間的一些信仰的造像,還有附屬的陳設品。如神仙、羅漢、菩薩、達摩、八仙、彌勒佛、觀音、羅漢和媽祖等。
1.2 風格特色
蘇杭地區吳越大地,自古就是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中心,是一個物華天寶、人杰地靈、文化昌盛、經濟繁榮而又充滿生機活力的古府新市,融中國特色的藝術形式書法、繪畫、詩歌、戲劇等與雕刻藝術中,使這一地區的木雕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和濃郁的文化氣息,厚重的歷史感和人文蘊涵[2]。
東陽木雕的圖案造型繁雜細膩,采用了適當夸張變形的裝飾手法,使木雕具有極強的裝飾意味,所表現的內容受儒家文化的思想的影響,整體上呈現出謙和、內斂又超凡脫俗的藝術風格。木雕的題材多運用諧音、比擬、象征和寓意手法突出反映人們的日常生活、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倫理道德和祈望,造型夸張、變化突出內在精神的表達。作品多采用了中國傳統的散點式構圖,往往忽略正常的比例關系以突出主題。運用散點透視的構圖,把不同的時間空間里的物體組合在一起,形成豐富多彩的內容。以某種圖案為元素構成單獨紋樣、適合紋樣或二方連續、四方連續紋樣的形式,形成了統一又變化、或對或稱均衡的富有節奏變化的韻律之美。
1.3 文化特色
文化蘊涵上,杭州人民風優雅、文明、禮貌、聰慧、勤勞、精明,儒家文化底蘊深厚,儒家文化在木雕中明顯的體現出儒家思想的最精髓的中庸哲學。崇尚“多子多福,長命百歲”,崇尚教育,追求心目中的“小康盛世”,張揚孔孟之道,一直以來,在浙江社會中,都流淌著豐富的文人情懷,書卷氣息氤氳,而崇尚田園生活、隱居生活也是文人氣質的鮮明符號,這種思想在木雕作品中也有所反映,表現文人雅士對高品質生活的追求。
2 黑龍江省木雕的現狀及特色
當前黑龍江打造文化強省,確定了邊疆文化大省的文化產業發展戰略,木雕作為文化的載體彰顯著不同地域的審美意識、民俗風情和文化蘊涵,有著較高的藝術價值[3]。如何傳承古老的木雕藝術,如何打造黑龍江特色的木雕文化品牌,如何打造具有黑龍江特色的木雕風格,既是每一位致力于龍江木雕事業的設計師需要思考的命題,又是難得的歷史機遇和使命。
2.1 現狀
東北木雕是中國著名的民間工藝品之一,距今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東北木雕以椴木、樺木為主要原料,經雕刻技師精雕細刻而成,具有造型獨特美觀、形象生動質樸等特點。但是較之中原和江南發達地區,北方木雕發展明顯滯后。20世紀90年代的木拼畫、薄木貼畫曾經流行一時,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出現曇花一現的狀況,整體未形成產業。隨著旅游大省的發展,相應的文化產品、旅游產品發展嚴重滯后。可喜的是,近年來隨著打造黑龍江文化產業大省的倡導,隨著哈博會等文化藝術平臺的繁榮,不斷涌現出一些極有濃郁北方特色的木雕藝術作品和木雕藝術家,如翟孟義的系列民俗木雕作品、孫先軍的“環保雕塑”等。
2.2 特色
(1)獨特的地域風貌。民國之前黑龍江省的自然條件自古的印象是十分惡劣,氣候酷寒,人煙稀少,人稱“絕域”,所以統治者把這里作為流放地。但是,近年來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現代城市的發展,集中供熱使得昔日的苦寒之地室內溫暖如春,物流發達,四季蔬菜供應充足,當人們不再畏懼嚴寒重新審視自然的時候,分明的四季、美麗的雪花、大山大水、大片的森林、大片的草原、廣袤的田野、大片的濕地、湖泊、火山和油田這一切都是那么具有特色的美,獨特的蒼涼、雄壯的自然環境養育了龍江人的豪爽、大氣、熱情和幽默的性格,這一切都給黑龍江木雕提供了鮮活的創作素材和獨特的文化氣質。
(2)題材特色。很多木雕反應濃郁的鄉土生活氣息,采用適當夸張變形的手法表現農民的形象、生活場景、勞動場面和風土人情[4]。
表現“林海雪原”的自然景觀;表現北方動植物,如熊、狐貍、狼、鹿、野兔、松鼠、家禽和北方地區的山花野卉,代表作品有金蟾、木雕熊、木雕馬、木雕狼、木雕公雞、木雕駝鹿、木雕豬、木雕雄獅、木雕老虎、木雕十二生肖和木雕小鳥等。
少數名族風情、俄羅斯風情、大移民和抗日等題材都有所表現。
(3)風格特色。①造型粗狂大氣,充滿個性的雕塑手法,夸張的表現形式,完全不受拘束的藝術手段,作品鄉土氣息濃郁、生活氣息濃郁,反應北方人民豪爽、質樸、熱情和樂觀的性格特征以及原始蒼涼的地域風貌[4]。②天然的材質美。北方木雕就地取材,以椴木、樺木、板皮、角料、廢料、密度板和原木等為材料,質地純樸、自然紋理富于天趣,賦予了北方木雕天然的材質美感。在北方木雕中,分著色木雕和原色木雕,著色木雕以翟孟義的系列民俗重彩木雕作品為代表,原色的以孫先軍的“環保木雕”為代表,另外在黑龍江木雕發展衍生出板皮雕,樺樹皮雕,薄木貼畫等形式保留了木材本身的自然形態特征,作品整體呈現出樸質、生動的印象,讓人產生一種溫馨的自然情懷。
2.3 文化特色
多民族文化、邊疆文化、異域文化、移民文化、流人文化和抗日文化,碰撞出具有包容性的多元文化,更多表現為自由、粗獷、蒼涼、原始、自然、溫厚,同時又有洋氣、艷麗等文化特色。
3 結束語
通過對浙江東陽木雕和黑龍江木雕兩者在題材特色、風格特色和文化特色等方面的比較,發現兩者都各具特色,但從當前行業發展狀態對比中黑龍江的發展明顯滯后,黑龍江木雕地域風格明顯、新穎獨特,觀之令人耳目一新,但是在藝術的創造、工藝的開發以及產品的應用等方面還有待發展和提高,產業也尚未形成規模,藝術家們大都單打獨斗、自產自銷,應該借鑒東陽木雕在發展中取得成功的經驗教訓來大力開發具有黑龍江特色的木雕產品,保護扶持相關產業,對于促進區域經濟發展、提升龍江文化水平有積極意義。
[1]葉柏風.木雕——鏤琢纖巧[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
[2]馬時雍.胡雪巖故居[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3.
[3]那明君,李元強,劉中原.手動仿形雕刻機的設計[J].森林工程,2009,25(5):37-39.
[4]付國榮.黑龍江文化的基本構成與深層結構[J].邊疆經濟與文化,2004(3):106-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