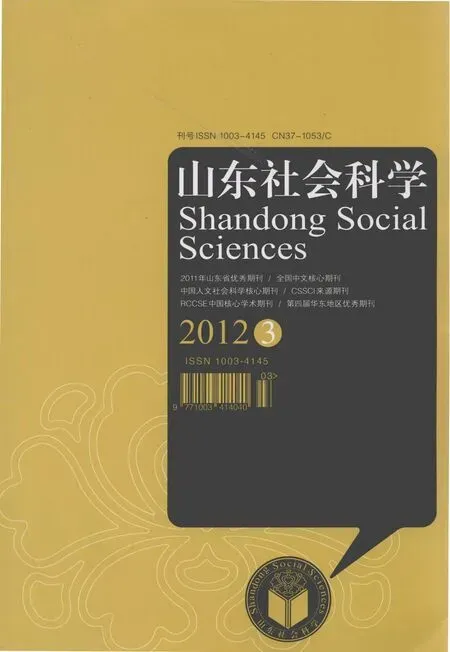論吉登斯、哈維、卡斯特對現代社會的時空診斷
牛俊偉 劉懷玉
(南京大學 哲學系,江蘇 南京 210093)
論吉登斯、哈維、卡斯特對現代社會的時空診斷
牛俊偉 劉懷玉
(南京大學 哲學系,江蘇 南京 210093)
辨識和判斷現代社會的基本性質是當代社會理論的核心問題。其中,時間和空間是眾多理論家進行社會診斷的基本工具。吉登斯的時空伸延理論、哈維的時空壓縮理論以及卡斯特的流動空間與無時間之時間理論,對時空問題在當代社會理論中凸顯的原因、時空問題在社會理論中的作用以及時空與社會的互動等相關問題進行了思考,對我們準確把握現代社會有所助益。
社會;時空診斷;時空伸延;時空壓縮;流動空間;無時間之時間
我們所處的時代正處于激烈的變動時期,為了能夠有效回應當今世界發展難題,對現代社會進行深刻反思并作出診斷就成為眾多有學術良知的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以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戴維·哈維(David Harvey)以及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為代表的一批學者,以時空問題作為切入點對當代社會展開診斷,在眾說紛紜的西方學術版圖中顯得格外引人注目。
一、吉登斯的時空伸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理論
吉登斯對現代社會的基本判斷是:“我們實際上并沒有邁進一個所謂的后現代性時期,而是正在進入這樣一個階段,在其中現代性的后果比從前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劇烈化更加普遍化了。”①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15頁。他將其稱之為“高度現代性時期”,而這個高度現代性的社會則是一個充滿風險的社會。那么,吉登斯是如何進行診斷的呢?
首先,時空分離導致前現代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巨大斷裂。吉登斯在社會歷史觀上明確反對線性的歷史進化論,認為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都存在著斷裂,而他特別關注與現代時期有關的特殊斷裂。在他看來,“現代世界是從和以往的世界所發生的斷裂中誕生的,而不是后者的延續”,②安東尼·吉登斯:《社會的構成》,李康等譯,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55頁。這種斷裂不僅變遷速度快、范圍廣,更重要的是社會生活史無前例的質的發展,完全把我們拋離了前現代社會秩序的軌道,在外延和內涵兩個方面引起的變革超過以往任何時代。這種巨大的斷裂和時間——空間的轉換密切相關。在前現代社會,時間與空間無法分離,“‘什么時候’一般總是與‘什么地方’相聯系,或者是由有規律的自然現象來加以區別”,③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15頁。而空間總是和地點(place)相一致,在大多數情況下都由人們實實在在的社會活動場所來規定。在這樣的時空矩陣中,前現代社會表現出強烈的地域性色彩。機械鐘的發明使得時間從空間中分離出來,時間標準化的同時也使時間虛化了,而航海圖的制定也使空間從地點中分化出來,空間的在場性為缺場性所破壞,空間也虛化了。這樣,由于人類經歷的時空維度被置于一個分離的想象的柵格里,社會關系得以自由重組,前現代社會的地域局限性就讓位于現代社會的世界歷史性了。這就是吉登斯所謂的“現代性的斷裂”。
其次,時空分離與重組構成了現代性的動力機制。吉登斯的社會時空思想在其思想體系中具有基礎性、根本性的重要地位,既是其社會理論的一個重要特色,也是其社會理論中的基本方法論。吉登斯認為:“現代性的動力機制派生于時間和空間的分離和它們在形式上的重新組合,正是這種重新組合使得社會生活出現了精確的時間——空間的‘分區制’,導致了社會體系(一種與包含在時空分離中的要素密切聯系的現象)的脫域(disembedding);并且通過影響個體和團體行動的知識的不斷輸入,來對社會關系進行反思性定序與再定序。”①②⑤⑥⑦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7、56-57、56、56頁。這集中體現了吉登斯對現代性為何在20世紀晚期會激進擴張的動力來源的診斷。他認為時間和空間的分離首先構成了時空無限伸延的條件,從而使社會行動得以從地域化情境中“提取出來”即“脫域”,并跨越廣闊的時間和空間距離重新組織社會關系。而脫域過程主要依賴象征標志和專家系統這兩種機制。脫域機制的發展使得知識的反思性運用成為常規,即關于社會生活的系統性知識的生產本身成為社會系統之再生產的內在組成部分,使得人類活動無論是日常的個人行為如開燈、駕車等還是集體行動如地區、國家甚至全球層面上的政治、經濟、文化活動,均依賴于非個人化的科學知識和社會規則,這些知識和規則均超越了個人直接的生理經驗,從而使社會生活從傳統的恒定性束縛中游離出來。正是通過對現代性的動力機制的揭示,吉登斯給出了現代社會的病理學診斷:現代社會是一個充滿高度風險性的社會,人類“猶如置身于朝向四方急馳狂奔的不可駕馭的力量之中,而不是像處于一輛被小心翼翼控制并熟練地駕駛著的小車中”,②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7、56-57、56、56頁。即現代性高度擴張又難以駕馭。
最后,時空伸延彰顯了全球化過程的本質。全球化是當今時代的最顯著特征,也是最莫衷一是的學術難題。吉登斯認為,全球化的內容“無論如何也不僅僅是甚至主要不是關于經濟上的相互依賴,而是我們生活中的時空巨變”。③安東尼·吉登斯:《第三條道路》,鄭戈譯,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33頁。吉登斯反對把全球化等同于經濟的全球化,認為“全球化的概念最好被理解為時空伸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基本方面的表達。……我們應該依據時空伸延和地方性環境以及地方性活動的漫長的變遷之間不斷發展的關系,來把握現代性的全球性蔓延”。④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趙旭東等譯,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3頁。因此,他給全球化下的定義是:“世界范圍內的社會關系的強化,這種關系以這樣一種方式將彼此相距遙遠的地域連接起來,即此地所發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許多英里以外的異地事件引起,反之亦然。”⑤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7、56-57、56、56頁。他同時也認為,全球化的內在原因在于現代社會變遷的動力,“現代性正在內在地經歷著全球化的過程,這在現代制度的大多數基本特性方面,特別是在這些制度的脫域與反思方面,表現得很明顯”。⑥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7、56-57、56、56頁。也就是說,時空伸延、脫域和知識性反思同樣也是全球化的內在動力。所謂時空伸延是指社會系統在時間與空間上的擴展程度和水平,正是它不斷把現場卷入(共同在場的環境)和跨距離的互動(在場和缺場的連接)之間的關節鑿通,從而使社會關系從彼此互動的地域性關聯中,從通過對不確定的時間的無限穿越而被重構的關聯中脫域出來,使社會活動和社會組織得以依靠非個人化的知識的反思性運用在全球層面上運作,從而構成了全球化的新的社會存在形式。正因為全球化以現代性的動力為動力,所以全球化實際上就是現代性的全球化。吉登斯對全球化的本質作了深刻的揭示:“在現代,時空伸延的水平比任何一個前現代時期都要高得多,發生在此地和異地的社會形式和事件之間的關系都相應地‘延伸開來’。不同的社會情境或不同的地域之間的連接方式,成了跨越作為整體的地表的全球性網絡,就此而論,全球化本質上是指這個延伸過程。”⑦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7、56-57、56、56頁。
總之,吉登斯以時空伸延的獨特理論視角把我們所處的社會診斷為一個充滿風險又難以駕馭的現代性社會,這個社會與前現代社會存在著巨大斷裂,而且正在高度擴張,但這并不意味著出現了新的斷裂,后現代性社會尚未變成現實。
二、哈維的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理論
哈維對當代社會的基本判斷是:“1972年前后以來,文化實踐與政治——經濟實踐中出現了一種劇烈的變化,這種劇烈的變化與我們體驗空間和時間的新的主導方式的出現有著密切關系。……然而,在與資本主義積累的基本規律進行對照時,這些變化在表面上顯得更像是轉移,而不是某種全新的后資本主義社會甚或后工業社會出現的征兆。”⑧戴維·哈維:《后現代的狀況》,閻嘉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頁。那么,哈維又是如何診斷的呢?
首先,時空壓縮是20世紀后半葉后現代主義崛起的直接原因。哈維認為,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出現了空前激烈的時空壓縮,導致社會政治和私人領域以及公共領域出現大量即時的和碎片化的時間,這意味著一個特殊的后現代時代的來臨。所謂時空壓縮,哈維意指“那些把空間和時間的客觀品質革命化了、以至于我們被迫、有時是用相當激進的方式來改變我們將世界呈現給自己的方式的各種過程”,①②③④⑤戴維·哈維:《后現代的狀況》,閻嘉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300、63、63、300、410頁。而后現代主義正是這樣一種呈現世界的激進方式。哈維對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在建筑、繪畫、電影、廣告、文學、語言、哲學等方面橫空出世的后現代主義作了詳盡考察,發現在眾聲喧嘩的背后,后現代主義共同的特點是偏愛“異質性和差異”、“分裂和不確定性”并將其推到極致,它不像現代主義那樣企圖“透過流變追求永恒”,相反卻只是在“分裂和混亂的變化潮流中游泳,甚至顛簸,似乎那就是存在的一切”,②戴維·哈維:《后現代的狀況》,閻嘉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300、63、63、300、410頁。也就是以迅速流動與變化包裹起來的絕對多數和難以琢磨的文化形式表達了分裂和短暫,從而凸顯了整個世界在時間維度上的崩潰和空間維度上的陷縮,因而是一種文化情感上的獨特體驗。
其次,20世紀后半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變是后現代主義崛起的深層基礎。既然后現代主義僅僅是人們在時空壓縮的條件下發生的一種“情感結構中的深刻的轉移”,那么就有必要對這種情感轉移的社會基礎進行探究。哈維從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出發,強調資本永無休止的流通和不斷尋求獲取利潤的新方法是導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始終處于革新和變動中的根本原因。哈維通過對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的細微考察,發現20世紀6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發生了一次顯著而深刻的轉折,即從福特主義向靈活積累體制的轉變。萌生于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并在1945年以后全面確立統治地位的福特主義,它是以大規模生產、大量消費和國家干預為特征的剛性積累模式,對于維持戰后資本主義世界的長期穩定和繁榮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在1965年到1973年間,福特主義的固有局限性開始越來越明顯地顯現出來,哈維用“刻板”一詞來概括,表現為大規模生產體系內固定投資刻板,阻礙了計劃的彈性和消費市場的穩定增長。同時,這種刻板也體現在就業和勞動力市場上,以財政為基礎的政府亦深受生產刻板的掣肘,特別是由1973年石油危機引發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衰退,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陷入滯漲的漩渦中,迫使新一輪的經濟重建和社會生活方面一系列新奇實驗開始實施,一種全新的“靈活積累體制”出現并日益成熟,它以更加靈活的勞動過程和市場地理上的流動性和消費實踐中的各種迅速變化為特征,使資本主義重新煥發出生機與活力。哈維認為,這種從福特主義向彈性積累的轉變是全面、復雜和深刻的,“資本更加靈活的流動突出了現代生活的新穎、轉瞬即逝、短暫、變動不居和偶然意外,而不是在福特主義之下牢固樹立起來的更加穩定的價值觀”。③戴維·哈維:《后現代的狀況》,閻嘉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300、63、63、300、410頁。換言之,正是20世紀晚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巨大變化,構成了后現代主義理論的深刻基礎。
最后,時空壓縮是后現代主義文化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關聯的中介。哈維認為,現代主義向后現代主義的文化轉變,與資本主義經濟由福特主義向更為靈活的資本主義積累方式的政治經濟轉變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二者的重要的中介就是所謂的“時空壓縮”。在哈維看來,時間與空間概念是社會地建構起來的,它們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并且會隨著社會政治——經濟體系實踐的變化而一同變化。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改變,社會再生產的物質實踐活動也發生改變,結果必然是空間和時間可能表達的客觀品質和意義也發生改變。而人們對變化著的時間和空間的體驗,又必然會在文化層面有所反映。福特主義向靈活積累的轉變,實質是通過時空轉移來解決資本過度積累危機的過程。時間轉換是通過加快周轉時間,以靈活多變、可以迅速收回投資的生產取代長期固定資本投資的生產計劃,通過縮短決策時間以迎合當下不斷變化的消費需求,大力開拓未來的消費市場。空間轉換是指通過地緣的擴展來吸收過剩的資本和勞動力,不僅空間界限逐漸消失,而且空間變得更具流動性和不平衡性。生產方式上的這種轉變,反過來強化了“時空壓縮”。時空壓縮在現代社會的加速極具破壞性,“對時空壓縮的體驗是挑戰性的、令人興奮的、緊張的、有時是使人深深憂慮的,因此能引起多種多樣的社會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反響”,④戴維·哈維:《后現代的狀況》,閻嘉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300、63、63、300、410頁。各種文化力量對混亂與不穩定時空狀態的激進解釋成為可能,于是就造成了這樣一種結果:“對時間與空間的體驗已經改變,對科學判斷與道德判斷之間的聯系的信念已經崩潰,美學戰勝倫理學成了社會和知識關注的主要焦點,形象支配了敘事,短暫性和分裂的地位在永恒真理與統一的政治之上,解釋已經從物質與政治經濟學的基礎領域轉向了思考自主的文化和政治實踐。”⑤戴維·哈維:《后現代的狀況》,閻嘉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300、63、63、300、410頁。簡言之,企圖在流變中追求永恒的現代主義受到了以分裂、短暫和不確定性為特征的后現代主義的有力挑戰。
總之,哈維以時空壓縮為中介把后現代主義置于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變的社會背景下加以診斷,揭示了后現代主義的出現是一種對某種形式的“盛期的現代主義”的反叛,本質上屬于文化層面的轉移,而非整個經濟社會秩序層面的根本躍遷。
三、卡斯特的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和無時間之時間(timeless time)理論
卡斯特對當代社會也有一個基本的判斷:人類社會正經歷著一場以信息處理和溝通技術為核心的信息技術革命,它使社會再結構化,“作為一種歷史趨勢,信息時代的支配性功能與過程日益以網絡組織起來。網絡建構了我們社會的新社會形態,而網絡化的邏輯的擴散實質地改變了生產、經驗、權力與文化過程中的操作和結果”,①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569、23、505、571頁。一種新的社會形態和新的社會模式正在形成,即網絡社會的浮現。那么,卡斯特又是如何診斷的呢?
首先,生產方式和發展模式的相互作用是產生新的社會、空間類型、發展進程的源泉。卡斯特認為:“社會是由一種包括生產方式、發展模式、經濟、能源和文化的錯綜復雜的網絡及它們的具體歷史關系所組成的。”②曼紐爾·卡斯泰爾:《信息化城市》,崔保國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頁。生產方式由社會生產關系定義,而發展方式由技術關系定義,二者存在著密切的相互作用,一方面,發展方式是在產品生產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不斷融合、相互作用的基礎上形成的,這些過程依賴于整個社會組織特別是動態的生產方式;另一方面,發展方式根據其自身邏輯也在變化,它并非機械地響應生產方式或其他社會因素的要求,而是和經濟、能源、文化一起構筑自己的結構領域并支配社會利益。當歷史條件使社會變革和技術變革具有相同點時,生產方式與發展方式的實際互動就能帶來重大的社會歷史變遷。
其次,信息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深度契合建構了新的社會形態。在卡斯特看來,最具決定性的歷史因素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逐步推進的信息主義再結構過程,它加速、引導與塑造了信息主義發展方式,其特征是以信息處理為核心、以彈性網絡為組織基礎、以效能整合為基本功能、以服務而非產品為主要形態,它的效果無處不在,人類存在的所有過程無不為它所塑造。至關重要的是,信息主義發展方式的擴散正好發生于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資本主義全球再結構的歷史時期,這并非偶然,相反它恰恰是這次再結構不可或缺的工具。二戰后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帶來將近30年持續繁榮的資本主義增長的凱恩斯模型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受到其內部限制的沉重打擊,主要表現就是難以遏制的滯脹危機。因此,從80年代開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進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重組和再結構過程中,這個過程致力于解除管制、私有化并解除使先前增長模型得以穩固不動的勞資間的社會契約。卡斯特將這次重組概括為四個主要目標:“在勞資關系中深化資本主義追求利潤的邏輯;提高勞動與資本的生產力;生產、流通與市場的全球化,捕捉每個地方最優越的利潤創造條件的機會;以及糾結與引導國家的支持,以增加生產力和經濟競爭力,但這經常會損及社會保護與公共利益管制。”③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569、23、505、571頁。卡斯特認為,技術創新與組織變動,集中于彈性和適應性,是確保再結構的速度與效率的絕對關鍵要素,而信息主義發展方式正好為其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質支撐和技術手段。在信息技術的基礎上,生產中由社會和空間決定的關系被轉化為信息流,為新的靈活的生產與管理體系的相互聯系提供了組織基礎,技術革命本身的發展和展現,為先進資本主義的邏輯和利益所塑造,信息主義和資本主義在一個技術經濟的重組過程中歷史性地融合在了一起,新的社會形式和新的空間變化從這個歷史性的融合中產生了。
最后,新社會形態是圍繞流動空間而組織起來的網絡社會。卡斯特把由信息主義的再結構與資本主義的重組之間的歷史性融合所建構出來的社會形態界定為“網絡社會”。其中,資本、管理與信息通過各種節點以網絡的形式連接起來成為一個高度動態和開放的社會系統。卡斯特認為,網絡社會是“環繞著各種流動——例如資本流動,信息流動,技術流動,組織性互動的流動,影像、聲音和象征的流動——而構建起來的”,流動不僅是社會組織里的一個要素,它還支配了經濟、政治與文化的活動過程。而作為社會實踐的物質支撐的空間是支撐這種流動的,因此是“流動的空間”,而“流動的空間”借由混亂事件的相繼次序使事件同時并存,從而消解了時間使其成為“無時間之時間”,將社會設定為永恒的瞬間。因此,流動空間是“通過流動而運作的共享時間之社會實踐的物質組織”,而共享時間之社會實踐則是“空間把在同一時間里并存的實踐聚攏起來”,這就解釋了社會活動不依靠物理上的臨近的那種同時性也有其存在可能的原因,而這正是網絡社會的支配性活動。④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569、23、505、571頁。在環繞流動空間和無時間之時間組織起來的網絡社會中,社會生產關系不再是一種實際存在,資本進入了單純循環的多維空間,勞動力則由一個集中的實體變為差別極大的個體存在。卡斯特特別強調,“管理與生產朝向網絡形式的演變,并非意味著資本主義的消亡。有各種不同制度性表現的網絡社會,此際還是資本主義社會。猶有進者,這是歷史上第一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塑造了整個地球的社會關系”,⑤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569、23、505、571頁。因為它是全球性的并且在相當程度上是圍繞著金融流動網絡而結構,資本四處流動,而其所導致的生產——管理——分配活動則散布于多變幾何形勢里相互連接的網絡之中,血肉之軀的資本家及其群體為無面目的資本后設網絡所代替,巨大的風險隱藏于全球電腦屏幕上股指變化的閃爍之中。
總之,卡斯特以信息技術與資本主義雙向重構為經,以流動空間與無時間之時間對地方空間和時鐘時間的支配為緯,把全球化中的社會形態診斷為一個正在浮現的“網絡社會”。
四、幾點反思
面對現代社會的劇烈變動,包括吉登斯、哈維和卡斯特在內的許多學者都不約而同聚焦于社會與時空的關系問題,把時空作為診斷社會基本性質的獨特視角,這絕非偶然,當有許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首先,為何在社會診斷的問題上都突出了時空問題?無論是吉登斯把現代社會判定為高度的現代性,還是哈維把后現代主義判定為文化現象,抑或是卡斯特對網絡新社會的超前反映,雖然分別使用了“時空伸延”、“時空壓縮”和“流動空間與無時間之時間”的不同術語,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時空都成為了判斷社會基本結構變遷與否的基準點。實際上,這并非只是他們三人的標新立異。今天,強調社會生活的時空向度、考量時空與社會的互動關系,以及主張時空在建構社會理論時據有核心位置,似乎成了標榜先進的社會理論的必備條件。究其緣由,這既是對傳統的絕對的自然時空觀的現代反撥,也是對現代生產方式引起的人類生活節奏快速變動和地理景觀大尺度變化的理論上的集中反映。
傳統上,時間和空間一直被視為是外在于社會現象的自然事實,具有客觀自證性,空間被視為一個靜止的“容器”,時間則是勻速流逝的“梭子”,它們都是客觀而宏觀的人類生活的背景性存在。20世紀,愛因斯坦相對論對牛頓經典力學的超越鼓舞和啟發了社會科學對時間和空間問題的重新思考。這些思考集中于對時間和空間的社會意義以及社會時間和社會空間的研究上。
就吉登斯而言,他批評了傳統上人們僅僅關注時空的物理意義,不假思索地把時間和空間看做是可以測量的鐘表時間和有確定地理位置的地點,也反對以往大多數的社會分析將時空視為人類行動的環境和社會活動的外部因素,反過來特別強調時空的社會意義,認為“時空關系是社會系統的構成性特征,它既深嵌于最為穩定的社會生活中,也包含于最為極端或者最為激進的變化模式中”,①安東尼·吉登斯:《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批判》,郭忠華譯,譯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頁。時空特性由此成為他建構社會理論的核心。就哈維而言,他同樣挑戰了把時空當做是獨立于社會物質過程的單一而客觀的自然事實的傳統觀念,明確地把時間和空間看做是社會力量資源,強調“時間和空間的客觀概念必定是通過服務于社會生活再生產的物質實踐活動與過程而被創造出來”,②戴維·哈維:《后現代的狀況》,閻嘉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55、309頁。“如果空間和時間是對各種社會關系進行編碼和再生產的話,那么對前者進行表達的方式的變化幾乎肯定會引起后者的某種變化”。③戴維·哈維:《后現代的狀況》,閻嘉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55、309頁。就卡斯特而言,他也明確地強調,“我分析的焦點是空間與時間的社會意義。但我提及這種復雜性并非只是在修辭上賣弄學問。這種復雜性提請我們考察時間與空間的社會形式,指出它們不能夠簡化為迄今我們所感知到的東西,因為那奠基于已經被當前的歷史經驗超越的社會——技術結構”。所以,在社會理論里,時空必須參照社會實踐而加以定義,“空間是一個物質產物,相關于其他物質產物——包括人類——而牽涉于‘歷史地’決定的社會關系之中,而這些社會關系賦予空間形式、功能和社會意義”,當然時間同樣如此。④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466頁。卡斯特不僅強調時空的社會意義,更重要的是,卡斯特所謂的流動空間乃是人類首次創造出來的技術空間,它已完全超越自然而進入人工再生階段,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空間。
總而言之,正是由于對傳統的自然時空觀的局限性進行了深刻反思,并就時空內在于社會,對社會行動、社會生活和社會過程具有重要意義達成了一般性共識,時空特性因此才凸顯出來成為人文社會科學認識社會的重要維度,尤其是對社會發展的研究更是如此。當然,這種理論上的反撥其深刻根源還在于現代人類社會實踐的深刻變革,無論就實踐的水平、范圍、方式,還是實踐的深度和廣度、效果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時間被擠壓,“現在就是全部”,社會生活節奏加快,社會情勢瞬息萬變;空間被延伸,“世界進入我們的視線,世界呈現給我們”,地理景觀在全球尺度上碎裂和重組;流動、斷裂、短暫、非連續成為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控制時間和空間成為獲取支配性利益的必要手段,時空不再游離于社會的邊緣而是內爆于社會的核心。因此,時空問題就突出出來成為人們把握現代社會的重要紐結。
其次,為何同樣以時空診斷社會卻得出了不同的結論?盡管吉登斯、哈維和卡斯特在時空的社會意義方面達成了基本的共識,但時空在構建其各自的社會理論中的地位卻是不一樣的。
對吉登斯而言,社會理論所要關注的最基本問題,不是像傳統社會學那樣指向社會秩序的問題,而是把對秩序的探討變為社會體系如何把時間和空間連接起來的問題,“秩序問題應該被看成是時間——空間伸延的問題,即:在什么條件下時間和空間被組織起來,并連接在場和缺場的?”,目的是把社會從關注于“有界限的實體”中解放出來。①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6頁。在吉登斯那里,時間帶有根本性,因為“統一時間是控制空間的基礎”,②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6頁。因此,以時間的延展性及其同空間的遭遇作為基本點去把脈各種社會制度,就成為吉登斯社會理論的基本原則。具體來說,吉登斯把時間和空間看做是社會結構變遷的動力機制,正是時間和空間的分離并在形式上重新組合所導致的脫域機制和知識的反思性應用,才使現代社會從傳統社會的恒定性束縛中擺脫出來,成為一個“馬力巨大而又失控的引擎”,到目前為止我們還尚未脫離現代性的制度而步入后現代之中。吉登斯把社會時間和社會空間概念作為建構社會理論的核心,把時空伸延引入社會發展的動力機制,富于啟發意義,正如赫爾德所評價的,“吉登斯可能是最關注時空問題對社會理論的關鍵作用的人,他有關時空對社會理論的關鍵作用的看法為分析社會生活中的一些最為重要的特征提供了分析工具”。③田啟波:《吉登斯現代社會變遷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頁。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時空結構雖然是構成社會現實的因素,但它本身并不能單獨存在,特別是不能脫離人的活動而存在,否則就會因為用單一的時空機制解釋社會而削弱其本身的說服力,正如羅森伯格對吉登斯所作的批評那樣,“因此,無論從哪一端來說,新的社會學理論的時空問題都將證明是處在一種持續的和不可避免的內向爆炸狀態中。在它的正面,它向外延伸以構建關于世界的堅實解釋,這些解釋因為缺乏人類社會內容而趨于崩潰……。”④賈斯廷·羅森伯格:《質疑全球化理論》,洪霞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頁。
與吉登斯直接從時空變化分析社會不同,哈維是以資本積累的邏輯來掌握社會,他也不像吉登斯那樣把時間凌駕于空間之上,而是把空間一并提升到和時間一樣重要的位置上。空間、時間和貨幣(資本)一樣,是具體的抽象,在資本主義社會,正是金錢、時間和空間的相互控制成為資本積累的重要機制,而且最終引起了人們文化情感的巨大變化。因此,在哈維那里,時間和空間以及時空壓縮是社會整體動態的邏輯的要素、中介,“它向前延伸可以從資本積累模式中尋找其社會經濟基礎,堅持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向后延伸可以表現為后現代的各種文化樣態,保持了與各種后現代主義話語的溝通”。⑤章仁彪、李春敏:《大衛·哈維的新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探析》,《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
卡斯特面對當前資本主義全球再結構的趨勢,辨認出信息主義發展方式下流動空間的邏輯為關鍵現象,是空間組織了時間,而空間本身則無定形、無邊界、即生即滅、自然流動。在卡斯特那里,一方面,“空間與時間是人類生活的根本物質向度”,⑥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466、504、562頁。它構成了網絡社會的物質支撐;另一方面,“空間是社會的表現(expression)”,⑦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466、504、562頁。既為整體社會結構的動態所塑造,也再現了這個動態過程。總之,空間和時間不過是社會整體的存在的基礎和特殊面向,這成為卡斯特建構整個資本主義社會變遷理論的重要環節。盡管卡斯特批評了哈維在對當前社會經濟——文化轉變過程的分析中“賦予了資本主義邏輯過多的責任”,⑧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466、504、562頁。并一再辯解自己與技術決定論極為不同,但實際上,在時空與社會的關系上,仍然擺脫不了技術至上的嫌疑,雖強調了時空是社會的存在基礎和物質表現以及社會時空的重大意義,但忽視了時空對社會建構的作用,因而具有非辯證的傾向。
最后,時空與社會到底是怎樣的關系?吉登斯把時空伸延視為現代性的動力機制,將現代社會診斷為高度現代性的社會,哈維則以時空壓縮為中介將后現代主義與資本積累方式相關聯,診斷出了后現代主義文化的物質基礎,卡斯特也以流動空間和無時間之時間作為社會的物質支撐和表現,將信息化資本主義診斷為一個新型的網絡社會。我們不難發現,他們三人的共同點在于都是理解和把握身處的社會,只是特別地從時空伸延、時空壓縮、流動空間與無時間之時間等與時空相關的面向去切入和解析社會的,最終都是以廣義的社會為研究對象,這就涉及到時空與社會的復雜關系。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來看,時空既是社會的基本結構,也是社會演化的內部參量,當然也是社會運動的物質表現形式。作為一種結構,時空構成了社會的基礎性結構,它既為整體的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動態結構所形塑,同時也參與形成和建構了社會的生產和再生產結構,包括物質的和文化的結構以及形形色色的制度結構和觀念結構。作為一種參量,時空滲透到社會運動內部不同層次之間并由人的實踐活動耦合到社會運動的全過程中去,在創生社會演化圖式、模鑄實踐格局的同時,時空本身也被扭曲、變形和重構。作為一種物質形式,時空既是社會發展的物質性支持和社會活動的外部環境,也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內容。總之,時空是社會的一個切面,跨越社會的所有領域,是社會存在與運作的展現和結果以及憑藉、中介和參數。我們無法想象一個沒有時空而能存在的社會,所以對于社會的理解不能不包括時空的向度,但同時,時空本身并不能獨立存在,它和人類的實踐活動息息相關,我們無法藉由時空而完全地理解社會。
B089.1
A
1003-4145[2012]03-0024-06
2011-12-05
牛俊偉,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漳州師范學院政法系講師。劉懷玉,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歷史唯物主義的空間化問題研究”(11BZX005)的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周文升wszhou6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