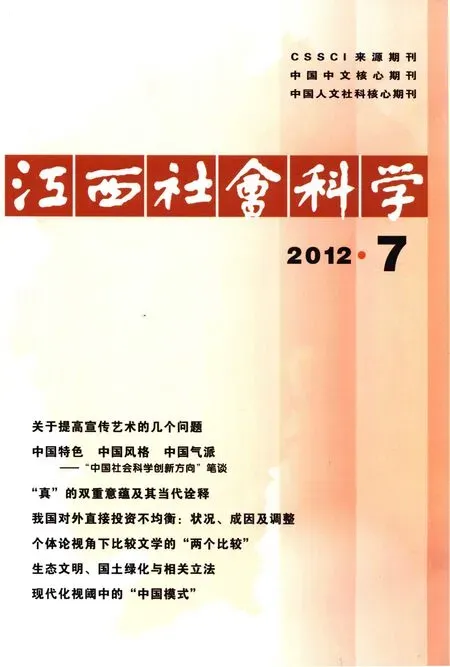啟蒙現(xiàn)代性敘事與黑格爾的承認(rèn)哲學(xué)
■陳良斌
啟蒙現(xiàn)代性敘事與黑格爾的承認(rèn)哲學(xué)
■陳良斌
承認(rèn)哲學(xué);主體間性;啟蒙現(xiàn)代性;解放政治
20世紀(jì)中后葉,西方學(xué)者對黑格爾承認(rèn)哲學(xué)的重新發(fā)現(xiàn)和全新詮釋,不僅顛覆了黑格爾作為主體性哲學(xué)集大成者的傳統(tǒng)形象,而且通過發(fā)掘承認(rèn)命題與20世紀(jì)主體間哲學(xué)的理論勾連,使黑格爾自身顯現(xiàn)出一種后現(xiàn)代主義的激進(jìn)色彩。一般來說,黑格爾承認(rèn)哲學(xué)的提出主要緣于對啟蒙所倡導(dǎo)的主體性立場的反思,黑格爾主張從個體的“我”走向交互承認(rèn)的“我們”,這是他對啟蒙現(xiàn)代性規(guī)劃開出的一劑“主體間性”藥方。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有必要對黑格爾在啟蒙現(xiàn)代性進(jìn)程中的復(fù)雜性地位進(jìn)行重新審視,進(jìn)而廓清這樣的理論問題:黑格爾究竟是一位保守主義的代言者,還是一個激進(jìn)的現(xiàn)代性異端?
一、啟蒙現(xiàn)代性與承認(rèn)的提出
啟蒙至今,解放政治的歷史敘事對于現(xiàn)代性的成長影響至深,以至于吉登斯指出,從近代到現(xiàn)代,無論是激進(jìn)主義、自由主義還是保守主義,“都共同受解放政治的支配”[1](P247)。因為解放政治體現(xiàn)了一種普遍的人類歷史觀念,即所有人類歷史都趨向一個作為終極目的的自由王國。所以,在啟蒙規(guī)劃的召喚下,林林總總的現(xiàn)代性理論其實(shí)都只是“解放政治”母題的一種具體敘事。[2]但各種紛繁的解放敘事顯然都忽略了實(shí)現(xiàn)解放的歷史路徑。啟蒙之后,上帝死了,解放政治的實(shí)現(xiàn)就再也沒有神的羈絆,因此解放政治首當(dāng)其沖要解決的就是主體與客體之間的沖突和矛盾。主客對立的結(jié)果是人不斷地嘗試主宰自然,但卻無時無刻不受到自然的制約。隨著近代生產(chǎn)力革命的爆發(fā),物質(zhì)基礎(chǔ)逐漸達(dá)到極大豐富,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完成現(xiàn)代化,開始率先進(jìn)入現(xiàn)代化的高級階段——大眾消費(fèi)社會。在這里,大眾消費(fèi)社會的形成標(biāo)志著物質(zhì)的束縛已經(jīng)達(dá)到極大緩解,主體與客體的矛盾終于得到了真正的和解,如果從物質(zhì)文明與精神文明的語境來說,那么物質(zhì)文明已經(jīng)非常強(qiáng)大,所以在主客體的矛盾得到緩解或解決的背景下,解放政治剩下的最后一個制約就是主體與主體之間的矛盾。
如何擺脫他者的束縛成為現(xiàn)代性進(jìn)程中揮之不去的一個主題。在黑格爾看來,主體之間的沖突就是承認(rèn)哲學(xué)所要克服的核心問題。黑格爾的解決之道就是揚(yáng)棄主體間的矛盾沖突,以交互承認(rèn)的方式實(shí)現(xiàn)主體間的和解,這就是承認(rèn)哲學(xué)的解放邏輯。具體來說,主體只有在他者承認(rèn)的中介下才能回到自身,才能獲得真正具體的自由,反過來,他者亦然。同時,交互承認(rèn)本身所蘊(yùn)含的前提就是將他者視為與主體自身均等的人,否則雙方只會導(dǎo)致虛假的不平等承認(rèn)的出現(xiàn),而不會實(shí)現(xiàn)真正的承認(rèn)。在黑格爾看來,承認(rèn)哲學(xué)構(gòu)成了實(shí)現(xiàn)解放政治的一種可行的歷史敘事,同時承認(rèn)哲學(xué)也構(gòu)成了對啟蒙現(xiàn)代性規(guī)劃的一種反思的視角。在此基礎(chǔ)上,黑格爾逐步豐富并完善了他的承認(rèn)哲學(xué),使之最終成為一個完整的承認(rèn)哲學(xué)體系。
值得注意的是,當(dāng)前國際學(xué)界對于黑格爾承認(rèn)體系的建構(gòu)過程始終眾說紛紜①,筆者主張將黑格爾的承認(rèn)哲學(xué)作為一個成長的連續(xù)體系,承認(rèn)的脈絡(luò)貫徹黑格爾思想發(fā)展的各個時期。因此,按照時間的順序,承認(rèn)體系的發(fā)展可以大致劃分為耶拿早期和成熟期這兩個階段,成熟期階段并不存在對于早期學(xué)說的拋棄。耶拿早期以《耶拿手稿》系列為代表,而成熟期以《精神現(xiàn)象學(xué)》、《法哲學(xué)原理》為代表。在《耶拿手稿》中,承認(rèn)主要表現(xiàn)為兩種類型:愛與沖突。愛將交往雙方統(tǒng)一起來。自我通過他者獲得自身的實(shí)存。因而將自我與自身的內(nèi)在關(guān)系經(jīng)由他者的中介達(dá)成一種同一。因此,每個人都是通過他者和在他者之中成為自為存在。但是這時的黑格爾認(rèn)為真正的承認(rèn)只能通過生死斗爭才能獲得,所以個體之間靠愛的情感來維系的聯(lián)系只能是有瑕疵的。這就必須過渡到另一類型——沖突。這種承認(rèn)類型直接反映了市民社會的形成及其法律規(guī)范的產(chǎn)生,它們都是以成員間的相互承認(rèn)為前設(shè)的。在這里,為承認(rèn)而斗爭可以被理解成個體為反抗侵犯(犯罪)或法律而發(fā)起的斗爭。黑格爾規(guī)定了他者對所有物的侵占或否定構(gòu)成了達(dá)成相互承認(rèn)的必要前設(shè),承認(rèn)斗爭正是由侵犯而產(chǎn)生的。被侵犯的這個客體與占有它的自我意識或自為存在的個體緊密相連,正是在客體中,個體找到了自身。事實(shí)上,所有物的侵犯影響著主體在自覺的個性中最深層的私人結(jié)構(gòu)。隨著侵犯的開始,個體為了獲得承認(rèn),一場生死之爭就不可避免地爆發(fā)了。[3](P125-127)黑格爾特別強(qiáng)調(diào)了承認(rèn)斗爭和死亡是實(shí)現(xiàn)純粹自我意識或精神的必要階段。在這里,黑格爾選擇將承認(rèn)的欲望激進(jìn)化至“斗爭到死”的地步。“承認(rèn)的原則不是自我限制,而是對他者的否定,它的實(shí)施沒有任何限制。”[4](P144)可以看出,黑格爾的思想已開始發(fā)生一種轉(zhuǎn)變,他在試圖克服自由主義立場的缺陷,但這種克服不是通過約束它的基本前設(shè),而是激進(jìn)地將個人自由推進(jìn)到極端或“否定性”,根據(jù)他的解釋,這種否定性凸顯了個人的主體性自由,進(jìn)而構(gòu)成了現(xiàn)代自然法的基石。
可以肯定的是黑格爾的觀點(diǎn)在耶拿時期發(fā)生了相當(dāng)?shù)母淖儭S绕涫撬膶?shí)踐哲學(xué)從絕對倫理性的概念逐漸發(fā)展成國家理論,這是對自由原則內(nèi)在批判的結(jié)果,同時國家理論因而也為個人自由給予了更多的空間。這可能是對黑格爾對于政治古典主義概念的態(tài)度轉(zhuǎn)變的最好的證明。”[4](P149-150)因此,承認(rèn)哲學(xué)對于黑格爾而言,其實(shí)可以被看做為一種克服國家與個人之間對立的努力。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法國大革命其實(shí)并沒有成功。因此,進(jìn)入成熟期之后,黑格爾進(jìn)一步站在承認(rèn)的立場上將這種對于個體自由和權(quán)利的關(guān)注深化下去,而在耶拿早期,黑格爾所構(gòu)筑的國家概念則始終是高懸于個人和權(quán)利領(lǐng)域之上,他甚至十分贊同馬基雅維利關(guān)于政治的觀點(diǎn),強(qiáng)調(diào)城邦中市民“順從”的重要性,因此,正是承認(rèn)哲學(xué)給黑格爾帶來了這種巨大的轉(zhuǎn)變。在成熟期中,最初的一個標(biāo)志就是主奴之間“承認(rèn)辯證法”的提出,黑格爾在這里提出了奴隸的解放是經(jīng)由勞動的陶冶而實(shí)現(xiàn)的,因而提出了一條承認(rèn)的替代路徑,也就是勞動。通過主奴之間的沖突,黑格爾把為承認(rèn)而斗爭發(fā)揮得淋漓盡致,但是他也發(fā)現(xiàn)了沖突模式的局限性,因此,黑格爾希望能找到一條克服的途徑,最終他回到耶拿早期關(guān)于愛的模式,希望以愛來溶解交往的雙方,并將愛視為相互承認(rèn)的理想模式。這種理想模式雖然能夠理想地克服沖突,但它并沒有窮盡倫理的形式與內(nèi)涵,按照黑格爾的設(shè)想,國家才是相互承認(rèn)的最高階段和實(shí)體性自由的實(shí)現(xiàn),但是黑格爾對于國家相對應(yīng)的承認(rèn)形式并沒有詳加論證,因此,阿克塞爾·霍耐特(Axel Honneth)按照這種設(shè)想提出了團(tuán)結(jié)的模式[5](P127-134),作為國家層面相對應(yīng)的承認(rèn)類型而與前面的家庭、市民社會的承認(rèn)類型相對應(yīng)。
二、承認(rèn)方案與主體性的診斷
啟蒙現(xiàn)代性所帶來的是獨(dú)立自主的“大寫”的人,因此,“啟蒙的根本目標(biāo)就是要使人們擺脫恐懼,樹立自主。但是,被徹底啟蒙的世界卻籠罩在一片因勝利而招致的災(zāi)難之中”[6](P1)。當(dāng)人們在“二戰(zhàn)”后陷入啟蒙價值的迷思之后,就會越發(fā)理解黑格爾的深刻。黑格爾對于啟蒙現(xiàn)代性的主體性立場始終保持一種明確的批判態(tài)度,但他并不簡單地就認(rèn)為主體性是錯誤的、需要拋棄的,而是給出了黑格爾式的辯證式診斷。他認(rèn)為,啟蒙現(xiàn)代性的主體性立場來源于笛卡爾-康德式的主體性理解,現(xiàn)代性傾向于將這種唯名論的主體性原則理解為一種抽象的個人主義,主張個體的主觀自由,在黑格爾看來,這僅僅是主體性真理的一部分,因而是片面的。而在國家的起源上,以盧梭為代表的個人主義主張將國家的概念建立在社會契約論的基礎(chǔ)上,黑格爾對此更是持否定的立場:“他(盧梭——筆者注)所理解的意志,僅僅是特定形式的單個人意志,他所理解的普遍意志也不是意志中絕對合乎理性的東西,而只是共同的東西,即從作為自覺意志的這種單個人意志中產(chǎn)生出來的。……為了反對單個人意志的原則,我們必須記住這一基本概念,即客觀意志是在它概念中的自在的理性東西,不論它是否被單個人所承認(rèn)或為其偏好所希求。”[7](P255)(譯文有改動)據(jù)此,黑格爾認(rèn)為社會契約論是把倫理國家與市民社會誤解和混淆了。為了克服啟蒙現(xiàn)代性的個人主義傾向,同時為了能達(dá)到作為倫理共同體的國家理論,黑格爾主張恢復(fù)源于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古典共同體的傳統(tǒng)來超越現(xiàn)代性的原子論,也就是提倡整體大于并優(yōu)先于部分,個體應(yīng)當(dāng)在國家中獲得真正的自由。但黑格爾并沒有止步于此,他對現(xiàn)代性的診斷顯然不是簡單地回到古典國家,而是采取揚(yáng)棄的方式以辯證的態(tài)度對古典國家觀同樣進(jìn)行了批判。黑格爾相信,現(xiàn)代性中也必然要求交互承認(rèn),同時也必然包含著主觀自由。這意味著黑格爾的觀點(diǎn)與柏拉圖的立場相反,也就是認(rèn)為善是良善意志,同時正是因此,善沒有現(xiàn)實(shí)地脫離主觀自由的行為,“其結(jié)果,普遍物既不能沒有特殊利益、知識和意志而發(fā)生效力并底于完成”[7](P260)。離開了自由,善將始終是抽象的[8](P116)。
由此看來,黑格爾雖然對于現(xiàn)代性所標(biāo)榜的自由主義之個人主義提出了批判,但這并不意味著他所構(gòu)想的國家共同體是以犧牲個體為代價的,同樣,黑格爾雖然主張恢復(fù)古典傳統(tǒng),卻并不是回到淹沒個體的古典國家中去。黑格爾的高明之處就是既看到了兩者都具有合理之處,同時也抓住了兩者的片面之處,因此他將兩者分別比作抽象的集體主義和抽象的個人主義,而他的任務(wù)就是在克服抽象個人主義和抽象集體主義的缺陷之后去獲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在此基礎(chǔ)上,黑格爾的現(xiàn)代性診斷就是對古典的集體主義與現(xiàn)代的個人主義進(jìn)行揚(yáng)棄的同時,提出了第三種選擇。在這個選擇中,交互承認(rèn)成為黑格爾所倚重的一個重要的批判維度。黑格爾首先從自為的存在出發(fā),提出作為主體間性的“我們”。自為的存在在黑格爾那里具有兩重截然不同的含義:一種是直接或抽象的含義,也就是第一人——“我”;另外一種是中介的和更為具體的含義,也就是第一人的復(fù)數(shù)形式——“我們”。黑格爾認(rèn)為,直接的自為存在是抽象的、正式的和空無的,因此實(shí)踐地表達(dá)在行為中就是任性(Eigensinn)或自我主義。正是出于這個原因,直接的自為存在僅僅是承認(rèn)的出發(fā)點(diǎn),而不是其基礎(chǔ)。所以交互承認(rèn)的過程是從簡單的、直接的自為存在發(fā)展到中介的、有限制的主體間性的自為存在,也就是從“我”到“我們”。[9](P152)于是,“我們”是個體的聯(lián)合,揚(yáng)棄并擴(kuò)大了他們的自我同一,同時要求和依賴于對他們個體自由的保護(hù)。這是對原初自為存在的一種交互式的豐富和擴(kuò)充。同時,相互承認(rèn)并不是在我和你之間簡單地保持一種主體間的對話,它呈現(xiàn)為一種有機(jī)統(tǒng)一的形態(tài),即意味著自在存在和自為存在之間的辯證的統(tǒng)一。個人從而在“我們”之中作為整體獲得更大的同一性。因此,黑格爾是以“我們”的交互承認(rèn)替代了費(fèi)希特和謝林的“我就是我”的觀念論范式。
在這里,交互承認(rèn)將主體性轉(zhuǎn)化為主體間性,而這與古典思想中整體大于并優(yōu)先于部分的觀點(diǎn)是一致的,同時個體也將充分的交互承認(rèn)作為發(fā)展主觀自由的目標(biāo),并在普遍性的社會意識中達(dá)到頂點(diǎn)。所以,交互承認(rèn)是國家的一種理想統(tǒng)一體,是對黑格爾國家理念的現(xiàn)實(shí)詮釋。承認(rèn)將黑格爾的實(shí)體性自由與主觀自由相統(tǒng)一。一方面,當(dāng)現(xiàn)代性傾向于把主觀自由進(jìn)行原子化解釋時,黑格爾就通過他者將主體性去中心化;另一方面,在他者中將主觀性改造為倫理的主體間性。擴(kuò)展了和去中心化的主體性不僅向倫理實(shí)體或?qū)嶓w性自由開放,而且在這些實(shí)體中發(fā)現(xiàn)自身,也就是在更大的整體中承認(rèn)自身。因此,實(shí)體性自由不是他律的,而是包含著將自由現(xiàn)實(shí)化的必要條件[8](P266)。于是,只有在交互承認(rèn)中自由和主觀性才能得到充分發(fā)展,進(jìn)而產(chǎn)生了客觀精神。黑格爾相信承認(rèn)的最終結(jié)果就是精神,而我就是我們。在這里,“精神就是規(guī)定的客觀社會世界,一種客觀理性的結(jié)構(gòu),或倫理實(shí)體”[8](P118)。
在此基礎(chǔ)上,黑格爾回到對古典思想和現(xiàn)代性規(guī)劃的診斷和改造上,認(rèn)為兩者都具有重要的啟示,但是他們都是以片面的方式表達(dá)出來的,所以黑格爾的選擇就是由交互承認(rèn)構(gòu)成的自由和公正的共同體來克服雙方的片面性。在黑格爾看來,這種共同體并不是給定的或是一種自然共同體,而是一種已實(shí)現(xiàn)的精神的共同體,它是通過自由來實(shí)現(xiàn)的。現(xiàn)代性與它的主觀自由以及古典城邦與它的社會結(jié)構(gòu)概念都表達(dá)了自由共同體的基本維度和內(nèi)涵。但是,它們自身對于共同體的闡述顯然都是不完善的。在黑格爾看來,啟蒙現(xiàn)代性的主體性思維對于基于規(guī)范文化的探討是不充分的,因為這樣的主體性會造成差異的絕對化。而古典思想的集體主義雖然為其提供了具有參考價值的結(jié)構(gòu)和內(nèi)容,但是最終會導(dǎo)致權(quán)威極權(quán)主義而無法容納主觀自由。由此看來,雙方的缺陷其實(shí)都能被另一方所彌補(bǔ):現(xiàn)代主觀性如果能滿足特定文化結(jié)構(gòu)上的條件,也就是整體優(yōu)先于部分,就能克服自身的局限。相反,古典的整體機(jī)構(gòu)只有通過主觀自由的擴(kuò)張同時經(jīng)由交互承認(rèn)進(jìn)入主體間性作為條件,才能達(dá)到批判的實(shí)現(xiàn)[8](P118)。所以,黑格爾的做法其實(shí)是通過承認(rèn)作為中介,使古代和現(xiàn)代和解,也就是“在倫理實(shí)體提供主觀自由的內(nèi)容與目標(biāo)的同時,主觀自由是一種為倫理實(shí)體的實(shí)現(xiàn)和現(xiàn)實(shí)化的工具”[8](P268)。只有完成了這種和解的國家觀,也就是結(jié)合倫理實(shí)體和現(xiàn)代主觀自由,才能最終實(shí)現(xiàn)實(shí)體性的自由——“具體的自由”,對此,黑格爾在《法哲學(xué)原理》中明確地指出:“國家是具體自由的現(xiàn)實(shí);但具體自由在于,個人的單一性及其特殊利益不但獲得它們的完全發(fā)展,以及它們的權(quán)利獲得明白承認(rèn)(如在家庭和市民社會的領(lǐng)域中那樣),而且一方面通過自身過渡到普遍物的利益,他方面它們認(rèn)識和希求普遍物,甚至承認(rèn)普通物作為它們自己實(shí)體性的精神,并把普遍物作為它們的最終目的而進(jìn)行活動。”[7](P260)
三、抽象的“我們”與黑格爾的困境
黑格爾站在交互承認(rèn)的立場上完成了對現(xiàn)代性的診斷和批判,以主體間性的“我們”來替代主體性的“我”成為他的解決方案,但是黑格爾專注于構(gòu)建一種抽象精神的思辨體系,在這種體系中,我們看不到有血有肉的歷史性主體,雖然主體處在黑格爾意義上的理想的承認(rèn)狀態(tài),擁有具體的自由,但是具體的自由依然是一種抽象的權(quán)利。顯然,黑格爾推崇的是在思想深處爆發(fā)革命,而不是在現(xiàn)實(shí)中體會真切的主體間性,這也是他與馬克思的最大區(qū)別。馬克思主張哲學(xué)應(yīng)當(dāng)改造世界,而黑格爾的哲學(xué)只是解釋世界。因此,密納發(fā)的貓頭鷹永遠(yuǎn)只是在黃昏才能起飛,哲學(xué)的解釋永遠(yuǎn)落后于歷史的車輪。由此看來,黑格爾的承認(rèn)方案抑或現(xiàn)代性的診斷無論持何種激進(jìn)的語調(diào),他的立足點(diǎn)始終決定了其本質(zhì)上的保守性和局限性。
在黑格爾的承認(rèn)體系中,比較明確地確立了承認(rèn)的兩種模式,即沖突與愛。沖突的模式換句話說就是為承認(rèn)而斗爭。在主奴關(guān)系中,兩個主體為了獲得承認(rèn)而不惜以生命為代價而發(fā)生沖突,雖然由于一方的畏懼而出現(xiàn)了主人和奴隸的結(jié)局,但是這種關(guān)系卻是不穩(wěn)定的,奴隸在黑格爾看來才是真正推進(jìn)歷史的動力,奴隸通過勞動的陶冶,揚(yáng)棄了自身的欲望,從而超越了主人,但是這種超越只是在奴隸的意識之中,在奴隸那里,真正的超越顯然必須通過現(xiàn)實(shí)中新一輪的沖突并且戰(zhàn)勝主人才能獲得。于是,奴隸成了主人,但是這樣的顛覆只會造成惡的循環(huán)。在這里,主奴的關(guān)系無法調(diào)和,在根本上其實(shí)是如何處理個人主義與集體/共同體價值的矛盾,因此,黑格爾雖然敏銳地抓住了這個問題的癥結(jié)所在,并為我們指明了一條主體間的發(fā)展方向,但是他的保守性卻注定了他無法在現(xiàn)實(shí)中真正地解決矛盾所在。
由于前路無果,黑格爾最后傾向于回到耶拿早期所提出的愛的模式來獲得對沖突模式的化解之道,但是,顯而易見,現(xiàn)實(shí)的沖突不可能依靠愛情來解決。雖然主體們在愛之中拋棄了自身對他者的排斥,并在愛之中相互融合,但是,黑格爾卻忘記了處于愛情之中的主體對于其他主體仍然具有排斥性,而成為親情的愛則局限于血緣的紐帶,對血緣之外的他者亦具有排斥性。所以,愛注定了它只能存在于婚姻和家庭的范圍內(nèi),一旦擴(kuò)大至市民社會和國家的范圍,就無法利用愛來消解主體間的承認(rèn)沖突,因此愛的模式只能停留在理論的層面,而無法現(xiàn)實(shí)地改造沖突模式下的惡之循環(huán)。因此,黑格爾的方案只會變成一種空中樓閣。按照黑格爾后期的思路,在倫理國家的層面應(yīng)該還要建立一種更為高級的承認(rèn)模式,但他在這里卻戛然而止。霍耐特正是受此啟發(fā),根據(jù)這條思路發(fā)展出了第三階段的承認(rèn)模式,即團(tuán)結(jié)的模式,但是,團(tuán)結(jié)的承認(rèn)模式并非霍耐特所說的那么完美,這種模式似乎更適用于市民社會,而非國家的層面。因此,迄今對于國家層面運(yùn)作過程中的主體間承認(rèn)形態(tài),仍然缺乏確切的規(guī)定。那么回到原點(diǎn),主體間的承認(rèn)抑或和解究竟該如何來達(dá)成呢?馬克思對此曾經(jīng)提出了一種替代性方案,那就是根據(jù)歷史的條件來選擇具體的道路,換言之,就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該用沖突的手段來完成的就用沖突去實(shí)現(xiàn)歷史,能夠?qū)崿F(xiàn)承認(rèn)的條件下就使用承認(rèn)來進(jìn)行主體間的和解。
除了愛與沖突的承認(rèn)模式,黑格爾其實(shí)還潛在地提出了另一種勞動模式,只是他對于勞動與承認(rèn)的關(guān)系沒有繼續(xù)探討下去。勞動模式在耶拿早期首先是作為個體占有物品的手段,實(shí)現(xiàn)了主體自身的對象化,并物化為排斥所有他者的符號,從而開啟了所有權(quán)概念的肇端,為主體實(shí)現(xiàn)與他者之間的交互承認(rèn)奠定了物質(zhì)基礎(chǔ)。其次,勞動是作為實(shí)現(xiàn)了滿足他者需求的工具手段,是主體體驗承認(rèn)的媒介,也是對交互承認(rèn)的補(bǔ)充,或者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看做是交互承認(rèn)的一種構(gòu)成元素。此外,黑格爾還在勞動的異化和工具/機(jī)器的異化的探討中,將異化勞動看做是對人的否定,同時也是對交互承認(rèn)的一種否定而對待。而在奴隸的解放中,黑格爾則強(qiáng)調(diào)勞動在奴隸顛覆主奴之間不平等承認(rèn)的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在勞動的陶冶下,奴隸意識由為他的存在成功地轉(zhuǎn)向了自為的存在[10](P247-248)。因此,這時的勞動顯然是被視為對承認(rèn)模式的一種替代,這種替代模式的潛在價值卻在愛以及國家對承認(rèn)辯證法的超越之后被擱置了。黑格爾的保守性決定了他對勞動模式的放棄,但是勞動的模式在日后卻激發(fā)了馬克思的靈感,勞動范疇最終成為馬克思承認(rèn)構(gòu)架的一塊基石。
綜上可知,黑格爾試圖從“我”到“我們”的主體間性來調(diào)和個人與集體之間不可避免的矛盾,但是,“我們”終究是抽象的“我們”,同樣,黑格爾那里也有世界歷史,但我們看到的只是抽象的歷史。對此,杜威則十分恰切地抓住了黑格爾的癥結(jié)所在,他認(rèn)為黑格爾的調(diào)和似乎“能應(yīng)付對于極端個人主義和極端社會主義的一切異議,免除柏拉圖和邊沁兩人的錯誤”,但是,黑格爾的“錯誤在于以一般的觀念概括特殊的情境”,他抽象的倫理國家的設(shè)想“把附屬于普通觀念的意義和價值放在特殊的具體情境上面,遮蓋了它的缺陷,隱蔽了迫切改革的需要”。所以,它“縱然不是有意的,卻抵抗著法國革命所掀起的激進(jìn)思想的潮流,而筑起了用以支持當(dāng)時的政治局勢的一個堡壘”[11](P114-115)。
注釋:
①迄今為止,國際學(xué)界對于《耶拿手稿》中的思想是否與此后黑格爾成熟時期的哲學(xué)體系一脈相承,也即承認(rèn)主題是否貫穿黑格爾整個思想體系始終存有較大的分歧,而這也成為當(dāng)前黑格爾承認(rèn)學(xué)說的研究熱點(diǎn)之一。一方認(rèn)為耶拿時期的理論體系是黑格爾早期不完善的思想,并為其自身所拋棄,因此承認(rèn)理論只存在于早期,這方以霍耐特和哈貝馬斯為代表;另一方則以羅伯特·皮平(Robert Pippin)、特瑞·平卡德(Terry Pinkard)、羅伯特·威廉姆斯(Robert Williams)等人為代表,他們認(rèn)為耶拿時期所建構(gòu)的思想體系為黑格爾成熟時期的宏大哲學(xué)體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石,而承認(rèn)學(xué)說則是黑格爾思想體系中一直被遮蔽的一條重要的理論線索,它貫穿于其思想的始終。
[1](英)吉登斯.現(xiàn)代性與自我認(rèn)同[M].趙旭東,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8.
[2]姚大志.朝向二十一世紀(jì)的西方哲學(xué)[J].浙江學(xué)刊,2002,(1).
[3]G.W.F.Hegel.Hegel and the Human nature:A translation of the Jena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Spirit(1805 - 1806)with commentary.Ed.& trans.Leo Rauch.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3.
[4]Vladimir Milisavljevi,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in Hegel’s Jena Writings, Belgrade Law Review(Annals of the Faculty of Law in Belgrade), International Edition,2007.
[5](德)霍耐特.為承認(rèn)而斗爭[M].胡繼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6](德)霍克海默,阿多諾.啟蒙辯證法[M].渠敬東,曹衛(wèi)東,譯.上海:上海世紀(jì)出版集團(tuán),2006.
[7](德)黑格爾.法哲學(xué)原理[M].范揚(yáng),張企泰,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7.
[8]Robert R.Williams.Hegel’s Ethics of Recognition.Berkeley &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9]Robert R.Williams.Recognition:Fichte and Hegel on the Other.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
[10]G.W.F.Hegel.System of Ethical Life(1802/3)and First Philosophy of Spirit(Part of the system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1803/4).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79.
[11](美)杜威.哲學(xué)的改造[M].許崇清,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58.
20世紀(jì)中后葉,西方學(xué)者對黑格爾承認(rèn)哲學(xué)的重新發(fā)現(xiàn)和全新詮釋,不僅顛覆了黑格爾作為主體性哲學(xué)集大成者的傳統(tǒng)形象,而且發(fā)掘出黑格爾內(nèi)蘊(yùn)的一種后現(xiàn)代主義的激進(jìn)色彩。一般來說,黑格爾承認(rèn)哲學(xué)的提出主要緣于對啟蒙所倡導(dǎo)的主體性立場的反思,黑格爾主張從個體的“我”走向交互承認(rèn)的“我們”,這是他對啟蒙現(xiàn)代性規(guī)劃開出的一劑“主體間性”藥方。黑格爾推崇在思想深處爆發(fā)革命,而不是引向現(xiàn)實(shí)的實(shí)踐,因而無論語調(diào)如何激進(jìn),他的理論基點(diǎn)就決定了其承認(rèn)哲學(xué)本質(zhì)上的保守性和局限性。
B516.35
]A
]1004-518X(2012)07-0039-05
陳良斌 (1981—),男,東南大學(xué)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講師,法學(xué)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江蘇南京 211189)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xué)研究青年基金項目(項目批準(zhǔn)號:12YJC720004)、江蘇省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項目批準(zhǔn)號:11MLC008)、江蘇省教育廳高校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研究指導(dǎo)項目(項目編號:2011SJD710001)、東南大學(xué)人文社科重大引導(dǎo)項目(項目編號:SKYY20110010)的階段性成果。
【責(zé)任編輯:龔劍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