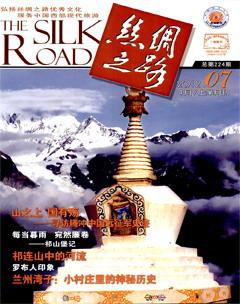山之上 國有殤
陸安



抗戰文化熔鑄的極邊第一城
簡直難以置信,號稱“極邊第一城”的滇緬邊境小城騰沖就在飛機的機翼之下,開始只是若隱若現,最終赫然在目。若不是當今民航交通運輸事業的發達,長期置身沿海城市的我,怎么可能輕而易舉地來到這座位于祖國西南邊陲的小小縣城。
騰沖,現隸屬于云南省保山市。在印象中,保山地區并不發達,甚至有些貧窮落后,時不時地還與境外的金三角地區和販毒等令人驚悚的概念產生聯系。然而,就是這么一個地級市,航空運輸業卻相當發達。保山有機場,其下轄的騰沖縣竟然也有機場,這在全國恐怕并不多見。我想,這應當歸功于當年的中國遠征軍和美國第十四航空隊(“飛虎隊”)。在那炮火連天、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騰沖簡陋的綺羅機場承擔起舉足輕重的戰略使命,成為“駝峰航線”與“中印公路”的交匯點,亦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盟軍與日寇生死博弈,血腥廝殺,反復較量,一度讓這里成為一片焦土,最終,侵略者的“膏藥旗”從騰沖城頭被拋落,勝利屬于中國人民。小地方決定大命運,用在騰沖身上,是再貼切不過的了。
穿過藍天白云,我乘坐的飛機緩緩降落在騰沖那小巧玲瓏的機場。艙門打開,我發現這里既沒有其他機場常見的連接機艙與抵達大廳的機動通道,也無需“擺渡”大巴,機場面積十分有限,目力所及,僅有一兩架飛機寂寥地停放在那里。中國其他機場見怪不怪的飛機晚點、延誤等現象,在這里很難碰到,不管是來還是去,不管是起還是降,一般都很準時,給人一種少有的清爽感和利落感,如同騰沖這座未加刻意雕飾的原生態小城一般,總是給造訪者留下極好的第一印象。
我隨著并不熙攘,甚至有些稀落的人流走下飛機,步行穿過機場大廳,雖不習慣,卻也體味了些許簡約之美,感覺愜意不少。大廳廣播中傳出“歡迎來到騰沖駝峰機場”的聲音,猛然間,一種歷史的穿透感豁然浸入心田。駝峰機場,這不就是當年威震寰宇的美國第十四航空隊(“飛虎隊”)所使用的軍用機場嗎?60多年前,“飛虎隊”沿著“駝峰航線”不斷為中國抗日戰爭運送物資,輸血打氣,成為抗戰堅持到最后取得勝利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撐。這駝峰機場,還有它所在的小小縣城騰沖,見證了一段血與火交織、情與淚共生的艱苦歲月,更記錄下了中國人民不屈不撓、保家衛國的生動歷史。我正是為著這凝固的歲月和歷史來的。
來到小城騰沖,對于常年從事歷史研究的我來說,是機緣巧合。騰沖人引以為傲的除了翡翠文化、馬幫文化之外,還有難能可貴的抗戰文化,抗戰文化已經無孔不入地浸透進騰沖的每個角落和每個人的血脈之中,揮之不去。在這里,深入生活,體味那一絲絲稍縱即逝的抗戰文化,參觀那一處處浸染著血肉和硝煙的史跡,尋訪那一個個從歷史中走過來的親歷者,之于一直對抗戰史情有獨鐘的我,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寶貴機會。
我非常珍視在騰沖的那些日子。一個星期的時間,我流連于騰沖的大街小巷、山間地頭,試圖感同身受這個擁有血與火熔鑄的非凡歷史的小城的獨特韻味。為此,我特地選擇距離埋葬成千上萬中國遠征軍忠骨的國殤墓園不遠處的酒店住下。近在咫尺的墓園、觸手可及的歷史、流芳千古的英靈,讓我無時無刻不處于一種莫名的激動與沉醉之中。隨時進出這座墓園,感受那寧靜之中的莊嚴與神圣,對于置身現代喧囂浮躁社會中的人來說,無疑是一種心靈的洗滌和靈魂的凈化。“山之上,國有殤”,是騰沖抗戰文化的最好寫照,也是這座小城獨具特色的地理標志和文化品牌。我甚至在想,騰沖,不用刻意描繪,僅憑當年成千上萬抗日軍民的血肉和英魂,就足以雕鑿出舉世無雙的城市形象。這種城市形象,還有哪個城市可與之媲美?最好的城市形象,往往是內在、內秀、永恒、魂魄的東西,而不是那些外在、外形、曇花一現、附著于外物的東西。
遙想一個多甲子之前,當騰沖從日寇鐵蹄下光復不久最為艱苦的時刻,騰沖人民眼含熱淚,懷著無比悲傷的心情,將無數犧牲的遠征軍將士的尸骨收殮,埋葬在這片蒼松翠柏覆蓋、綠意生機無限的山崗之上,為的就是讓后世永遠銘記和懷念這些為國捐軀的勇士們的英魂。
走進騰沖,走進墓園,分明就是走近正在離我們漸行漸遠卻又無論如何難以忘卻的歷史,走近激勵我們這個多災多難卻又生生不息的民族昂揚進取的精神。
墓園中埋藏著蕩氣回腸的歷史
在晨曦初露的清晨、陽光普照的中午和落日余暉的黃昏,我幾度進入國殤墓園。
墓園開放,并不收費,管理到位,秩序井然。游客不多,大多是隨導游而行的旅行團隊,急急地來,匆匆地走,屬于當代旅游的常態。也難怪,在時下這樣一個浮躁、功利的社會,有誰會靜下心來細細參觀,認真憑吊呢?這是一個身體需要停下來等等靈魂的時代,前行的速度過快,靈魂往往跟不上。我總喜歡一個人在國殤墓園中靜靜地走,細細地看,不想放過任何一個細節、任何一個角落,為的就是找尋那些失落在這里的忠魂,憑吊那一個個在天堂凝望著我們這片沃土的英靈。幾天下來,墓園里的每一片區域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跡,墓園中的每一個角落都留下了自己的身影,墓園中展示的每一張照片都留下了自己的目光,我簡直可以將這座國內獨一無二的遠征軍墓園裝進自己的心中了,一景一物、一字一圖,盡入腦海,刻骨銘心,揮之不去。
冬日的陽光照進國殤墓園,顯得有些清冽。南國的清風,吹去了墓園外大興土木而不斷掀起的陣陣浮塵,參天而又筆直的大樹,還有大樹底下無盡的茵茵綠草,過濾了塵世的浮躁,將喧囂隔絕在這生死分界線之外,為安息在這里的英靈營造了一個難得的清靜幽雅的環境。置身其間,肅穆感、沉重感、神圣感、崇高感……諸多感覺,一并襲來,讓人不由自主地放慢腳步,放輕步伐,靜氣屏息,謹言慎行,生怕攪擾那些九泉之下安眠的烈士。
墓園不大,卻很精致。進門之后,沿著石砌甬道前行,左右兩邊,均為綠樹環繞的草坪,不時有青銅雕塑撲入眼簾。為修筑滇緬公路而攜家帶口、婦孺上陣的當地民眾雕塑,為中印公路和“駝峰航線”做出突出貢獻的史迪威、陳納德并肩佇立、眺望遠方的雕塑,曾經發出義正詞嚴、浩氣凜然的《告滇西父老書》和《答田島書》名垂青史的愛國官吏李根源、張問德雕塑……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擷取的都是浩如煙海的史冊中感人至深的片段。其中,最能讓人駐足流連的莫過于三尊雕塑:一是“滇女情深”,一位傈僳族婦女在深山中遇到一位身負重傷、昏迷不醒的盟軍飛行員,因一時找不到救命的水源,她毅然用自己的乳汁展開急救,使其得以脫險;二是“雷打樹下”,愛國將領寸性奇為國壯烈犧牲之后,其父寸大進誓不獨生,為激勵同胞堅持抗戰,不惜在那棵有名的“雷打樹”之下絕食身亡;三是“餓死不食軍糧”,一個傳統的小腳婦女,支援前線,背著軍糧,長途跋涉,最后餓死在途中,軍糧卻完好無損。多么可尊可敬的民眾,多么感天動地的事跡,勾勒出在那風雨如晦、刀光劍影的歲月中支撐我們這個風雨飄搖的國家最終走向勝利的意志和斗志,這是任何敵人都無法戰勝的力量。
繞過于右任先生題寫牌匾的忠烈祠,沿著山坡間一道狹窄陡直的石板路拾階而上,周圍密密麻麻遍布著排列整齊的小小墓碑,一種久違了的震撼與激動猶如排山倒海般襲來。墓碑上的紅字,僅僅表明了軍銜與姓名,再無任何其他信息。“二等兵周榮華”、“少尉任鼎正”、“下士班長李萬榮”、“上等兵羅少華”……這些遠征軍的勇士,其個人履歷,早已被歷史的煙云所籠罩,變得日益模糊。我們素來“將歷史視為宗教”卻又缺乏真正的“歷史情懷”、缺乏對歷史“起碼的溫情與敬意”,這是一種陋習,容易犯下將活生生、具體的人加以泛化、使之淪為空洞無物的概念的錯誤。這一點,不像以色列。猶太人經歷了戰爭的屠殺和劫難,為了牢記歷史,建的所有紀念設施,無一不將殉難者、犧牲者的詳細個人資料考訂周全,姓名、籍貫、生卒、生平、家庭、子女,一應俱全,為的是對逝者的尊重,因為“每個生命都是高貴的存在”。盧梭的這句名言之所以放之四海而皆準,就因為它切準了人性的脈動與人心的根本。只有生命意識得到充分尊重,每個在歷史中走過的人都擁有自己無可替代、不可讓渡的尊嚴,歷史才能變得鮮活且可觸摸。
在國殤墓園,當年血灑疆場的勇士們,一排排,一行行,昂首挺胸,就是以簡潔得不能再簡潔的方式,留給后人無盡的懷念和追思。
山頂之上,聳入云霄的便是遠征軍紀念碑,底座上“民族永雄”四個藍色大字,赫然入目,仿佛在向人們昭示當年那場戰爭的性質和將士的偉大。站在山巔之上,仰視高高的紀念碑,一種高山仰止的感覺油然而生。環視四周,便是按建制排列的墓碑,整整齊齊,顯示出那種軍人特有的紀律性和組織性,烘托出山頂民族英雄的崇高意蘊。是啊,正是千千萬萬英烈們的存在,才讓我們不斷體會民族英雄所蘊藏的深刻含義,才讓我們擁有了今日之和平生活。
騰沖,當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重要戰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其激戰的慘烈及全殲日軍而聞名于世。從1942年5月10日淪陷到1944年9月14日光復的859個日日夜夜里,騰沖軍民以732天的游擊戰牽制日軍,消耗日軍,以127天的戰略反攻全殲日軍,光復騰沖。
騰沖抗戰創造了三個“第一”:第一次取得戰略反攻的全面勝利,第一次全殲入侵之敵,第一座在全國收復的縣城。出現了兩個“絕無僅有”:一是日軍侵騰,縣城百姓全部出走,逃往他鄉,與敵不共戴天,留下一座空城,這在全國淪陷區絕無僅有;二是戰爭異常慘烈,戰后騰沖城一片焦土,無一間完整的房屋,無一片沒有被槍彈和炮火擊穿、熏染過的樹葉,是真正的焦土抗戰,這在中國抗戰史上絕無僅有。
騰沖的光復,有力地促進了滇緬戰場的勝利,更加堅定了全國軍民抗戰必勝的信念,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上譜寫了光輝的一頁。
騰沖收復后,當地百姓最先想到的,就是為戰死的官兵修一塊墓地,40多萬元的捐款很快籌齊,幾個大戶人家也無償地將風水寶地——小團山捐獻出來,作為烈士的安息之地。1945年7月7日,在全國抗戰尚未完全勝利、紀念“盧溝橋事變”的特殊日子里,國殤墓園已經落成。
抗戰勝利之后,內戰的熊熊戰火燃起,國殤墓園經歷了有驚無險的一幕幕,最終保存到現在。
在墓園忠烈祠門前,我發現了一塊黑色石碑,上書“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布告”,警示不得改變墓地的屬性:“……賴我將士忠勇,與敵周旋,前赴后繼,遂克騰沖,恢復滇緬國際路線,促成偉大之勝利。豐功偉績,薄海同欽。茲建此墓園,永垂矜式。除按此舉行祀典及隨時開放任人瞻仰外,不得擅自駐兵及移作別用,以示愛護、尊崇之意,倘有干犯例禁,定即嚴懲不貸。”落款是“蔣中正”。
然而,時代變遷,江山更替,蔣中正落荒而逃,退居孤島,其手諭也就自身難保,形同廢紙。史無前例的“文革”,波及偏遠的騰沖。鐫刻著國民黨黨徽和國旗的國殤墓園,豈能幸免?國殤墓園遭到沖擊。當年安葬于此的將士有9000多名,“文革”之后,經過清點,劫后余生的僅有四塊墓碑。好不容易從當地修建廁所的圍墻中找到了當時的名錄碑,據此拓出了3000多名將士的姓名,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3000多塊嶄新墓碑的來歷。
不堪回首的蒼茫一頁終于翻了過去。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到來,讓國殤墓園恢復了原有的風貌,也讓遠征軍將士恢復了應有的尊嚴。隨著《我的團長我的團》、《中國遠征軍》等影視作品風行銀屏,騰沖,這座浴火重生的邊陲小城再次贏得了人們的垂青,很多人不遠萬里來到此地,不為別的,就為了到國殤墓園獻上一束花,獻上自己的憑吊和敬意。
在國殤墓園中徜徉,經常會看到一些墓碑前擺放著或黃、或白祭祀英靈的鮮花,不知是該碑主人的后代循跡而來有意為之,還是素不相識的吊唁者無意所為,至少,都給我們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安息吧!遠征軍的先烈,后人沒有忘記你們,歷史沒有忘記你們,你們是中華民族的英雄,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凝固在照片和大地上的歷史
自從人類發明了照相機之后,原先躲在字里行間的抽象的歷史終于有了栩栩如生、形象呈現的可能。
在騰沖這座以抗戰文化著稱的邊陲小城之中,我刻意搜尋著那些能帶來感官刺激的、形象的、可觸摸的歷史。為此,我按圖索驥,循著地圖,尋找路徑,穿街走巷,找到了兩處抗戰博物館,身臨其境,去感受那里別具一格、不同凡響的歷史氛圍。
一個彈丸之地,一處偏遠小城,竟然同時擁有兩座幾乎題材相同的抗戰紀念館,實在出乎我的意料,足見此地濃郁的抗戰文化和民眾對遠征軍的感情,也折射出騰沖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地方。
一座紀念館,位于國殤墓園山崗之下,曰“滇西抗戰紀念館”,是公立的;另一座紀念館,則位于和順鄉下,曰“滇緬抗戰紀念館”,是私營的。兩處紀念館,遙相呼應,珠聯璧合,各有側重,相互補充,共同展現豐富多彩、波瀾壯闊的抗戰歷史。前者,以照片為主;后者,以實物為主。很多照片和實物,讓人過目難忘,牢牢地刻進了記憶之中,經久不息,歷久彌新。
記得在公立的那家紀念館中,有兩幅清晰的黑白照片,看到的那一瞬間,我的鼻子一酸,眼睛一熱,好不容易才控制住了自己的眼淚使之沒有奪眶而出。
一幅是《遠征軍中的少年兵》,兩個穿著軍裝的少年兵,10歲出頭的樣子,其中一個挑著擔子,一頭是裝滿了軍糧的麻袋,沉甸甸的,一頭是碩大的一個斗笠,所謂“碩大”,其實只是相對而言,相對于他瘦弱矮小的身材,斗笠過大。另一個少年兵,背著軍用水壺、背包等裝備。無一例外,面對鏡頭,他們兩人都露出了自然而淳樸的笑容,一個還打出了時髦的象征“勝利”的手勢,沒有任何矯飾,那種未成年人的自信和幸福寫在他們的臉上。不知這是誰家的孩子,不知他們的父母當時是否健在,是否忍心讓自己的骨肉走上血肉橫飛、前途莫測的戰場。他們是否堅持到勝利那一天,后來的命運又如何呢?直到今天,只要一想起那幅照片,一翻看數碼相機中翻拍的并不清晰的那幅照片,我的心頭總會翻江倒海般痛楚。戰爭中的孩子,遠征軍的少年兵,你們在哪里?照片背后究竟隱藏著怎樣心酸卻又不為人知的故事?所有這些,只能讓人無限遐想,無盡酸楚,難以解脫,難以忘懷。
另一幅是《騰沖光復后站在城內日軍地下坑道之上的遠征軍》,更令人驚嘆和震撼。在我的印象中,原本以為,遠征軍得到了盟軍的大力支援,裝備雖稱不上一流,但在中國抗日軍隊中也絕非后進。看過這張照片,顛覆了我原先的認知。照片中的遠征軍,年齡也不大,基本上也算是一個孩子,渾身上下惟一像樣的裝備竟然是與其身材不大相稱的美式鋼盔,除此之外,用“衣衫襤褸”來形容并不為過,他光腳穿著一雙草鞋,沒有綁腿的肥大且不夠尺寸的“高吊褲”,上身的軍裝最為寒磣,洗得已經褪了色的軍服,背后縫綴著兩塊深色的大補丁,即使這樣,還無法掩飾已經破開來的一個局部……遠征軍都如此,其他的中國軍隊裝備可想而知。就是在如此艱苦卓絕的環境中,中國健兒與日寇血戰到底,豎起了一座座永放光芒的歷史豐碑。中華民族的英氣、骨氣、傲氣,濃縮在滇西的這座小城以及遠征軍這些熱血男兒身上,盡管他們中的很多人年齡很小,但小小年紀就被國仇家恨逼上了生死抉擇的戰場。
至于那座私立的紀念館,本身就是一個奇跡。身在銀行工作的段先生,窮畢生力量,搜集遠征軍的遺物,終于集腋成裘,聚沙成塔,蔚為大觀,一家蜚聲遐邇的民間抗戰紀念館由此誕生。其中,歷史實物很多,美軍吉普車,美軍和日軍飛機的殘骸,美、中、英、日各國的軍事裝備和武器,各種抗戰時期當地出版的報刊宣傳品,五花八門,琳瑯滿目,應有盡有。創建這樣一個抗戰民間博物館,不正是老百姓對那段難以忘卻的歷史的最好記憶和對遠征軍將士的最好緬懷嗎?
在騰沖,我對照著地圖,滿城轉悠,為的是尋找收復騰沖時戰斗最為慘烈的那個地方——英國領事館。當年,遠征軍在盟軍飛機掩護之下,與龜縮在這里負隅頑抗的日軍反復較量,血腥拼殺,反復拉鋸,幾易其手,最后全殲敵人。騰沖光復以后,一片焦土,幾乎沒剩下一座完好無損的建筑,千瘡百孔、彈痕累累的英國領事館,因為結構過于結實堅固,框架留存下來了。根據知情者的介紹,我得知這座建筑現在是騰沖縣糧食局的辦公地。于是,在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里,我沿著騰沖縣文化廣場后面一條喧嘩熱鬧、塵土飛揚、市井味道很濃的土路走過去,在糧油市場大院內,終于找到了這座在抗戰史上赫赫有名的建筑。不過,現在整幢建筑已經被密密麻麻的腳手架環繞了起來,正在整修,我只好隨便拍了幾張照片,算是到此一游。
開放的邊陲小城海納百川
在回賓館的路上,我再次經過文化廣場,發現縣城的文化氛圍很濃,博物館、文化館、圖書館、體育館一應俱全,全部環繞在廣場周圍。我逐一觀覽,甚至一時興起,進入騰沖縣圖書館,過了一把讀者癮。不用出示任何證件,也無需繳納任何費用,在報刊閱覽室,我盡情地翻閱報刊資料,長達兩個多小時。沒想到,這里的報刊資料很豐富,除了《騰沖報》、《保山日報》等地方報刊之外,竟然還有香港《大公報》,讓人不由得稱奇、贊嘆。小小圖書館,竟有如此廣闊的視野,超越了一般邊陲小城的閉塞,其開放性由此可見一斑。
騰沖,高黎貢山孕育出的一方人杰地靈的土地。高黎貢山是世界名山,有人說站在高黎貢山頂,一雙腳踩著兩個大陸,向東邁一步是亞洲大陸,向西跨一步是印度大陸,古往今來,南方絲綢之路和中印公路都穿越高黎貢山,從某種意義上說,高黎貢山就是騰沖的母親。高黎貢山與其他高山大川的不同之處,就在于它從來就是一個開放的山,多元民族聚居和多元文化薈萃的山。2400多年前,中國先民開辟的南方絲綢之路,即“蜀身毒道”,就是從四川的成都出發,經云南的大理、騰沖出境,進入緬甸、印度、阿富汗、伊朗等地。依托這條古道,騰沖開放較早。地理學家、旅行家徐霞客稱騰沖為“迤西所無”、“極邊第一城”。《騰越州志》載:“騰居天外,地廣土肥,十八省之人云集。”歷史上有“昔日繁華百寶街,雄商大賈挾貲來”的昌盛景象。民謠廣泛流傳“金騰沖銀思茅”、“琥珀牌坊玉石橋”,世界翡翠的90%以上曾在此地加工或聚散,因此,騰沖又被稱為“翡翠城”。由于騰沖是“南方絲綢之路上的最后驛站”,是“云南近現代工商業的發祥地”,是“跨國商幫的始發點和歸宿地”,是“恒河、伊洛瓦底江連接揚子江的環鏈”,是“東南亞、南亞、西域文化的窗口”,因而,歷史上的騰沖,是一個文化發達、商貿活躍、經濟繁榮的邊陲重鎮。
騰沖是馬幫出沒的山城,不靠海,卻擁有海納百川的開放氣度。騰沖的開放,表現得淋漓盡致,可謂無微不至。誰能想到,就是在騰沖的和順鄉,不僅擁有中國罕見的規模很大的鄉村圖書館,鄉民們一有空閑便會文質彬彬地進入這座優雅寬敞的圖書館讀書看報,擁有難能可貴的書香氣息,而且,這里還走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大眾哲學》的作者艾思奇。誰能想到,騰沖“走夷方”的傳統源遠流長,騰沖籍華僑華人和港澳臺同胞多達35萬人,分布在23個國家和地區。在和順鄉,意大利的文物、德國的器皿、美國的器械、日本的和服,并不鮮見。在抗戰最晦暗的歲月中,日軍從緬甸攻入騰沖,占領了縣城,卻投鼠忌器,沒敢在咫尺之遙的和順鄉造次,沒有放肆地進行侵擾和破壞,使得這里原汁原味的文化還有那古老的圖書館完好無損地保存了下來,與日軍對騰沖縣城的屠戮和搶掠形成鮮明對比。
漫步騰沖縣城,生活雖談不上浮華,卻總有那么幾分慢悠悠的安逸與閑適。騰沖人臉上總是洋溢著幸福而自信的笑容,翡翠店、木器店,鱗次櫛比,到處都是,出租車、摩托車,川流不息,無處不在,描繪的是和平中的生活圖景。走在騰沖街頭,偶爾還能見到幾個皮膚黝黑、形象迥異的外國人,一問,原來不是緬甸人就是印度人。我就曾經與一開烤肉店的緬甸密支那人和一看收費廁所的印度雷多人做過深入細致的交談,得知從騰沖縣城出發,沿著抗戰中修建的著名的中印公路(史迪威公路)前行,經猴橋口岸,即可出境,至密支那200公里,至雷多600公里。騰沖,是名副其實的邊境小城。
在騰沖的日子里,我走了足夠多的地方,看了足夠多的景致,足以打撈起一段在歷史長河中沉沒已久的往事。硝煙已經散去,我們仍然需要小心翼翼地聯綴歷史的碎片,是為了不讓那刻骨銘心的時光失落;歲月已經淡忘,我們之所以執著地收藏那場戰爭,是為了彪炳中華民族的正氣與勇氣;時代已經前行,我們再次打開記憶的閘門,重溫那一幕幕血色的歷史場景,是為了人類永遠不再有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