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彼此聆聽中追夢
○陳言
在彼此聆聽中追夢
○陳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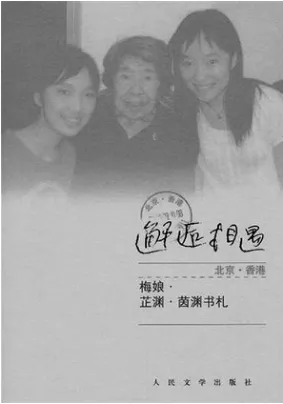
《邂逅相遇:北京·香港》,梅娘等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11月版
相差70歲的忘年交間的傾訴
名曰《邂逅相遇:北京·香港》的通信集中,邂逅相遇的雙方,一方是正處韶華的香港黃家小姐妹芷淵、茵淵,一方是年近百歲的內地老作家梅娘。
據悉,梅娘與香港黃家小姐妹結識于1990年代中期。其時芷淵充滿童趣的繪畫開始在香港刊物上發表,梅娘為芷淵的畫配以文字,合作的作品1997年在香港登場。相隔70歲的兩人開始互通信札。2000年,二人合作推出《大作家與小畫家》一書。十多年過去了,梅娘日漸衰頹,黃芷淵成長為鳳凰衛視的新丁。在中國船員湄公河遇難、泰國水災等重大事件發生的現場,她柔弱的面容、濃郁的深情、簡潔的報道吸引了眾多觀眾;受家庭氛圍的熏陶,妹妹茵淵亦有藝術天賦,時有繪畫作品發表,也成長為一名大學生。始終不變的,是姐妹倆一直用彩畫信箋給梅娘寫信。這一寫,就是幾百封。
信札涉及的話題廣泛。梅娘的信里,有介紹臘八粥、東北年始年末祈神的風俗民情,有講述塞外景觀、華北冬小麥的生長狀況,有對非典等社會事件的評介,還有對趙樹理、史鐵生等作家的簡介;而對“姑娘”、“閨女”等詞的解釋更是延伸到了封建社會男女的地位問題。當芷淵把給梅娘的郵寄地址誤寫作“海濱區”時,梅娘不厭其煩地給她講述“海淀區”的“淀”字的來歷。在分享姐妹成長的喜悅的同時,她也會告誡道:“芳華正茂的女孩,最怕的就是‘飄’,這會迷失人的根本而誤入歧途。”梅娘耐心聆聽小姐妹成長的煩惱,將人生的經歷、閱讀經驗用細膩、優美、明快的語言,娓娓談來,對小姐妹的純真心靈和勇于進取的精神熱忱贊揚,也會向晚輩流露出老之已至的苦惱。
梅娘的一生好像替近代中國人活了一遍
梅娘,原名孫嘉瑞,1920年出生于海參崴,是中國東北、華北淪陷區著名的女作家。1936至1945年間,她主要從事小說創作和文學翻譯,發表了大量的作品,在翻譯上也成績斐然。從梅娘淪陷時期的創作看,她在以細膩的筆觸反映女性受凌辱、受歧視命運的同時,多方探索了女性自強自立的途徑。悖論的是,盡管她的作品不涉親日思想,反而獲得日本文化殖民機構“日本文學報國會”設立的大東亞文學賞。
經過抗戰勝利后幾年的漂泊生涯之后,梅娘帶著兩個幼女及腹中的胎兒回到大陸。梅娘回到北京后,曾在中學短暫任職,教授語文;1949年10月加入北京市文聯和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1951年調入農業部,任農業電影制片廠編劇。1955年在肅反運動中,她被定為“日本特務嫌疑”,1957年被打成右派,開除公職,關進勞改農場。1961年解除勞教,成為無業人員。為了糊口,她在車站干裝貨車的重體力活、當保姆、刺繡,靠做各種粗活、累活、零工維持生計。1978年平反,回到中國農業電影制片廠。
作家梅娘將再次登場的舞臺選擇在香港。1979年,她以“柳青娘”為筆名,在《大公報》上一口氣發了11篇文章,廣涉科普、游記、讀書札記等多種題材。從1986年開始,她在大陸發表的作品恢復使用筆名“梅娘”。
1980年代以來,隨著淪陷區文學研究的逐步深入,研究者根據淪陷區中國作家的創作和言論,對其進行甄別,發現淪陷區文學豐富的內涵和多姿的面貌。梅娘,就是在這個歷史甄別過程中被當作出土文物重新發現、納入中國現代文學史的。
梅娘的一生好像替近代中國人活了一遍:1917年12月于海參崴出生后不久,街巷遍插英、日、美、俄多國旗幟,中國人遭到驅逐,她隨父母返回長春;始于長春的人生記憶插的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1928年12月張學良“改旗易幟”,換成了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滿洲國”時期每天上學要對著日本的方向升起象征五族和諧的五色旗;從日本戰敗到解放,青天白日旗變成了五星紅旗。政權頻繁更替與國土淪陷下的生存,注定不能平順。她又好似替女人活過了一遍,將女人有可能經歷的苦難疊加一身:幼時喪母、少年喪父、青年喪子/女、青年喪夫、中年喪子/女。作為一個新興實業家兼長春鎮守使女婿的庶出女,她享盡榮華的同時也飽嘗母愛缺失之苦。父親的去世、家族的沒落隳敗、家族羈絆與亡國奴命運反而催生了作家梅娘。屢次的政治運動,她經歷了生存臨界線上的種種殘酷,也一一承受住了。
如果說梅娘多難的青春時光無法與黃家小姐妹的韶華相互重疊,那么或許可以說,青春的梅娘是一直在與黃家小姐妹牽手前行的。因為芷淵借德國文學家塞繆爾·烏爾曼的話這樣來定義青春:“青春不是年華,而是一種心態;不是玫瑰般的臉龐、紅潤的嘴唇和敏捷的雙腿,而是堅韌的意志,豐富的想象力,以及無窮的激情;青春是生命深處的一股清泉。”三個追夢的人,給了我們很多暖意和潤感。
我們很需要長者的指導,更需要彼此傾聽的心靈
小姐妹中,芷淵寫得更多一些。她詳細描述了每一個學習階段的課程、內容,也就自然而然地讓內地人了解了香港的教育制度,而其中對于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習流露出深切的文化認同;她會傾訴一個女孩子成長的煩惱,也會關注內地社會事件,比如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汶川地震和奧運會等,而對社會的關注是否對芷淵后來的擇業有潛移默化的影響?芷淵對梅娘提出的問題會琢磨、回應,而她回應的方式也很特別,除了直接答復,也會通過講述自己的閱讀經驗來增加人生經驗。比如咀嚼殷海光所說的文化蛻變時期年輕一代心靈的失落、脆弱和不凝練問題,比如用蘇格拉底說的“未經檢視的生活不值得去過”,比如通過閱讀《藝術與哲學》、《藝術問題》等著作,來反省自己是否有創新的勇氣,等等。
她們共同探討張藝謀的電影和藝術家的擔當,梅娘每每提及的“哀民生之多艱”與悲天憫人的情懷,到了芷淵那里,則化為一個新聞人對那些沒有選擇地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市民命運的關注。當我們艷羨黃家姐妹的成功和順遂——芷淵在高中階段是香港領袖生計劃的代表,獲選香港“十大杰出學生”;2011年5月,入職鳳凰衛視——的時候,可否想過、并且驚嘆她倆小小年紀,就懂得用心傾聽長者的成長經歷、教誨、讀書經驗,滿心歡喜地分享長者的憂樂?有多少孩子從幾歲起就懂得耐心傾聽,能夠聰明地利用他人的人生來豐富自己的人生的?她倆做到了,所以在追夢的道路上少走了很多彎路。
從某種意義上說,梅娘是個自我流亡的人,在人生的多個階段,會從所謂的“主流文化”、“中心文化”、“霸權文化”以及男性中心文化中自我放逐,然而她從來不放棄對美好人性的追求。誰說夢想僅僅屬于青春年少者?再讀這一封封淳厚、樸直的信札,我在想,人生也許并不需要太多的微言大義,然而如果預備在矛盾復雜的人生里健康地活下去、自由地追夢,我們的確很需要這樣的長者,更需要彼此傾聽的心靈。
梅娘當初打算出版這本通信集,就是基于兩地不同的歷史背景下形成的迥異價值取向和審美追求。梅娘以為,黃家姐妹的成長歷程,將會成為內地青年成長的參照系數,也會幫助她自己重疊青春。反過來,自己的經歷或是黃家姐妹進入自己深感隔膜的中國近代歷史、反觀自身的絕佳途徑。
(本文編輯 謝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