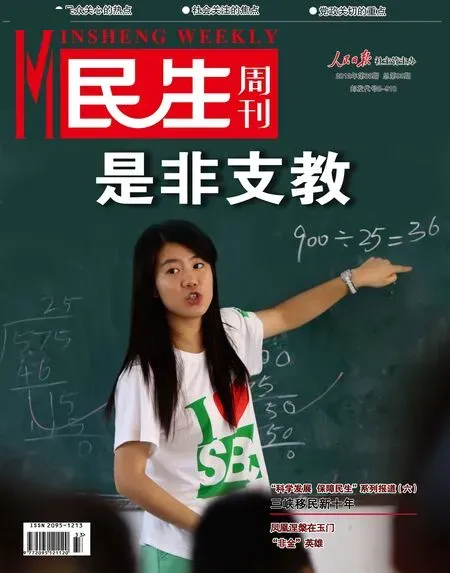鳳凰涅槃在玉門
□ 本刊記者 苑二剛
鳳凰涅槃在玉門
□ 本刊記者 苑二剛
甘肅省玉門市是中國石油工業的搖籃,中國第一口油井就誕生在這里。但是隨著石油產業的逐漸萎縮,玉門市不得不經歷“遷城之痛”,靠轉型尋求重生。作為“世界風口”,玉門風電自然擔起了轉型的重任。從昔日的“石油之城”到今日的“捕風之城”,玉門在遷城轉型中獲得了重生。
沿312國道向西北方向前行,綿延幾百公里的戈壁灘上,拔地而起的風力發電機巨大的葉片靜悄悄地隨風緩緩轉動,形成一道美麗的風景線,給沉寂的戈壁增添了幾分生氣。
為使風電1500萬千瓦的近期目標得以實現,甘肅玉門市發改委主任高生文和能源辦主任趙敏幾乎每天都在玉門、酒泉和各大風電場之間來回奔波。
“很辛苦,但很有意義。”豐田越野車呼嘯著穿過高聳林立的一排排風機,高生文遠眺著窗外綿延不斷的祁連雪山,一臉的喜悅。
“陰風蔽日天無色”,清代詩人馬爾泰筆下的玉門風沙足以讓人震撼。現在,對玉門來說,這些風沙卻已成為寶貴的資源。
九年前,石油產業的迅速萎縮,讓玉門不得不遷城尋求重生。而最終,玉門的“綠色發展”被認為是上天賜予的機會。2011年,全市實現地方生產總值125億元、工業增加值73億元,分別較2006年增長91%和65%;年內風電裝機突破200萬千瓦,玉門入選“全國綠色能源示范縣”和“全國新能源產業百強縣”,新能源產業成為玉門經濟轉型的主導接續產業。從昔日的“石油之城”到今日的“捕風之城”,玉門在遷城轉型中獲得了重生。
遷城之痛
玉門老市區老君廟坐落的山溝里,至今仍舊能在斷流的河水表面看到漂浮的黑色“油花”。1939年,正是在這里,國內外地質學家們發現了中國第一口油井。而今,油井仍在,繁華已成過往。
2009年3月6日,這天讓玉門人心情異常復雜。這一天,國家公布了第二批資源枯竭城市名單,玉門名列其中。宣告資源枯竭,意味著從此能享受到國家的優惠政策和資金扶持,同時也意味著依靠石油的優渥生活一去不復返。 玉門的經濟重心必須調整,轉型在所難免。
這個因油而生的城市,高峰時期的人口總量曾接近29萬,經濟總量的65%、財政收入的60%、工業產值的75%都來自石油。
半個世紀后,伴隨著玉門油田的儲量下降,玉門油田辦公及生活基地一并遷至酒泉,玉門市只作為生產作業區。曾經的輝煌成為向前發展的負擔。2003年4月,國務院向甘肅省政府發文, 批準玉門市遷址,遷回曾經的玉門鎮。
從這一年,2.5萬名油田職工和近6萬名家屬不得不離開玉門市,遷回70公里外、1957年玉門建市前的老玉門鎮。30多家依賴油田生存的企業破產,數萬人失業下崗,轉型之痛侵襲著政府、企業乃至每個市民。 在接下來的數年間,又有9萬多玉門人從曾經繁華的玉門老城遷出。城中基礎設施老化,大量建筑變成廢墟。
“無論是移民,還是搬遷,在那個時期對玉門來說都如雪上加霜”,玉門市老市區管委會副主任高建海說,“遷走5萬人,遷進5萬人,遷走的是有消費能力的,遷進的是連生產資料都不完備的移民。”
就業困難也是當時最為嚴重的社會問題。2004年,玉門油田生活基地搬遷以后,玉門市7000多名石油三產工人失業下崗,加上原玉門石油管理局有償解除勞動關系推向社會的6331人,全市累計失業、待業、下崗人員超過1.5萬人,這其中還未包括1.3萬左右的困難群眾,這給玉門市的重建工作帶來極大的壓力。
失去石油稅收以后,玉門市開發區前期建設的大部分項目基本上都是靠貸款、借款、集資或施工單位墊資完成的。2003年底,玉門市財政滾存赤字達4061萬元,政府債務累計達1.18億元。
“老城搬遷,新城建設,安置就業……百廢待興,處處都需要錢,每天都有要賬的,我都不知道那段時間是如何熬過來的。”時任市長、現任市委書記雒興明回憶起2006年老城完成搬遷之前那段日子,感慨萬千。
老樹新枝
從嘉峪關開往玉門老城的班車繞過巨大的“鐵人”塑像,緩緩停在路邊。夏日的無限生機反襯得玉門老城那寬闊的主干道格外冷清。道路兩旁的電線桿和各種建筑管材東倒西歪,建筑物門窗大多用磚瓦封起,玻璃殘破不堪。醫院、學校、飯店、旅館、商鋪大多閘門緊鎖,間或能聽見里面傳來的犬吠聲。車過解放路上一個沒有紅綠燈的交通崗亭,過往的車輛開始多些,主要是石油管理局接送員工的藍色大巴,還有肆意穿行的灰色小面包車,招手即停,一元錢的價格代替公交。
相比昔日的繁華,玉門的老城雖顯得冷清,但并沒有失去希望。玉門決策者們也從沒想過放棄老城。
統計顯示,玉門老城搬遷留下50萬平方米的房屋,占地300萬平方米的設施。這些總價值近3億多元的資產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一直在閑置。“利用閑置資產招商引資,玉門找到了一條發展的路子。”高建海副主任說,從2005年起,玉門老市區一刻都沒有停止過招商。
“玉門石油資源地位的下降,在國家層面來說,影響幾近于無。但在地方,石油仍然是財政支柱和經濟支柱。在河西走廊整個區域內外,石油仍然是玉門的優勢。”玉門市政協主席張勇表示。
玉門新紀元石化公司現在的廠房是原玉門油田的俱樂部,在偌大的生產車間,記者見到了該公司總經理黃元。他告訴記者,這個車間以前是個大禮堂,如今稍加改造,就成了兩個適用的生產車間。
黃元說,“公司開發和生產石油下游產品,當初來這里投資就是看中了現成的廠房和一些比較完善的基礎設施,節省下的3000多萬元直接用在產品的開發上了。”
和新紀元一樣,許多企業看中的是玉門老市區現成的廠房和優惠政策。7年來,玉門市盤活了老市區的資產,建立了石化、建化、高新技術三大工業園區,在全力支持石化產業做強做大的同時,培育并形成了電力、農副產品加工、建筑建材、礦產品采選冶煉等產業,形成規模以上工業企業107家,初步構建起了地方工業經濟新體系,老工業城又煥發了新的活力。
“捕風之城”
搬遷是解決生存問題,轉型是解決發展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轉型甚至比搬遷更重要,意義更重大。
2008年的金融危機,讓國家開始重新調整能源產業政策,對風電等新能源寄予無限希望,并投入巨資,輔之以鼓勵新能源發展產業的多項優惠政策。這讓玉門人看到了新的發展機遇。
南倚祁連山,北望馬鬃山,浩瀚的戈壁在兩山間形成峽谷,地處其間的玉門于是成了有名的“世界風口”。根據當地氣象部門30年資料評估分析,這里被劃定為風能資源豐富地區:境內平均風速超過3.5米/秒,70米高空平均風速7.9米/秒,平均風功率密度506瓦/平方米,年有效風速時數8085小時,年滿負荷發電2300小時。
因為石油枯竭而搬遷的玉門,格外重視上天賜予的新能源,也格外珍惜這次新機遇。
圍繞風電開發,玉門市政府幾乎動用了所有可以調動的資源、時間和人力。記者采訪期間,玉門市市委書記雒興明正趕往南方考察風電企業項目,而發改委新能源辦公室主任趙敏則告訴記者,她已經連續幾周撲在風電場,沒有休息了。


左圖:“鐵人”王進喜是玉門人的驕傲和精神偶像。圖為甘肅省大學生志愿者在王進喜塑像前宣誓。
右圖:近年來,玉門新城采取新建、接管、維修的辦法,加大保障房的建設力度,為困難群眾解決住房問題。圖為玉門市新建的廉租房。
新城20公里開外,1.5兆瓦的風機整齊地豎立在原本荒蕪的戈壁灘上。2009年一年,玉門風電發展迅速,其風電裝機容量超過了前12年的總和。按正常稅收計算,玉門每年可實現稅收1.8億元。
上更多的項目,建更多的風電場,似乎成了玉門新城自我救贖的唯一出路。中節能、大唐、華電、中海油等國內主要風電企業,都在這里開建或者正在建設風電基地。
該市發改委主任高生文告訴記者,從1996年到2011年年底,國電龍源、大唐、華能、中電國際、華電、中節能、中海油這7家“國字號”電力企業已在玉門注冊了9個風電運營公司,在玉門的三十里井子、低窩鋪、昌馬、黑崖子、七墩灘等地共計建設了11個風電場,安裝1000臺以上的風電機組,總裝機容量已達到200萬千瓦。
玉門清潔能源工業園區,是甘肅省提出的建設千萬千瓦級河西風電走廊的重要基地,也是全國五大風電基地之一。當地規劃建設500萬千瓦的裝機容量,占到了河西風電走廊的半壁江山。
風電似乎成了玉門轉型的代名詞,談轉型必談風電。風電,擔起了玉門轉型的重任,也被玉門人寄予了更多的期望。
然而,一個必須考慮的現實是,目前國內風電企業普遍處于微利狀態,玉門風電所依賴的西北電網建設和升級仍然滯后。與同樣發展風電的新疆、內蒙古相比,甘肅風電資源沒有新疆好,起步也較晚。風電產業目前沒能為玉門帶來現實的財力。但這些困難并沒有阻礙玉門人前進的決心和方向。
“新能源是國家未來發展的方向,玉門利用自身得天獨厚的條件發展風能也絕對是未來發展不可動搖的方向。”市委書記雒興明十分堅定地說。
雒書記這一態度也幾乎是玉門上上下下所有人士的共識。盡管風電的未來尚有不明朗之處,但玉門在焦灼地等待著這些風電產業早日產出“金蛋”。這一心情, 絲毫不亞于1998年,在玉門油田儲量逐漸衰竭的時候,人們等待鉆井工人鉆出青西百噸高產油井時的迫切之情。
中心愿景
距離老城區70公里之外的玉門新城,在西風中迎接著玉門的未來。
徐生宏在新市區的步行街上開了一間二十多平方米的小超市。7年前,他選擇“下山”,從玉門市老城遷到了新城。2005年,他以500元/平方米的價格,買了一套緊靠步行街、80平方米的住房。如今,這里的房子已經漲至1000元/平方米。
沒事的時候,徐生宏最喜歡在新城里溜跶,去看看火車站建設的進展,再看看新廣場建設得怎樣了。
“人越來越多,房子也越建越多,城市越來越漂亮。”這是徐生宏對這個城市最直接的感受。
走出困境后的玉門市“雙輪驅動、兩翼發展”,加快建設新市區,鞏固發展老市區,新老市區一體化發展,使兩個小城建設與經濟發展實現良性互動。如今,來自甘肅少數民族地區和貧困干旱地區的移民以及玉門周邊鄉鎮農民,都在逐漸向這個新城匯集。
玉門市政府計劃在2020年前,玉門經濟要立足石油資源開發,振興年產值百億元的石化工業基地;立足風電水電開發,打造百萬千瓦清潔能源基地;立足礦產資源,建設年產值超50億元的化工基地;立足特色農業,壯大農副產品精深加工基地。
“把新市區建成蘭新線上嘉峪關至哈密段的一個接力站,逐步實現縣域經濟與‘酒嘉經濟帶’和‘西隴海蘭新線經濟帶’的對接,使玉門成為絲綢之路西端輻射周邊100公里范圍的新型中心城市,成為河西走廊的經濟中心。”雒興明向記者描述他對這個城市未來的設想,這也是他自己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