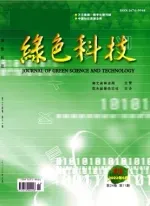透視地域性住區空間環境與鄰里交往——對廣東省肇慶市城區居住區的調查
盧素英,章美玲
(1.肇慶學院 生命科學學院風景園林教研室,廣東 肇慶526061;2.上海深圳奧雅園林設計有限公司,上海200052)
1 引言
鄰里交往是居住環境和社區生活中重要因素之一。城市化進程的高速發展使得鄰里關系被大大削弱[1];隨著城市居民生活節奏的加快,人們可以在工作、學習以及其他社會環境中獲得所需要的社會關系,這也是鄰里交往重要性被削弱的另一原因。然而,事實上阻礙現代居住區鄰里交往的除了上述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居住區空間的營建不夠合理,使得小區規劃忽視了社區感和家居感。城市住宅從過去寬敞自然的住屋形式演變為現代高度密集的“鴿子樓”形式,僅僅解決了人們生理上的需要,卻忽視了鄰里交往的社會生活質量。有限的居住區外環境,正是現代居住區鄰里交往的重要渠道及物質載體,因此居住區戶外交往空間的設計與居民鄰里間的交往有著密切的關系。
2 鄰里交往與地域性
2.1 鄰里交往與地域性內涵
鄰里是1915年Robert E.Park首先提出的概念,后由佩里發展為鄰里單位理論。盡管鄰里包含一些密切住戶社會交往的思想,但它更強調居住的物質方面。直到二戰后Milton Kolter關于“鄰里”的理論才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他認為鄰里是與居民關系密切、非常熟悉、經常使用而認為是“自己”的區域,其邊界因為個人愛好、年齡、文化、職業的不同而呈現出不固定的“游移”狀態[2]。在這里我們主要是指從居住空間鄰里交往自然發生的自愿行為的交往。
所謂“地域性”從地理學角度來講,主要包括地理環境、外部社會環境兩方面。根據人地關系互動理論,居住區建設也有明顯突出的地域性特征。一方面因為住區成員單位、群體的不同會形成不同的社會空間;另一方面因為居住區地理環境及地理位置差異會形成不同的地域空間。
我國居住區建設與國外相比有較大的區別,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居住區建設。由于地域性的差別,我國城市化存在著地區發展不均衡情況,這在沿海地區表現得尤為突出,在這些地區的住區建設中,城市居住問題也隨之突顯出來。概括地說有兩點問題:首先是以高層為主的城市居住區人口密度大、制約條件多與穩步提高的居住環境質量之間的問題;其次是廣東沿海地區因為改革開放的沖擊,從全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遷移進來的居民較內地的多,再加上外來務工的流動人口,從某種程度上切斷了原有社會網絡、人際交往環境、社會支持系統等,使商住區居民同質性降低,社區文化開始貧乏,歸屬感減弱。種種原因給社區管理、社區環境、鄰里交往等帶來了一定的影響。這類問題的解決遠非建筑師、規劃師所能做到的,但也并非無能為力,可從環境、規劃方面給鄰里交往營造空間,使得社區環境更加完善。
2.2 肇慶居住區地域背景及發展
廣東省肇慶市地處發達的珠三角地區,享有著“國家歷史文化名城”、“首批中國優秀旅游城市”、“國家園林城市”、“中國硯都”之美譽,2006年又被國家環保總局認定為“國家環境保護模范城市”,因此被形容為有著“西湖之水,陽朔之山”的“一方秀土”。2009年廣佛肇城際輕軌全面開工,為廣佛肇1h經濟圈的開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城際交通的迅速發展,“城市邊界”的日漸消融,使“工作在廣州,居住在肇慶”成為可能。肇慶的眾多美稱及其不可復制的自然資源和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使其房地產行業迅速發展。有著“珠三角后花園”之稱的城市如何著手共建美好的人居環境、創建和諧的鄰里空間,將是規劃者的首要任務。
3 肇慶城區鄰里交往空間調查現狀
鄰里交往的成因由多方面因素影響,研究人們通過何種方式認識鄰居或住區其他居民有助于我們了解鄰里交往產生的機制,從而通過一系列規劃設計手段強化這一機制,進而有助于交往的形成[2]。為了從總體上把握居住區居民鄰里交往現狀及居民期望的鄰里空間,本次問卷調查以肇慶市端州區有代表性的8個商業居住小區為例,其中每個小區發出問卷65份,共520份,組織2008級園林的學生分為8組分別對8個居住區進行調查,探討特定地域背景下的住區園林環境對居民交往空間的影響。時間上主要選擇在下午5~7點,分3天進行,分別選擇工作日和周末休息日進行調查。問卷中主要涉及性別、年齡、職業等對鄰里交往的影響,居民交往途徑,小區戶外環境與鄰里交往的關系,居住區道路設置與鄰里交往等方面。
3.1 性別、年齡、職業與鄰里交往
對8個小區520份的居民問卷調查中,男女比例基本持平。年齡段主要分為:1~12歲、13~18歲、19~26歲、27~45歲、46~65歲及65歲以上;從問卷結果中發現:從戶外休憩活動頻繁、鄰里交往頻度總體上說女性高于男性,并且以46~65歲年齡段的居多;交往途徑通常是因為遛寵物、散步、閑坐休憩或照顧幼兒。1~12歲的兒童主要分為3個階段:1~3歲一般有家庭直接看護,其活動范圍及地點很大程度上受到看護者的影響;4~6歲入幼兒園的幼兒已經有一定的自主性,中小學生對環境的選擇相對有更多的要求,但主要是尋找年齡相仿的伙伴玩耍。兒童對環境的感受——鄰里關系、安全感、舒適感等表現并不敏感,但游戲是他們的天性,對戶外活動的熱愛更是其他年齡群的人們無法比擬的。中青年雖然是住區的主要居住者,但正職壯年的他們既要成就自己的事業,又要培育下一代,有時還需要照顧長輩,閑暇時間較少。由此可以看出,老年人和嬰幼兒對住區環境利用率較高,而且中青年也往往是因為老年人或孩子的關系與鄰里發生交往。
從職業的角度看,不同的社區居民的職業構成有所不同,調查起來相對較為復雜。調查中發現教育工作者、行政機關等事業單位的居民對居住區的環境及鄰里交往要求更為迫切;而對于私營企業、個體或工作時間不固定的居民來說,大多對鄰里交往、社區環境持“不反對”意見。
3.2 居民戶外休憩活動的時間特征與鄰里交往
問卷中涉及居民一天中在小區戶外進行戶外活動經常是在什么時間段。8個小區中調查結果大致相似(表1)。從調查結果可知,居民到戶外活動、休憩選擇在傍晚(16~19點)和晚上(19點以后)的居多,而選擇中午(11~13點)和下午(13~16點)兩個時間段的相對較少。

表1 居民一天戶外活動時間分布%
3.3 鄰里之間發生交往的主要途徑
現代的商業居住小區——特別是最近幾年新興的居住區,如中源名都、錦繡萊茵、嘉湖新都市等,居民通常是來自不同單位、不同地域,加之肇慶的地理位置屬于相對發達的珠三角地域范圍,每個小區居民基本屬于各個地區的大融合,在問卷中還設置了關于居民鄰里交往及認識的途徑(表2),調查中發現在8個小區中的結果基本上是一致的,最可能的認識方式是“經常碰面”和“戶外休憩、溜寵物”,其次是“通過孩子”,出乎意料的是通過“戶外環境鍛煉”方式認識的機會相對較少。這也證實了日本學者應用社會測量學方法對鄰里關系進行的調查結果:鄰里關系的密切程度符合社會心理學的“鄰近性”原則,即住得近的人容易成為朋友[2]。

表2 居民鄰里交往途徑分析 %
3.4 鄰里交往與社區園林環境
此次調查的目的即社區園林環境、地域性差別對鄰里交往的影響,筆者此本次問卷中重點調查了居民對所居住的居住區園林環境的看法、要求以及期望有什么樣的空間場景等(表3),8個小區的調查結果也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期望“優雅舒適的戶外環境能促使更多的人到戶外,激發鄰里交往”的均在50%以上,其次是居民認為鄰里交往與居住區園林環境關系密切,戶外活動場地是交往發生的主要場地。這說明居民期望通過合理利用室外空間、改善園林環境以促進鄰里交往的發展。為進一步了解園林景觀中各景觀要素對鄰里交往的影響,調查中還了解了居民渴望在小區環境中有什么樣的景觀要素、景觀場所等(表4)。

表3 鄰里交往與住區園林環境關系 %

表4 園林環境景觀要素對鄰里交往的影響 %
根據表3的調查結果可知,居民期望通過改善戶外園林環境來彌補鄰里之間交往機會的不足,從表4的調查結果可以看出,每個小區的調查結果基本是一致的,其中,最迫切的期望是“有較多的休閑空間和設施”,其次是“有可以供許多人共同活動的設施”;這兩方面的訴求加起來幾乎占每個小區調查中的65%,這也印證了楊·蓋爾所說的“與駐足停留對物質環境的要求相比,步行和小坐的要求更多,也更綜合性”。從某種意義上講,停留可以看做步行狀態因某種原因而中止,而且是可能發生的小坐行為的必然起點。
3.5 鄰里交往與住區步憩空間
楊·蓋爾在《交往與空間》中曾提到:步行首先是一種交通類型,一種走動的方式。但步行的目的有多種,如因公務而步行、觀光或散步等,但步行交通的特點從生理和心理的角度決定了對物質環境的一系列要求[3]。居住區中的“步行”不能單純地看做一種“交通類型”,而是身體和心理放松狀態的低強度活動,即可以稱之為“步憩”。步憩行為是步行過程中對環境信息把握的過程,也是發動視覺、聽覺、嗅覺等各種感官去體驗空間的過程,同時也是尋找興趣的一個過程。因此居住區中道路空間的處理對居民戶外活動也起著一定的影響。作者在問卷中設置了關于小區道路建設對鄰里交往的影響,題目是:“從實現更好的鄰里交往的角度,您認為小區道路需要做哪些改進?”(表5),從8個小區的調查結果顯示,平均有40%的居民期望在居住區道路兩旁適當布置休息空間和休憩場所,同時有30%以上的居民期望改善道路兩旁的綠化以吸引居民停留腳步。這也說明了步憩過程中的停留需要某種條件,即適當的休憩空間及設施和優美的環境,如圖1所示,可在小游路上設置與環境融合的花架,供步憩者停留下來小憩或欣賞景觀。

圖1 小區道路空間

表5 小區道路建設對鄰里交往的影響 %
4 調查結果分析
此次問卷調查主要涉及16個問題,基本都是圍繞住區園林空間構建對鄰里交往產生的影響問題展開的。從調查結果可以看出,居住區的園林環境建設能促進鄰里間的交往。為了提高住宅設計水平,促進肇慶城區住區環境的發展,改善居民交往現狀,根據調查結果得到以下幾個觀點。
4.1 突出住區園林風格及地域識別性
特定地域的物質和精神形態,是在特定環境的條件下,長期以來所形成的“氣質”——這種與生俱來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使人們能夠區別一個地方與另一個地方,喚起公眾對特定地方的認知[4]。居住區環境建設中園林風格及喚起居民對居住環境場所的識別性是不可缺少的。所謂園林風格,能反映地域性差別,補充居民對環境的識別性及歸屬感。肇慶地處珠三角地帶,具有著豐厚的嶺南古典園林氣息,又加上其獨有的歷史文化,為其住宅文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熟悉的、可識別的地域園林文化能吸引居民走出居所享受戶外環境,為鄰里交往提供可能。
4.2 開辟住區休憩娛樂場所,為居民提供交往場地
4.2.1 加強宅旁綠地場所開發
從交往途徑看,“同一棟樓經常碰面”幾乎是所有情況下都處于第一位途徑,這表明,在規劃設計中創造使住區居民能經常碰面的機會和可能性,對促進住區鄰里的形成、改進交往環境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加強宅旁綠地建設可以為“就近”的居民進一步接觸、交流提供場所(圖2)。

圖2 宅旁休閑綠地
4.2.2 加強點、線、面結合的“多義景觀場所”建設,營造動、靜結合的流動空間
從調查結果可以看出,住區步憩空間建設對鄰里交往有著一定的影響,其中要求在“道路兩旁布置休息空間和休憩設施”的,在8個小區中均占35%以上;同時50%以上的居民認為舒適優雅的園林環境能促進居民之間的交往;從交往途徑看,除了“同一棟樓經常碰面”外,“戶外閑坐、休憩”、“散步、溜寵物”等也是最可能的認識方式(圖3)。

圖3 戶外休閑場所
以上幾個因素表明,住區景觀環境是以視覺為主要感知途徑,以休憩環境的美學功能為價值取向的。因此,住區環境景觀建設中盡量加強線形道路、點式小憩與面式綜合休憩空間,營造具有多種使用可能的流動的“多義景觀場所”。
4.3 注入住區文化建設,促進住區鄰里交往
在問卷調查過程中,通過與居民聊天還發現,居民除了對實質環境方面的追求之外,營造和諧、有序、賦予歸屬感的社區空間也是他們一直以來的愿望。根據肇慶的地域特點及人口特性,應在居住區中營建反映地域生活的空間環境,創建有肇慶特色的各類文化設施,如地區性文化雕塑、鄉土植物、文化宣傳、體育、娛樂活動等,也是增加鄰里交往、增強社區歸屬感的重要途徑。
[1]徐磊青,楊公俠.環境心理學[M].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2.
[2]杜宏武.珠江三角洲住區休憩環境設計[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6.
[3]楊·蓋爾.交往與空間[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2.
[4]楊茂川,王 琛.城市公共空間的地域特色與可識別性[J].江南大學學報,2006(12):117~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