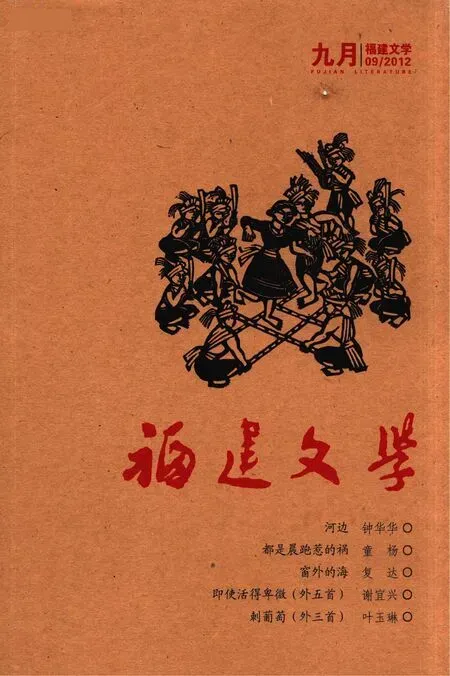哈密瓜情緣
曾 珊
朋友、熟人或同事只要聽說我曾在新疆哈密工作過,馬上就會很自然地聯想起哈密瓜,“哈密啊,好地方哦,呵呵,那可是產哈密瓜的地方!”瓜以地名,地以瓜聞,的確如此,哈密早就因出產哈密瓜而聞名遐邇。
我對哈密的最初了解,也是從哈密瓜開始的。記得上中學時,語文課本里有一篇文章叫《哈密瓜的故鄉》,寫的就是關于哈密瓜的故事。文中描寫了哈密瓜名稱的由來、哈密瓜故鄉的爭議、哈密瓜栽培技術、哈密瓜的種類以及品嘗哈密瓜的美妙口感哈密當地少數民族風土人情。這使我很早就向往那神秘的地方和那神秘的瓜。后來我毅然遠赴大西北新疆哈密當兵,多少受了這篇文章的影響。
記得我剛參軍那會兒還是初春,離哈密瓜上市的日子還早。每當老兵們提起吃哈密瓜,那眉飛色舞的表情,都會讓我們新兵更加對哈密瓜朝思暮想,垂涎三尺。真盼望夏天早些來臨。
我第一次嘗哈密瓜,是在入夏的一天晚飯后。連隊通知我們到食堂去領哈密瓜,新兵們歡呼雀躍,三蹦兩跳地就往食堂奔去——哈哈,每個人都分到了五六個哈密瓜。注目細看,那哈密瓜外表黃綠相間,中間大兩頭小,看上去像個橄欖球,瓜的皮表癩了巴幾的,橫一道紋豎一道紋,皺皺得像個烏龜殼。老兵們說,這是“炮彈瓜”,是哈密瓜的一種。這種瓜,皮越不好看越好吃!大家都忙不迭地把自己的瓜切開,一會兒就擺滿了一大桌子,黃瓤的、橙瓤的、綠瓤的,吃起來脆生生、甜絲絲的,還略帶一點甘草味,口感很爽也很特別。一時間,你吃吃我的,我嘗嘗你的,就像是在開一場盛大的哈密瓜宴。呵呵,在哈密第一次吃上了哈密瓜,終于遂了我的心愿,我樂不可支。
要想真正體驗到哈密瓜的甜蜜和美妙,那就得嘗一口被老哈密人稱為“蜜極甘”的哈密瓜。“蜜極甘”個頭沒有“炮彈瓜”大,表皮黃中帶青,光滑且色澤鮮亮,一刀劃下去,粘粘的瓜汁便順著刀刃流淌下來,那瓜瓤是翠綠色的,肉質嫩嫩的,還沒進口就已讓人垂涎欲滴。一口咬下去,感覺柔柔的,瞬間蜜糖般的瓜汁就糊滿了你的嘴。那個甜真是沒法形容,我平生從沒吃過這么甜的瓜。
在哈密工作的那些年,我每年都會把哈密瓜吃個夠,以致到后來我都被哈密瓜甜“怕”了。
離別哈密,我回南方后,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吃過哈密瓜。近些年來,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交通的便利,哈密瓜在我們南方的水果攤和酒樓的餐桌上已司空見慣,人們在茶余飯后吃上幾片哈密瓜,已不再是什么稀罕事。我卻始終沒能再找到在哈密吃哈密瓜的那種甜蜜感。我盼望能有機會重溫當年那些個甜蜜的舊夢!
前些年夏天,我終于得到一個去新疆的差事。重回哈密的那天晚上,我就近下榻在火車站附近的賓館,安頓停當后,我就急不可耐地匆匆奔向街頭。火車站周邊路口上有許多維族小攤販正套著毛驢小板車在兜售哈密瓜。
在哈密工作那些年,我多少也學會了一點維族方言,如“喲勒達喜”,大意是“同志”或“老鄉”;稱小男孩為“巴郎子”;表示“不高興”或“生氣了”,就說“肚子漲”。
我走近一個維族老人家的小板車前。老人家身邊倚著一個十來歲的“巴郎子”。小板車上擺放著大大小小一車黃燦燦的哈密瓜。
“嗨,喲勒達喜,巴郎子,你們好!”我上前跟老人家和小男孩打著招呼。“這瓜怎么賣啊?多少錢一公斤?”
在新疆計量單位是按公斤計算的,這與內地不一樣。內地的一斤是指一市斤,而新疆的一斤是指一公斤。
“巴郎子”伸出一個食指。
“嗯,不算貴。”我在心里想。一公斤十塊錢,一市斤五塊錢,我們南方市場上的哈密瓜好像也是這個價。
“有蜜極甘嗎?”我問道。
“有呢。”老人家拖過來一個藤筐,“這個嘛,自己地里種的呢。”
“給稱一哈(下)嘛,多少錢的呢?”我挑了一個約五市斤左右的金黃色的小哈密瓜,拿出三十元錢遞給老人家。
老人家沒有接錢。“巴郎子”沖我笑了笑,還是伸出一個手指頭。
“一公斤一塊錢?”我有點疑惑了。
老人家笑了,一字一句地告訴我說:“一個嘛,一塊錢。”
我有點吃驚:“這是蜜極甘嗎?”我心里打著嘀咕。
“放心的很呢,真…真的蜜極甘!”老人家一本正經地說。
“我們嘛,老哈密的呢,如果不甜的呢,我們嘛肚子漲!”我想跟老人家開個玩笑。
老人家習慣地拉長了音調說:“你嘛,拿回去嘗一哈(下),甜得很…很的!”
這瓜的價錢使我感到很意外。在我們南方海邊城市那兒,今天這個瓜少說也得賣二三十元啊!呵呵!現在只要一元錢!
我興高采烈地把一元錢的“蜜極甘”抱回賓館,順著瓜兩頭的紋路用小刀把瓜拉成一片一片的月牙形,然后就迫不及待地啃了上去。哇,一股蜜糖般的瓜汁頓時溢滿了我的口,濃濃的瓜汁使我的口腔里感到黏黏的,兩只手也仿佛涂了一層薄薄的膠水。我好久沒有吃到這么甜的哈密瓜了,一塊又一塊,不一會兒,居然把那個五斤的“蜜極甘”全部吞進了肚里。舊夢重圓,我感到心滿意足。看著滿桌狼藉的哈密瓜皮,回想起剛才的不雅吃相,我不禁自嘲地搖了搖頭。
那天夜里,我的肚子真的漲得很,但我睡得很香,很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