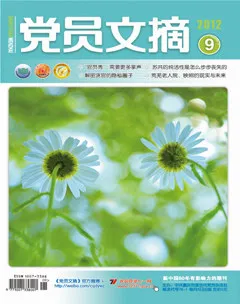外企里的黨支部
劉俊 方可成 賈雪梅 楊健 張博嵐 姚雪鵬
很多外企意識到: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黨團員扮演了重要角色。黨支部是一種建立聯系的方法,可以讓外企更好地了解共產黨,然后可以將公司的工作和黨考慮的事情聯系起來
以“承諾到家”、“關愛到家”、“積極到家”為價值觀的家樂福,最近提出了“和諧到家”的新口號。2012年6月26日,家樂福在北京舉行“和諧日”活動,一個重要環節是:成立北京家樂福黨總支、團委。
在華外企的黨建工作至少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北京家樂福算是趕了個晚集。但作為世界知名的大型外資零售企業,家樂福成立黨團組織,被輿論視為外企日益本地化的風向標。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在華外企建立了工會和黨團組織。
自上世紀80年代外企重新進入中國開始,中西方不同的企業和政治文化,經歷了怎樣的磨合過程?
曾經吃了不少閉門羹
相對于國企齊備的基層黨組織,外企的黨組織要薄弱得多。2010年,商務部一項涉及16.5萬多家外企的調研表明,只有1.4萬多家外企建立了黨組織。
外企陸續設立獨立的黨組織,是上世紀80年代后期的事。1990年,第一家入駐上海浦東新區的世界500強企業杜邦,在上海外企中最早成立了黨組織。但雙方意識形態的鴻溝不言自明。
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師唐睿說:“很多外企按照在本國的理解,認為政黨就是一個競選組織,于是不準政黨類組織或者競選類組織在企業內活動,害怕影響企業。他們覺得政治組織是另一種利益組織,而企業是創造利益的組織,二者不搭調。”
上世紀90年代初,北京市外企黨建工作剛開始時,主管部門的黨務工作人員拜訪外資企業管理者,常要提前半個月或一個月約定日期。到了約見日,往往還要坐冷板凳等上大半天,甚至吃閉門羹。見面時,外方聽說要在企業成立黨組織,通常十分不解。一個美國老板甚至提出:我們現在有三位共和黨員,可不可以也申請成立“共和黨支部”?
廣東南油對外服務公司黨委副書記柯榕林還記得,1997年,有個員工去外企面試,各方面表現都不錯,最后外國老板問,你是不是共產黨員?他猶豫了半天說“是”,結果被刷下來了。
新世紀以來,隨著外企在華持續擴張,隱形黨員急劇增多。十六大修改的黨章首次對非公企業黨建作出明確定位。2005年,中組部下達有關非公企業黨建的五年全覆蓋規劃。
2005年前后,一場地毯式尋找“隱形黨員”的行動在上海密集展開。陸家嘴金融貿易區綜合黨辦主任吳愛靜回憶,當時黨辦在大樓里張貼告示,逐棟逐層挨個找,吃了不少閉門羹。
黨支部“法寶”:為員工服務
曾當過一個國有銀行某支行副行長的董述寅,2005年加盟渣打銀行(中國)。當時除了他自己,沒有人知道他是黨員。在外企入職表上,沒有“政治面貌”欄,很多黨員直接隱藏了自己的身份。
入職渣打銀行時,董述寅去吳愛靜那兒轉組織關系。吳愛靜發現他之前在國企和學校都擔任過黨支書,問他愿不愿意為黨做些工作,董述寅最初沒答應,“當時對外資銀行文化還不了解,擔心對職業生涯有負面作用”。但經不住吳愛靜的游說,董述寅應了下來。
之后,渣打銀行每新來一個黨員員工,到吳愛靜那里轉關系時,吳愛靜就把他介紹給董述寅。遍布陸家嘴的大小餐館,成了董述寅跟“部下”的約會地點。“就是閑聊,外企都是直線管理,橫向部門之間溝通很少,這可以讓我們很快熟悉起來”。
但光閑聊是遠遠不夠的。2008年,馬來西亞銀行上海分行營運經理劉韶華剛接任招商大廈聯合黨支書時,去金茂大廈里跟黨員收黨費,對方問:“你們黨支部在做什么?好像除了收黨費,沒搞過什么活動。”
在機關和國企,組織生活和政治學習可以把黨員召集到一起。“外企員工比較現實,如果過組織生活就是開會,效果往往不如人意”。一些有想法的黨支書開始“搞搞新意思”。德國工商會上海代表處黨支部書記宋昀考慮到外企收入都還算不錯,決定在精神追求上做點文章,組織了一些讀書會和畫展活動。她第一次向黨員們推薦的書叫《公平》,是哈佛大學哲學系的一位教授寫的。
公益活動因為與外企的企業社會責任有重合之處,成為外企黨支書們的重點工作。
渣打銀行每年都給員工三天帶薪假,鼓勵員工用這三天時間做志愿者活動。董述寅便組織黨員到敬老院搞臨終關懷,還專門去民工子弟學校鼓勵下一代。
為基層員工提供服務,更是黨支部在外企站住腳跟的“法寶”。許多外企黨支部從幫助下層普通員工開始,有的幫助成立醫療基金,有的則協助解決員工工作餐問題,獲得認同后,再讓中高層認識到黨組織對其企業的幫助或者重要性。唐睿認為,“構建利益認同”是黨組織扎根外企的核心手段。一家外企的黨支部書記甚至作出承諾:“要力保員工的收入高于CPI上漲。”
由“地下”到“地上”
外方領導的態度,決定了外企黨支部能否從“地下”轉為“地上”。
董述寅先從試探上司的口風開始。他的直線經理是個澳大利亞人,很信任他。閑聊時,董述寅有意無意說起自己是中共黨員,結果經理很感興趣。董述寅又點了幾個同事名字,問經理印象如何,經理說:“這些不錯啊。”董述寅說:“他們都是黨員。”
許多外企決策者到中國久了,也發現企業內部的黨組織擁有一些黨政資源,能為企業發展帶來一些看得見的好處,甚至幫助企業解決麻煩。
“外企的性質決定了黨組織的角色和地位:不會是企業的領導核心,只能是發揮服務作用。”一位在某美資企業工作的黨支部書記說,除為黨員和基層員工服務外,黨組織更重要的是為企業發展提供幫助,讓老板意識到,黨組織對企業的發展有好處。
對于追逐利潤的企業而言,支持黨支部在眼皮底下活動,自然是理性思考之下的選擇。安可咨詢有限公司董事副總經理唐亞東表示,在中國政府鼓勵外企成立黨支部的情況下,家樂福等公司的做法可以傳遞出信號:我們遵守了中國的法律和政策,“很多外企意識到,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黨團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黨支部是一種建立聯系的方法,可以讓外企更好地了解共產黨,然后可以將公司的工作和黨考慮的事情聯系起來”。
董述寅最后得到了幾任老板的支持,渣打銀行黨支部最終成立。
在董述寅的努力下,渣打銀行黨支部升格為黨總支,下轄六個黨支部,管理著兩百多名黨員。
上海被認為是外企黨建做得最好的城市。上海對外服務有限公司作為中國最大的國有對外人力資源服務機構,下面已經掛靠了500家外企黨支部。
董述寅無疑是幸運的,更多外企黨支部仍面臨和外方老板相處的煩惱。唐睿曾對四個國家級開發區中的外企黨建情況進行過調研,“我曾遇到的一家外企,他們開黨支部會議,在公司內部都要半躲著開”。
2012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下發文件,要求各地加快非公經濟組織的黨建步伐。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把非公有制企業黨務工作者納入黨員干部教育培訓總體規劃,推薦符合條件的黨組織書記作為各級黨代會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人選。新近出爐的十八大代表名單,出現了外企黨支書的身影,諾基亞西門子通信技術(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人事總監成莉當選上海市的十八大代表。這對于外企黨員和外企黨建工作,都是頗具鼓舞作用的。
(牟大裕、邱寶珊薦自2012年7月19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