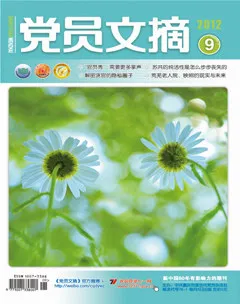蘇共的純潔性是怎么步步喪失的
李永忠 董瑛
蘇聯共產黨在93年的建黨、74年的執政歷程中,由建黨之初幾十人的小黨發展成為近2000萬黨員的世界性大黨。然而,其純潔性則呈現出重力加速度下降的現象,執政時間越長,純潔性流失越明顯,由一個發展上升、先鋒模范、核心領導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政黨演變成為隱性流失、顯性流失,最終急劇崩潰的殤黨。
發展上升期
列寧建黨和執政時期,是蘇共純潔性積累發展和顯著上升期。
一是主張組織建黨。1903年,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首次提出了組織建黨的原則:建立一個有組織有紀律的集中統一的黨;凡是黨員,必須承認黨綱、在物質上幫助黨,必須參加黨的一個組織;堅持地方服從中央、少數服從多數的組織原則。
二是注重質量建黨。打天下和建立政權期間,列寧十分重視黨員隊伍的質量建設。他強調:“世界上只有我們這樣的執政黨,即革命工人階級的黨,才會不僅注重黨員數量的增加,而更注重黨員質量的提高和清洗‘混進黨里的人。”
三是實行紀律固黨。列寧強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無產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要有嚴密的組織,還要有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統一紀律,以維護和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四是依靠群眾建黨。列寧用古希臘關于安泰的神話來強調黨群關系建設。他形象地將無產階級政黨和黨的領導干部比作安泰,把人民群眾比作大地母親,并指出,我們戰無不勝的力量源泉,就在扎根于人民群眾中,就在與廣大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里。
正因如此,列寧領導的蘇共,從一個不太為人所知的地下黨,迅速成為一個具有強大凝聚力和號召力的革命黨,進而發展成為一個經受得住血與火、生與死的多重考驗,展示出先進性和純潔性形象的執政黨。
顯性提升與隱性流失并存期
斯大林執政時期,是蘇共純潔性顯性提升與隱性流失并存的時期。在近30年的時間里,斯大林借助列寧的革命權威和政績紅利,依靠蘇聯模式的短期效應,明顯提升了蘇共的先進性形象,推進了蘇共的純潔性建設。
其一,列寧革命和建設巨大紅利的延續效應。列寧革命和執政期間,是艱苦卓絕、出生入死的創業期,也創造了蘇共的輝煌成就、革命政績和崇高威望。但不幸的是,列寧過早離世。后來執政的斯大林,充分享受和運用了列寧的革命和建設紅利。
其二,衛國戰爭和二戰的重大勝利形成的光環效應。斯大林執政時期,他領導蘇共成功擊退了國內外反動勢力的反撲和圍攻。由此,不僅樹立了蘇共的先進性、純潔性形象,而且在全世界樹立了蘇聯社會主義的神圣形象,確立了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核心地位。
其三,斯大林權力結構模式的短期效應。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在斯大林時期形成的,蘇聯模式是以“議行監合一”和等級授職制用人體制為主要特征的。斯大林依靠這一模式,動員和集中全國資源和力量,建立了強大的國防軍事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基礎,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社會主義制度,形成了蘇聯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基礎體系,成為當時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的旗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
但是,在斯大林執政期間,為了壟斷絕對權力、打造“教主”地位,斯大林依靠不受監督制衡的無限權力,以“紅色恐怖”手段,不斷搞政治清洗、等級授職和造神崇拜三大運動,消滅敵人與對手,消除對斯大林模式的不同看法和聲音,培養在冊權貴和“圣劍騎士團”,給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造成了重大的隱性損傷。
隱性流失加劇期
斯大林之后,從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他們執政時期的蘇聯,盡管綜合國力、軍力達到了頂峰,經濟實力居世界第二,與美國分治世界近半個世紀,盡管勃列日涅夫將飛船送上天,將導彈部署到美國的家門口,盡管形成和擁有了改革的最佳機遇和條件,但由于他們既是斯大林模式的產物和受益者,又是斯大林模式的執行者和傳承者,所以,他們共同將斯大林模式推向了固化和極化的境地,不僅消耗完了斯大林模式的紅利,而且隱性地損傷和流失了蘇共的先進性、合法性和純潔性,留下一個盛極而衰的蘇聯給戈爾巴喬夫。
赫魯曉夫充分利用這種體制的獨裁主義結構及無法擺脫絕對權力和諂媚的腐化作用,同樣搞黨政合一、個人極權、個人崇拜、黨內斗爭、霸權主義,重新走向斯大林式的極權道路,致使斯大林“議行監合一”的權力結構模式和等級授職制的用人體制反彈和回歸,使蘇共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受到了隱性損傷。
勃列日涅夫無能研判和把握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無心融入和順應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潮流,無力擔當和推進繼往開來的時代變革重任,痛失蘇聯歷史上的最佳改革時機,維穩抑變18年,使斯大林模式更加成熟、更加固化,走向極化,成為蘇聯歷史上的“超穩定時代”。特別是從1982年到1984年,在不到三年的時間內,蘇共連續三任年老病弱的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相繼在職病逝,成為蘇共執政危機和純潔性危機的隱性加劇期。
顯性流失與急劇崩潰期
經過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時代,蘇共喪失了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革新的最好時機,也由純潔性的隱性流失期迅速走向顯性流失與急劇崩潰期。
1985年3月11日,在“別無其他的選擇”的情況下,在蘇聯人民發出“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了”的怒吼聲中,蘇共挑選出舊體制內“最合適”的人選戈爾巴喬夫上臺執政。但此時的蘇聯已到了“極度蕭條衰退時期”,出現了全面危機,黨和國家開始顯露出“蘇聯之災厄”。
加之,戈爾巴喬夫在改革過程中,始終在激進派與傳統派的夾縫中猶豫搖擺,始終在“議行監合一”的權力結構中折騰回復,始終在等級授職制的用人體制中選人用人。在內外交困、慌不擇路的情況下,他超越黨內分權和黨政分工兩個階段,直接搞黨政分開,最后將最高權力中心由黨內轉移到蘇維埃再到總統,讓自己成了擁有無限權力的超級總統和民主利己主義者。
由此,激進改革派拋棄了戈爾巴喬夫,黨內保守派也放棄了戈爾巴喬夫,各階層和人民群眾都對戈爾巴喬夫感到極度失望,蘇聯已再也沒有改革的時間和空間了。這一時期,成為蘇共執政危機總爆發時期,成為蘇共合法性、純潔性顯性流失乃至急劇崩潰破產時期。
(誼人、寶珊、賢焜、良槐、張源、興方、昌喜、傳中、王煒薦自2012年6月20日《黨史信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