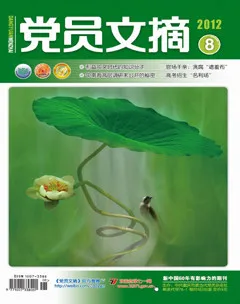很高興,我不認識你
陳薇
明信片、書信、電子郵件、漂流瓶、陌生短信……這些承載著秘密與心情的陌生訊息,使正在努力和陷于迷茫的這一代人感到安全、親切,隱約中,還夾雜著這樣的慶幸:很高興,我不認識你。
從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
一張,兩張,三張……莊笑穎數了數手上的明信片,從今年1月底開始參加“換片”(交換明信片)以來,她已經收到了60多張明信片。
三年前,莊笑穎大學畢業后來到北京,在一家少兒出版社做圖書編輯。“換片”是莊笑穎在豆瓣網“我愛明信片”小組里發現的小樂趣。小組已有43000多名組員,全都素不相識。
莊笑穎起初是沖著明信片去的。去年底,24歲的她平生第一次收到明信片。一位朋友去杭州旅行,寄來一張江南水鄉白墻黑瓦的明信片。不久,另一位朋友獨自旅行去了敦煌,也寄來一張飛天壁畫的片子。明信片里的不同世界和人生,勾起了莊笑穎的“癮”。于是,她搜索進入了豆瓣網的“我愛明信片”小組。換片的對象,從熟人變成陌生人。
喜歡寫信的貴州女孩張瀟文,也從給熟人寄信發展到寫信給陌生人。她現在在北京某大學讀大二。從小學起,身邊發生的大小事兒,張瀟文都寫信講給一位閨蜜聽。“寫信從小學四年級開始,是和最好的朋友、最親密的人之間的神奇紐帶,所以我想給你寫信”。一天傍晚,她在豆瓣網“一個陌生人的來信”小組發了帖子。此時,她早已和那位閨蜜失去了聯系。她突然想給自己創造機會,遇到一些“可愛的陌生人”。
從熟悉到陌生,網絡讓莊笑穎和張瀟文的心愿成為可能。明信片、書信、電子郵件、漂流瓶、短信,還有隱私網、樹洞網,以及無數網友博客、自建站點、聊天軟件……如今,與陌生人交流已有了種種現實版本和虛擬途徑。
“如果沒有網絡,中國很難變成陌生人社會。” 北京師范大學人格與社會心理研究所副教授王芳說。
騰訊QQ郵箱漂流瓶上線后第一天,發信量即超20萬次,兩天后就超100萬次。微信創始人張小龍說,“搖一搖”(一種通過搖晃手機即刻尋找到同時搖晃手機的陌生朋友的應用程序)上線后,很快就達到每天一億次以上的使用次數。
強大的需求使得與陌生人進行情感交流的網絡產品還在不斷被開發或被模仿。一種在線認識陌生人的全新服務是這樣的:當你登錄時,系統便會隨機選取另外一位用戶與你聊天,沒人知道你是誰,你也不知道對方的任何個人信息。這種方式還使你擁有簡單粗暴的主動權:一旦聊得不爽,你可以立即單方面點擊“換人”,然后邂逅下一個陌生人。
北漂的夢想
和其他北漂一樣,莊笑穎覺得自己就像生活在北京的一座孤島。每天早上,她坐40多分鐘的公交車晃到單位,下班再原路返回。平常的工作內容之一,是為小學生的投稿修改錯別字,單調、重復。
在這個黑白色系的生活中,陌生人寄來的卡片,就像上天送來的五顏六色的禮物。一切獨自漂流的孤寂,似乎都能從明信片中得到撫慰。在明信片里,有孤獨癥孩子的繪畫,有木版年畫“天女散花”的郵票,有上世紀80年代略顯土氣和樸素的廣告女明星。有片友推薦了一部上世紀60年代的科幻電影,莊笑穎立即找來看。還有位片友用樹葉標本做了一張手工明信片給她寄過來。
在王芳看來,“這正是人和人之間情感傳遞帶來的溫暖和快樂”。王芳曾參加過一個名叫“鞋盒禮物”的公益活動:將一個禮物裝在鞋盒里寄到陜西一所小學,然后隨機分配給一個小學生。
不久,王芳收到一張表示感謝的明信片。“我覺得最溫暖的是木帛襖。”孩子寫道。字下面的空白里,孩子還用鉛筆畫了一支蠟燭。看了半天,王芳才辨認出孩子說的是“棉襖”。“收到這張明信片時覺得很意外,也很溫暖。”王芳回憶道。
如著名心理學家弗洛姆所說,現代工業化社會一方面使人變得越來越自我疏離,另一方面,這種孤立感讓人們潛意識中仍然渴望與他人結合、聯系。在王芳看來,與陌生人而不是熟人的交流正滿足了這樣的悖論。
被需要的情感
“他明天生日,能不能直接幫我發‘生日快樂?他手機號是150
****6755,我沒有勇氣發給他。”
“老公老公,明年我們一起跨年!新年快樂!號碼是151****2829。”
“多多讓我告訴你,會一直等你回來。”
…………
這些都是女孩唐翠得到的委托。2010年的最后一天,她在網上發帖,愿意受人所托代發短信,長期有效——她曾在豆瓣網“想不想很多人幫你群發短信”小組里晃悠,知道有這么一種表達方式,可以幫助別人說出那些他們想說的話。
在同一天,唐翠其實也得到了別人的幫助。她寫了十句話,請十個人轉發給男友。此時,她與相戀五年的男友正處于分手邊緣。很難說清楚是想挽回這段感情,還是因為分手時的情緒無處發泄,從此之后,代發短信成了唐翠每天早晚的必做事項。
“其實就是一種覺得自己有價值、被人需要的感覺。”從男友身上沒能得到的滿足感,卻在陌生人的短信中意外地得到了,唐翠最終結束了與身處異地的男友的這段戀情。
眾多陌生人完成的日記
這是一個尋常的日記本:淺棕色封面,灰色內頁。日記本前半部分寫滿了藍色、黑色的筆跡,字體不一,夾雜著貼紙、小畫兒。
這是本“漂流日記”,不屬于某個人,是由“有意思吧”網站組織的——將一個日記本以快遞或面傳的方式在網友之間依次傳遞,收到本子的人可以寫字、畫畫、拼貼……簡單來說,它是一本由眾多陌生人共同完成的日記。
五年來,這項活動已經吸引3000余人報名,共有11本日記本在傳遞。
如今,其中一本日記本走過了南京、武漢、青島等十個城市,外皮上已有了青黑色折痕和磨損的毛邊。第11站,北京,收件人是在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學習的研究生黃杰輝。
黃杰輝翻看著日記本。作為慣例,每篇日記的開頭,都要對前一站的禮物和故事作出回應。
他的前一站網友記錄著:“昨天一個朋友去云南了,離開這邊的一切,甘愿一個人在那邊拿著一份低薪過著自己想要的生活……這是他壓在心底的一個夢。許久我才說:‘那你記得,出去,是為了回來。”
再往前翻看,黃杰輝發現,這些同齡陌生朋友的苦惱讓他感同身受。
離家上學一年半的第一位漂友不那么喜歡他所在的城市:“還是經常掛念老家的海,想著所有赤腳在沙灘上奔跑的日子。秦淮河邊的月亮再皎潔,還是會浸沒在現代夜生活的燈紅酒綠里,而當我站在河邊,不會欣賞了,卻只剩了一點孤獨……”
第二位漂友抱怨學校老師的按部就班:“理想這詞太過傷人,我早已把它遺忘在心里某個角落。”
第三位漂友則不喜歡她所學的大學專業:“在作出這個決定的時候,我也無比地沮喪,但自己選擇的路,爬著也要走完。但我不知道自己親手丟掉的青春以后還能不能撿回來。”
這些在現實生活中相互交織的焦慮、不安、自憐、期望等諸多復雜情緒,是向陌生人傳遞信息的主要內容。
“這句話你已經說了一萬遍了,了解你的人可能會把它當作你性格軟弱的表現。”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劉能分析說,“放在一個熟人環境,遭到負面回應的可能性很高;而陌生人缺乏判斷這句話的背景信息,因此一定會以常規模式來反應,即附和并鼓勵。”
在劉能看來,這是向陌生人傾訴煩惱的安全感來源。很多人不愿意在熟人面前展現出“負面自我”,然而,在陌生人的環境中,人們會更放松也更真實地展示自己的內心。當看到別人也面臨同樣問題時,還會產生某種“我并不是一個人在戰斗”的共同感,因此完成某種自我認同的心理舒解。
當然,不僅是焦慮,向陌生人表達的內容,還有自我暗示、自我期待或承諾。黃杰輝發現,盡管有些不如意,這些年輕人仍然沒有失去希望。
抱怨所學專業的漂友最終以這句話結尾:“whatever(無論如何),這世界雖有時令人心碎,但終究是值得我們為之奮斗的吧。”
寫完日記后,黃杰輝選擇了下一站漂友——翻開書,隨機翻到某一頁,按順序數出下一位漂友。他附送了禮物:一條紅繩,掛著一只骨瓷小兔。
“為什么我會花時間做這樣一件事——寫心里話給陌生人看,卻不和朋友們聯系?”在封裝禮物與日記本時,黃杰輝突然冒出這個想法。他封上信封,決定天亮后,一定要給那些曾經親密無間、如今卻疏于聯系的朋友們認真打個電話。
(摘自《中國新聞周刊》2012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