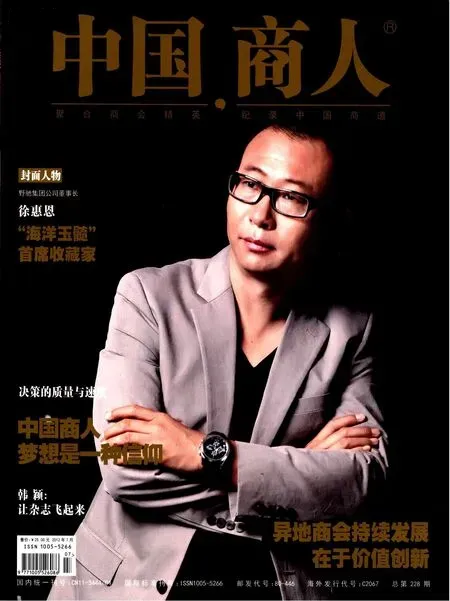忘了它,其實沒那么難
記者:如何忘記過去曾受過的重大挫折?忘記別人對自己的傷害?
濟群:忘卻痛苦的方法有二,一是培養正面情緒。情緒有負面和正面之分,哪種力量更強,就會將我們導入相應的心理軌道。所以,我們要壯大正面情緒的力量,就像以增加體質來對抗疾病干擾那樣。
二是面對它,想想是哪件事令我們痛苦。狹隘的心是無法承受傷害的,這就會形成巨大的心結。其實,真正傷害我們的,往往是自己的心結,而不是具體的某個人、某件事。許多人心中都有這樣或那樣的心結,一旦產生作用,我們馬上就被它抓住,一頭扎進痛苦中。現在,我們要從更高的角度來審視這些,將問題重新思考一遍,再思考一遍,一直思考到你覺得這其實沒什么,然后把它放下。若能這樣,即使還不會馬上忘卻這件事,但它能造成的影響就微乎其微了。
當然,還有更高的辦法,就是當下解決。因為心有制造煩惱的能力,也有當下解除煩惱的能力。一旦將這個能力調動起來,煩惱就像雪花落入燃燒的火爐,立刻會自動化解。這是比較高明的用心方法,多數人可能一時用不起來。
這樣,那樣,矛盾了嗎?
記者:《壇經》講“不思善、不思惡”,與“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教法是否對立?
濟群:“不思善,不思惡”與“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并不對立,而是代表兩個層面的修行。佛法修行中,基本貫穿著“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原則。但修行不僅是止惡行善,更要超越對善惡相的執著。因為修行最終要契入空性,以哲學角度來說,即通達絕對真理。空性又名真如,超越一切善惡,這就必須擺脫二元對待的心。
我們眼中的世界,是相對的世界;我們現在的心,是二元對立的心。換言之,每個心念都有相應的對象。比如想起某個人,某件事,都有“能想”和“所想”。而在空性層面是沒有對待的,是“不思善,不思惡”的絕對世界。凡夫活在相對的世界,而圣賢同時活在相對和絕對的世界。體悟絕待的空性時,是超越善惡的。安住于相對時,則要“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對于普通人而言,相對現象與絕待的心似乎會發生沖突。但對圣者而言,心的相對層面和絕待本質是可以并存的。
記者:佛法說“諸行無常”。我理解,無常就是沒有恒定不變的東西,并不是說事物沒有客觀規律。我是學中醫的,我們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周易》衍生的陰陽、五行、藏象、經絡等,也是統領客觀規律的原理。作為中醫,在治病過程中,這些理論是必不可少的工具。我想知道,作為學佛者,應當怎樣認識、對待并應用這些規律?
濟群:作為中醫來說,需要了解我們的生理結構和脈絡,這種了解并不影響學佛。緣起法確實有規律可循,干任何一行,都要鉆研它、了解它,在這一前提下,才有能力正確認識乃至應用。
至于佛教所說的“無常”,和這些規律并不矛盾。所謂規律,必須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只要是客觀規律,一定是相通的。區別只是在于,對規律的認識存在程度深淺的不同。另外,佛教對客觀規律的認識,目的是為了斷惑證真,了脫生死,不同于單純的治療疾病。當然,學佛能幫助我們深化對身心世界的認識,也是有助于學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