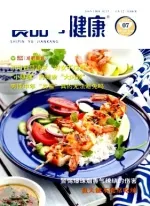夏日的蠶豆飯
宜晴
時(shí)至夏日,粉嫩的蠶豆花兒也抖落了她美麗的花瓣,結(jié)出了一個(gè)個(gè)飽滿的厚實(shí)的豆莢子,此時(shí)的蠶豆,最是鮮嫩不過(guò)的了。
江南這邊,農(nóng)人愛(ài)在田埂斜溜上有序地植上一排又一排的蠶豆植株,不挑地兒的蠶豆竟也長(zhǎng)得茂密從容。仔細(xì)剝開(kāi)厚厚的豆莢子,嫩綠色的蠶豆便活躍地跳到你的眼前,卻又是如此乖巧妥帖地睡在一個(gè)個(gè)豆莢房子里,直叫人想起古老童話中那位溫秀明麗的豌豆公主。
晨起,生活在城鄉(xiāng)近郊的農(nóng)人們便勤快地兜起一網(wǎng)袋新摘的蠶豆莢坐攤販賣了,揀選三四塊錢的蠶豆,往往能裝上一大袋子帶回家。用竹淘籮盛上這些鮮嫩的蠶豆,母親就愛(ài)打開(kāi)家門,搭出一把小板凳,順手帶上一只貼花白瓷碗,命稚時(shí)的我安靜地坐著剝豆。不知道江南這邊的孩子們是否都曾擁有這樣的剝豆記憶,總之,當(dāng)后來(lái)自己看魯迅先生的《祝福》時(shí),總對(duì)祥林嫂拎著一籃豆讓阿毛坐在門檻上剝豆的情節(jié)倍感親切。
每當(dāng)這時(shí),家里的飯桌上便會(huì)添幾道用蠶豆烹制的家常菜,像是雪里蕻炒蠶豆、韭菜苗燒蠶豆、干鍋煎蠶豆、瓠瓜絲蠶豆羹等。蠶豆是最好配菜的了,因?yàn)槔闲Q豆口感沙綿軟爛,所以適宜調(diào)羹燜燉,而新上市的蠶豆則脆嫩細(xì)滑,油鹽煎炒最合適不過(guò),所以,無(wú)論是哪種煎炸烹炒,蠶豆都適宜取用。而在所有的蠶豆菜里,最令我癡迷的,還是那道咸肉蠶豆飯。
前些時(shí)日,揀了一部去年TVB的臺(tái)慶劇《公主嫁到》來(lái)看,看著里面陳豪飾演的駙馬沖公主要求考究地備飯時(shí)嚷嚷道:“煮飯呢可不能隨便了事,要七成香米,兩成糙米,一成黏米,不要井水,要溪水,飯要三蒸三烤,第三烤才好放肉……”,言之鑿鑿的腔調(diào)令人忍俊不禁,隨之轉(zhuǎn)念又想到自己少時(shí)傍在母親的身邊,看著她頗費(fèi)心思地挑選了糯米與粳米預(yù)先浸泡在清水之中告訴我:“只有四分糯米配上六分粳米,這樣做出來(lái)的蠶豆飯,才能口感綿軟有嚼勁,又與立夏當(dāng)季的蠶豆同鍋燜熟,合在一道,糯滑可口。”這樣的親親言傳,謹(jǐn)身相授的片段,怕是要印到我骨血深處,說(shuō)不定在未來(lái)的某個(gè)片段中,我也會(huì)用母親那般的心意、那般的語(yǔ)氣,將一個(gè)個(gè)關(guān)于烹制蠶豆飯的小竅門款款地道出呢。
取一塊上好的五花咸肉,油脂部分可以多一些。用刀將咸肉塊均勻地碎成連肉帶皮的小塊,按著山村土法來(lái)做,就開(kāi)旺火,在鍋底輕輕舀上半勺菜油,將咸肉塊放入熱油煎炸,吱吱的煎炸聲誘人地響起,就漸漸改為小火,用平鏟輕壓肉塊,將五花油脂部分的油潷取出來(lái),瀝干肉上的油脂,將肉塊撈出備用。取干凈的粳米和糯米,按六分粳米和四分糯米的比例入油鍋輕輕翻炒,使每一粒米都被咸肉油脂浸泡。大火稍稍翻炒炸香之后,天然米香便與陳年咸肉特有的清新熏腌味美妙地融合起來(lái),而獨(dú)特的油脂又經(jīng)火浸入米粒表面,而合適的火力又使每顆米粒得以稍稍炸起膨脹,如此,等到入水經(jīng)飯鍋燜煮出來(lái)后,其香絕倫。將米撈出,取用同樣的一部分咸肉油,用來(lái)煸炒蠶豆瓣,為了保持蠶豆的原汁原味,建議不加任何香料與調(diào)味料。
米、肉和蠶豆都準(zhǔn)備齊全了,就把炒過(guò)的米粒放入飯鍋,注入開(kāi)水使之沒(méi)過(guò)米粒,然后放入煸炒過(guò)的咸肉,最后是過(guò)油的蠶豆瓣。不用急于蓋起鍋蓋煮飯,此時(shí),就讓咸肉與蠶豆特有的味道慢慢地釋放到水米混合物中,而炒過(guò)的米粒也在開(kāi)水的浸泡中慢慢地舒張其米粒特有的黏糯性。根據(jù)各人的口味加入適量鹽巴。因?yàn)橄倘獾木壒剩苑披}需謹(jǐn)慎甚至不放。浸泡十分鐘之后,便可以蓋上鍋蓋燜制了。將食用時(shí)將豆瓣、咸肉與米粒均勻翻動(dòng),使三者充分黏合。盛裝的時(shí)候,若是選用景德鎮(zhèn)的青花紋瓷碗和調(diào)羹,配上簡(jiǎn)單的竹筷或潔白的牙箸,那就再好不過(guò)了。淡黃色的米粒,焦紅的咸肉丁,又有綠色的豆瓣穿梭其間,觀之怡情。濃郁的雙合米香,油潤(rùn)的煎熏肉味,還有蠶豆香氣,品之實(shí)則悅心。怡情悅心,又雅合時(shí)令,取節(jié)令之物,應(yīng)時(shí)感氣,妙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