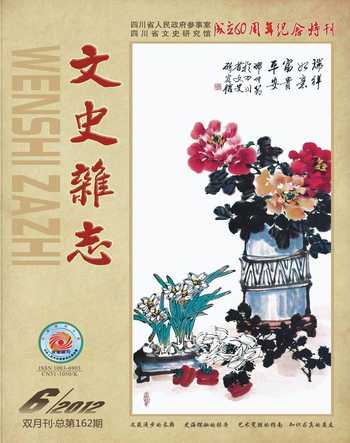大熊貓追尋記
金勗琪
九寨溝撲空
1979年6月,我到四川南坪縣(現九寨溝縣)采訪。這里森林遮天蔽日,險峻的雪峰寒光閃閃。星羅棋布的湖泊,有如鑲嵌在高原的明鏡,微風拂過,水光瀲滟。
“你們運氣好!”林區工人介紹說,不久前有位畫家來此寫生,正當他沉醉于湖光山色之際,一頭大熊貓突然蹣跚地出現在面前。畫家一驚,拔腿就跑。大熊貓卻慢慢地走到畫板前站定,搖頭晃腦,儼然像一位“行家”在欣賞他的大作,許久才離開。
聽了這迷人的故事,更加激發起我拍攝大熊貓的強烈愿望。
我踏著鋪滿落葉的小徑,鉆進了密林。茂密的箭竹沿著綿延的山巒,仿佛筑成一道道屏障,無法逾越。天色幽暗,似乎籠罩在一片水霧之中。視線只及幾步之遙。我用濕漉漉的身子保護著相機,注視著周圍。
我們在密林中隱隱聽到熊貓的叫聲,同行的人高興地說:“有希望了!”然而待我們走近,卻絲毫不見熊貓的蹤影。有時我們在箭竹叢中看到大熊貓的糞便與活動痕跡,以為機會到了,但是它卻像捉迷藏似的,消失得無影無蹤。熊貓這種出沒無常的習性,對于急性的我,好像是一種有意的磨煉。十多天過去,沒有緣分和大熊貓相遇的我,只好依依不舍地向九寨溝告別。
平武相識
經過上次的挫折,隔了一段時間,省林業廳的同志告訴我,他們在平武縣捕捉到一只大熊貓,正打算送往臥龍保護區,建議我去一長見識。
平武縣位于四川西北部,記得數十年前的范長江在《中國的西北角》一書中,曾對它有過記載。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中,國民黨為截阻紅軍北上抗日,沿途滿布碉堡,把繁華的街市燒得“只存一片瓦礫”。今天,涪江依舊繞城而過,而廢圮的土碉上空只有幾只寒鴉在盤旋憑吊……
我到達平武時,在林場特設的熊貓館里,看到這只新捕獲的七八歲的雄性熊貓。我原以為它是憨厚、溫和的動物,可是當我舉起相機時,它突然怒目圓睜,張開大嘴,發出“吭!吭!”的叫聲,上下牙扣得咯咯作響,還把爪子伸向我們。
正是這只大熊貓,幾天前拉彎籠子的鐵條逃上了大街,咬傷了追捕者的小腿和三個手指頭,竄進附近農場的廚房,把儲藏室里的面粉、大米、鍋灶搗得一片狼藉,連炊事員的鋪蓋、蚊帳都給撕破了。最后,不知誰的主意,拿了幾根甘蔗作誘餌,才把它慢慢地引回籠子里。
這出諧劇似的敘述,增加了我護送熊貓的興趣。我和一行護送人員同熊貓一起擠在一輛中型吉普車里,準備隨時拍攝。一路上,熊貓怒氣沖沖,不斷伸出爪子,想逃離鐵籠。因為熊貓怕顛簸,為了防止它暈車致死,汽車不能按正常速度行駛,只能以每小時20公里速度前進,沿途還要不時停車休息、喂食。
汽車緩緩行駛,熊貓漸漸安靜下來,甚至伸出爪子向我們討甘蔗。然而,中午當我們在江油停車準備午餐時,人群把汽車圍得水泄不通。熊貓突然咆哮起來,把鐵籠搖得東倒西歪。我急中生智,建議把車開到公安局請求保護。這樣,才避免了一次難測的事件。
雪山傳奇
位于邛崍山脈南麓的寶興縣,是四川大熊貓產區之一,也是近幾年捕獲熊貓最多的縣。從1972年以來,這個縣已先后有五只熊貓出國定居。已是隆冬季節,我決心再到寶興縣去一試機緣。
寶興縣的熊貓主要棲息在夾金山一帶。當年紅軍北上抗日,一度攻占縣城,震驚全川。如今,當我抵達夾金山林區時,經過幾場大雪,群山已是白皚皚一片。熊貓性喜孤獨,茫茫林海到哪里去找它呢?
森林工業局的同志熱情地向我介紹:箭竹被雪覆蓋后,熊貓覓食困難,經常下山找吃的。有的工棚廚房常常被這些不速之客搗得亂七八糟,甚至把鍋蓋、鋁鍋當做玩具來拋擲。所以當地農民上山挖藥、打獵,都要把鍋子掛得高高的,以防熊貓拿來“玩”。
“大熊貓還喜歡啃骨頭。”這個縣的五龍公社社員高德華說,有一只大熊貓,是他家的常客,每隔十天半月總要“走訪”一次。它啃完骨頭,還要闖進廚房舔舔鍋蓋、勺把、水桶;有時干脆就在廚房酣然大睡,天亮了還不肯走。
這些故事鼓舞了我找熊貓的信心。但一天一天過去了,卻一直沒有遇到熊貓,我又撲空了。
巧遇“醉熊貓”
1980年4月,我到平武縣白馬藏族居住區采訪。這里層巒疊嶂,陽光透過晨霧,把漫山的云杉、冷杉、箭竹照得飛金點翠,仿佛特意為大熊貓安排了這樣一個天然的棲息地。
一天,我走進一片箭竹夾道,遠處瀑布高懸,腳下流水潺潺……我禁不住跳到湍急的溪流中,站在石頭上,準備拍照。同行的一位工人突然拉拉我的衣襟,貼著我的耳根驚喜地說:“你聽,就在右面……熊貓!熊貓!”我屏住氣息,傾耳細聽,果然有一種細微的簌簌聲傳來。我抱著相機三腳兩步跳到岸上,一抬頭,就見距我不到3米遠的箭竹叢中,端坐著一只大熊貓,正在悠閑地啃著竹子。
我的心怦怦地跳著,迅速舉起相機,目不轉睛地注視著這個我夢寐以求的不速之客。但是,茂密的箭竹遮擋了熊貓的身軀。在鏡頭里,我只能隱隱地看見一團白色,真是可望而不可即。我擔心它受驚逃跑,又怕它猛地向我撲來,急得團團轉。
“慢!”同行的工人提醒我:“這兒是上風處,熊貓的鼻子靈,一聞到人的氣味,要逃走的。”誰知話猶未了,熊貓已經起身,邁著蹣跚的步伐,朝著竹叢深處走去。
我來不及多思索,鉆進竹叢,沿著它的腳跡,緊追不放……摔倒了,爬起來;荊棘扎在身上、手上也感覺不到痛。
這只熊貓在竹叢中竄了一陣,忽然跑到一處陡峭的巖壁下,背靠懸巖坐下來,既不發怒,也不驚恐,更沒有撲人的跡象,只是安然地端詳著我們。一個工人悄悄地走近它的左側,用手撥開竹子,讓它顯出“尊容”。它仍然一點也不動。接著,這個大膽的小伙子竟敢伸手去摸它的鼻子,它也只是用前爪輕輕地一推,頭往旁邊移一移,毫不反抗。啊!既有趣,又真實,這不正是我想要的情景嗎?我舉起勃朗尼卡相機迅速拍下這個難遇的場面。后來,我想起身上還掛有一個裝著彩色膠卷的來卡相機。一看,上的是廣角鏡,但已顧不上換鏡頭了。我作了最壞準備,走到距熊貓不到一米的地方,抓緊時機,一張又一張地拍下了大熊貓旁若無人的憨態。
一陣山風吹來,滿山箭竹沙沙作響。大熊貓終于起身告辭了。此時,我才感到渾身疼痛,滿臉淌著汗水,衣服也濕透了。事后,回到住處,大家聽了我們的奇遇,都很羨慕。有經驗的人告訴我說:“這是一只‘醉熊貓。”
為什么叫“醉熊貓”呢?原來,每當春天,山上積雪融化,大熊貓常常下山找水喝。它有個習性,在平靜的水面,看見自己的影子,以為還有一只大熊貓也在喝水,于是就拼命地搶著喝。熊貓在流水淙淙的溪邊喝水,聽到水聲不斷,總想把水“喝斷”。于是喝呀,喝呀,直到肚子脹得不能動彈為止。喝“醉”了的大熊貓特別溫順,不會傷人,直到過了三四小時,它“醉”醒了,才恢復自衛反擊能力。
人們向我祝賀:“你是第一個在野外和大熊貓相遇的攝影記者!”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館(成都)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