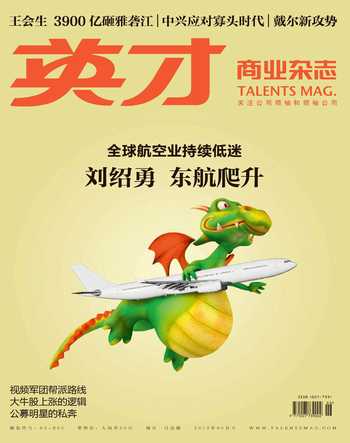中興吃平衡飯
孫瑜

在一場關于“老IT新路”的思辨中,比華為還早2年成立、已經“27歲”的老牌通信企業中興,仍舊被總裁史立榮稱為“小伙子”。
位居全球通訊設備商第五的中興,與排名一二的愛立信與華為相比,100多億美元與300多億美元的營收額差距仍然顯著;不過,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中興在歐美市場中的逆流而上、以及年均30%以上的增長速度,同樣讓競爭對手難以望其項背。
中興意圖“彎道超車”的信號,在史立榮上任后的2年內,已經被更加清晰的釋放出來。但是,未來3年能否真正逆轉局面,首當其沖要驗證其在全球分析師大會上的預言能否成真:從一家電信設備提供商向通信綜合服務商轉型。
2011年,中興與老對手華為,不約而同遭遇“增收不增利”的尷尬。歐債危機仍在蔓延、全球宏觀經濟的下行已傳導到全球電信業,上游運營商受經濟不景氣、互聯網應用和終端廠商爭奪利潤的影響,盈利能力正逐年下降,導致2011年以來全球電信運營商資本開支更趨謹慎,對于“靠運營商吃飯”的通信設備巨頭而言,盈利境況可見一斑。
“中興與華為都在積極尋求轉型,不約而同的走向三個新方向:終端市場、企業級市場以及運營商服務市場”,獨立資深電信分析師付亮對《英才》記者稱。
2011年中興財報,已經初步印證三種轉型方向。終端業務增速達到60.4%,手機進入全球前50個運營商中的43家,年出貨量位居行業第四,智能手機發貨量增長400%,同時,政企網市場國內增長超過90%,而且,中興服務整體業績增長40.9%,遠超競爭對手。
盡管如此,傳統電信管道市場是否真正觸及天花板?中興國際化潛力還有多大?在三種趨同的轉型中,“牛文化”的中興與“狼文化”的華為,將演繹怎樣的差異化?在與《英才》記者獨家對話時,史立榮另有一番解讀。
國際化思路要轉
在2012年的巴塞羅那通信展上,中興頗為意外的展示了一張關于“中國功夫”的膠片。
正如中國功夫中分為武當、少林、太極不同門派,但是到最高境界Master時卻不講門派一樣,史立榮認為,未來通信設備與技術的最高境界是融合與集大成。
“過去從2G向3G、4G不斷演進,有人問我什么是5G,就像是中國功夫Master的境界,5G時代應該不再講技術和門派,在這個時點和地點,實現最高速的寬帶、最便宜的價格,就是最佳的接入”,史立榮稱。
近年來,當年眾多活躍的歐美日廠商出現分化,北電破產、摩托分拆,阿朗出售業務、愛立信退出手機領域,諾西賣掉固網收縮市場以及萬人大裁員,讓通信公司陷入“寡頭競爭”的局面。
電信專家、Frost&Sullivan中國首席顧問王煜全對《英才》記者指出,近幾年國際運營商設備更換速度趨緩,在主流通信設備廠商中,價格昂貴的企業都瀕臨崩盤,幸運的是,中興華為靠“性價比”熬了下來。
對于中興而言,新機遇恐怕已經很難出現在2G和3G領域,因為在全球市場占比只接近6%,大逆轉比較困難,LTE/LET-A才是改變格局的關鍵。
專利儲備上,中興已有所倚重。截至2011年底,中興已經向3GPP提交了大約9300多篇提案,其中SAE/LTE相關提案超過了5700篇,有超過1700篇的SAE/LTE相關提案被3GPP采納。截至2012年1月底,中興通訊已在ETSI(歐洲電信標準研究所)聲明了381件SAE/LTE基本專利,大約占所有ETSI聲明的SAE/LTE基本專利總數的7%。
“雖然管道端進入寡頭競爭,但是可供挖掘的金礦非常多”,史立榮稱,隨著云計算的發展,通信內容和數據需求爆炸式增長,對帶寬要求將非常高,未來沒有一項單獨技術可以滿足管道端的需求,只有依靠融合性技術。
不過,比起技術改造,中興近年來國際化上最根本的變化還在于向“大國大T(大T:大運營商)”戰略轉移。
“放眼全球電信市場,按區域和國家劃分,有一個二八原則,甚至是一九原則。”史立榮分析指出,盡管運營商市場巨大,但是,歐美日中占據市場容量大頭,加上印度、巴西、俄羅斯和南非等金磚四國的影響力,實際上,只有抓住大國、大運營商,才能抓住產業鏈核心。
其實,中興16載國際化歷史路徑,并不依此推演。“這是中興的經驗,關鍵是教訓”,付亮稱,過去中興通過亞非拉進入國際市場,卻發現拿下市場之后掙不了錢。真正主流市場在發達國家,比如北美、歐洲,中興需要在這些市場集中優勢資源兵力,才能有所斬獲。
如果說,開拓發展中國家的意義更多在于擴大規模,那么,對歐美市場則在于提升利潤。對比運營商市場,美國ARPU值(每用戶平均收入)在50美元左右,而印度只有幾美元。很顯然,中興下一個野心,正是包抄和夯實主流運營商市場。
目前,總部在歐洲的全球TOP50運營商中,中興已經進入了90%,與除北美之外各大洲的排名一二的運營商基本建立了合作。但是,從“農村包圍城市”轉移到“大國大T”,中興海外戰略潛力能否真正釋放,還待觀察一場攻堅戰。
在中興歷史博物館中,有一張史立榮上世紀90年代只身一人參加日內瓦ITU世界電信展的照片。作為中興國際化中開疆辟土的第一人,史立榮拿下過在巴基斯坦的第一張海外訂單,這也是當年中國企業在海外的第一個上億美元訂單。從單點突破到系統化,從本地化到全球化邁進,史立榮親自見證,也親歷兇險。
“以國家安全”為質疑的流標事件,不僅僅針對在澳大利亞合同競標中的華為。“總有人說安全問題,導致運營商不敢用,實際上純粹為了政治,政治到底還是為經濟服務”,史立榮直言。
如今,在歐洲市場,中興已經形成全線產品進入態勢,但是,在美國市場只能以終端手機為切入口。
“真正進入北美,需要時間也需要轉變思路”,業內專家分析,這是中興華為的共性問題,高層應該從全球視野重新思考,不管是資本結構、人才結構,還是戰略和品牌規劃,都應該更加國際化。
對比華為和中興,前者是一家營收規模巨大的非上市公司,“華為、中興的董事會和決策中,應該多出現一些不同膚色的人,一年花費幾億擁有具備影響力的外腦也很值得”,付亮稱,中興也可以選擇與國內一些有差異化的通信設備公司,如普天、烽火以及國際上相對專業的公司進行資本交叉和入股,在規模化上結成盟友合力開拓國際市場。
大量砍手機產品線
當喬布斯攜蘋果iPhone、iPad“干掉”諾基亞之時,受到震驚的不僅僅是手機制造商。最近一兩年紛紛加入移動終端新戰場的玩家中,包括傳統軟件巨頭微軟、互聯網巨頭百度、騰訊、阿里巴巴,當然,在中國,還有最不容忽視的兩支生力軍:來自傳統運營商市場的中興與華為。當下的如火如荼,誰曾想到當年任正非甚至將“不做手機”寫入《華為基本法》。
“當初做判斷,我們看清了兩個方向:第一,手機市場容量、金額比系統設備還要大,而且通信系統5—10年換一次,手機1-2年換一次;第二,如果說手機像個小盒子,那么,通信設備就像大盒子,技術相近只是有濃縮”,史立榮稱。
其實,早在國產手機風生水起的2002-2003年,“ZET中興”就曾與波導、夏新和TCL一同出現過。只不過,2004年之后,遭遇國內“山寨”與國際高端品牌雙面夾擊時,中興于2005年第四季度后“戰略性”的轉移陣地了。
如今,隨著智能化的大幕拉開,中興又迂回到“主戰場”中國。此番,后進者華為正在以高舉高打的姿態鋪設品牌與零售渠道,相反,中興似乎秉承一貫低調穩健,顯得更多依賴運營商渠道。按照史立榮的說法:“別人跟著學,自己就要有更好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