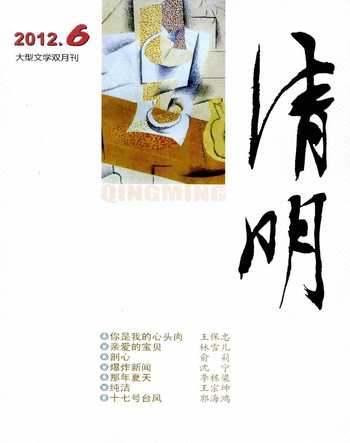十七號臺風
2012-04-29 05:53:00郭海鴻
清明
2012年6期
郭海鴻
佛龕上兩枝蠟燭被風吹歪,左邊那枝竟然熄了。老肖踮起腳,伸手將它們扶正,把熄滅的那枝拔起來,對準另一枝重新點燃,然后插回原處。干這個老肖不在行,老板和老板娘從臺灣過來的日子,這是他們每天早晚的功課,平時則有公司的重臣們負責禮敬這尊地藏菩薩像。很多工廠供奉的是關公或者觀音,而老肖他們的老板喜歡地藏菩薩,據說開廠那年,夫婦倆特別從臺灣將這尊白玉陶瓷菩薩像請到了大陸。對這尊手持金錫杖,掌上托著明珠的光頭菩薩,老肖是到了這里才曉得怎么稱謂的,以前他沒聽說過“地藏王菩薩”。老肖不信佛,但老板兩個多月沒來了,員工們、重臣們也都幾乎走散,這段日子都是他惦記燒香點燭的事。不信佛沒關系,他樂意這么干,這是工作的一部分。公司的日常總管李經理已告假三天,沒預留多少錢給他。“老板沒宣布關門,香火怎么能斷!”老肖對自己說,也對著地藏菩薩像說,“就是我自個掏錢,這香燭也得買。”
從西南方向越過圍墻盤旋而來的風“啾啾”叫著從老肖的兩耳邊上擦過,他撣撣手上的香灰,拿起擱在一旁的鋁皮鑰匙盤,準備回到保安室。從早上開始,這一小股一小股的風就不停地刮了起來——這是臺風的先遣部隊,按老肖的判斷,這回的臺風不會再像上一次那樣中途掉頭跑掉,絕對是正面襲擊,弄不好級數比預報的要大。
這時大門外響起兩聲凄厲的警笛。“準是姓張的鳥毛。”老肖嘀咕著,跨出幾步就到了公司大門口,站在鐵柵門內,左手拎著鑰匙盤,右手搭在門柵的鐵條上。……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