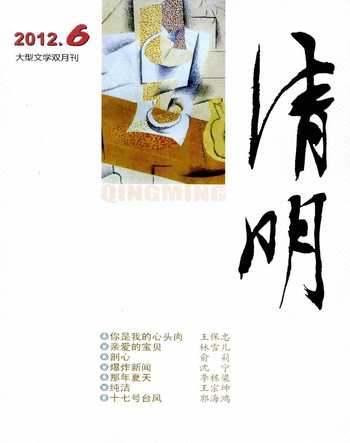草命
江耶
秋天,中午,陽光很好,空氣中流動著微微的熱。這些流動應該是秋風了。它把整個天氣吹涼了,從深藏的衣柜里把厚實的衣服吹了出來,吹上了人們的身體。現在,它仍然承擔變動推手的角色,把陽光落在空氣里加升的熱度散發開來,在這午后的時光中把氣溫稍稍往回撥動。
這是這個城市中心的一座立交橋,立交橋下面圍繞著相當于城市公園的游園,游園中間有幾條交錯的水泥路,它們把游園切成幾塊。管理者在上面種上不同的草、花、樹,它們相對獨立又密切聯系,給在這里行走、休閑的人們以視覺反差,偶爾生出游走在不同世界之中的別處之感。我現在走在其中的一條狹窄的水泥路上,路兩邊是已經枯黃了的草坪。南邊的草坪再往南,越過邊界就到了鐵路,一列火車正好經過,它裹挾著巨大的震動拽動得這一帶的大地都搖晃了起來,仿佛這一次經歷要把一塊地拽起來帶走一樣。火車過后,一陣窒息一般的安靜,像一個巨大的事物緊緊壓了下來,把一切都擠了出去,造成了短暫的空洞和空白。但這空洞和空白立即被沖開了,幾個孩子背著覆蓋住半個身子的書包雀躍著從鐵路另一邊飛跑過來。他們中的一個手里拿著打火機,伏到草坪上面,打著火,湊到草上。火走到枯黃的草尖子上,成為一種尖銳,迅速地在微弱的風聲中傳遞著。
我仿佛聽到了哭泣聲、呼號聲、哀告聲,它們也借助著微弱的風在盡量傳遞、相互轉告。然而,這些草并不能走動出一步,它們擺脫不了被焚燒的命運,它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根抱住,深深地扎入地下,保持最后的生命能力,等待下一個生長的季節。由于風,由于幾個孩子仍然跑動著點燃,火還在擴大、蔓延。
在我少年時代的農村,這是一種罪孽。那時物質極端匱乏,哪怕是生長在田埂、大壩、河灘上的野草,如果不遭遇野火,不遭遇作惡多端的調皮孩子,它們將會像莊稼一樣被我們收割,它們是有用的,或成為最樸實能吃枯草的耕牛一頓美餐;或被碾碎加入糠皮麥麩為從不挑剔的豬提供豐盛的佳肴;最不濟的,也是被填入灶膛用熊熊的火團幫助一鍋生米轉為熟飯,為窮困的日子增加一份必要的溫暖。
眼前的這些草不同于農村的草,它們是高貴的,出身名門。它們由專家、專門人員悉心栽培,之后一直是嬌生慣養,要風得風要雨得雨,順理成章地成長成一道美麗的風景。順利長成的草坪,散布在城市的公園里、廣場上、公路邊、花壇旁,還是由專業的人員養護著,待遇優厚,為一個城市的視覺增加品質、提升品位。它們在柔順中透著優雅,被眾多的目光抬升得高高的,被來來往往的市民和游人欣賞著,贊美著。它們的命運被人很好地安排著,經常被人修剪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是天天梳理得整整齊齊的。早晨和傍晚,柔和的陽光撒下金色的光芒,設置好的自動旋轉噴泉把金色的光芒攪拌成碎片,用水的形式開始為它們澆灌,細致入微地給它們的一個日子以良好的開始和結束,以非常好的心情來保持著亮麗的容顏。
然而,草仍然只是草。比如現在,它們就很難逃脫被焚燒的命運。更多的時候,它們匍匐在人的腳下,遭受各式各樣的腳的蹂躪。草不言不語,逆來順受著。風吹來,草全都低下了頭,雖然并沒有躲避掉一場打擊,但它們已經形成習慣,在災難前不張皇失措,不痛心疾首。它們不想有多大的作為,沒有骨頭,沒有骨氣,風吹草低見牛羊,現出草叢里的所有東西,不替別人作任何的承擔。如果有幸或者是不幸,被安置在一個高處,成了墻頭上的草,它們仍然登高不會望遠,高瞻不能遠矚,不會高屋建瓴,而是一再屈服、順從,試著看哪邊強勁就服從哪邊,向另一邊倒伏。是的,它們沒有主心骨,沒有堅毅挺立的形象,更沒有自己堅挺的實質精神。沒有實質也許就是實質吧。這也是優勢,最起碼不會骨質增生,不會像很多人一樣得上頸椎、脊椎的毛病,整天有事沒事地在沒有任何外力的情況下扭動屁股、搖頭晃腦。即使被焚燒,它們也不計前嫌,一個季節過后,在可能的情況下,它們仍然會再次破土而出,現出生機勃勃的長勢來,把曾經屈辱的生命再重新來過。
這就是草命,卑微而倔強。只要有很少的一點土就行了。有很少的一點土就能活命,就能保命,就能很旺盛地生存下去,在一片土地上增添綠色,保持水土,做著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在墻頭,高處不勝寒吧,也只是有點小危險。如果不是墻倒眾人推,如果那些土不會全部喪失,它們也不會完全失去生命能力,而是在另一個角落毅然重生。
再向前走,就是立交橋了,它在這個城市中心承擔了交通方面的標志性建筑的角色。在草坪圍繞的大橋陰影下,有幾個賣盒飯的攤子。我剛調到這里上班時,是一個人生活的。在下班之后,經常在那里經過時買上一盒,把肚子里的饑餓給對付過去。有時心情好時間充裕的時候,也會讓老板給我炒上一個菜,再拎上一瓶啤酒,端到一個低矮的桌子上,坐在一個更矮小的塑料凳子上,慢吃慢喝。對于我來說,這就算是享受生活了。一般情況下,他們會用那種很小的一次性塑料杯子,為就餐者免費提供一杯湯。說是湯,其實和水差不多,也就是多點油花,再加上一兩片菜葉,使水在加熱的過程中從清明變向了渾濁而已。就是這樣沒滋沒味的湯水,對那些像我一樣無家可歸者的生活給予了一定的滋潤,讓再簡單不過的一頓午餐有模有樣起來,讓這個城市里最貧寒的胃有了豐盛大餐一樣的小小排場。
我經常光顧的是看上去像夫妻倆經營的一個炒菜攤子。在一個巨大的傘棚下,女人擇菜、配菜、打飯、端菜、拿啤酒、收錢,男人主勺炒菜。他們一律煙熏火燎地滿臉灰黃,上上下下都是油漬麻花的,使仍然能看出白色底色的大褂變得異常復雜。大部分時間里,他們總是半睜著眼,躲避著油煙,也不看面前的人。來這里吃飯的大都是在這周圍打工的農民、附近學校的學生,還有的就是像我這樣已有家室但孤身在外工作實質上是單身的一族。這些人都沒有什么講究,或坐或站,有時時間緊張了還能端著飯菜邊走邊吃。大家很少說話,像一棵棵相互獨立的草,在風中各自搖曳。這樣的場景為我熟悉。在我上下班經過的許多地方都可以看到,馬路邊上,一棵大樹下,小區門口,等等。攤子是一樣的攤子,吃飯的人大都裝束一樣,吃飯時的場面也大體一致。由于自身的生活狀態和特別心情,每每走過這樣的攤子時,我都會前瞻后顧地看上幾眼,心里說不出是什么滋味。
這些是散落在城市里的草。我也是其中的一株,“在大地上,我不停地走/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膚淺地深入和看著/紅塵飛揚//多么簡單的一個事件/只要一點點/大地上的塵土/就可以養下我這一條小命//我就是這樣微不足道的/一顆塵埃/我反復說/可以死于一滴雨,一陣風/一次閃電,一場很小的地殼運動”。這是我的詩,也是我的生命的真實寫照,簡單,簡約,簡潔,容易滿足,容易成活,也容易覆滅。在城市里,沒有大樹好乘涼的我們,的確經不起任何風雨,只要有一個很小的打擊,都可能立刻讓我毀掉。我們就是這樣走在草一般的命數里,在不被人注意之中自給自足,自生自滅。
如果能自給自足、自生自滅,倒也不失為一種完整甚至完美的命運。很多時候,這只是我們一廂情愿的向往。像草一樣,我們寧愿被踩在腳下,也不愿進入一個人的視線。這些被忽視中的蹂躪所形成的痛苦應該輕于被關注下的滅頂之災吧。比如,這些枯黃的草被一群孩子發現了,引起了他們的興趣,它們就要遭遇到被焚燒的苦難。在現代這樣政治高度成熟的社會中,所有的人都要被納入到管理的視野里。我曾經問小老板,你們這樣的簡單經營有人管嗎?炒菜的兩個人異口同聲地說,怎么沒有?收稅的,收衛生費的,城市管理的,等等。他們異常激動地說了一大串,我也記不住。他們中午在橋下面炒飯,傍晚挪到另一條街上去,他們看哪里流動的人多就奔向哪個地方。他們不怕累,他們希望一直忙碌著,希望能掙更多的微薄利潤。他們來自農村,現在他們不種田了。他們知道稼穡艱難,現在他們又知道了不事稼穡更加艱難。他們是來自農村的草,在城市的水泥地里是扎不下根的。他們只是在城市道路的寬闊路面上,待在一點浮灰里將就著存在。他們應該是能夠挪動的草,是漂移的浮萍,他們最終肯定還是要回到農村的。這樣脆弱的存在方式還時不時地經受城市上層建筑的關心,比如環保,比如城管,比如治安,比如工商稅務,等等,使他們的存在動蕩、狹窄、短暫、難堪。這個炒菜的攤子,就曾經經歷了從橋下水泥路移到南邊的鐵路邊上,又從鐵路邊上移到橋下涵洞里。每次被驅趕都能得到一個正規而合理的理由,然而卻并不能按下他們心里的憤憤不平。
俗話說,民以食為天,吃飯問題一直是歷朝歷代關注的大問題。小時候在農村,吃飯時捧著飯碗還能串門,串到誰家往往還要就地取菜(也只是咸菜,最多不過是自家田里的蔬菜)。也有不少時候,特別是農閑季節,一個村子的人,都能端著巨大的飯碗,蹲到一棵大樹下面,或者坐到誰家的門口,邊吃邊說,東家長西家短、今天雨明天晴的,干的稠的稀的食物,不知不覺地下到肚子里了。這樣隨意的吃飯形式頗有點田園風味,讓人想象起來似乎還彌漫有許多詩意。這也許就是鄉土吧,它顯示出鄰里之間的和諧和親密,顯示出鄉土里的養分在大地下面不分彼此,無界線地相互供給可能的生命。
現在這樣的情況不多見了。村子里的房子不像以前那樣蓋成一條直線,有集中的走勢。村子不像村子,七零八落的,而且相隔很遠,客觀上說走動起來也不大方便。在村子里轉上半天,遇到的都是老人和孩子,而且他們還忙個不停。村莊空了,像那些被拋荒的土地,像土地上的農作物,從過去根本的位置上下滑到邊緣,成為另外一種草。特別是過去聚集地居住的地方,大都剩下一塊空地,最多也不過是開裂了的房子和半截的墻頭。青澀的莊稼或棘叢里,它們在十分強烈的陽光下獨自頹廢著,像是人跡罕至的沒落文明,荒草叢生,滄桑而荒涼。
村子里的青壯年都走了,在各種各樣城市或者通向城市的工地、車間,卑微地勞作著。他們不出來也不行,農業收入早已經不可能維持有一兩個孩子上學的日常生活。雖然現在國家調整了農村政策,給農民以各種好處,大大緩解了村民們的窘迫。但受大的經濟走勢的帶動,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漲幅驚人,幾乎把這些政策惠民的空間給擠占完了。我的很多親戚都在城市,但我很少能遇見他們。他們從不停歇地忙活著,掙點錢拿回家,辦公共事情,給孩子上學。他們從農村來到城市,但仍然是低賤的草。他們必須交納所有的稅費,但他們病了沒有醫保,找不到活干吃不上低保,老了殘了干不動了也退不掉休。他們不如城市草坪中的草有安定可靠的歸宿。他們不僅要為水泥森林襯托出一定的高度,為城市風景作必要的補充,他們還要用草一樣柔弱的身子,承攬下繁重的體力活計,為城市建設墊下沒有思想卻無比堅實的根基。
我認識的人都老了,他們是我心里的鏡子,我從老人那里能看到很多東西。我以前走的小路都躲在草叢里,路面上的土質柔軟而單純。偶爾有一條新路,在田地里寬闊起來,可以行走農耕機械。到了冬天、年節,這些路上,還可以開進從城市里來探親訪友的小轎車。我聽到的也是某某在什么地方掙錢了,某某的家又搬走了,在某個城市駐扎下來。變化太大了,我曾經熟悉的村子也不復存在了,雖然我還能從眾草繁盛中尋找一點蛛絲馬跡,看到曾經輝煌過的影子,給我的懷舊情結留下一條可以捉摸的線索。
在村子里走,我自己也是一條小路,或者就是一棵有所變化的草,在家鄉越來越茂盛的荒草里出沒。當年,我考上一個師范學校,是村子里第一個通過上學吃上商品糧的。親友們紛紛來祝賀,家里擺了多次酒席,熱鬧了很長時間,讓父母的臉上很是風光了一陣子。在村里人看來,我大概算是從草叢中長出來的大樹,將來會給家鄉、家庭支撐起一片天宇,多多少少地遮風避雨,蔭及親故。我從學校畢業后,沒有回到家鄉工作,后來又幾經變遷,來到一個城市。我在城市里買了房子,安下了戶口,娶妻生子,結識了很多城市里的朋友,在他們的生活中來往穿梭。我沒有給老家里的人以多少支持和幫助,在大街上行走,我看上去更像一個城市人了。然而,我自己卻一直這樣定位,我骨子里還是一個農村人。我總是覺得那個正在沒落甚至走向消亡的村莊才是我的家,那個土墻草頂的老房子才是我靈魂的歸宿。經常在夜夢里,我的手里捏著一張考試成績單,奔跑在鄉間的小徑上,奔向那個低矮、光線稀少的房子。現在,這一切都沒有了。我家的房子早幾年因為修建高速公路就拆掉了,父母在大哥的瓦房后面搭建了幾間小屋子。再后來,父親生病去世,母親跟了我們在城市生活,那個小屋子也破敗下去,曾經用作廚房的屋子已經倒塌了,里面光線斑駁、晦暗,像是記憶中理不出頭緒的一件舊事。我還是要回去的,每隔一段時間就找個理由回去看看,到父親的墳邊上走走,燒點紙,磕幾個頭,然后定定地看上半天。有一個清晨,我還專門跑到老屋的舊址處,坐在一條田埂上,看高速公路上的汽車“呼呼”地飛來奔去。那個時候,一種宿命的東西控制了我,我的思想幾乎凝固了,我想不出什么,任時間無聲無息地溜走。
是的,是時間在悄悄地改變著一切。不光是改變著我們的容顏,改變著我們的心境,也改變了我們的家園、我們的山河。很多次,我們一轉身就發現,所有的事情都物是人非了。草命堅強。“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草在我們的視線里只是暫時消失了,要不了多長時間,它們還會出來,朝氣蓬勃,生命力旺盛。也許這些草已經不是原來的草了,也許這些草本身已經秘密地發生了巨大的變異。我們發現不了,認識不到。人呢?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是不能和草較勁的,人在時間里一個一個明顯地變化著,暗淡著,消失了,不留下一絲痕跡。有時我想著這些,想到了輪回。
夏日,夜色漸濃,高架燈下亮如白晝。立交橋上汽車飛速奔馳,橋下草坪上的草異常柔軟,草的上面已是熙熙攘攘。開闊的廣場上涼風習習,從人們嚴實的縫隙里穿過,給更多的人送去涼爽。人們悠閑而自在,有的三三兩兩在說著話,有的三五成群圍坐著在打牌,有的干脆什么都不做,躺在自帶或租來的草席上,看著天看著星星,發呆發愣發懵,做著清醒的夢。孩子們幾乎是到達了天堂,跑來奔去,或追逐一只球,或廝打著游戲。還有精明的商人推來了冷飲柜,擺起吃食攤點,懷抱熒光玩具招引著孩子。不同的腳不同的身體在無形而確定的路線上行動著,他們在踐踏著越來越多的草,當然而無意。草不再尖銳,而是用身體默默地承受著,盡量讓人們覺得自然、舒服,感覺不到它們的存在、存活。
這是草的用處,是草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