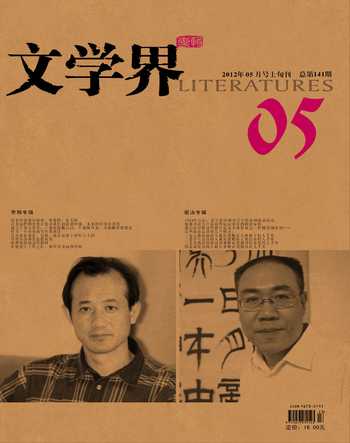在歷史追尋中行走
復旦起步,幼稚而興奮
一九七八年春節期間,剛剛參加過高考的我,在家鄉湖北隨縣(今隨州市)期待著錄取書的到來。元宵節將近,一天我去打(當地話“打”即零買之意)醬油和醋。拎著空瓶子,走在街上,忽然迎面碰到我所工作的工廠———湖北油泵油嘴廠———負責招生的師傅,他喊道:“李輝,你的入學通知書來了。是復旦大學的。明天到我那里去取。”
半個月后,一九七八年二月,我走進了復旦校園。成了復旦大學中文系七七級文學專業的學生,我們班的信箱號為七七一一,這個數字,從此成了我們班級的代號;我的學號是771102611,它也是畢業證上的號碼。
未來的三十年行程,在這個春天起步。
當時真正稱得上是歷史轉折時刻。真理標準討論、思想解放、平反冤假錯案、改革開放,一個新時代,仿佛早在那里做好了準備,在我們剛剛進校后不久就拉開了帷幕。印象中,當時的復旦校園是一個偌大舞臺,國家發生的一切,都在這里以自己的方式上演著令人興奮、新奇的戲劇。觀念變化之迅疾,新舊交替的內容之豐富,令人目不暇給,甚至連氣都喘不過來。上黨史課,一個星期前彭德懷還被說成是“反黨集團”,一個星期后就傳來為他平反昭雪的消息;關系融洽的同學,一夜之間,變成了競選對手而各自拉起競選班子;老師和學生在課堂上會因見解不同而針鋒相對,難分高低;班上同學發表《傷痕》《杜鵑啼歸》,點燃了許多同學的文學夢……現在,有不少論者將“八十年代”界定為“新啟蒙時代”。就其時代特性而言,準確地講,一九七八、七九兩年,與八十年代應該是一個整體。除了“真理標準討論”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外,這兩年期間發生的重大事件,如平反冤假錯案,為地主、富農等階層的子女摘帽,數以千萬計的人擁有了平等的公民身份;重視知識,重視人才,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重新得到重視……一切都為八十年代的行進做了最好的準備和鋪墊。
我有幸在這樣一個時代巨變的轉折之際,從內地一個縣城,從社會經驗膚淺、見識狹窄、知識貧乏的舊我,走進了一個讓人眼花繚亂、充滿新奇與吸引力的校園,擁有了一個永遠值得留戀的班級。
一九七八年秋天,一次我與同窗陳思和閑談,我們發現雙方都對巴金的作品有興趣,遂產生合作研究巴金的念頭。陳思和雖比我只大兩歲,但在進校之前,他已在圖書館工作數年,且有文藝評論的寫作經驗,有理論深度,擅長思辨。而我,雖二十有一,但自兒時起從未接受過好的教育,在名著閱讀、寫作訓練諸方面,尤其顯得幼稚與膚淺。當時自己最大的本錢,不過是好奇、熱情、大膽。我絲毫沒有考慮到自己的先天性知識欠缺,竟然毫不遲疑地決定與他一起研究巴金———當時非常陌生、非常棘手的一個課題。
現在想來,把巴金確定為最初研究對象,的確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首先,巴金是“五四運動”的“產兒”,從無政府主義運動的理論家和活躍分子,到成為著名的文學家、出版家,其豐富性、復雜性,值得系統研究。這促使我們一開始就必須盡可能把視野拓展,從思想史、文化史、文學史的多角度來閱讀,來搜集資料,來加深我們對歷史的認識與理解。其次,巴金在經歷“文革”磨難后,重新拿起筆,發表《隨想錄》文章,開始以反思歷史與關注現實的特點與新時代同行,這為我們的關注與研究,提供了新的話題,使我們可以不限于故紙堆式的研究,而與現實有了直接關聯。陳思和后來嘗試將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打通,提出“新文學整體觀”的思路,并把當代文學創作也作為重要研究對象;我后來從巴金研究,延伸到撰寫與他同時代的其他作家的傳記,以及研究相關文化史的專題;各自取向雖不同,但與我們的最初選擇,有著必然聯系和內在發展邏輯。
幸運的是,在剛剛確定合作研究巴金之際,我們便結識了賈植芳先生。賈先生在一九五五年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干分子”,此時還未平反,但結束了在印刷廠的勞動,臨時回到中文系資料室工作。
中文系在校園西南角一幢三層舊樓。樓房多年失修,木樓梯和地板走起來總是格吱格吱發響。樓道里光線昏暗,但走進資料室,并不寬敞的空間,卻令人豁然開朗,仿佛另外一個天地。資料室分兩部分,外面是閱覽室,擺放著各種報刊雜志;里面則是一排排書架,書籍按照不同門類擺放。一天,我走進里面尋找圖書,看到里面一個角落的書桌旁,坐著一個矮小精瘦小老頭。有人喊他“賈老師”,有人喊他“賈先生”。我找到書,走到他的身邊,與他打招呼,寒暄了幾句,具體說了些什么,已記不清楚了。從那時起,我就喊他“賈先生”。后來,到資料室次數多了,與先生也漸漸熟悉起來。面前這個小老頭,熱情,開朗,健談,與他在一起,沒有任何精神負擔和心理壓力,相反感到非常親切。每次去找書,他會與我多談幾句。有一次,我正在資料室里找書,看到一位老先生走進來與他攀談。他們感嘆“文革”那些年日子過得不容易,感嘆不少老熟人都不在人世了。那位老先生當時吟誦出一句詩:“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后來知道這是杜甫的詩句,寫于安史之亂之后。
說實話,當時我對他們這樣的對話,反應是遲鈍的。更不知道先生此時剛剛從監督勞動的印刷廠回到中文系,歷史罪名還壓在他身上,對變化著的世界,他懷著且喜且憂的心情。我當時進校不久,雖已有二十一歲,但自小生活的環境、經歷和知識結構,使得自己在走進這個轉折中的時代時不免顯得懵懂。許多歷史冤案與悲劇,許多歷史人物的是非曲直我并不知情。然而,不知情,也就沒有絲毫精神負擔,更沒有待人接物時所必不可少的所謂謹慎與心機。我清晰記得,當時自己處在一種興奮情緒中,用好奇眼光觀望著一切,更多時候,不是靠經驗或者知識來與新的環境接觸,而是完全靠興趣、直覺和性格。
我和陳思和漸漸成了賈先生家里的常客。
在賈先生家,喝得最多的是黃酒,吃得最多的是炸醬面。后來,還是喝酒,還是吃面。聽得最多的則是動蕩時代中他和師母任敏的坎坷經歷,以及文壇各種人物的悲歡離合、是非恩怨。他講述文壇掌故與作家背景,關于現代歷史與文學的廣博見識和真知灼見,時常就貫穿于類似的閑談中。他所描述的一個遠去的時代,和那個時代的五光十色的人物,引起我濃厚的興趣。將近三十年過去,這種興趣依然未減,首先歸于賈先生的熏陶,是他為我開啟了走進歷史深處的大門。
與課堂教學相比,我更喜歡這種無拘無束、坦率的聊天。在我看來,這甚至是大學教育真正的精華與魅力所在。一位名師,著書立說固然重要,更在于用一種精神感染學生,用學識誘導學生。在我眼里,賈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名師。他教育我們:走學術之路首先要學會搜集資料、整理資料;研究作家必須讀最早的作品版本;不要人云亦云,要有獨立思考。他總是說,做人比什么都重要,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人格不能卑微,要寫好一個“人”字。許多年后,經歷風風雨雨之后,我才更加深切地體會到這些教誨的重要性。
不久,賈先生邀請我們一同參加他主持的《巴金研究資料匯編》項目的工作。這是搜集資料、整理資料的基本功訓練,我們眼前,一個新的天地頓時跳躍而出。
一九七九年年底,我和陳思和寫出了第一篇論文《怎樣認識巴金早期的無政府主義思想?》,賈先生幫我們寄給了《文學評論》的王信先生,后經過陳駿濤先生之手,刊發在一九八○年的《文學評論》雜志上。文章雖改成通信形式,但觀點基本保留。我們當時還只是大學三年級學生,文章能在學術界權威刊物上發表,可以想見我們的興奮。
我們的合作研究巴金,從大學期間一直延續到畢業之后的一九八四年,前后達六年。最初的研究成果結集為《巴金論稿》,一九八六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是我們倆第一次出版著作。不能說最初的研究成果是出色的,但是客觀地說,最初邁出的步履是認真而踏實的。為了第一本書的誕生,我們付出了全部心血,在此過程中,得到了搜集資料、文本校勘、論文寫作、理論分析等多方面的基本功訓練。同時,最初的學術研究對象的選擇,成為日后不可缺少的文化背景、思想背景。
記者的角色,記者的筆
一九八二年年初,大學畢業后我離開上海,到《北京晚報》成了一名記者。
初到北京時,我懷揣著賈先生寫的幾封信。他說我一個人獨自來京,諸多不便,故介紹我去看望胡風梅志夫婦等一些他的親朋好友。他雖不在身邊,依然熱心呵護我,引導我前行。在隨后幾年的來信中,他以自己的人生經驗不斷給我以教誨。他勸我一定要堅持學好外語:“千萬不能放棄外文功夫。”(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四日)他不止一次在信中開導我要借從事新聞工作的機會了解社會,認識歷史:“你還年輕,在新聞界工作,接觸的面較廣,藉此也可以多積累一些生活經驗,了解中國社會現實,那對做學問是大有裨益的。”(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七日)
開始幾年,我是當文藝記者。一段時間里,晚報文體組只有兩名文藝記者,一是過士行先生———后來以劇作家著稱,創作了《鳥人》等話劇,負責話劇、戲曲、曲藝、雜技;一是我,負責文學、影視、音樂、舞蹈、美術等。當時尚無“娛樂記者”之說,更無娛樂專版,而是文、體新聞每日共同一個版。我得感謝這一安排,它讓我能夠很快熟悉北京這座城市,熟悉文藝界的人與事。
我很快進入了角色,每天在電影院、劇院、會場跑來跑去。如果不是當年的采訪本幫忙,我真記不得這一年到底看了多少電影,聽了多少音樂會,看了多少展覽。好在剛剛二十六歲,又未成家,一個人住在集體宿舍,有的是時間和精力,也就全身心擁抱新的刺激了。
文體組記者少,版面卻每日都有,這就給我這個新手提供了一個大舞臺。只要你不想閑著,只要你愿意寫,幾乎都有見報的可能。記得有一天從頭版到文體版,居然同時發表了我寫的通訊、消息四篇。
由于做記者,時間與寫作顯得零碎而人難以沉靜下來,加之個人也缺乏理論修養和嚴密的邏輯思維能力,在大學開始的文學研究與論文寫作,最終未能繼續下去。此時,晚報副刊同事辛述威先生調至中國文聯出版公司,我去看他,他鼓動我選一個熟悉的人物寫一本傳記。我挑選了蕭乾———他是巴金的朋友,又是沈從文的弟子,三十年代“京派文人”中的重要一員;他是文學家、翻譯家,還是著名記者和副刊編輯。他的豐富一生,對我很有吸引力,特別是“二戰”期間在歐洲擔任戰地記者的傳奇經歷,尤其讓我興趣濃厚。為他寫傳,既可以拓展我的視野,又可以使我在忙碌與瑣碎的工作中,找到相對適合我的性格和新聞特性的寫作方式。于是,我轉向了傳記文學寫作。八十年代中期,除《浪跡天涯———蕭乾傳》之后,我又撰寫了另一位新聞界前輩劉尊棋先生的傳記《監獄陰影下的人生》。這兩本傳記的創作,是新的嘗試,也是為后來的寫作積累經驗。
在八十年代后期,對于我真正具有重要意義的、付出心血最大的,無疑是《文壇悲歌———胡風集團冤案始末》一書的寫作。
早在復旦大學與賈先生交往的過程中,我就陸續認識了他的一些友人。這些曾被描繪為“青面獠牙”的文人,在我眼里卻是那么親切、可愛。他們性格各異,文學成就不一,在命運折磨面前的表現也互有差異。他們是歷史漩渦中一片片落葉,被拋起又摔下,落葉上,記錄著歷史的季節替換。
一九八四年,做記者的我,萌生了搜集和記錄胡風集團冤案過程的念頭。當時,胡風集團的平反還不徹底,許多話題在報章上甚至還是禁區。我只是本能地覺得,應該趁許多當事人健在的時候,盡量進行采訪,留下第一手的口述實錄,為后人的研究留下一些資料。四年之后,編一本資料集的想法有了改變,轉而創作了一部三十余萬字的長篇歷史紀實,即一九八八年十月發表于《百花洲》第五期的《文壇悲歌———胡風集團冤案始末》。
研究中國現當代史,不難發現,由于中國的文學和政治的密切糾纏,使得文人之間、文人和政治之間的起伏、交叉、糾纏關系,有相當大的理解難度。特別是胡風集團冤案,牽扯到文藝界的宗派主義、毛澤東與知識分子的關系、歷次政治運動的相互影響……遠非一個單一角度或單一層面能梳理清楚。我為此感到困惑。復雜性如何理解,如何描述?譬如,我本人和賈先生的師生關系,是否會影響到我對胡風集團事件相關人與事做出客觀、冷靜的描述?寫作過程中,想法漸趨明確,寫胡風集團冤案的全過程,不能簡單地為受害者的辯誣叫屈———當然應該為受害者求得歷史的公正———更重要的,應該把歷史漩渦中內在的東西,如,權力與自由精神、宗派與宗派主義、個人崇拜與集體瘋狂、人性與獸性、清醒與懵懂……盡量客觀地呈現出來。我并未做到這些,但我卻試圖這么去做。
《文壇悲歌》殺青,其時正好是我將迎來三十二歲生日,我在后記中坦承,自己無法做到深刻,但卻愿意當好一名“記者”。
如今,再看當年作品,我覺得以“記者”身份來追尋歷史、記錄歷史,其實是一個明智選擇。隨著更多史料的發現,隨著每個研究者思想深度的不同,對于歷史事件的論述必然會有所變化并逐步深入。近些年來,關于胡風以及胡風集團冤案的回憶錄、研究專著已出版多種,它們在史實提供、理論分析、歷史思考諸方面,其豐富性、準確性和深度,遠非拙著所能企及。但我所親歷的事件過程,所采訪到的當事人的口述,卻無法重現。我為自己以“記者“之筆而成為較早的歷史敘說者感到自豪。
將近三十年過去,我所采訪過的、熟悉的一些前輩,相繼辭世,我永遠懷念他們:胡風、梅志、路翎、賈植芳、任敏、魯藜、曾卓、羅洛、王戎、王元化、耿庸、彭燕郊……
我至今仍覺得周揚是一個值得花大力氣研究的重要對象。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界,周揚是跨越時代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自三十年代初與魯迅發生矛盾,發展到后來對胡風、馮雪峰、丁玲的打壓,周揚的宗派主義貫穿了中國長達數十年的左翼文藝運動。與此同時,他自己的思想演變脈絡與歷史變革密切相關,左聯時期———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后———一九四九年至“文革”爆發前十七年———“文革”結束后討論人道主義異化問題時期……在這些不同歷史時期,由于個人地位、身份的特殊原因,周揚身上表現出的復雜性、特殊性,在思想文化界可能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與之相比,作為研究對象,他有著沉甸甸的歷史分量。
基于這一考慮,盡管九十年代初沒有完成周揚傳,但我采寫并整理出一本《是是非非說周揚》,也算對自己的一個安慰。因為這畢竟是與《文壇悲歌》的一個自然銜接。當時想到,既然暫時無力系統而深入地描寫周揚,還不如借用國外“口述實錄”的形式,采訪與周揚不同關聯的人。我先后采訪夏衍、林默涵、梅志、賈植芳、陳明、曾卓、溫濟則、王若水、于光遠、李之璉、王元化、賀敬之、華君武、袁鷹、龔育之、顧驤等數十人,他們中間,或是與周揚親近的友人,或是他的家人,或是他的同事,或是受到過他的打擊的受害者……關系不同,視角不同,細節不同,甚至同一事件同一場面的敘述,因為每人的親疏不同而有差異。現在看來,采取“口述實錄”雖然不是我最愿意采用的寫作方式,但卻有其意外收獲,因為多角度的個人敘述,正可以避免先入為主,避免單一性敘述,從而能立體地多角度地凸現出周揚的復雜性,為讀者和研究者,提供更大的認識空間和思考空間。
由此來看,在敘述歷史的過程中,當好“記者”角色,用好“記者”之筆,無論何時何地,都有其特殊作用和價值。從這一意義上說,我為自己在大學畢業后一直從事新聞工作而感到滿足與高興。
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
我常說自己是個運氣很好的人,常能在人生關鍵時刻遇到文化前輩的指點與幫助。在大學,我遇到了賈植芳先生,他深深影響了我的研究與人生。而在八十、九十年代,對我的文學寫作影響最大的是蕭乾先生。
蕭乾先生是新聞界、文學界的前輩,編輯副刊的高手,我到北京后,他既是我的采訪對象,又是我的作者,八十年代他的幾個重要系列文章,如《北京城雜憶》《“文革”雜憶》《歐戰雜憶》,都是交由我在《北京晚報》“五色土”副刊發表。一九八七年我調到《人民日報》“大地”副刊后,他依然不斷賜稿,一直到一九九九年去世。《蕭乾傳》則是我創作的第一本傳記,他還推薦與介紹我去寫新聞界老前輩劉尊棋的傳記,鼓勵我去寫吳祖光新鳳霞夫婦……
蕭乾寫給我的信近二百封,每次翻閱它們,都讓我重溫往事,感受溫暖。這些信,記錄了他在將近二十年的時間里對我的關愛和幫助。從傳授寫作技巧、詞語修飾,到推薦寫作對象、針砭時弊;從指點行事風格、交際方式,到關心婚姻、評論作品……有批評,有誤會,有開導,人生遇到的方方面面,他幾乎都在信中寫到了。一次,我寄去一篇文章請他看。他回信說:“短文讀了,也做了些改動。你很會抓題材,寫起來也能抓到要點。文字還可以再考究些。首先語法上要順,其次,句子組織的不宜過松散。我是很在乎標點符號的———學過外文的人,一般這方面較嚴格。我改了不少你的標點。……”
最令人難忘的,是他在一九八九年鼓勵我,鞭策我,使我得以繼續以文化方式追尋歷史。記得那一年,我一度感到郁悶、困惑與迷惘,心情極其糟糕,幾個月寫不出一個字。得知我的精神狀況,歷盡滄桑的蕭乾連續給我寫來好幾封長信,以他的親身經歷和人生感悟開導我。他希望我不要沉淪下去。他在信中說:“我強烈建議你此時此刻用具體、帶強迫性的工作,把自己鎮定下來。什么叫修養?平時大家都一樣,到一定時候,有人能堅持工作,有時心就散 了。人,總應有點歷史感,其中包括判定自己在歷史中的位置。心猿意馬?我認為韁繩不可撒手。在大霧中,尤不可撒手。這幾年你真努力,你應肯定自己的努力。要有個‘主心柱兒,不因風吹草動就垮。”(一九八九年)一位前輩,能夠如此推心置腹,讀之豈能不為之感動而奮起?如果說自己這些年沒有消沉,沒有離開溫馨的文化園地,蕭乾在關鍵時刻的敲打,無疑起到重要作用。
那一年的秋天,我終于讓自己沉靜下來,開始一項與以往的寫作完全不同的工作———校勘沈從文的傳記作品《記丁玲女士》。啟發、鼓動我做這一研究的,是作家、藏書家姜德明先生。
早在《北京晚報》時期,我因約稿而與姜先生結識。當時他已離開《人民日報》副刊而擔任人民日報出版社社長,正是在他的鼓勵下,我在寫蕭乾傳的同時,圍繞蕭乾早期的著作《書評研究》編選了一本《書評面面觀》,集中反映三十年代中國書評理論與實踐的狀況,交由他出版。我一九八七年秋天調至人民日報社文藝部,恰好與他在同一棟辦公樓工作。他在一樓,我在二樓,我有了更多向他討教的機會。
一九八九年秋天,一次閑談中,我與姜先生談到了沈從文。他告訴我,沈從文抗戰前后在良友圖書公司出版的《記丁玲》與《記丁玲(續)》,與先期發表于天津《國聞周報》的連載《記丁玲女士》相比,有不少刪節。他說,年輕時他曾想找出來進行校勘,卻因人總是處在社會動蕩中而未能如愿,如今終于安靜下來,年歲卻大了,已無更多精力來做這種事情。他建議我,不妨花些氣力與時間,做做這項工作。
人正在飄的感覺中,以校勘來磨練自己性情,來充實學識,確有必要。何況,因為研究巴金和蕭乾的緣故,到北京后我就與沈從文有了接觸,寫過關于他的報道和評論,現在,從他的文本研究入手來深入認識他,應該說是一個有趣的課題。
十分運氣,報社圖書館里正好藏有一整套三十年代的《國聞周報》。我分別從唐弢先生和范用先生處借來《記丁玲》及續集兩種,再借出《國聞周報》,一頁又一頁,一句又一句,對照著字句的細微變化。幾個月時間里,我成了圖書館的常客。靜靜校勘中,我告別了一九八九年。靜靜校勘中,我看到了許多年前生動的歷史場景,看到了兩個著名作家個體生命在時代大變革之中發生的復雜變化,而這種變化又折射出了整個知識分子群體的分化、矛盾甚至對立。
有一天,校勘最終誘發我開始追尋這兩個作家的交往史。我試圖借梳理六十年間他們由相識、相助、合作、友好到隔閡、淡漠、矛盾、反目的全過程,描述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的苦悶、彷徨、奮斗、抗爭乃至寂寞、磨難等等。走出圖書館的我,又像過去一樣,開始了四處訪談、通信求證的工作,最后完成了《恩怨滄桑———沈從文與丁玲》一書。
至今我仍然喜歡這個作品,不僅僅在于它幫助我完成了兩個年代的替換,也在于它使我對寫作形式的運用,有了新的認識與體驗。就敘述風格而言,受其直接影響的,就是隨后連續三年的“滄桑看云”系列文章的寫作。
大約在一九九二年春天,《收獲》的李小林女士約請我開設一個專欄,集中寫“五四”時代之后的文化人物與文化事件。在此之前,我在《讀書》上發表過《恩怨滄桑》中的部分章節,還為《收獲》寫過關于沈從文的《平和或者不安分》、關于巴金的《云與火的景象》等散文,她喜歡這種人與事的敘述方法,鼓勵我按照同樣風格寫一個系列。
我欣然答應。我喜歡“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詩句,這是一種個人與現實的生存狀態,也是寫作者與描寫對象之間的歷史呼應關系。基于此,我把欄目定名為“滄桑看云”。連續三年,十八篇“滄桑看云”,我選擇郭沫若、梁思成、老舍、鄧拓、吳晗、聶紺弩、姚文元、趙樹理、胡風、瞿秋白等文化人物作為敘述對象。時值“文革”爆發三十年之際,對“文革”期間人物與事件的考察與敘述,成了三年寫作的重點。因此,除相關人物外,我還特地選擇紅衛兵運動和“五七干校”作為敘述對象,力求從歷史角度予以解讀。
“滄桑看云”系列的寫作,對自己的挑戰是多方面的。
這是歷史研究的挑戰。一篇文章寫一個人物,雖非完整的傳記,卻需要對其一生有較為系統與完整的把握,需要盡可能地擇選出凸現其命運與性格的人生環節。這也是寫作風格的挑戰。為《收獲》這一文學刊物寫,就應與《讀書》等文化類刊物有所不同。資料運用與文學渲染兩者關系如何處理,人物命運與歷史場景如何相互映襯,都必須細加處理。寫作時,我并沒有考慮到底屬于“學者散文”還是“作家散文”,我只想以濃縮的方式,挖掘所寫對象的性格與時代的關系,假如人物命運的描述中能夠漫溢出詩意,當然更好。
我一直看重史料在研究與寫作中的作用。寫《文壇悲歌》如此,寫“滄桑看云”時如此,寫“封面中國”和“絕響誰聽”也是如此。都說史料是死的,是枯燥的,然而,一旦它們與人物命運緊密相連,就不能不讓人產生種種難以言說的感覺。茫茫然,這是悠悠歲月中的回望。如同佇立于秋風的日子里,凝望飄然而下的落葉,你無法理清思緒,也無法準確地尋找到表述的語言,就在這樣一種感覺中,歷史煙云中許許多多的人與事,在我的面前呈現出它們的意義。